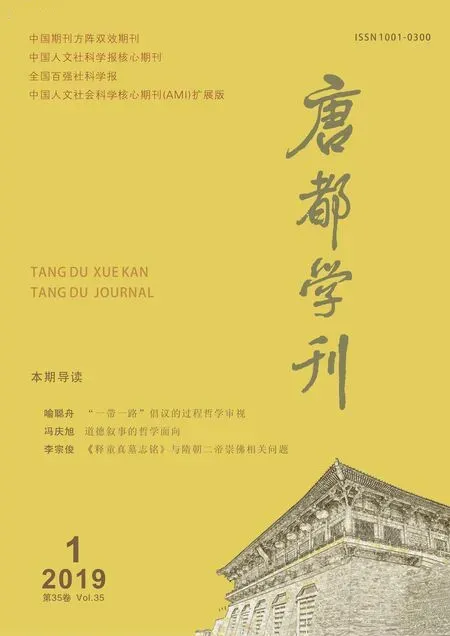理学探索与文献研究的双向开拓
——林乐昌著《张载理学与文献探研》述评
2019-12-16邸利平
邸利平
(西安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1)
张载(1020—1077),是北宋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张载学说体大思精,其学素称难治,至今仍歧见纷纭,令人困扰。然而这也恰恰让研究工作充满挑战,吸引研究者对张载理学持续地加以探索,解决其中的疑难和歧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林乐昌教授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从张载文献的搜求、整理和研究入手,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对其理学思想的探索,多有创获。《张载理学与文献探研》(以下简称《探研》)一书,便是他在这一领域辛勤探索与研究的新成果。
除《前言:张载哲学研究的跨世纪回视与前瞻》之外,《探研》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题为“张载理学探索”,分别讨论了张载的宇宙论、人性论、成性工夫论、礼学思想,以及关学学风、“关学”概念等问题;下编题为“张载文献研究”,内容涉及张载著述研究,张载佚著、佚文的研究,以及张载族裔家藏文献的实地调查。最后有附录“散论短稿”三篇。在笔者看来,《探研》一书的总体特点是,在理学探索与文献研究的双向开拓中,力图以张载文献作为理学研究的“实证”基础,据以解决研究中的疑难和歧见,并避免哲学上的过度阐释。由于《探研》一书涉及的内容比较多,限于篇幅,以下将择取其中的四个方面评析其特点。
一、多方校理张载文献史料,夯实研究基础
重视张载文献史料的校理,是《探研》一书的突出特色,这同时也夯实了诠释张载理学思想的基础。《探研》一书对张载文献史料的校理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张载传世文献的校勘整理。《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误》,是《探研》的第十二章,这是作者对张载晚年代表作《正蒙》进行校理所取得的成果。《张载集》,是学术界第一个张载著作集的整理本,由出版家章锡琛(1889—1969)点校,于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载集》是中华书局“理学丛书”中重印次数最多、印量最大的理学家著作集,作为被海内外研究者广泛使用的通行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张载集》毕竟已经出版40年,研究者有理由对其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林乐昌教授指出:“据不完全统计,通行本《正蒙》文字讹误近七十处,这相对于《正蒙》十七篇五百一十三章而言,大概不算是小数字。”[1]168林乐昌教授从两个方面分析了通行本《正蒙》的讹误类型和致误原因:“一是其选择版本有局限,即局限于清代版本,而未能据宋、明古本进行对校和本校,结果导致文字讹误频频出现;二是其校勘方法有偏差,即偏好于依他书校改本书,具体分析则包括依他书对本书分别改字、删字、补字等种种情形。从这两方面的关系看,由于校勘者限于条件不了解《正蒙》版本源流的全局,结果便只能舍宋、明本而单用清本;又由于校勘方法的偏差,则进一步加剧了通行本《正蒙》文字的讹谬程度”[1]168。林乐昌教授的辨误工作主要是,从通行本《正蒙》的约70例误校中选出13例,澄清异文之是非,辨析致误之原因,并提出新的校勘原则,为整理一个更可靠的《正蒙》新校本确定了基本思路,从而能够保证理论研究的文本准确性。
其次,张载佚著的辑校考论。林乐昌教授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探研》第十四章对张载佚著《孟子说》的辑佚与考论。南宋以来的公私史志书目,皆著录张载有“诸经说”,但目前传世的只有《横渠易说》一种。林乐昌教授遵循佚著辑录的原则,依据朱熹所著三书亦即《论孟精义》《四书或问》和《四书章句集注》,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多种,从中辑出张载解说《孟子》的语录133条,合为一编,以见张载佚著《孟子说》的梗概。在辑录张载佚著《孟子说》的同时,林乐昌教授还揭示了这一辑本的学术价值:第一,该辑本可以印证张载哲学思想的孟子渊源;第二,该辑本提供了把握张载理学思想演变轨迹的史料;第三,该辑本为张载其他著作提供了改误补阙的校勘依据。
再次,张载家藏文献的调查研究。长期以来,张载理学研究多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对于与研究有关的张载家藏文献则重视不够。《探研》第十六章《〈张载族谱〉和明、清、民国官府公文述略》,及第十七章《中国哲学史个案研究的实地调查尝试》,则分别考察了张载家藏文献,并结合传世文献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林乐昌教授考察的张载家藏文献主要包括:陕西凤翔县张载后裔捐赠给宝鸡市档案馆的明、清、民国三件官府公文,以及凤翔、眉县和湖北荆门三地族裔编撰或刊刻的五种《张载族谱》。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其中的第一件官府公文为例,略述其内容及其价值。第一件官府公文,是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五月初五日,陕西关内道按察司副使、凤翔知府沈自彰经申请抚院批允动支府库银一千两置买房地,迎聘横渠张先生第十四代孙张文运等五人回陕奉祀的公文原件。迎聘张载族裔归陕之后,改变了张载去世后陕西故里五六百年间无族裔的局面,并使凤翔、眉县两地的横渠书院得以恢复,由官府出资刊印《张子全书》,更直接推动了张载学说在关中地域的传播。据笔者看,这件官府公文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史料价值:一是为晚明关学复兴的社会政治背景提供了重要佐证,二是对于考察张载后裔的繁衍、迁徙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三是对于研究晚明关中的社会史和经济史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全面展现张载学术历程,提供研究参照
中国学术史研究素来有“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哲学思想虽然有超出于时空之外的反思性特点,但中国哲学史研究绝非抽象概念的演绎,因而研究人物个体学术生命可以为其思想的把握提供重要的参照。
众所周知,青年张载有志于兵,因范仲淹劝读《中庸》,才把人生的方向扭转到学术道路上来。今人对张载学术经历的了解,仅以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的寥寥几句话为依据。难能可贵的是,林乐昌教授依据《经学理窟》等张载自述和其他相关资料,把张载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后期[1]22-23。
张载学术生涯的早期,是其思想探索期,大约经历从21岁到40岁之间二十年的时间。从范仲淹在其21岁劝读《中庸》开始,张载先是“访诸释老之书”,大约用了十多年。之后,三十多岁的张载“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2]381。张载曾总结说,“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2]278,说明他对六经的系统研究又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
张载学术生涯的中期,是其思想的正式形成期,约在40岁到50岁之间的十年。张载在《经学理窟·义理》中这样自述:“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2]277从21岁开始读《中庸》算起,经过二十年,这时张载40岁出头。此后,张载思想在形成中渐趋成熟。
张载学术生涯的后期,是其思想成熟期,约从50岁到他去世之间的七八年。张载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经历说:“某学来三十年,自来作文字说义理无限,其有是者皆只是亿则屡中。……比岁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复出,天下之议论莫能易此。”[2]288从范仲淹授《中庸》,“某学来三十年”,刚好指他已步入五十岁。“入至其中”,可以认为张载的学术已经能够登堂入室,其思想已经成熟。
把张载的学术生涯从只限于早期的两次转折,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从而使张载思想演变的脉络得以全面展现。这一划分,能够为研究张载论域的相关问题提供有效的参照。例如,仁宗嘉祐初(1056),37岁的张载与二程兄弟于京师论学之后,二程的门人杨时、游酢等人竟认为,张载之学“源于二程”[1]34。这一看法的影响一直延续至现代学术界。若据张载学术历程三阶段的划分,则不难看出,京师论学属于张载早期学术活动的范围,是三位有志于复兴儒学的青年学者之间的切磋,当时无论张载还是二程都未形成独立的学说,思想也远未成熟,各自也没有形成学派。在双方学说都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便判定张载之学发源于二程,显然是门户之见。又如,林乐昌教授依据朱熹所撰《孟子精义》《孟子或问》《孟子集注》三书,以及《近思录》《朱子语类》等多种典籍,辑录张载佚著《孟子说》133条[1]192。据推断,《孟子说》很可能是张载学术发展中期的著作。依据这一辑本,其中约40多条被编入张载晚年著作《正蒙》各篇。这表明《正蒙》与张载早期著作或中期著作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这对于研究张载思想的发展过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首次搭建张载宇宙论哲学诠释框架,解决研究难题
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张载理学研究的难度很大,这尤其集中在如何理解其宇宙论哲学的性质,特别是在关于“太虚”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在林乐昌教授看来,搭建两层结构的宇宙论哲学诠释框架,有可能为解决这一难题探索出一条出路。
经多方面分析,林乐昌教授认为,汉儒只讲宇宙生成论,却不讲本体论;与此相反,魏晋玄学只讲本体论,却不讲生成论。哲学发展到宋代,理学家克服了汉儒和魏晋玄学各自的片面性,把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整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既包括本体论内容,也包括生成论内容的新型的宇宙论哲学。他还进一步提出,应当从两个不同角度,把这种宇宙论哲学划分为两个层次:把强调宇宙最高实在的理论称为宇宙本体论层次,把强调宇宙万物生成过程的理论称为宇宙生成论层次。在张载那里,“太虚”与“气”是既有分又有合的关系。一方面,二者相分,“太虚”具有本体意义上的超越性和先在性,这使宇宙本体论层次得以构成。另一方面,二者相合,充分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并批判佛教以世界为“幻化”的观点,这使宇宙生成论层次得以构成。宇宙生成论层次的基本概念是“道”和“性”。
林乐昌教授对张载宇宙论哲学两层结构的这一理解,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早在发表于1992年的《张载“太虚即气”命题散论》[3]一文中,作者就强调了“太虚”这一概念的本体论意义。发表于2008年的《张载两层结构的宇宙论哲学探微》[4]一文,则是对此观点的系统阐发。在后面的这篇论文中,林乐昌教授还把《正蒙·太和篇》“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性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四句话称作“《太和》四句”,认为这是张载理学的“四句纲领”[1]51。但是,这一判断在当时还缺乏文献依据。随着张载理学新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在林乐昌教授所编校的《张子全书》[5]中,辑补了张载佚著《礼记说》。《礼记说》辑本,是张载理学新文献之一。依据张载佚著《礼记说》辑本发现,“《太和》四句”原来是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等三句话的解说。而朱熹曾经把《中庸》第一章的前三句话视为“《中庸》纲领”[6]。这就是说,《礼记说》辑本,既还原了“《太和》四句”的语境,又提供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文献资料,使“《太和》四句”作为张载理学纲领的性质和地位得到确证。
由林乐昌教授的研究可见,无论是张载“《太和》四句”,还是《中庸》第一章的前三句,都把“天”置于最高概念的地位。《中庸》第一章前三句,根本没有涉及“气”。“《太和》四句”虽然言及“气”,但却仅仅是把它置于“天”“道”“性”“心”四个基本概念之外,属于辅助性的概念。从思想宗旨和运思方向看,张载的“《太和》四句”与“《中庸》纲领”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把张载的“天”“道”“性”都归结为“气”,那就扭转了《中庸》以“天”“道”为宗旨的根本方向。依据林乐昌教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张载宇宙论哲学的两层框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张载理学中,并不存在所谓“气本论”,而只存在“气化论”。因为张载理学以“天”为本体,所以可以把它的性质确定为“天学”,而不能把它的性质确定为“气学”[1]51。
四、重新界定“关学”概念,梳理关学源流
宋明理学对于近世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影响甚巨,这不仅是由于理学家人格和思想的高远所致,更是在于他们之后所形成的学术流派的持续历史影响。因此,理学思想研究也有必要向学派、学术史甚至社会史研究领域拓展。对于张载思想的历史影响,早在南宋,就有学者提出“濂洛关闽”的理学四大学派的称谓。晚明冯从吾编定《关学编》,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理学传统的学术意义。这些都是在“为往圣继绝学”的价值关怀意义上对学派观念的理解。现代学术界在定义“关学”概念时,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把“关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派”。不同的是,有的学者把“关学”的下限定在“北宋亡后”,有的学者则把关学的下限定在明清之际。
在《探研》第十一章《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和方法意义》中,林乐昌教授对“关学”概念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的看法。他认为,所谓“关学”,是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是由“时间”“空间”“学传”三个维度构成的。在“时间”维度上,关学历史的上限开始于张载创建关学的北宋中期,下限断至标志清末关学近代转型完成的刘光蕡(号古愚)。在“空间”维度上,关学自始至终都是依托关中地域这一自然条件而存在的。此外,关学在其演化中往往受跨地域学派乃至跨国文化的影响。在“学传”维度上,既包括关学学派的学术渊源、学术传播,以及后继者的承接及其方式,还包括由明清关学学派分化所导致的学术传承方式及其对象的复杂、张载学说被明清关学接受的多寡程度以及判别的标准。对于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进行具体论析。
除了关学概念的新界定,林乐昌教授还提出了关学演变三阶段的新构想。与以往的关学史研究都把“关学”视作“一个独立学派”不同,林乐昌教授认为,可以把作为关学源头的北宋关学视作单一的独立学派;这与作为关学流变的明清关学有别,因为明清关学的学派现象特别复杂。对于明清关学,一方面,可以从统一性的角度看,把它视作一个“大学派”。这主要是就关学依托于关中地域维度而言的。另一方面,则可以从特殊性的角度看,把它视为这一“大学派”当中所包含的多元并存的“小学派”,例如,以吕柟为代表的“河东学派”,以马理和韩邦奇为代表的“三原学派”,以冯从吾为代表的“甘泉学派”,以王徵为代表的“关学别派”等。这主要是由于各“小学派”对张载理学思想的传承关系有所不同。据此,林乐昌教授主张把关学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北宋时期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学派的独立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明代关学的学派多元并存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清代关学的学派多元并存发展以及向近代转型的阶段。
林乐昌教授关于“关学”概念和关学流派的见解,先期曾以学术论文发表。[注]参见林乐昌《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载于《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第59~65页。之后,曾引起新加坡以研究地方史见长的学者王昌伟先生的注意。在一篇讨论关中理学传统建构的论文[注]参见王昌伟《王心敬《续关学编》与康乾之际关中理学传统的建构——兼论清代学术的区域化进程》引自余英时,黄进兴,王汎森《思想史5》,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版。中,他引用并认同林乐昌教授提出的宋代以还的“关学”并非一个统一的独立概念的论述。这表明,经林乐昌教授重新界定的“关学”概念在学术界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未来有可能成为关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诠释模式。此外,林乐昌教授所提出的关学演变三个阶段的新构想,与此前长期流行的把不同时代的关学都视作“一个独立学派”的观点相比,可能更符合北宋至明清关学史的实际。
总之,以上的论析虽然只涉及《探研》一书的四个焦点问题,但由此已足以看出作者对张载文献挖掘的用功之勤,对张载理学诠释的运思之密。一斑窥豹,于此亦可见新世纪以来张载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和仍需进一步拓展的课题方向。未来的理学研究,必然会出现多元拓展、彼此互补又不乏争论的局面。但无论何种研究,文献功夫、历史视野和现代诠释意识恐怕都是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探研》一书在以上几个方面所展示出的示范意义,对未来的张载理学研究,乃至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普遍争论问题的解决,都具有启发性,并能够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