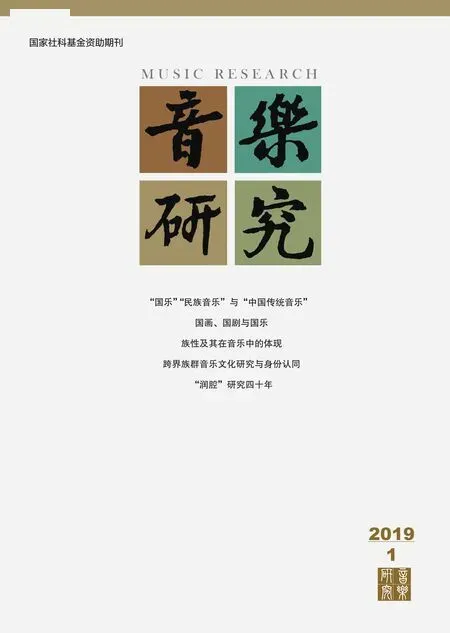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国乐”“民族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
——并非作“历史变迁”理解的现象观察与思考
2019-12-16文◎刘红
文◎刘 红
引 言
自《民族音乐概论》于1964年出版以来,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思考。《民族音乐概论》成就、成熟之前的“民族音乐”情形如何?民族(或说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是怎样的?具体而言,曾经以“国乐”作称而形成的“国乐观念”“国乐行为”及“国乐教育”,与之后的“民族音乐”这一概念、现象和行为有否承接、关联?再后来于当下,“民族音乐”到“中国传统音乐”之名称与概念转换,从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有了怎样的转变?对此转变应当做如何解释?
显然,从“国乐”到“民族音乐”再到“中国传统音乐”,不应简单当作名称上的更替、变化和演进理解,而应关注其于当时和当下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下,自身内在基本元素和本质特性被不同看待和理解而成就的事实。基于此,文章并非只是从史学的角度把历史上和曾经发生过的涉及名称、概念及其相关行为之改变的现象作罗列和梳理,而是欲求带着实际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①文章生成于笔者为研究生开设“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科认知”专题研讨课的教学过程。撰稿时,除摘录笔者部分授课笔记之外,参与课程学习的王悦、张若尘和高川惠三位同学亦协助进行了资料搜集及整理工作,特此致谢!
1964年,《民族音乐概论》出版。至此,以民歌、民族器乐、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为主体内容的“民族音乐理论”这一学科(专业)随之形成。近年来,“民族音乐”作称的这一学科,主体内容由原本“五大类”(亦或不包括歌舞音乐的“四大类”)增加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等类项而更多地被“中国传统音乐”所替代。针对改变了的这一事实,本文关注、思考并讨论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由于“民族”本身具有明确的“国家”含义,因此,学科渊源、理论基础,部分与该体系建立之前的“国乐”有关联。于是,需要深究的是,在国体、政体发生重大改变的新时代,“国”为主体的“民族音乐”,在学统、传统层面,无论是理论、理念还是现实、现象,与旧“国乐”的深度关联到底体现在哪里?“民族音乐”悄然冠之以“中国传统音乐”,不仅仅只是学科使用了新的称谓,更重要的是其实体也产生很大变化。名称上,原先的“民族”,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概念上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的“国家”之含义,实际包含着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基本属性,因此,“民族音乐”可以理解为“人民大众的音乐”,重视和强调的是人民共和国之“人民”这一根本。改称“中国传统音乐”之后,立于“文化中国”的视野和角度,更为强调的是概念最大化产生、形成并传承于“中国本土的”“中国人的”音乐。实体上,之前不被“民间”所包容的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被纳入了这一“传统”范畴。如果说,这一名称、概念的改变是因为原先“民族音乐”未能完整和全面地涵盖“中国音乐”现象,而使用“传统音乐”之名的“大家庭”有了本身就存在的“新成员”扩充,令实际内容、理论体系更为完善的话,那么问题是,传统大家庭里的新旧成员,是否可以在传统的“传统观念”下做出一致的解释?由表及里作探究,名与实,今与昔,“传统”二字如何辨析、认知?
是为问题的提出与缘起。
一、“国”之名义,“国乐”如何?
国乐,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概念和定义。1943年,陈洪在《国乐的定义》一文中说:“‘国乐’这个名称还是很新的,以前大都称为‘中乐’。‘中乐’也不是一个顶旧的名称,在闭关自守的年代,乐便是乐,无所谓中西;海禁开,‘西乐’来,才有人给它起这个称号,叫做‘中乐’,借以区别于‘西乐’;和用‘中文’、‘中画’、‘中医’等名词用以区别于‘西文’、‘西画’、‘西医’等一样。……爱国之士们,便又把‘中’字改成‘国’字,于是‘国画’、‘国医’、‘国术’等名称乃相继出现,‘中乐’也便改成了‘国乐’。”②陈洪《国乐的定义》,《音乐教育》1943年第2卷第12期。
众所周知,国乐是于20世纪上半叶在“新音乐”发展变化的背景下,随着西乐进入本土而出现的新称谓。正是因为伴随着西乐的进入而产生出国乐之名称和概念,因此,“国乐”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区别于或说比较于“西乐”而形成。
魏廷格对国乐形成的历史背景做了三种情形的概括③参见魏廷格《反思中国现代音乐文化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关于杨荫浏先生〈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18页。:
“全盘西化”主张。持此论者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所谓‘国乐’,而是世界普遍优美的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建立,要‘全盘西化’,……使基础先立定了然后再创作新的中国音乐”。④欧漫郎《中国青年需要什么音乐》,《广州音乐》1935年第3卷第617期。转引同注③。
“全盘中化”论。此论,直接见诸史料的不多。从间接材料可知,持此论者是两种背景截然相反的人士。一种是所谓“旧派乐师”,总以为“声音之纯正与精微,举世界当推吾国第一,他日西方乐师,必来吾国研究”。另一种是西方音乐家。例如当时活跃于上海的意大利指挥家帕奇,⑤Mario Paci(1878——1946),该观点见青主《论中国的音乐(给上海交响乐队指挥Mario Paci一封公开信)》,《乐艺》1931年第1卷第5号。转引同注④。就主张将来的中国音乐要由中国人指挥,用中国乐器演奏。
与前述二者取不同的角度,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种观点,即“内容决定国乐”。只要“内容”是中国的,形式方面西式中式均无不可。既然西方的工具比我们的先进,工具就应当“全盘世界化和现代化(也可以说是西化)”,但是“内容”则要“彻底中国化”。⑥陈洪《新国乐的诞生》,《林钟》1939年。转引同注⑤。
总体而言,彼时国乐观念大体不离乎此。那么,国乐的实质内容及其特征如何呢?
李岩对冠有国字的音乐的特征进行过这样的总结:⑦参见李岩《论国乐改进观念的衍变(1899—1949)》,载洛秦编《朔风起时弄乐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5页。
第一,历史最为久远。如叶伯和在《中国音乐史》中提出“古时的国乐”:“古来一朝一代,都要制一个曲子,拿来纪念,并且一切仪式都要用它,恰像现在的国乐。”⑧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卷),成都冒福公司1922年版,第19页。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音乐。如陈洪在《国乐的定义》中阐释的“‘国乐’是和‘西乐’不同的,用的是我国的乐器(其中虽有多种来自夷狄,然而经过了历史的磨练,文化熏陶,已经被同化了),唱的是‘合四乙上……’,写的并没有五线谱那么难懂……这便是‘国乐’”。
第三,能够代表民众意愿、情趣的音乐。如匪石曾指出古乐与国乐的区别:“古乐者,其性质为朝乐的而非国乐(的)者也,其取精不弘,其致用不广,凡民与之无感情”;王光祈也就国乐做出论述,他认为:“国乐是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之间所公认。因此之故,凡是‘国乐’须备具下列三个条件:一、代表民族特性;二、发挥民族美德;三、畅抒民族感情;这样的音乐才配称‘国乐’”。⑨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中华书局1924年版。
第四,是一种意义宽泛的,并受到西方音乐技法深刻影响的,并不囿于以往“国乐”范围、界限的音乐。如廖辅叔提出:“国乐,顾名思义,自然是指本国的音乐,中国人管中国事,那末,国乐就是中国的音乐。但是积习相沿,有些人竟把国乐解作中国的乐器”⑩廖辅叔《凑热闹谈国乐》,《新夜报·音乐周刊》第16期,1935年3月7日。。青主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尽真、尽善、尽美的音乐艺术,并没有国乐和西乐的区别。中国人如果会做出很好的所谓西乐,那么,这就是国乐。”⑪青主《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载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再看看直接或间接影响、促成“民族音乐理论”形成的一些国乐事实。
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以国乐之称进行的具体行为包括:组建国乐社团、国乐演出、国乐创作、国乐刊物出版和国乐教育,等等。
“五四”运动前后,南北各大城市里有许多民族器乐的爱好者组成各种社团,定期进行练习,不时也举行一些公演。其中比较重要的社团有:“天韵社”“国乐研究社”(1919),“大同乐会”(1920),“霄雿国乐会”(1925),“云和乐会”(1929),“今虞琴社”(1934),“上海国乐研究会”(1941),等等。这些社团的成员大多数是城市中的旧文人、职员、店员以及中小学教师等,研习的范围包括丝竹、吹打、古琴、琵琶以及戏曲(如昆曲和京剧)的清唱等。他们对传统乐曲的整理、研究、改编和民乐曲谱的刊行以及在对民族乐器的改革和制作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演出和灌制唱片等活动。如“大同乐会”柳尧章等人曾将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为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同乐会创办者郑觐文曾邀蔡元培、梅兰芳和周信芳等为赞助人,聘汪昱庭教琵琶,苏少卿、陈道安教京戏,杨子永教昆曲,郑觐文本人任乐务主任并教琴瑟,早期还曾请欧阳予倩教歌舞。乐会成立之时即设有研究部、编译部和制造部,负责出版音乐理论书籍、乐谱,教授乐器演奏,研制乐器,创作改编器乐曲。编译部先后出版了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和《笛箫新谱》,另作有《中西乐器全图考》《雅乐新编》,惜已佚。1930年1月,《国民大乐》在游艺会上首演,并将演奏实况摄制成影片,同年6月开排《中和韶乐》。1931年制成全套仿古乐器,共计163种。⑫陈正生《郑觐文与大同乐会》,《乐器》1994年第2期,第39—41页。1935年由于主任郑觐文的逝世,其活动亦不复往昔。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职业化音乐社团,在国乐的实践中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不难看出,此时的国乐社团发展的兴衰,与创办人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国乐”这一概念更多地被理解为中国器乐(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民族器乐”)这一面向,其创作的乐曲大多通过改编的方式而完成。
1922年,刘天华至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任国乐导师,接任王露先生的琵琶课,并于1927年成立国乐改进社,该社团主要针对国乐的调查、整理、提倡而进行。具体工作包括:刊印《音乐杂志》作为提倡音乐的至要工具;设立研究部,解决国乐各项问题;保存古音乐(合乐);音乐演奏会;举行国乐义务教育;开设乐器制造厂;名奏蓄音(保存现有国乐最紧要问题);创办《国乐改进杂志》。⑬刘天华《我对于本社的计划》,《国乐改进社成立刊》1927年2月。面对所做的这一些,刘天华曾说:“这种整理国乐的工作,哪里该人民组织团体去做,该是政府的责任。它早应立出正式机关去办理。”但“后来一想,现在国内政府如许之多,可是哪一个能注意到这件事的,还是省说废话罢!”⑭同注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对于国乐的整理和研究,主要还是以民间的社团自发性的活动为主,而国家对于“国乐”的关注度显然是不够的,也并未设立相应的研究机构进行调查和整理。在这一时期,“国乐”之“国”,更大程度上是民众出于一种新的国体的认同而对音乐进行的搜集与整理。
类似上述国乐艺术活动进行的同时,国乐教育也随之出现。
1918年6月,由成立于1916年的北京大学音乐团改组而成的北大乐理研究会,由蔡元培校长亲自草拟章程,宗旨是“敦促乐教,提倡美育”,下设“国乐部”和“西乐部”,并设置一些课程。如音乐学、音乐史、乐器和戏曲等。但因初创,先暂以教师之便设琴、瑟、琵琶、笛和昆曲五项。其中最早来北大任教的王露(王心葵)先生,受邀演奏古乐之后,被蔡元培聘为国乐导师,教授琴、瑟等古乐,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古琴教学进入高等学府之先河。⑮李静《北大的美育传统与音乐教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141—145页。1927年,萧友梅与蔡元培创建国立音乐院之初,即树立“一方输入世界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期趋向于大同,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志及其艺术”的办学宗旨,在选修或副科开设国乐课,朱英即受聘于该院,教授琵琶、笛子,吴伯超教授二胡,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培养国乐人才之先河。朱英作为首批在中国专业音乐学府任教的国乐教师,是全程见证国乐成为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亲历者,也是将琵琶引入高等专业音乐学府的重要奠基人。他对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在初创十年间逐步确立的中国高等专业国乐人才培养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⑯肖阳《朱英其人其事及其贡献——朱英在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十年间对国乐表演和教学经验的总结与思考》,《音乐艺术》2016年第4期,第74—81页。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在杨仲子担任院长期间,大力推行国乐教育,增设国乐系,并聘请杨荫浏、储师竹、陈振铎和曹安和等担任国乐导师。对于国乐教育的目的,杨仲子在《“国立音乐院”三十年度增设国乐系计划大纲》中写道:“1.造成兼长独奏伴奏及合乐之技术人才;2.造成国乐材料收集整理及研究之干部人才;3.造成国乐曲调修改及作曲人才。”⑰参见汤斯惟、张小梅《杨仲子音乐教育思想的演变探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128—137页。国乐系常设组别为研究组、合乐组、古琴组、琵琶组、二胡组、昆曲组以及一个其他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国乐导师兼任国乐教研室主任的杨荫浏,于1942——1944年间在《乐风》杂志连载专论《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为满足教学需要,还先后编写《国乐概论》《笛谱》《箫谱》《三弦谱》《音乐物理学》等教材。其中《国乐概论》被视为20世纪中国高校最早编写的“国乐”教材和专修课程。⑱乔建中《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教材的历史回顾与评述》,《人民音乐》2016年第12期,第32—35页。
基于上述事实,联系本文关心的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国乐”与其后的“民族音乐”在概念、现象和行为上有否承接或关联?
作为一个音乐概念,“国乐”的提出与主张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和状态有着密切关系。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之后,当时的“国”是由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国乐”因此具有彼时“国家”之属性和特性。民国承接晚清,中国社会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经历着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国家政治发生重大变革,成为共和制度。由于当时各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并立,使得在文化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地域、社会阶层分布上均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整个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作为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意识形态表现的文化也同样呈现出更为错综混杂的状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当时的文化状态有这样的概括:“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⑲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8页,第693页。这些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文化,在民国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化组合与激烈交锋,形成了复杂的文化场景。
“国乐”与“民族音乐”这两个称谓都包含有国家的概念和属性。我们虽然从上述国乐现象和行为中,很容易地看到其中涉及国乐社团、国乐演出、国乐创作、国乐刊物出版、国乐教育等相关内容在之后“民族音乐”中的部分延续或保留,但是,国体、政体、国家关系及国家实体的改变,先后出现于新旧两个不同的“中国”的“国乐”与“民族音乐”因此而有了某些(或某种)本质上的区别。其中显明之处在于,如果说国乐的名称是相对于、区别于或比较于西乐而出现,实体内容即是唯中国所有、唯中国人所为的话,那么,这一国乐之“国”,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具体于国乐为谁所为、为谁所用、为谁所有的主体、主人意识尚处于并不十分明确的状态。“民族音乐”则不同,它呈现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的主人。因此,具有国家概念和属性的“民族音乐”,“人民”是其主体和主人,此前中国的“国乐”中有违背人民意愿,不被人民拥有,不被人民享用的音乐事实和现象因此而未被“民族音乐”所采用。
这从《民族音乐概论》如何成就即可见一斑。
二、“民族”作称,“民族音乐”如何成就?
据当年参加过《民族音乐概论》编写工作的孙幼兰介绍,1958年文化部批示,将中央音乐学院附属的民族音乐研究所改为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于当年5月1日划归艺术局领导。1959 年5 月1 日,文化部艺术科学研究院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改属研究院领导,改名“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研究所在完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一至五编(未定稿)及参考资料15 种(约340 万字)后,为向全国各艺术院校提供《民族音乐概论》教材,于1960 年8 月举办“民族音乐”研究班。该班由全国23所艺术院校和文化局等七家有关单位的音乐专业干部39人和音乐研究所二十多位研究、资料人员共同组成。最终完成《民族音乐概论》的编写,于1964 年3 月由北京音乐出版社公开出版。《民族音乐概论》的公开出版,实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零的突破,为在民族音乐理论建设方面立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也为今后的继续研究开拓了一个新起点。从最早的五十多人写出的草稿,到八人的统修稿,再到四人的送审稿,《民族音乐概论》一步一步地从低到高、从粗到精、从松散到缜密、从不合出版要求到符合出版要求。《民族音乐概论》一书及12 本参考资料,不仅为全国音乐艺术院校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教材,也为教授这一课程提出理论指导。同时通过研究班的举办,培训了一批民族音乐理论的教学、研究人才,民族音乐理论的种子撒向了全国。这个重大的工作项目,应该说是开创时期的一次成功的实践。⑳参见孙幼兰《“民族音乐”研究班与〈民族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4期,第47—50页。
毫无疑问,“民族音乐”的理论建构,是以《民族音乐概论》的问世为标志的。
《民族音乐概论》从理论基础来讲,间接地可联系民国时期“国乐理论”“国乐观念”。具代表性的理论资源为杨荫浏1942—1944年连载于《乐风》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专论,1943年完成的油印本《中国音乐史纲》,以及《国乐概论》教材。较为直接的理论资源部分来自于延安“鲁艺”的民间音乐研究成果。“民间音乐研究的命名直接来源于1939年开始的延安鲁艺从‘民歌研究会’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历程,当时,身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吕骥给该系高级班讲授新音乐运动史,针对抗战之前对民间音乐的不够重视,发起了民间音乐的研究与采集活动。其时正值抗日歌咏运动的高潮,因此该会的成立深具标志意义。”㉑萧梅《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述要》,《黄钟》2009年第2期,第62页。《民族音乐概论》具体参考、参照的文献包括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绥远民歌集》《陕北民歌研究》;冼星海《为什么研究民歌》《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等。㉒刘永昌《延安鲁艺开辟民族音乐之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57—58页。尤其是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民间劳动音乐、民间歌曲音乐、民间说唱音乐、民间戏剧音乐、民间风俗音乐、民间舞蹈音乐、民间宗教音乐和民间乐器音乐等八类㉓参见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民间音乐论文集》,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版。的基本框架,对《民族音乐概论》产生直接指导作用,而且每类以“民间”作定性、定义,也为《民族音乐概论》之“民族”的界定起到指导作用。除此之外,1946 年3月31日,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第三教室成立的“山歌社”,也为《民族音乐概论》的成就提供了部分资源。“山歌社”以集体学习方式收集及整理民间音乐,其具体影响主要有以下四点:为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发掘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民歌;引领民族音乐走向音乐课堂教育;促进民族音乐走向大众。㉔参见吴璨《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发展的奠基者——音乐理论家郭乃安先生》,《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4期,第72页。“山歌社”的宗旨与实践,应该说与延安“鲁艺”的实践目的是有一定重合的。
《民族音乐概论》的实际资源便是该书编写过程中于1960年10月——1961年11月间完成的12本参考资料,即《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讨论选录与专题报告》《中国古代乐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民间歌曲》《城市小调》《古代歌曲》《歌舞与舞蹈音乐》《说唱和曲种介绍》《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㉕同注⑳,第50页。除《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讨论选录与专题报告》之外,其余基本上就是《民族音乐概论》所含民歌、民族器乐、说唱音乐、民间歌舞音乐和戏曲音乐等的专项分册。
综上可以看到,《民族音乐概论》的理论概括与总结,有保留、有取舍地承接了之前“国乐”的某些理念和主张。相比较于其后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却又缺少“非民间”而不包含在“民族”范围之内的一些内容。
原因何在?
据沈洽先生介绍,最早提出“民族音乐理论”这一术语,并把它用作一个独立专业名称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已故教授沈知白先生;接着,已故教授于会泳先生又提出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最初的学术框架;而“民族音乐理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学术上得以相对定型和推广则可以《民族音乐概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沈知白先生在1956年提出“民族音乐理论”这个学科名称。是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民族音乐系,沈先生为主任,即创设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沈知白提出的“民族音乐”概念比“民间音乐”要宽,它可以包括 “宫廷音乐” “宗教音乐”和“士大夫音乐”“文人音乐” 等。㉖参见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3期,第10页。很显然,沈知白提出的“民族音乐理论”构想与其后《民族音乐概论》由“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共五章构成的框架是不完全一样的,反倒是与当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相若。
《民族音乐概论》之所以没有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等纳入其中,书中引言部分已道明原委:“民间音乐,民主性的反封建的内容,是它的基本的主导的倾向。……其它的非民间音乐(如封建时代的文人音乐创作、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等),它们虽不都是劳动人民的创造,而且从它们总的倾向上来看,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㉗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第4页。在当时的编者们看来,“民间音乐”和“非民间音乐”“在总的倾向上有本质的差别”“渗透着两种文化的斗争”。因此,历史上由“臭老九”创作的文人音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宫廷音乐和宣传“封建迷信”的宗教音乐当然不能包括在教材中。㉘杜亚雄《“五大类”还是“四大类”?——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改革的建议》,《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2期,第16—17页。很显然,编写《民族音乐概论》时,是有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
1960年10月,《民族音乐概论》研究班编选、铅印了学习参考资料:《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小册子左上角特别注明“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字样),人手一册。该册子分“毛泽东同志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党和中央负责同志对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文艺界负责同志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三部分,摘录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周扬、郭沫若、沈雁冰、茅盾、夏衍、吕骥和周巍峙等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学艺术中的关键性问题》《继承和否定》等言论和文章68篇。小册子摘录的言论,具有旗帜鲜明的纲领性指导意义,对如何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有明确的主张。例如: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㉙《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1960年,第4页。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1页。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㉚《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1960年,第5页。摘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00—701页。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㉛《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1960年,第8页。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小册子上错写为1942年3月,笔者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7页,第62页。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㉜《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1960年,第12页。摘自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42页。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的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㉝《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1960年,第8页。摘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4页。
要继承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必须广泛地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首先对于目前在群众中最流行的旧有艺术形式进行改革的工作。……在音乐方面,应继续加强民间音乐的研究工作,并注意中国的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及中国民族器乐的研究与改造。……我们整个文艺工作的任务,主要的不是保存民族旧文学、旧艺术,而是发展民族新文学、新艺术。㉞《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1960年,第17页,摘自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讲话,见《文艺报》1951年6月第4卷第5期,第6—7页。
无论继承传统或学习外国,都必须有批判的态度。……继承传统,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加以保存,也不是无批判地模仿。保守主义,故步自封,只能使传统陷于停滞和衰落。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的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继承。㉟《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1960年,第30页,摘自《周扬同志的发言》,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510—516页。
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论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中表述得十分明确,即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批判地继承”,“民族”之根本由此体现。具体于如何“取”“去”以及怎么“批判”“继承”,《民族音乐概论》的立场和呈现出的样貌已经有所体现。缘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编写《民族音乐概论》时,我国正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社会上弥漫着极左思潮,音乐学界当然也会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㊱同注㉘。
三、“中国传统音乐”,承载着怎样的历史和现实之内涵与外延?
早年,杨荫浏先生曾说过:“国乐全部的事实,决不是某一点理论,某一种乐曲,某一种乐器,或某一样技术所可以代表的。从纵的方面说,我国有史以来,凡有音乐价值的记载、著作、曲调、器物、技术等等,都是国乐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从横的方面说,中原以及边地各省各市各村各镇的音乐材料,和曾与、正与、或将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的他国音乐的材料,也都是国乐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㊲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4页。这是从全部互有关系的古今中外音乐中审视国乐问题。㊳魏廷格《再议杨荫浏的国乐观》,《民族民间音乐》1994年第2期,第4页。
在笔者看来,面对当今中国传统音乐的事实,学者们仍然保持有杨荫浏当年倡导的对国乐进行研究的态度,正是“从全部互有关系的古今中外音乐中”“审视全中国”现象。在回答什么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问题上,已经展示出这种精神和态度:“中国传统音乐是指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包括现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音乐品种。所谓‘历代产生的’:既包括了古代的也包括了近、现代的(如某些乐种有上千年的—古代—历史,也有些乐种只有几十年的—近、现代—历史,像某些地方小戏)。”㊴参见董维松《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分类问题》,《中国音乐》1987年第2期,第41页。具体到传统音乐的实际包含,则大体将之分为四类:一是民间音乐,二是文人音乐,三是宗教音乐,四是宫廷音乐(当然都是“中国的”)。此外,有些品种可能还不能归到这四类中去,那么,就只好笼统称之为“传统音乐”。㊵同注㊴。从这一架构、体系中可以看出,原本“民族”的概念和属性仍然保留,没有改变,整体以“民间”作归纳放置于其中,展示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而创造、流传的民间音乐面貌。非普通民众创造和享用的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与“民间”并列,共同列入“传统”之中。于是,各有其所,本质、属性相异的民间、文人、宫廷、宗教四大类别共存相容,形成传统音乐学科调整后建立在宏大历史、文化观念上的新体制。
以《中国传统音乐概论》㊶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为例,在编著者博大深广的视野里,中国传统音乐,实际上是以历史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来定义的一个概念和范畴。与之前的《民族音乐概论》相比较,增加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内容而扩充了新体量的传统音乐体系,不能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先民族音乐理论这一学科的基本框架、实质内容和理论观念,但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补充或改写了民族音乐理论的历史。“民族音乐”被“中国传统音乐”取而代之,很显然不只是简单的易名改称。如果说“民族音乐”是因为包含国家、民众、民族诸关系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人民”属性而有此称谓的话,那么,改称“中国传统音乐”则是具体、实质性地以文化为主导,现象、事实为依据,以传统概念作定性而规约、规范形成的学科或者说学术体系。我们看到,名称的改变,不仅仅有上述实际指代关系和范畴的改变,改称后的实体内容更有超出我们一般认知程度上的重大调整。《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总体将始于《民族音乐概论》作概括的民歌、民族器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歌舞音乐统归到“民间音乐”为一大类,与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另外三大类并列构成传统音乐新体系,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编著者之一的杜亚雄看来,“全面了解我国传统音乐,是建设中华民族新音乐文化的需要,为达此目的,我们应当加强对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同时在教学中改变用民间音乐五大类代替传统音乐四大类的情况,在教材中适当地增加有关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下一代全面地了解我国的传统音乐,使他们能够继承、利用和改造传统音乐,为发展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做出贡献。”㊷杜亚雄《什么是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1996年第3期,第17页。
建立起“中国传统音乐”这一理论体系,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政策落实,思想观念、文化觉悟、文化态度发生改变、对传统文化重新认识的体现。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几许相似于当年五四运动之后的社会状态,而且影响更加猛烈。改革开放,一方面是要将国门打开,向西方开放,向全世界开放,另一方面要对国家自身旧有的体制进行改革。从部分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尤其是农村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农业政策的改革和实施,使得“民族音乐”的主要创造者和接受者——“人民”,不再以“劳苦大众”的身份和状态出现在国家、社会之中,而是逐步走出原本固有的生活模式,开始以多元、多样化身份成为国家的主人。
所以,从民族音乐到中国传统音乐这一转变,首先是“人”的转变。这里的“人”,即传统音乐现象的观察者和传统音乐现象的当事者。观察者有了新的觉悟,不再是带有部分主观色彩的“批判者”持“批判地继承”态度,有取舍地看待或对待观察对象;当事者有了新的姿态和身份,不再是“被压迫阶级”“劳苦人民”,而是享有同等社会权益的国家公民。“传统音乐”因此而由被“批判地继承”变为受“尊重地呈现”。其次是音乐体量有了调整、增大,而这一体量的增大,并不是因为传统音乐理论诞生之时,传统音乐实际状态发生了改变,学者们将之增补进去的,而是某种程度上原本存在的现象得以再认识的结果。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在于,如果在我们的理论认知、文化觉悟以及我们对待传统音乐的态度和方式有了改进、完善,对传统音乐理论的体量做重新审视、规划时让上述传统得以回归的话,那么,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就是,被重新纳入中国传统音乐体量中来的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这三大部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和具体行为上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由此引发出来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它,认识它,进而如何研究它的问题。
在认同传统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世代相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作品”㊸同注㊶,第3页。这一基本概念和界定的同时,在面对如何解释“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属性和特征时,仍然存在着是将它们当作“历史”现象看待,还是当作“传统”现象看待的实际问题。毕竟,历史与传统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
回到具体现象本身来探讨。
先说宗教音乐。宗教音乐之前被排除在“民族音乐”之外,是因为它不是劳苦大众享用的音乐,属性上不吻合“人民”的概念、要求和标准。因为它唯心、迷信,是有悖于唯物主义世界观而“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所以它从人民可以认知、受用的范畴中被剔除。当它再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音乐的视角之后,它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毫无疑问,国家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有了宪法保障,应该说普通民众开始对之有了重新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对宗教音乐的研究这几年迅速成为热点。以道教音乐研究为例,对道教音乐研究的文献进行检索和统计不难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呈迅猛增长态势,并一直持续至今。㊹参见拙文《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1957—2008)》,《音乐研究》2008年 第2期,第115—127页。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宗教音乐回归到了传统音乐理论的大家庭后被认同、被认知而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更主要的是有了被普通民众接受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条件。所以,这一问题于学界看来,是中断了以后,恢复、重构再继续研究的状态。
于文人音乐而言,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下时代还有对应得上 “文人音乐”的现象存在吗?回答这一问题,如何认定、理解和解释“文人”是前提。
“文人”一词,字面上可解释为有着较高文化修养和底蕴的群体。它衍生于周王朝的“士”阶层,最初是指为官之人。后来指有才能之人。而“文人”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诗·大雅汉江》中:“告于文人,锡山土田。”这里沿用了“士”的解释,意指有才能之人。从后来的一些文献中不难看出,“文人”就其字面义而言,一直用以指带有文德之人。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人的身份却处于一直变化的状态中。五代以前,文人以王公贵族居多,社会地位较高,“养士”之风盛行。比如在《孔丛子》中就说道:“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到了五代,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些文献记录中看出,文人的身份发生了转变。除原本帝王文人以外,这一时期出现了贫庶文人、僧道和女冠。由此可见,文人的身份出现了阶层下移的现象。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取消彻底打破了原本“士、农、工、商”的阶级排序,文人的身份再次发生变化。
到了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促使文人从众星捧月般的位置,变身为百业之一,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等都是有文化的人,但他们从事的职业,已经与文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分界,显见的事实就是文人的边界已经模糊。
“传统音乐”中所见的文人音乐仍然归于古旧的文人概念。当今,如何看待文人音乐遭遇到的现实情形是,旧时的文人状态、文人品格、文人修养以及文人所享用的精神和物质状态,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文人音乐已经走进“历史”不再“传统”,我们如何解释和认知置之于“传统音乐理论”之中的它呢?
再说宫廷音乐。帝王制度的灭亡和封建体制的消失,宫廷早已废除,伴随着宫廷而产生的宫廷音乐便随之载入史册成为历史现象。当它被纳入我们今天所认知和使用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于传统的角度、传统的观念将其当作传统音乐现象来看待呢?必须肯定的是,今天大量存在的传统音乐现实状态中,可以窥见古代宫廷音乐之遗存。但无论遗存也好,还是部分转换、变通到其他传统音乐类别中保存至今也好,作为宫廷音乐之概念作解释,从宫廷音乐独有的特性、特质上来看待,这种形式,这种现象于今天体现在哪里呢?
值得一提的相关现象是,当今纳入高等院校教学体系中的相关中国传统音乐课程的教学,并没有在已经从名称到实际内容发生了改变的状况下做应变调适。也就是说,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仍然还是以当年《民族音乐理概论》的理论框架和实际内容作为主体教学内容。其中增补的宗教音乐多见专题性讲习或单独开设课程,文人音乐和宫廷音乐则在音乐史课程中教授。出现这一现象,与其说教学安排上已经习惯旧有格式,改名而不变其实,还不如说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这一概念和学科,仍然面临一些实质性的无论是来自于理论体系本身,还是实际操行中的现实难题。
从“国乐”到“民族音乐”再到“中国传统音乐”,从单一逻辑看,似乎是固有传统音乐一个渐次发展的路向和轨迹。但通过三个阶段的回顾与梳理可以看出,它并非如同我们想象那般,是历史自然发展的顺序和规律,而是在我们认知体系、认知觉悟以及对待文化的态度、观念受制于特殊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状态下,有人为取舍、干预甚或改变的事实记录。
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已自成体系。而对其进行系统而又相对独立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否也已经形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