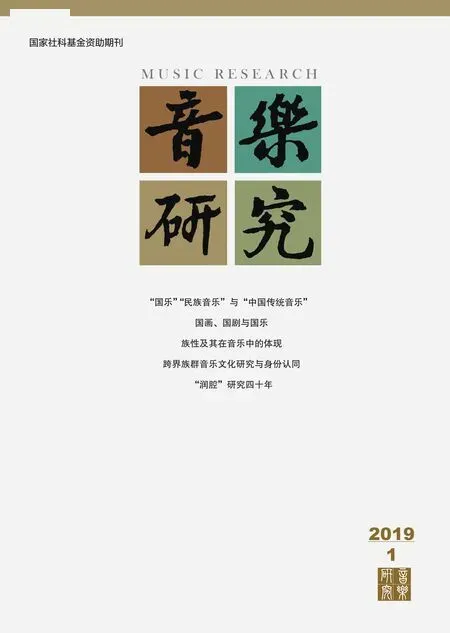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润腔”研究四十年
2019-12-16郭克俭
文◎郭克俭
在我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实践中,“依心抒怀”的即兴创作现象由来已久,古代曲家不乏精辟论述。明人王骥德在“论腔调”中便开宗明义地道出堂奥:“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①(明)王骥德《方诸馆曲律》,载傅惜华编《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曲有格范而唱可生变,显然在王氏看来,中国戏曲音乐是由“基本曲调”和“歌唱把握”两部分构成,那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唱腔种类以及异彩纷呈的歌唱风格流派,便是由演唱者的方音、曲调、歌节的“润色”变化生发形成的,故有“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几变更矣。大都创始之音,初变腔调,定自浑朴,渐变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极矣”②同注①,第46页。之慨叹!
将“腔”辅以“润”字修饰而拟构为一个音乐专用术语③参见《文汇报》1963年6月10日第四版载《对声乐民族化、群众化的一些看法——从马国光同志的演唱谈起》一文。,道出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创作与表演中最惯常使用的一种音乐艺术实践轨范,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师于会泳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重要总结提炼。④关于“润腔”概念由来考证,笔者拟专文详述,此不赘言。此概念创设不仅是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创作与演唱现象的创造性总结,而且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润腔”概念析出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创作与表演中腔词关系处理经验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并没有得到中国音乐理论界的足够重视,令人遗憾地戛然而止。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春天来到了,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迎来了新的生机活力,“润腔”问题迅即引来音乐人的高度重视,成果丰硕,成绩斐然,本文拟从新时期理论接续、“国音”学者理论自觉和新世纪有效拓展三个方面,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润腔”的学术之旅给予历史追溯与理路思考。
一、新时期理论接续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伊始,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民族音乐学者连波和沈阳音乐学院青年民族声乐家丁雅贤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润腔”。连波率先在其专著《弹词音乐初探》(以下简称“连著”)中专设一章讨论唱法润腔问题,作者认为影响演员唱腔韵味的决定因素,是演唱者对所唱的内容理解不深,以及唱法上的润腔加工不够。“务须根据各自的理解,在平面的曲谱上予以细致的艺术加工,使它成为活生生的、立体化的音乐形象。”⑤连波《弹词音乐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页。作者通过大量的曲谱实例,从吐字归韵、收放摧撤、颤音唱法、装饰音作用(强音式、弱音式、韵味式、整字式)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弹词演唱润腔的技巧。毫无疑问,“连著”在运用“润腔”基本理论对具体曲种——“苏州评弹”的个案研究上是具有精当的理论把握和深入细致的型态分析的,不仅鲜明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学术承继性,而作者对江南语音谙熟所凸显出语言上的优势,成为该著学术超越,最为突出的亮点。或许是所谈对象影响力以及著作出版发行数量等所限,该著以及“润腔”成果在学界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以致“连著”成果在其后的相关文论中鲜有提及。
在1979年10月辽宁省音协举办的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大型学术报告会上,丁雅贤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题为《民族唱法浅论》的发言,在其中的第八个论题“润腔行腔法”中,从装饰音润腔法、音色变化润腔法、力度变化法和速度变化法四各方面,重点分析民族声乐演唱中的润腔方法。丁雅贤的声乐学术报告得到现场专家的高度认可和充分肯定,引起中国音协辽宁分会领导的重视,遂指派专人协助丁雅贤整理该学术报告文稿,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民族唱法浅论》于12月12日定稿⑥丁雅贤《民族唱法浅论——学术报告提纲(1979年12月12日)》,载《心灵的歌唱》,沈阳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页。;并先后以《对民族唱法的认识与体会》⑦《中国音协辽宁分会会刊》1980年第2、3期连载。和《谈民族声乐演员基本功与训练》⑧载《第三届沈阳音乐周理论、学术报告选编·论乐篇》,1980年编印。发表,作者在后文“润色唱腔的基本功”部分,又将润腔方法进一步细化为“装饰音润色唱腔法、旋律进行的连、断润腔法、音色变化润腔法、力度变化润腔法、声音造型润腔法、用节拍和速度的变化来润色和处理唱腔”六种润腔方法。⑨丁雅贤《谈民族声乐演员基本功与训练》,载《第三届沈阳音乐周理论、学术报告选编·论乐篇》,第269—280页。
为了使民族声乐润腔演唱更加规范、直观,丁雅贤从连腔、断腔、装饰音、音色的变化、力度的变化、速度的变化和音高的微变7大类61个子类,对相关润腔法给予符号编码设计,同时就各自的动作要领、艺术效果、符号和简短谱例等进行概要说明,⑩丁雅贤《关于编定民族声乐润腔技法符号的意见》,《乐府新声》1989年第2期,第27—32、26页。此学术成果在中国音乐学院于1986年6月23——29日举办的“全国部分高等艺术院校民族声乐教学教材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引起与会专家同行良好反响。吉林艺术学院民族声乐教师张淑霞在演唱教学实践中亦对民歌“润腔”感同身受,是次会议上作题为《“润腔”技巧在民族唱法中的意义》发言,她把“润腔”作为永葆民族声乐教学特色的首要条件和装饰旋律的方法,认为它是“我国传统歌唱技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是最能体现民族风格特点的一种表现手段。”⑪张淑霞《“润腔”技巧在民族声乐中的意义及分类》,《艺圃》(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55页。作者将“润腔”艺术表现分为与“字调”相关的、风格色彩性的和与表情达意相联系的等三种,并结合北方民歌实例分析,探讨民族声乐演唱中的“润腔”问题;认为对于“润腔’能力的培养,既是技巧训练也是乐感的训练,而首先是乐感的训练。
应该说,作为从事民族声乐教学丁雅贤、张淑霞能够有如此超前的理论自觉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对民族声乐演唱、教学和理论探索无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丁雅贤的研究在音乐理论界产生较高的赞誉度,是故,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其中“润腔”条目便由丁雅贤撰写。显然,丁雅贤关于润腔概念的阐释,比1984年出版《中国音乐词典》中将“‘润腔’和‘加花’等同”⑫参见《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的做法,相对要更为精准、细致和具体,也更为学术化。
继上述三人分别从曲艺(苏州评弹)、民歌(民族声乐)等视角研究“润腔”问题之后,河南戏曲学校陈小香在对其母亲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舞台演唱艺术进行研究时,便专题论述常派演唱艺术的润腔方法,明确指出“润腔既是一种创作手段,又是一种演唱技巧。润腔是指润饰唱腔的韵味而言,同一曲调,同一唱腔,如果采用不同的润腔方法,就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⑬陈小香《常香玉演唱艺术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由于自幼耳濡目染,随母学习豫剧声腔演唱,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积累了丰富的感性体验;而后又到河南大学跟随声乐教育家武秀之教授学习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系统地学习了中外音乐(声乐)理论知识,开阔了艺术眼界,为系统研究豫剧“常派”演唱艺术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陈小香关于润腔的学术成果在地方戏曲演唱流派研究中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二、“国音”学人理论自觉
以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为己任的中国音乐学院复校后,音乐理论家薛良及其指导的国音器乐学生席强,从“吟唱”视角切入“润腔”的学术探索,成果颇为丰富,其间还合作一篇长文,从中西管弦乐队发展的历史回顾入手,运用比较音乐学研究的方法,思考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乐队编制组合、民族乐器改革和民族管弦乐曲创作等问题,最后提出弘扬中华音乐文化,继承和发扬民族器乐传统,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排除阻碍,为振兴民族器乐艺术事业而共同奋斗的宏大命题。⑭薛良、席强《从中西比较看民族管弦乐队》,《中国音乐》1994年第3期,第5—9、12页。在通俗音乐潮涌、电声乐器风行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思考上述问题充分体现了老少两代学者对传统音乐文化自信和使命担当。题外之言,此不赘述。
薛良先生从民歌演唱中窥视出“依字润腔”现象,通过运用“倚音、滑音、颇音、直音、连音、断音、摇音、擞音,等等”手法润色曲调,达到润腔艺术效果:“歌唱者意识地或下意识地按着字音的调值,用其惯用的美化手法去‘润色’基本曲调,并在歌唱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品种、地区、个人的特有风格与韵味。”⑮薛良《吟唱与咏唱》,《中国音乐》1982年第2期,第46页。十年之后,薛良依然从“吟唱”音乐理论体系视角观照“润腔”,呈现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东方音乐特别是中国音乐,是以吟为基础的音乐体系。即传统上所说的:‘框⑯应是“筐”,可能是校对有误。格在曲、色泽在唱’。也就是说,乐谱只写出曲调的框架,唱奏者在唱奏时,要对骨干音调进行润色,名之为‘润腔’。”⑰薛良《论“框格在曲,色泽在唱”》,《中国音乐》1992年第3期,第5页。连续十年持续关注“润腔”问题,体现一位资深音乐学者的学术坚毅,为后学树立楷模。
应该是在薛良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青年学子席强对“润腔”学理有过一个时段的持续研习,在两年内连续发表四篇关于“润腔”的较有个人见地的文论。⑱席强见刊四篇润腔文论分别是:《“润腔”初探》,《中国音乐》1991年第4期,第52—53页;《民族曲调中的“润腔”结构》,《中国音乐》1992年第1期,第34—35页;《润腔与记谱的关系》,《中国音乐》1992年第2期,第11—12页;《调式与润腔》,《中国音乐》1992年第4期,第46—48页。他同样以声乐中的“吟唱”入手,类比至器乐上的“吟奏”,认为“润腔”是“吟唱”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音乐歌唱传统中的一个基本规律,而“吟唱”方法运用的层级水准是关系我国音乐风格把握准确与否的根本。作者两次对“润腔”概念给予定义,开始直言润腔“就是在‘吟唱’的基础上对某个基本曲调进行装饰性的华彩演唱。中国音乐的曲调(主要指汉族音乐)在歌唱时往往因歌词、乐种、歌者、时间、地点等因素的不同,可以对它即兴地加以变化、装饰和发展,使之产生丰富多彩的音乐效果。即‘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润腔的形式多种多样,它主要是运用上、下倚音、复倚音、颤音、滑音、顿音、连音、擞音等方法,在歌唱中,使曲调的音高与字音的声调保持相应的一致性,从而,增加其鲜明的艺术风格。”⑲席强《“润腔”初探》,第52页。由此引申,认为“润腔就是以曲调的核心音或音调(骨干音)为主,辅之以不同形式的装饰音(如颤、滑、连、顿、擞、假声等)来构成一个完整的音调结构。在这种过程中,其音高、时值、力度、音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⑳席强《润腔与记谱的关系》,第11页。作者从润腔概念界定延伸到润腔与曲调结构、润腔与记谱、曲谱与调式,学术关涉阈限颇为开阔,展露了良好的学术潜力和发展前景;但“中国音乐的曲调(主要指汉族音乐)在歌唱时……,可以对它即兴地加以变化、装饰和发展,使之产生丰富多彩的音乐效果”“‘吟唱’是我国音乐中所特有的”等类似绝对化且并不十分严谨的语言表达,是年轻学者大多难以避免的学术瑕疵,而或许是工作性质的缘故,作者没有就此课题继续深入下去更是大憾。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家董维松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研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音乐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在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学、民族音乐结构、民族音乐形态和戏曲声腔分析等方面都有独到创见。21世纪又推出宏篇大札《论润腔》㉑董维松《论润腔》,《中国音乐》2004年第4期,第62页。(以下简称“董文”),成为作者最具代表性学术之一。“董文”开宗明义地对“润腔”给予定义:“润腔,是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家们,在他们演唱或演奏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的乐曲(唱腔)时,对它进行各种可能的润色和装饰,使之成为具有立体感强、色彩丰满、风格独特、韵味浓郁的完美的艺术作品。”㉒同注㉑,第62页。正文首先从字、情、韵三方面总结润腔的功能,进而从音高式、阻音、节奏性润腔、力度性润腔、音色性润腔和其他润腔手法六个方面重点论述润腔的类型及其技法。
作者以演唱(奏)表演为出发点,在借鉴并吸收前人及同辈成果的基础上,以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缜密条理的篇章结构、平易准确的语言阐释、丰富多样的乐谱实例,撰写了一篇高质量、高水准的传统音乐学术专论,凸显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非凡的学术表达,不仅在我国传统音乐学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作为教师通过课堂上的言传身教,哺育了一批批“国音”学子。如2004年秋季于该校声歌系进修的湖北民族学院声乐教师梁佶中,便将理论学习心得整理成篇刊载,㉓梁佶中《民族声乐的润腔艺术》,《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5期,第48—53页。四十多个引用率足以表明该文业已成为新世纪颇有学术含量和影响力的润腔篇什。
毋庸置疑,洋洋万余言《论润腔》是自“润腔”概念提出之后长达四十年间最为集大成的力作,是一位资深的学者长期孜孜以求关注和思考的学术成果。“董文”见刊十多年来已被国内作者转引高达193次、篇目下载1494次之多,㉔参阅中国知网检索数据(截止2018年12月15日)。更有学者专文对《论润腔》给予赞誉性评介。㉕冯光钰《润腔研究的新角度——写在董维松教授80大寿之际》,《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第1—3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此文开启了新世纪“润腔”学术研究的崭新篇章。
三、新世纪有效拓展
长期从事声乐教学与歌唱理论探索、在歌唱与语言研究方面建树颇丰的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声乐家许讲贞,其主持申报艺术科研项目“原生态民歌演唱的润腔特色研究”,成功获得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课题立项㉖立项批准号:05BD027。;经过近四年的辛勤耕耘,作为国内唯一国家级艺术科学“润腔”研究项目成果出版的第一本专事“润腔”的学术专著《汉族民歌润腔概论》㉗许讲真《汉族民歌润腔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内容由理论、特色、案例分上中下三篇共19章组成,作者广泛吸收和借鉴既往理论研究成果,运用文字阐述、谱例说明和音响佐证相结合的方法,广延系统、言之有物、形象具体、有声有色,洋洋洒洒近五十万言,及时地填补声乐理论“润腔”研究专著的空白。作者给出“润腔”定义是:“润腔是在‘吟唱’的基础上,对某些基本字调进行装饰性的华彩唱奏,其基本字调是框架式的、相对固定的,对于唱奏者来说带有很大程度的灵活性、即兴性和随意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唱奏者可根据基本字调,因时、因地、因人、因曲唱奏出种种不同的花样,以形成多变的色彩和风格。”㉘同注㉗,第3页。不难发现,这个定义是对前述薛良、席强关于“润腔”观点的吸收、借用和引申,作者对“润腔”作用和意义的总结,可以看作是其对“润腔”概念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的立体表达和认知升华:“润腔是唱奏者将‘死音’变为‘活曲’的再创作过程,是唱奏中行腔的主要艺术特色,也是标新立异、平中出奇、鲜活靓彩、丰富多彩艺术风格的内核,是构成韵味、风格、流派的决定因素,是我国民族声乐中最有审美价值、最为独特、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㉙同注㉗,第5页。这种论述成为《汉族民歌润腔概论》写作重要的内在动力和展开的逻辑出发点。
受董维松先生的影响和启发,戏曲音乐家汪人元以京剧为对象考索“润腔”论题。尽管作者依然围绕音色、旋律、节奏、力度和字音等五个方面展开,但文字论述细致深入、逻辑谨严,曲谱例证精准确凿,两万余言的长大篇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京剧音乐功力。“汪文”将“润腔”视为中国民族声乐表演技术技巧的专属:“润腔,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中一种对唱腔进行润饰以获得美化、韵味、以及特殊表现力的独特技巧与现象。”同时将“润腔”提升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高度认识:“润腔作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中将死谱变为活唱最为重要的基本手段,决不只是一个浅层次的技术技巧,而有一个从外到内、从形到神的技术体系,从而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独特的风格、意境和精神。”㉚汪人元《京剧润腔研究》,《戏曲艺术》2011年第3期,第1页。并不无感慨地说:“润腔是与中国民族音乐自身的传统与精魂及其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㉛同注㉚,第2页。“汪文”对润腔的意义所作的“是为了‘达意’、是服务‘表情’、是获得‘美听’、是形成‘风格’和是追求‘韵味’等五方面”㉜同注㉚,第9—11页。的阐发,成为承上启下且最为全面的概括。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假借《腔词关系研究》著作公开出版发行㉝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的学力助推,“润腔”研究的学术魅力愈益彰显,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重点关注,特别是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求索的目光,昭示着“润腔”研究在新时代的光明未来前景和良好发展态势,研究的兴趣点从概念释义转向演唱实践的求索,出现了一些很有质量的篇什。㉞卓松年、杨珍《京剧旦角润腔规律初探》《戏曲研究》2010年第1期;张盈《论“歇气”润腔法——福建南音泉州派和厦门派的唱腔差异》《乐府新声》2010年第4期;沈德鹏《浅谈中国声乐作品中的腔》《乐府新声》2011年第2期;阳梅《程砚秋京剧润腔分析——以〈荒山泪〉〈锁麟囊〉为例》,《齐鲁艺苑》2011年第3期;张莺燕《宋代唱论中的润腔探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何益民、欧阳觉文《湖南花鼓戏润腔二十一法初探》,《音乐创作》2013年第8期;令狐青《中国民族声乐理论研究刍议——以汉族民歌“润腔”理论研究为例》,《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樊凤龙《润腔及其在晋剧唱腔中的运用》,《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1期;胡晓东《佛乐唱导韵腔技术分析——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唱腔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陈燕婷《南音润腔之美》,《音乐与表演》2016年第3期;韩菽筠《梅派京剧“咬字吐字”和“润腔”技巧在京歌中的运用——以京歌〈梅兰芳〉的演唱为例》,《人民音乐》2016年第7期;郭茹心《润腔语词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润腔辨析——以上党梆子〈窗前梅树是我友〉为例》,《中国音乐》2016年第2期;王亮《中国民族旋律润腔读谱方法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石尉《从“润腔”看霍俊萍五音戏演唱特色》,《戏曲研究》2017年第4期;邢晓萌、徐敦广《汉族民歌合唱润腔的韵味及其表现》,《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孙晓洁《润腔技巧在唱腔中的应用》,《中国京剧》2018年第10期。令人欣慰的是,器乐表演艺术润腔技巧研究方面同样有一定的突破和进展,㉟包爱玲《浅论蒙古高音四胡演奏技巧的“润腔”手法》,《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赵琦:《王建中钢琴作品的润腔特色》《大舞台》2014年第2期;张丽《精湛作品的隐秘结构研究——“微”视角下闵惠芬二胡润腔艺术力度形态解析》,《人民音乐》2015年第11期;戴维娜、王佳怡《江南丝竹琵琶昆曲化之润腔演奏初探》,《艺术研究》2016年第3期;唐荣《论杨立青的〈荒漠暮色〉与中国传统音乐的润腔》,《音乐艺术》2017年第4期;郑怀佐《闵惠芬二胡“声腔化”演奏技法探究》,《音乐与表演》2018年第3期。凡此种种,无不为“润腔”学术研究提供诸多颇有价值、可资借鉴的学术案例。
结语:更待未来
自1963年“润腔”概念首创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前述众多专家特别是以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为己任的“国音”学者群体吸纳、认同、领悟和探索,“润腔”概念命义内涵已基本明晰。由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润腔”,就是指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唱奏)过程中,根据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感情内涵、风格流派的要求,充分调动并合理运用音色、旋律、力度、顿挫、节奏、语音等技艺手段,遵循艺术内在的规律对唱腔曲调进行各种有效的润泽、修饰、着色和美化,使之成为人物生动、形象逼真、感情饱满、意境深远、风味醇正、气韵超拔和美善统一的艺术臻品。“润腔”是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段、艺术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特色,是唱奏者将“死音”变为“活曲”、化“僵谱”为“妙乐”的创造性转化的、再创作升华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艺术性、地域性和时代性。
杨荫浏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对(中国音乐)风格、传统都要扎扎实实地去研究,不要老讲空话,追求表面的东西,以个人的好恶代替科学的研究工作。自己不下功夫,企图简单地一两句话就想概括了,那是懒汉思想。”㊱杨荫浏述、李妲娜整理《谈中国音乐的特点问题》,《中国音乐》1982年第1期,第10页。作为中国传统音乐表演重要理论话语,虽然“润腔”四十年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距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广博的音声外延、丰厚的学术底蕴和强大的理论张力,却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对我国各民族音乐风格品类的整体把握和全面探究更是不足,更是缺乏持续深入的探究者。就让我们牢记杨先生的教诲,不做懒汉,争当一个中国音乐学术的勤快人,期待有志于传统音乐研究的八方学人联合攻关,呼唤共建“中国润腔学”宏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