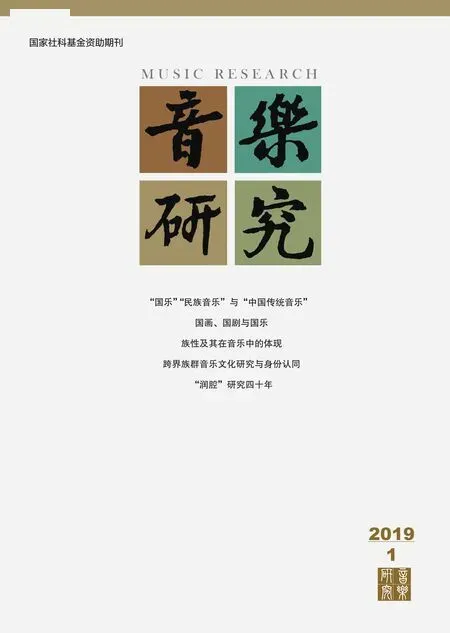宏观与微观: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认同研究的双重视角
2019-12-16张应华
◎张应华
随着人类学“文化认同”研究的深入,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除“根基论者”的观点外,①当代社会人类学对于“族群认同”有四种观点:客观论、主观论、根基论与工具论,依照王明珂的观点,根基论与工具论均属于主观论,根基论代表人物有西尔斯(Edward Shils)、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伊萨克(Harold P.Isaacs),他们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源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界: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其他学者总是把认同看成是一种关系思维,一种在与他者互视中确立自我或他者的心理诉求。关系思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认识论观念,它引导着研究者采用宏观的研究视角,在多点、动态的策略中进行多主体的比较研究,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区域、族群、跨境甚或“文化通道”的语境中,说明音乐的观念和行为所表达出来的诸如“我是谁”“我属于谁”的主体性属性。然而,当我们回到定点个案进行微观田野体验和深描时,我们将会再次发现同一族群或同一乐种内部的差异性表述。这种差异性表述类似于“根基论者”的结论,它原发于历史性、原位性和根基性的情感心理诉求,亦或像“工具论”②工具论的代表人物有德普雷(Leo A.Despres)、哈兰德(Gunnar Haland)、科恩(Abner Cohen),他们基本上是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界: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的观点,是族群或乐种内部竞争与分配的结果。文化认同研究的宏观视角是一种“跳出来”的领悟与理解,一种从具象层面到抽象层面的理论思考,而文化认同的微观视角则是一种“走进去”的体验与深描,一种从理论观照到具体事项的民族志调查。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跳出走进”的田野过程中,以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角予以叙事与书写的。
一、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认同研究的宏观视角
当下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往往采用宏观视角的策略,其起始点源于杨民康组织的国外“音乐与认同”文论的译介③杨民康《“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研讨专题主持人语》,《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3—11页。,尤其是魏琳琳对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两篇评论性文章④蒂莫西·赖斯著,魏琳琳译《民族音乐学中音乐与认同的反思》,《音乐探索》2014年第1期,第49—58页;蒂莫西·赖斯著,魏琳琳译、温永红校《建构一条“民族音乐学”学科新的路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0—125页。的翻译,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民族音乐学界有关“音乐与认同”的研究成果与特点。依照魏琳琳的译介,当下美国“音乐与认同”的研究主要以“音乐与现代民族——国家”“音乐与种族、族群”“音乐与离散族群、移民”以及“音乐与性别”作为研究主题,⑤魏琳琳《海外民族音乐学视野下“音乐与认同”研究》,《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第152—157页。其中前三者是当下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的焦点,分别在历史、区域、族群、跨境以及“文化通道”的叙事中予以展开。
(一)历史民族音乐学与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内地文化认同研究
就当下研究实践来看,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内地文化认同研究始于西方“音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但在研究的理论基点和目标取向上,走的却是反向的路径。在西方,“音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往往选取与现代性相对应的乡村音乐作为对象,并在“共时性”层面将其与种族问题、民族主义倾向和社会权利问题联系起来,张扬文化间的压制与抗争,比如《来自民间的叛逆》一书充满着躁动和矛盾,展示的不仅是美国民歌的历史,也是种族、社会权利抗争的历史。⑥参见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彼得·曼努埃尔(Peter Manuel)研究美国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他者性文化,认为萨尔萨舞曲(salsa)“在美国是一种他者性”建构。⑦转引自蒂莫西·赖斯著,魏琳琳译《民族音乐学中音乐与认同的反思》,《音乐探索》2014年第1期,第49—58页。瑞格韦(Regev M.)认为以色列摇滚乐受到阿拉伯音乐的影响,表现出一种他者性的喧嚣和争执,美国黑人的音乐是在“农奴面对西方产品、反对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⑧同注⑤,第152—157页。。
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内地文化认同研究则是历史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历时性”研究,并以此建构西南社会“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思维,阐发学者对于民间的学术思考,叙述宫廷音乐在西南少数民族族群中的“移植”,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对于汉传音乐文化的“借用”,进而揭示西南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心理及其历史成因。
历史民族音乐学结合民间口述史的研究表明,历史上西南土司王府的礼俗用乐是为了建构少数民族社会“蛮夷—土司—朝廷”的“权利级序关系”,然而这种级序关系即表现为西南土司用乐的“内地文化认同”。有研究表明,云南禄劝彝族凤氏土司王府的礼俗用乐来自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汉传文化,实则是一种“边疆王府”的身份表达。⑨杨嘉兴《武定禄劝彝族土司府礼仪乐探微》,《民族艺术研究》1995年第6期,第29—34页。项阳、张咏春以曲牌【朝天子】为研究对象,在历时性的文献梳理中描述了禄劝土司王府的【朝天子】与明代官方礼乐、乾隆钦颁导迎大乐以及流传在长沙、苏州等地的【朝天子】的“家族相似性”⑩项阳、张咏春《从“朝天子”管窥礼乐传统的一致性存在》,《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1期,第33—42页。。傅利民在历时性的唱腔曲牌比较研究中发现,贵州地戏是江西弋阳腔的“活化石”⑪傅利民《弋阳腔之活化石——贵州安顺“地戏”音乐考察》,《音乐探索》2005年第3期,第18—22页。,肖可则认为贵州地戏是明代“军屯人”在与“黔中夷”处于严重军事对抗中表达汉民文化身份的戏剧唱演。⑫肖可《从布依族地戏的分布看布依——汉的文化接触》,《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31—34页。有学者在民间口述的追述中发现,历史上石阡木偶戏的唱演是汉传道德观念在少数民族族群中“教化”的行为方式,“在文化观念上逐渐内地化、中心化、国家化”⑬张应华《湘黔交界少数民族社区的汉传戏班——以石阡木偶戏为例的艺术人类学考察》,《艺术探索》2011年第6期,第51—54页。。胡晓东从西南地区佛教历史变迁的角度展开当地佛教音乐的调查研究,发现其社会教化与社会治理功能实际上是“国族认同”的表现。⑭参见胡晓东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佛教音乐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课题编号16BMZ069。由之看来,历史民族音乐学从史学视角切入,结合民间口述材料,构成了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内地文化认同之历史成因的研究维度。
(二)区域音乐研究与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区域文化认同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区域文化认同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区域民族研究一脉相承。在这里,“区域”是一个抽象理论关照的概念,如周大鸣所言,“区域研究一个多学科合作的概念”,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突出“跨文化的比较观和整体性的视角以及全貌性民族志的撰写方式”。⑮周大鸣《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脉络与反思》,《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36—46页。当下,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在西方早期“他者”区域研究的反思中进行着中国本土实践,出现了“藏彝走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华北农村”“珠江三角洲”等区域民族志研究。
与此相同,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也从文化地理学出发,走向区域性的音乐研究。在乔建中的主持下,2011年,《音乐研究》刊发了区域音乐研究专栏,探讨了区域音乐研究现状、理论、个案书写等问题。⑯参见《音乐研究》2011年第3期,编发了蔡际州《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张晓红、郑端《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博特乐图《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多元构成及其区域分布》、李敬民《论音乐文化的过渡与融合——以淮河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区的基本特质为例》四篇文论。杨红讨论了区域音乐静态、动态、关系、意识的空间级序、“乐种—乐类—乐丛—乐系—乐圈”的文化系统、“主文化—亚文化—跨文化”层级关系以及流动的“人—音—地”的声音景观及其与社会文化的整合关系。⑰杨红《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区域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4期,第103—111页。项阳则认为区域音乐研究要有“区域与整体”“行政区划与生活区划”的学术敏感,要注重“多民族聚居区的意义”“历史人类学学术理念之运用”和“区域研究中的国家存在”。⑱项阳《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人民音乐》2013年第2期,第42—45页。有学者提出,区域音乐的研究“不能忽视与区域音乐认同之间的关系”⑲赵书峰《跨界区域历史认同——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四个关键词》,《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21—29页。。
沿着这一学术理路,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区域文化认同研究凸现出来,它往往选择边界相对清晰的地理文化空间,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不同族群音乐文化的区域性多点参与体验,并在此基础上跳出单个研究对象的文化圈层,在宏观观察的视角中“探寻各族群文化之间的相互‘借用’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域风格特征”。⑳同注⑬,第51—54页。如张黎临的田野调查发现,象脚鼓舞流传在八个民族中,形成了“一元多支”的区域文化认同特征。㉑张黎临《滇西南象脚鼓与象脚鼓舞的演进及流播研究》,云南艺术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区域文化认同研究更为关注同一文化地理空间内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涵化以及对于第三方文化的共同享用。李继昌、张仁卓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水族芦笙的形制和结构与苗族一致,这是水、苗一家共同聚居、文化互渗的结果。”㉒李继昌、张仁卓《山奇水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页。有学者认为,黔东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地域文化认同的原动力来源于各世居少数民族族群的生产、生活或者经济交往,最终促成了族群间的文化涵化与认同。㉓张应华《“古苗疆走廊”与黔东民间音乐的三重认同》,《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6—23页。另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区域文化认同往往“借用第三方文化”作为沟通的渠道,许甜甜的田野调查和量化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一张贵州各少数民族借用汉传民歌“赶马调”的结构性山歌文化网络。㉔许甜甜《论贵州汉族母体民歌“赶马调”及其同宗民歌》,贵州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三)族群音乐民族志研究与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族群文化认同研究
族群音乐文化认同研究与以往以族群为个案的“微观”音乐民族志研究取向不同。微观音乐民族志研究指向具体的田野实践,聚焦研究对象“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的文化事实,其方法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微观地选取、观察或体验一个相对闭合的文化结构;其二是全面地定点田野调查,详细记录调查对象的文化事实;其三是排除调查者的主观思考,尽可能地客观呈现调查对象的观念、行为及其生态、历史和社会控制。
但是,族群音乐文化认同研究则往往聚焦于音乐文化事项背后的身份心理认定和确证,因而,尽管族群音乐文化认同的研究仍然是以某一族群为研究对象,但它是一种抽象的关系思维,是在多点主体之间的比较分析和理论探究,是通过“另一个我”的差异,来反观自己的身份特征。在方法论上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是从宏观视角出发,在更为广域的空间中探寻同一族群不同空间文化事项的关系网络;其二是采用线索民族志㉕赵旭东《线索民族志的线索追溯方法》,《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47—57页。的方法追踪该文化事项的历史变迁脉络和空间多点轨迹;其三是承认研究主体主观思维的合法性,通过研究主体和文化事项之间的“视界融合”,对不同文化事项进行宏观的多点比较分析,从而确立相似的文化因子。
比如,同样是“族性歌腔”研究,张中笑的书写属于微观民族志考察,而赵书峰的研究则属于多点族群文化认同的宏观比较。前者选取的田野调查点相对封闭,是一种定点的微型田野调查和客观的音乐形态描述,其目的是表明“在水族的民歌中存在着一种民间共同采用的族性歌腔”㉖张中笑《水族“族性歌腔”及其变异——民族音乐旋律结构探微》,《中国音乐》1989年第3期,第58—59页。。后者则是在跨区域多点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对湘、粤、桂“过山瑶”民歌进行形态分析和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不同区域“过山瑶”民歌拥有共同认同的族性歌腔,从而在历时性线索民族志的追溯中揭示其盘弧崇拜与族群迁徙历史,在共时性线索民族志的链接中深描其空间流布。㉗赵书峰《“认同的力量”“逃避统治的‘艺术’”——湘、粤、桂过山瑶“族性歌腔”的文化隐喻》,《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6期,第27—32页。
(四)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跨境认同研究
依照赵塔里木的观点,在跨境的视域中探索跨越国家边界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属于“同源跨境”的民族音乐学研究。㉘参见“赵塔里木为中国音乐学院‘国音讲坛’第91期活动作学术讲座”,中国音乐学院官网http://www.ccmusic.edu.cn。所谓“同源”,是指文化的历史传统同源,所谓“跨境”,是指文化空间跨越国家边界。这一视域的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子系统,一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研究,这一论域往往借用人类学“文化圈”的理论和方法,着力深描这些跨境民族音乐文化的共性特征;二是跨越国家边界的“迁徙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往往采用线索民族志的理论与方法,追述这些迁徙民族音乐文化的祖先认同。
对于前者,赵塔里木的国家重点课题“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和杨民康一系列的跨境“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具有典型意义。赵塔里木的课题是以河流文化作为区域限定,对当下国内“流域人类学”研究㉙参见《社会科学战线》2017第2期“流域文明研究”专栏:(1)周大鸣《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宏观视野下的人类学研究》;(2)彭兆荣《“流域”与“域流”:我国的水传统与程智慧》;(3)赵旭东《流域文明的民族志书写——中国人类学的视野提升与范式转换》;(4)田阡《村路·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另外还有田阡《重观西南:走向以流域为路径的跨学科区域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82——86页等文论。进行跨境视域转换,并在这一视域下划分出中越、中老、中泰、中缅、中柬“次级文化跨界区域”,在宏观整体和微观深描的双重视域下,进行“整体性、大空间”的“跨族群——地域”音乐文化概览和“个案性、微景观”的音乐文化个案描述。㉚同注㉘。杨民康的相关系列研究是在宗教学和文化圈理论的视域下,经过多点田野调查之后,取宏观俯瞰的研究视角,对一些南传佛教信仰的跨境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较大空间的“跨族群——地域”比较分析,最终形成他的学术结论: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的空间结构,是一个以佛教音乐为“凝聚核心”的文化丛,具有“父系”和“血缘”文化基本性质的“较大的功能整体单位”㉛参见杨民康《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民族艺术》2014年第1期,第45—51页;《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103—114页。。
实验组子宫几率残留率以及子宫肌瘤复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成功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4。
对于后者,则以赵书峰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为代表,该课题以中国、老挝瑶族为比较个案,在多个定点微观个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老挝瑶族的迁徙历史,采用共时与历时双重线索民族志的研究思路追踪历史,梳理空间迁徙路线,进行瑶族祖先文化认同的深描与叙事。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1)深入的田野调查,对其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造与体验等维度进行深入研究;(2)采用多点民族志方法对不同政治语境的文化事项进行多角度观察;(3)对不同音乐形态特征进行比较分析。㉜参见赵书峰《“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项目简介》,《民族艺术》2015年第6期,第2页。
(五)西南文化通道的音乐认同研究
民族学研究将西南地区的文化通道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纵向文化通道包括藏彝走廊、西南官道西线、渝黔桂商贸通道、武陵民族走廊;横向文化通道包括南岭走廊、西南官道东线(古苗疆走廊)等。㉝曹端波《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76—85页。这些文化通道有些自然地形成于民间经济贸易活动中,有些则是封建王朝开辟的官道。
近年来,西南文化通道的音乐认同研究集中在藏彝走廊、古苗疆走廊的调查和研究。其中藏彝走廊的音乐文化认同研究以杨曦帆的个案为代表,他以文化身份为主线展开叙事,具体涉及白族村寨的音乐生活、藏传佛教的寺庙音乐和彝族音乐的巫术仪式,提出藏彝走廊上多民族音乐的唱演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表达。㉞杨曦帆《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的民族音乐学探索》,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随着民族学界对古苗疆走廊的调查与研究,有学者开始对古苗疆走廊上的民间音乐文化进行调查与研究,提出古苗疆走廊作为一条“先军事、再经济、再文化”的官修通道,在黔东地区形成了一条以汉传音乐文化为参照的“文化线块”,随着历史的演进,“墨汁式”地扩散到整个黔东地区,并以此为参照系构建了黔东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内地化认同”“族群性认同”和“区域性认同”。㉟同注㉓,第16—23页。
历史上苗瑶族群的迁徙线路从中南、西南延伸到东南亚,其音乐文化认同研究在赵书峰的国家课题“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立项之后,赵书峰、吴宁华对国外瑶族传统文化研究进行了综述,文本暗含了文化身份的讨论,㊱赵书峰、吴宁华《国外瑶族传统文献研究现状综述》,《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第24—28页。2018年春节期间(1月28日—2月22日),赵书峰、张应华又对老挝、泰国北部的瑶族、苗族音乐文化联合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涉及老挝琅南塔省、乌都姆赛省、琅布拉邦省、沙耶武里省的苗瑶村寨,在此期间,赵书峰还对老挝博胶省、泰国北部清莱市清盛、清孔等县的瑶族音乐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
西南通道的音乐文化认同研究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宏观视角的抽象学术思辨。首先,它表现为文化历时性与空间性的综合研究,即在历史延续的经济通道、政治通道以及迁徙线路上追溯历史,在空间结构上从“线”“线网”“线块”“区域”到“墨汁式整体涵化”再向内地与境外延伸;其次,它是一种目的取向上的综合研究,在这一视域的研究中,文化的内地认同、区域认同、族群认同以及跨境认同实现了“综合一体”多向度的描述与书写;再次,它是一种理论视角上的综合研究,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解释人类学、历史民族音乐学、跨境民族音乐学、线索民族志、区域民族学、多点民族志等理论资源,均得到了合法性的平等综合。
二、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
如果将上述几个方面的探讨视为音乐文化认同研究的宏观视角,即在动态、多点、线索等研究策略中讨论音乐文化的共性特征,侧重不同文化主体、文化空间之间相互认同的文化叙事和理论探究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视角则是音乐文化认同研究的微观视角。微观视角的音乐文化认同研究是一种具体的民族志田野实践,强调以相对静态、定点、结构分析的方法,去描述不同音乐事项内部的差异性特征,突出其结构内部相互“认异”的文化叙事。当“identity”(身份)一词作为“认同”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流行开来时,它便转换成一个带有价值判断和情感色彩意味的心理学概念,更多地强调它的心理情感倾向性,而这一心理倾向则直接指向文化逻辑思维中的同一性特征,但是同一性总是对应于差异性而存在的,因而当我们聚焦同一性,在宏观比较的视角中讨论文化的认同心理时,我们也应该同时关注它的对应面——差异性,即在一种微观描述的视角中去探索文化的“认异”心理。
音乐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表明,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事项结构内部相互“认异”的特征客观存在,并通过不同的口传历史、形态策略或行为方式表达出来,与其结构外部有关历史的、区域的、族群的宏观认同研究接通起来,最终形成其音乐文化身份“和而不同”“同中有异”的主体性建构,这里我们将结合阐释人类学学者格尔茨(Clifford Geertz)针对仪式研究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和个体适应”的分析观念㊲杨民康《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兼论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观》,《音乐探索》2014年第1期。及其启示下蒂莫西·赖斯所提出的“历史构建、社会维护和个人创造三重立体结构思维”㊳孟凡玉《建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立体结构模式》,《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予以探析。
(一)音乐文化历时性的“差异性认同”:口传历史的规约
石阡说春班社有关历史建构的口述文献,是当地民间社会围绕“说春人”来确立正统与非正统名分,划分表演空间以及音乐形态创造和行为方式建构的关键因素,从而在历史民族音乐学宏观叙事的另一端,建构起一个微型的民间音乐事项内部的身份差异性叙事。
2010年以来,笔者在多次对石阡说春进行实地调查之后了解到,石阡民间有多个说春班社,他们的共同信仰是“说春劝农,祈福平安”。这一信仰使得所有说春人和当地及周边县市各民族族群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春文化认同。但在对说春传承人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一则“唐王封官”的民间口述故事,以历史建构的方式将石阡说春班社之间的身份差异突显出来,形成不同班社之间身份“差异性认同”的规约。由于唐王恩赐石阡封姓为“春官”,因而石阡不同说春班社之间便有了血统之分:(1)封姓班社是正统的,其他班社则不是;(2)封姓说春被民间认定为“说正春”,其他班社被看成是“说野春”或者“花花春”;(3)封姓班社一般在石阡本地以及周边比较大的县市或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说春,而其他班社则较多在比较偏僻的地方说春;(4)封氏可以唱正统的“说春根由”“渔樵耕读”,而其他班社则以演唱其他的“野调子”为主;(5)在旧时,封氏说春人出行说春时,县衙要举行盛大的送行仪式,县长亲自护犁牛耕,以表示对“春官”的尊重,而其他班社则不能享受此等殊荣。这一个案表明,我们既要采用历史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民间音乐的同一性认同进行历时性追问,也必须在此理论视角中拷问民间音乐文化内部的“差异性认同”。㊵采访时间:2014年6月7日—9人,采访地点:贵州省石阡县花桥镇大塘坪村,受访人:封付元,参与人员:石阡县文广局干部张传贵。
(二)音乐文化空间性的“差异性认同”:社会维护的规约
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区域文化认同研究,往往是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空间中,选取不同族群的杂居区进行同一音乐事项的文化认同叙事,揭示同一音乐事项在不同族源族群中流播的认同心理。然而,在对较大区域同一族群、同一音乐文化事项进行田野调查及其文化认同研究时,我们则需要采用一种微观的视角,借助格尔茨的社会维护观点,㊶格尔茨认为社会是文化的实体,他在《文化的解释》最后一章“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中认为“斗鸡是社会的中心活动”,“斗鸡时使用的鸡是男性的象征”。进行文化空间结构“差异性认同”的深描与叙述,这是一种认同理论的具体田野实践,是一种源自观察、体验、描述或解释的文化空间的民族志叙事。
音乐文化空间性的“差异性认同”是民间族群社会维护的结果。如果同一音乐文化事项在较大区域空间的同一族群中流布,那么,民间社会则会以一种社会维护的方式区分出内部相互之间的“不同”。
有学者在文化空间的“地缘”中考察南部侗人的“亲缘”,进而考察侗族大歌民间表演行为的“差异性认同”心理。这一调查发现,不同村寨的“嘎老”(侗族大歌的民间称谓)在音乐形态和表演行为上存在差别,“嘎老”的演唱传统是“南部侗人‘亲缘’与‘地缘’文化生态产生的一种‘以乐交友’方式。南部侗族一般将婚姻圈固定在同一村寨之内,相同村寨不同房族之间异性青年男女的‘嘎老’演唱即为‘亲缘’内演唱;同一‘款’(南部侗族的一种古代社会组织的遗存)内不同村寨之间异性青年男女的‘嘎老’对唱即为‘地缘’内演唱。”南部侗族正是通过这种“嘎老”对歌的唱演,使得交际圈超越婚姻圈,在婚姻圈的认同中实现交际圈行为方式的共同性或差异性认同。“不同侗族区域有不同的音乐形式,不同区域的侗族对其音乐也有不同的界定和分类。”“用某一区域或村寨的侗族大歌取代另一区域或村寨的侗族大歌,从而遮蔽了侗族音乐及侗族大歌的多样性。”㊷参见曾雪飞、罗晓明《侗族大歌的演唱传统与地域认同》,《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6—61页。
(三)民间艺人角色性的“差异性认同”:个人创造的规约
蒂莫西·赖斯曾经在一篇论文中问道:“人们如何创造音乐?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人们如何历史地建构、社会地保持和个人地创造与体验音乐?”㊸同注㊳,第11—17页。当我们走近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某一乐种、某一艺人群体,在蒂莫西·赖斯的发问中关注那些民间艺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个人创造置于民间音乐的种种规约,这些规约有时是对传统的守护,有时是对传统的解构,有时是内部的排他,有时又是内部的调适。这是西南少数民族音乐认同研究微观视角的又一个论域,需要研究者较为长期地多次深入某一音乐事项的内部,与该音乐事项的民间精英亲密接触,在对该音乐事项的田野体验中发掘民间艺人的“差异性认同”心理。这是民间艺人对“自我”有别于“他人”的差异性的肯定和辩护。
民间艺人的“差异性认同”心理既会发生在同一文化事项内部的不同组织之间,也会发生在同一组织内部的代际间。前者往往是同一音乐文化事项内部差异性存在的重要决定因素,后者往往推动着音乐文化事项生发变异。霍小琼调查了南部侗族地区潘萨银花(小黄侗寨)、龚喜发(榕江侗寨)、石贵昌(增冲侗寨)、杨玉林(肇兴侗寨)、吴玉竹(占里侗寨)和吴老桥(高增侗寨)六位歌师,这些歌师在角色身份上分别“自我认异”,比如小黄侗寨的潘萨银花以发舌尖颤音模仿蝉鸣声音标识了小黄侗寨的大歌特征,又如龚喜发善于教唱古歌类型的大歌,使得榕江侗寨的大歌以古香古色为名,再如石贵昌善于编歌,将大歌编成套曲,因而增冲侗寨的大歌往往以创新闻名乡里。㊹参见霍小琼《论侗族歌班、歌师及其在侗族大歌传承中的历史性贡献》,贵州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同一组织内部民间艺人的代际间“差异性认同”心理往往是指师徒观念的变迁,欧阳平方调查了石阡木偶戏第八代传承人刘超,他实际上存在多种社会身份:其一,他作为石阡木偶戏第八代传承人,是一种民间的选择,是由他的师父付正华老艺人认定的; 其二,他也是国家政府认定的传承人;其三,他还是石阡民族中学木偶戏的教师主体。㊺欧阳平方《“非遗”视野下石阡木偶戏的现状分析与传播策略研究》,《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56—62页。这种多重身份使得他有别于师辈的操持理念,在他师父的经验里,木偶戏如何才能立足乡里是其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在刘超的观念里,木偶戏如何传承下来,如何创新发展,如何依托现代媒体传播到国际社会,则是最为关切的问题。另据赵晓楠调查,㊻赵晓楠《芦笙的制作与芦笙工匠的传承》,《中国音乐》2001年第4期,第66—67页。同一组织内部民间艺人的代际间“差异性认同”也将打破家族辈分结构,而在艺人组织内部按照师承关系建构“艺人辈分”。从事侗族芦笙制作的石增高家庭作坊由五个人组成,按照师承关系,其叔叔石敏贤是他的徒弟,在赵晓楠对于这一关系的访谈中,石敏贤与石增高“家族辈分”和“艺人辈分”的关系泾渭分明。
三、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理论取向及比较
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视角的区分,关键在于理论取向和方法论观念的区分,不同的研究视角需要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予以支撑,反之,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又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视角。李银兵、甘代军在《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一文中勾勒了大陆人类学界近十年来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观念:在理论层面,随着王铭铭、高丙中等人对解释人类学、反思人类学的译介,民族志书写开始批评和反思科学民族志的主观性和真实性。在操作层面对民族志书写的方法进行了多维度探索,不断拓展民族志书写的外延。㊼李银兵、甘代军《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第72—81页。受后现代现象学解释学的影响,人类学一方面着力反思科学民族志的研究主体权威,一方面又对反思人类学对于对象主体的过分张扬以及研究主体的过分“放空”进行了再反思和再拷问,提出一种研究主体与对象主体均具“合法性”的研究模式,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互为对象,“共在”现场相互对话、互文解释、交互理解,从而在研究主体和对象主体的合作中创生文化意义的“主体民族志”书写模式。㊽朱炳祥《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39—50页。人类学的理论反思与方法论的多维度探索,推动着音乐民族志的书写也朝着批判性、反思性、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演进,并集中地体现在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的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中。
第一,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是科学民族志“客位观察”取向的“潜在的”与“显现的”综合。科学民族志创自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Kaspar)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哲学上表现为科学主义的认识论。高丙中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确立了科学民族志准则:田野调查、客位观察、主位体验。㊾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58—63页。然而这种研究方法遭到了反思人类学的诟病,指出科学民族志的写作是研究者的独白,研究者的客位描述、客位解释,使得读者无法了解对象主体的文化真实。但是这种反思在现象学解释学的认识论看来是有失偏颇的,依照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观点,研究主体的客位观察不仅不能从文本写作中消失,而且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民族志是研究主体与历史文化的“视界融合”。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观点,当下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并没有抛弃科学民族志客位观察的理论取向,而是将其潜在地或显现地综合在田野调查和文本书写的过程之中,即在宏观视角的认同研究中,科学民族志的“客位观察”往往“潜在”于多点比较和解释之下,是宏观多点研究的前提;在微观视角的研究中,科学民族志的客位观察是显现的,是同一音乐文化事项内部“差异性认同”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二,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是解释人类学的双重解释与描述的综合。有学者认为,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理解等领域的研究都是解释人类学的,“即肯定人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符号的和解释性的,作为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也是解释性的。‘深描说’的宗旨是理解他人的理解,站在一个‘异文化’的位置上体察人类学家自身的‘本文化’。”㊿王铭铭《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第23—31页。在笔者看来,“深描”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认识论,是“解释的解释”,前一个“解释”是对象主体的解释,后一个解释则是研究主体的理解。在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的宏观视角中,多个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性解释属于前一个“解释”,是一种隐性的解释,研究主体的解释以这一解释为前提,属于第二重解释,其文本书写正是建立在这种“双重解释”的基础之上。微观视角的研究同样存在着多个文化持有者的解释,但它是显性的,在文本书写中作为文化内部“差异性认同”的主体性表达而给予直接呈现。
第三,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是线索民族志多点空间性与定点历时性的综合。线索民族志表现为关系思维的认识论,赵旭东认为线索民族志分为空间性线索研究和历时性线索研究两个向度,具有“可观察”“可理解”“可追溯”“可关联”“可启发”“可把握”六大特征。[51]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47—57页。当下,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宏观视角主要强调可观察性的“多点空间线索”,表现为“多点领悟”式的理解,突出空间上的可追溯性、可关联性以及多点空间文化认同的启发性意义和文化身份的全局性把握。其微观视角的研究则强调“定点历时线索”的可观察性,表现为“定点解释”式的理解,突出音乐事项内部结构的可追溯性和差异性事实以及来自文化内部差异性表述的启发性意义和某微型个案的整体性掌控。
第四,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是“文本历史”与“口传历史”的综合。近年来,历史的民族音乐研究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的重要论域,在哲学上表现为“视域融合”的现象学解释学观念。依照项阳的理解,历史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两个学科的接通,“在音乐文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接通之后的学科理念,恰恰是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从‘活着的’音乐文化形态切入,即从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立体的、多层次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52]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1—7页。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是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文化认同的研究总是在历史的追问中确立身份的“相同”或者“相异”。当下,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历史追问往往从文本历史和口述历史两个维度入手,即在宏观视角的研究中以文本历史与口传历史的结合追述,突出其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心理,以口传历史辅之以文本历史突出其区域认同和族群认同心理,同时又在文本历史与口传历史的双重视域下讨论跨境的音乐文化认同心理。而在微观视角的研究中,则以口传历史突出其空间、角色的“差异性认同”心理,同时在文本历史与口传历史的双重视域下讨论其历时性的“差异性认同”心理。
第五,就方法论而言,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是“定点与多点”“静态与动态”“解释与理解”等具体方法的综合。首先,定点与多点的综合,即是指定点民族志描述与多点民族志解释的综合。在宏观视角的认同研究中,定点观察、体验和深描是多点比较、分析和理解的前提,其目的是理解多个音乐文化事项之间的文化相似性特征;在微观视角的认同研究中,其中的“多点”是“定点”范围内的多点观察、体验和深描,目的是描述某一音乐文化事项内部的差异性结构特征。其次,所谓“动态”是指文化的空间变动和时间衍变。而“静态”则是指单个文化事项的“相对静止状态”。宏观视角的认同研究往往以动态为主,在相对静态的音乐结构功能的观察、体验与深描的基础上走向动态的比较、分析和理解。微观视角的认同研究则取相对静态的视角,在相对静态的范围内对某一音乐文化事项内部的差异性进行动态的观察、体验和深描。再次,音乐与文化认同的文本书写是“解释与理解”综合的文化叙事,在宏观视角的认同研究中,是在多点、动态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实现研究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的对话,在相互之间对话过程中实现文化的相互认同和理解,进而生成新的文化意义。而在微观视角的认同研究中,是在定点、相对静态的观察体验的基础上,对某一音乐文化事项的内部结构与功能进行深描,在研究对象主体性的表达中表述某一音乐文化事项内部的差异性存在。
结 语
近年来,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论域,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以其宏观视角的“认同”研究与书写,以及微观视角的“认异”研究与书写,成为当下国内学术界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的“实验场”,可以说,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的西南“实验”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当下,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掀起了热潮,并向多维度、多论域延伸:一是寻求跨学科对话,聚焦身份转换与权力、场景与历史叙事、不同身份话语体系、认同的多层面等话题;[53]参见魏琳琳主编《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文化对话》,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二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反思现代性基础、本质、理性、真理的有益性和有限性,探讨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变迁问题;[54]赵书峰《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三是与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广泛联姻,将音乐及其认同放置于人的信仰观念、国家观念、价值观念中予以思考;[55]参见胡晓东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佛教音乐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课题编号16BMZ069)。四是反思音乐研究的现代性“独白”和现代音乐理论的工具性论调,在民间解释与现代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探讨民间音乐的独特含义。[56]参见张应华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苗族黔东方言社区民间音乐形态术语口述调查”(课题编号13BD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