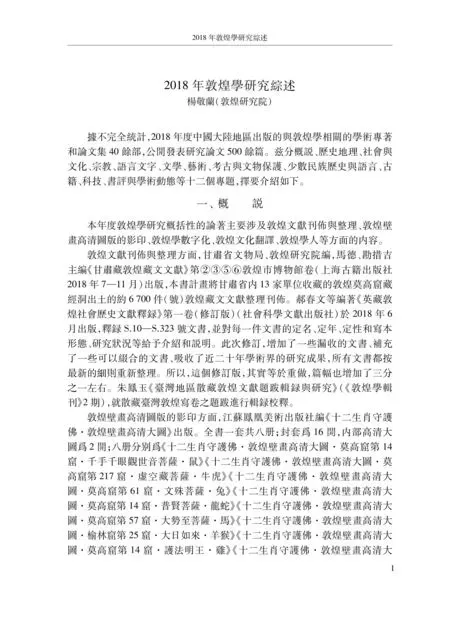振聾發聵,令人深省
——重讀耿昇先生譯《吐蕃僧諍記》《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有感
2019-12-15胡同慶敦煌研究院
胡同慶(敦煌研究院)
耿昇先生的譯作《吐蕃僧諍記》《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分别出版於1984年10月、1987年5月和1993年4月,都是耿昇先生的早期譯作,也是筆者自1984年到敦煌後最早讀到的國外學者研究敦煌的重要著作,當時便使筆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時光荏苒,如今再重讀耿昇先生的這幾部譯作,温故而知新,加上斯人已去,感慨甚多。
回想起來,當時耿昇先生敢於翻譯和出版社敢於出版這幾部譯作,實屬不易。20世紀80年代初期,雖然國家已步入改革開放,人們的思想有所解放,但“文革”的極“左”思潮仍然存在,在許多問題上人們仍然心有餘悸。特别是在敦煌學方面,因一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日本”引起學界乃至全國人民愛國熱情的高漲,如果翻譯出版外國人的敦煌學研究成果,難免會令自尊心極强的國人更感臉上無光。因此儘管學界許多專家學者期望瞭解國外有關敦煌學的研究情況,正如季羨林先生在1984年所説:“時至今日,我們要學習的東西日益增多,我們要研究的課題之廣度與深度日益加强,我們不可能廣泛閲讀所有原著,我們更有必要參看别人的翻譯。這一點,對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來説,更是迫在眉睫”,但“我常常看到或聽到有人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流露出鄙薄翻譯之意”(1)季羨林《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譯叢序》,載[法] 戴密微著、耿昇譯《吐蕃僧諍記》,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頁。。當時要出版這些譯作非常不容易,也正如耿昇先生在1987年時所感慨:“譯出之後,又苦於無處出版。經過多年周折之後,甘肅人民出版社高興地接受出版。没有學術界和出版界的慷慨幫助和熱情操勞,這本書的漢譯本是很難與中國學術界見面的。所以,這部譯著是一種‘千人糕’式的集體成果。”(2)[法] 伯希和著,耿昇、唐健賓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頁。
由於幾十年來的文化封閉,當時面對所謂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日本”這個説法,雖然激起了國内學術界人士的愛國熱情,雖然許多學者憋著一口氣,試圖奮起直追,高呼要大雪國恥,但當時國内的絶大多數學者連國外有關敦煌學的研究具體是什麽情況,他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範圍,以及究竟是什麽水平,等等,幾乎茫然不曉。爲此季羨林等先生清醒地認識到:“學習他人之長,包括一切方面。專就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而論,同樣有向别的國家學習的任務。……特别是日本學者和法國學者在這方面的成就,更是值得我們借鑒。”(3)季羨林《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譯叢序》,載[法] 戴密微著,耿昇譯《吐蕃僧諍記》,第1—2頁。
因此,耿昇先生當時出版的這幾部譯作和其他先生的一些譯作,再加上一些原著,對於國内學界人士來説,具有大開腦洞的意義。不僅令學者們大開眼界,既看到自己的差距,也看到自己的長處,同時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得到許多有益的啓示。如法國學者謝和耐先生的《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一書,書中“以社會學的觀點,根據漢籍、印度經文、敦煌和其他西域文書,分析了從南北朝到五代期間的中國寺院經濟。書中對於佛圖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長生庫、社邑、齋供、三階教無盡藏都作了深入探討”,是研究敦煌經濟文書的一部重要著作。不僅“日本學者十分重視這部著作,多次發表書評。法國學者也將此書與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諍記》並列爲兩大敦煌學名著”,“我國學者、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姜伯勤先生對此書頗有研究,多次在論著中引用該書的觀點和資料。我國敦煌學界的其他學者也很重視它”(4)[法] 謝和耐著,耿昇譯《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頁。。另外,當時的中國學者,也從池田温、松本榮一等日本學者那裏學習到許多有益的東西,甚至到了21世紀的2011年,仍然還有中國學者在參考引用池田温等外國學者數十年前的研究成果。(5)參見張榮强《唐代吐魯番籍的“丁女”與敦煌籍的成年“中女”》,載《歷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諍記》,原著於1952年在法國巴黎出版;謝和耐先生的《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原著是1956年在當時尚設在西貢的法蘭西遠東學院發表的一篇博士學位論文,作爲《法蘭西遠東學院叢刊》第38卷刊佈;《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則是伯希和1908年在我國新疆、甘肅探險時,在敦煌逗留期間,在莫高窟留下的,在法國最早是以《筆記本A》《筆記本B》的影印件而流傳。也就是説,這幾部著作的撰寫年代,實際上距今長達六十多年甚至一百一十一年了,分别反映了當時法國漢學家的學術研究水平。時至今日,重讀這些著作,其中的許多内容仍然令人有新鮮感,其中的許多研究方法仍然值得我們今天借鑒。正如2013年7月12日耿昇先生在《法國漢學史論》“自序”中所指出:“(法國漢學家的)這些論文中談到的問題,在中國基本上没有人涉及過,大都是首次被論及。它們在中國學術界,縱然不算是‘創新’,那也應該是全新的。它們必爲中國學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使人視野開闊、耳目一新,開闢了新領域,提供了新的思考課題。”(6)耿昇著《法國漢學史論》(上册),北京: 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2頁。
確實,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由於受“文革”等思潮的影響,中國的許多學者習慣於搞假、大、空的東西。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學者們特别是從事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學者逐漸看到不少日本、法國、英國等國家學者的研究論著,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對中國學者産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用。如近三十年來有關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與其他學科相比,學術性更强、學術氛圍更濃,其研究的内容較爲具體、實在,假大空現象較少,學術論著的品質相對較高,應該承認這與該學界人士較多地學習、借鑒日、法、英等國學者的研究經驗有關。
不過,當筆者重新閲讀耿昇先生所翻譯的《吐蕃僧諍記》《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等著作,再關注、審視、反思國内的學術研究情況,感到我們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看到儘管這些年來敦煌學研究人才不斷湧現,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成倍增長,但其品質與半個世紀甚至一個世紀前的戴密微、謝和耐、伯希和的論著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如近些年有關敦煌學研究的雜志所刊發的文章大多仍然是考證壁畫内容、年代和校勘敦煌文獻的文章,另外出版的著作也大多是考證壁畫圖像或泛泛介紹敦煌藝術的内容,像戴密微、謝和耐先生那樣從宗教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敦煌學研究的論著很少。而且,最近又出現了熱衷於假大空的研究現象。如自2013年1月成立的甘肅省敦煌哲學學會,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裏,便把主要任務放在建立所謂的敦煌哲學體系,組織有關人員將主要精力、時間放在撰寫所謂的《敦煌哲學概論》一書,東拼西湊出“敦煌宗教哲學”“敦煌人生哲學”“敦煌社會哲學”“敦煌藝術哲學”“敦煌哲學方法論”“敦煌哲學與絲綢之路”等空泛無物的章節,而不是實實在在地利用敦煌藝術或敦煌文獻研究一些具體的有關哲學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諸多原因,這一類文章和著作在當今社會很容易發表和出版,被《人大複印資料》《新華文摘》等刊物轉載,同時更容易獲得國家級或省級的優秀論著大獎。這種情況,勢必會引導有關的學術研究走向歧路。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注意到,之所以敦煌哲學研究出現這個情況,是因爲我國現在的哲學、美學、倫理學等學科的論文或著作幾乎也都是這類空泛的内容。由此可見,戴密微、謝和耐先生的論著,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以及關注現實的態度,不僅值得敦煌學界借鑒,同時也值得我國哲學、美學、倫理學等學界人士反思。
這次重讀耿昇先生的譯作,注意到一個情況,即如果將一些法國人(還有一些日本人)的著作或論文中的作者姓名改换成中國人的姓名,幾乎都看不出是外國人寫的東西,似乎都是中國人寫的自己國家的東西。這些法國人(包括一些日本人)的著作或論文是從世界人、地球人的角度進行客觀考察、介紹和分析研究的。而中國學者寫的國外的東西,幾乎都是從中國人角度寫的,大多探討的都是中國和該國的關係,特别關注該地區的中國元素,關注中國對該國的影響,如關注陶瓷、絲綢、青銅器等等,一看就知道是中國學者寫的。猶如當前許多中國旅遊者,到國外博物館,最關注的該博物内所珍藏的中國文物;中國學者亦是,很少關注具有該國該地區特色的文物古迹。
特别是重讀距今一個世紀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感慨更多。中國學者到國外的所謂學術考察,大多是走馬觀花,或拍拍照、搜集一堆資料,很少有像伯希和這樣認真進行考察、編號、記録和分析研究的。如中國學者到印度考察,關注的大多是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佛教遺迹,很少關注和研究印度的印度教等其他内容。如果説在國外考察可能受到經費等諸多原因的限制,在國内考察應該是很方便了,但我們很少看到國内學者有像伯希和這樣在實地詳細考察、記録和分析石窟内容的,大多也是拍照和作一些簡單的記録或抄録一些自己需要的題記等資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許多專家學者,缺乏伯希和所具有的淵博知識和學術研究水平,没有能力像伯希和那樣在實地便能對許多考察内容的價值作出比較科學的判斷,只有回家後慢慢查資料進行研究。筆者孤陋寡聞,至今没有發現哪位國内學者的學術研究水平有超過伯希和、戴密微、謝和耐等先生的。
同時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將中國整體的敦煌學研究與法國或日本的整體的敦煌學研究進行攀比,既不科學,也不合理。我們是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進行我們自己國家的語言文字和歷史文化研究,外國則只是有那麽幾個或幾十個人在從事我國的語言文字和歷史文化研究。如果一定要攀比,就應該看我們中國人是如何進行法國、日本或印度等等國家的語言文字和歷史文化研究的情況。而且,還不應該只看某一種學科的研究情況,還要結合考察其他如哲學、美學、倫理學、社會學、宗教學乃至經濟學等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情況。否則,便有可能出現“一白遮十醜”的片面看法。
重讀耿昇先生的這幾部譯作,再結合閲讀耿昇先生近幾年的《法國敦煌學精粹》(7)鄭炳林主編,耿昇譯《法國敦煌學精粹》,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法國藏學精粹》(8)鄭炳林主編,耿昇譯《法國藏學精粹》,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法國西域史學精粹》(9)鄭炳林主編,耿昇譯《法國西域史學精粹》,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10)[法] 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和《法國漢學史論》(11)耿昇著《法國漢學史論》,北京: 學苑出版社,2015年。等譯作或著作,收穫甚多。不僅對法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情況以及治學態度和研究方法有進一步的瞭解,同時結合當前國内學界的許多情況,倍感到耿昇先生在複雜多變的國内環境中,從不隨波逐流,長期以來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敢於客觀介紹國外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正確評價伯希和等人功過,實在不易。耿昇先生人品之高尚,學風之嚴謹,治學之廣泛,學問之博大精深,確實是我國當代學者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