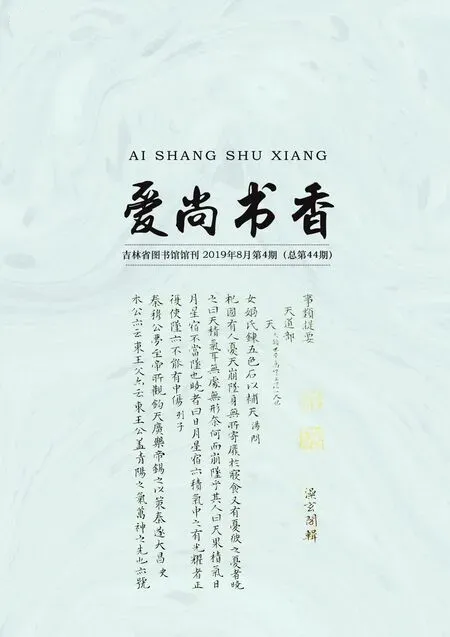我读钱春绮
—— 关于译诗及其赏析
2019-12-15桑永海
桑永海
一
真就不能不感叹,当下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神乎其技,一夜之间就会触动天下观众和听众的神经!就比如那位许渊冲老先生吧,高等学府里的著名老翻译家,如果不是前不久他在央视《朗读者》第一期上了电视,情真意切倾述了感人肺腑的一席话,除了喜欢外国文学的读书人,那么多读者(观众)怎么会知道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呢?
我不由想起了钱春绮先生。他是声名卓著的老翻译家,他浩繁的诗歌和散文译著,以功力深厚优雅抒情的文笔,打动了几代文学青年的心。可惜他去世早了些年,没赶上全媒体信息空前发达的时机,更不可能上电视。知道他的人较少,就不奇怪了。
人们都晓得,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一种再创作,诗歌很难翻译——甚至有个极端说法,诗歌不可译,可见诗歌翻译之艰难。所以,我们倾心的外国大诗人身边,都陪伴着汉译大家的身影,诸如戈宝权之于普希金,查良铮(穆旦)之于拜伦、雪莱和济慈,戴望舒之于洛尔迦,钱春绮之于歌德、海涅和尼采,等等。这些诗人翻译家当然也就成为我们敬仰的偶像。比如,诵读歌德和海涅,某种程度上不也是在阅读钱春绮吗?现在,即或一个年轻译者,初出茅庐,也会在出版物上介绍译者的身世。可是,直到钱先生去世前一年,我还无从知道他个人的任何信息。因此,他是我心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谜。
二
20世纪50年代末,故乡的小书店是开架的。钱春绮译的浪漫派大诗人海涅的成名作《诗歌集》虽然纸页灰黑粗糙,也还散发着墨香,高雅的豆绿色封面,精美又富于梦幻色彩的插图,捧在手里就不愿放下。特别是读了卷首海涅的“二版序言”,我就下决心买下它了(那时一个中学生买本书可不是小事)。那序言有几段我还另抄在一个手册上,至今也能成诵:“德国的缪斯啊!在故国煎迫之中她安慰我,在流亡中她追随我,在绝望的悲惨时期她鼓舞我,她从来没有遗弃我,甚至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她也知道支援我,德国的缪斯,善良的丽人啊!”这译文,铺排回荡,文彩飞扬,我还没见过把诗与痛苦与人生的关系写得这么简练优美的文字。译者钱春绮,他是谁呢?从此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记在了我心里。
在钱先生海量的诗歌译品中,我最喜欢的要算那首歌德的短诗《浪游者的夜歌》:
群峰
一片沉寂,
树梢
微风敛迹。
林中
栖鸟缄默,
稍待
你也安息。
这首汉译小诗,参差又整齐,有如元人小令,有如六言仄韵诗,貌似平实的诗句,却有一种直抵心灵的力量。诗人、德语文学著名教授冯至先生曾经评论歌德这首诗说:看不出作者用了什么艺术上的技巧,但多半是最杰出的诗人才能写得出来的杰作。我觉得钱译体现了这样的神髓。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从“五•四”到现当代,郭沫若、宗白华、梁宗岱、朱湘、冯至、绿原等精通德语的大家,都先后译过这首小诗。诗人屠岸先生40年代也曾译过这首诗,后来还一直想要重译,但他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感叹说:“自从见到钱春绮先生的译文后,就决心搁笔了。“(见屠著《倾听人类心灵的声音》P234页)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的由衷赞叹,也说明钱译确是诗歌翻译史上难得的精品。
我对这个小诗的喜欢,不仅仅源自这首译诗本身,与钱先生为此诗写的一个注文也有很大关系。那个注实际上就是歌德写下这首诗以后,一段绵延了数十年的“本事”:“1780年9月6日晚,歌德在伊尔美瑙的吉息尔汉山顶小木屋里将这首诗题在板壁上。33年后,在1813年8月29日(歌德诞辰之次日),他再游时,将题壁诗的铅笔字迹加深。又18年后,在1831年8月27日,歌德生前最后一个诞辰日前一天,又游该山,重读旧题,感慨无穷,自言自语地念道:‘稍待,你也安息!’然后抆泪下山。次年3月22日果然永远安息。”歌德活了八十三岁。
那时我正在念高中,读了钱氏的译诗和注文,就被歌德其诗和这段真实的人与诗的故事感动,而且历久弥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位文化巨人三去高山小木屋,就是为了叩问人类心灵普遍怀有的那一团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永恒的忧思。其实质,还是对热情的渴望,对生活的憧憬,对生命的留恋。钱氏撰写的这一段本事,犹如《世说新语》中隽永的古典小品,让你连同小诗一起咀嚼涵泳,爱不释手。如果像许多译家一样,钱先生不写这个注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段本事呢?我从心里感谢钱先生的一注之功!多有学人称道钱先生译著中大量注释的阅读和学术价值。确实,这已然成为钱氏译著一道独特的风景。
三
钱春绮先生在译诗集的编选上,还有一个人们多不曾注意到的亮彩之处,那就是他擅于运用对比的方法,引领读者打开眼界,让受众读到同一首诗的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译家的经典译作,激发人们的阅读情趣和审美愉悦。我以为,钱先生编选的《歌德诗歌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方面,就是一部难得的精品。这个选集收了歌德读印度诗人的经典剧作《沙恭达罗》后写的一首小诗,是钱先生译的:
你要把那春季的百花,晚秋的果实,
使人迷惑、欢喜、满足、颐养的一切,
你要把皇天和后土全用一言以蔽之,
我只要说起你,沙恭达罗,就囊括殆尽。
你看,钱氏对歌德这首诗现代汉语的直译,不是很像一段散文吗?我想,用白话直译歌德此诗,也许是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吧?但,钱先生不动声色地,在自己译的这首小诗下面,注引了另一首汉译,那是用文言意译的:
春华瑰丽,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沙恭达纶。
慢慢品味吧,这是百年前著名诗僧苏曼殊的遗译。如不加说明,几人会知道是同一首歌德之诗的汉译呢?其实,我们的先辈译介外国诗歌,“五•四”前后至30年代,大都是以旧体诗的形式,那是整齐的四五六七言,如诗经,如楚骚,如汉魏诗,如唐宋古韵。这首曼殊之译,就是译家之绝响,流传了下来。在1960年出版的钱春绮译《德国诗选》中,钱先生就在自己译作下边注引了苏曼殊这首文言译诗。这也说明钱先生编选译诗集,这个令人称道的指导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如果没有钱先生的对比推介,如今有多少年轻人会知道苏曼殊这个后来出家的和尚,当年留下一首独领风骚的汉译名篇呢?
在这同一部钱编的歌德诗集中,著名的《迷娘歌》,钱氏就选了三首不同的译文,马君武、郭沫若、郁达夫各一首,都是风格各异,而又文白参半、让你拍案叫绝的汉译。如果不是钱先生有着这样精心而又独到的编选之功,我们现代人很难在不同译品对比之中获得如此的审美愉悦了,那是不可替代的古典之美。
四
呜呼!像钱春绮先生这样的奇人,学识丰厚、从不张扬、自学通晓五门外语,本来毕业于医大,却在1960年计划经济时代辞去医生工作,不拿工资,甘于寂寞,为了精神追求,弃医从译,在动乱不已的世纪恪守己志,一面是名声大噪,一面是默默不语,六十余载始终把一腔心血倾注在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和传播上,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大译家,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中,也许很难再见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