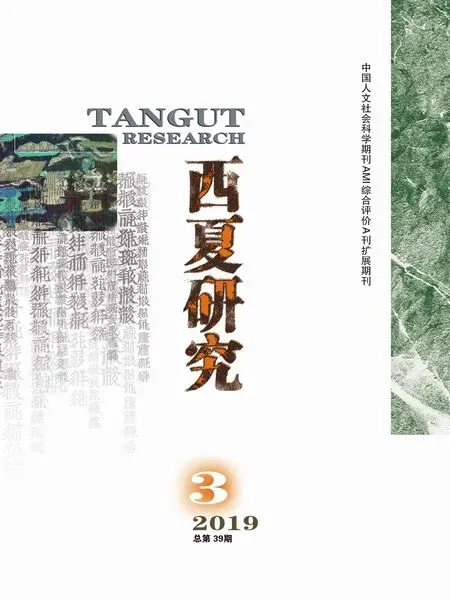《敦煌民族史探幽》评介
2019-12-15韩树伟
□韩树伟
《敦煌民族史探幽》作为杨富学先生的新出专著之一,与牛达生的《西夏考古论稿(二)》,王志鹏的《敦煌文学与佛教文化研究》,朱国祥、张铁山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研究》,杨富学、张海娟的《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共同入选“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第一辑。这部丛书由杨富学先生担任主编,聚焦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考古材料,充分掌握最前沿的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全新视角、创新理念探讨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其沿线地区的历史、宗教、语言、民族、考古、艺术等文化遗存。同以往相关研究丝绸之路的论著相比,“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更加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因此,《敦煌民族史探幽》的出版向“敦煌学”献上了一份殊礼,为学界了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提供了全新资料。杨富学先生的丰富材料、大胆构思、有力论证不仅启人深思,而且对打破学科壁垒具有重要意义。
一
《敦煌民族史探幽》一书共分十六章,视角广阔,内容丰富。
第一章《少数民族对古代敦煌文化的贡献》和第十四章《多种文字在古代维吾尔族中的行用》的体量相较其他几章稍微宽广,引用文献也较多,所涉领域颇为广泛。从语言上看,主要有汉语、古突厥—回鹘语、吐火罗语、古波斯语、梵语、粟特语、帕提亚语、古叙利亚语、古藏语、于阗塞语等语种;从文字上看,主要有汉文、吐蕃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回鹘式)、八思巴文、西夏文、梵文、佉卢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乙种龟兹文)、叙利亚文、摩尼文(摩尼教徒使用的“正式”文字)、希伯来文、婆罗米文(中古波斯文)等类型;从种群来看,主要有塞种、古羌、氐、戎、月氏、乌孙、匈奴、汉、鲜卑、吐谷浑、粟特、吐蕃、嗢末、苏毗、回纥、突厥、鞑靼、党项、蒙古、黄头回纥(裕固族);从宗教性质来看,主要有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综合这些内容丰富的历史文化,可以看出丝绸之路沿线曾有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中亚诸族文化系统、印度文化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蒙古草原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青藏高原文化系统相互碰撞、冲突、借鉴、融合、吸收,形成了以中原汉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为主导的世界四大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交织、相融的区域,正是季羡林先生所讲的新疆和敦煌。
第二章《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了曾生活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乌孙这两大种群,文中个别论点颇有新颖之处。例如,指出沙井文化属月氏遗存,骟马文化为乌孙遗存;比较分析“畜牧”、“游牧”、“农耕”的联系与区别;针对“月氏在东、乌孙在西”的说法,笔者以为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说法更有道理①。第三章《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与第四章《摩诃衍禅法及其在吐蕃中的流传与影响》、第五章《西域与敦煌吐蕃佛僧饮酒之风及其成因》、第十三章《敦煌汉藏对音资料所见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现象之一斑》为吐蕃专题讨论,使用文献众多,引用材料齐全,论证充分有力,对学界了解吐蕃文化大有裨益。第七章《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及其所见史事钩沉》与第八章《论黠戛斯在西域的进出》的体量虽然较为单薄,但仍能为学界带来很多启发性思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六章《关于沙州回鹘国的建立》、第九章《宗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第十章《回鹘佛教——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第十一章《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第十二章《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第十五章《回鹘文〈金光明经〉及其忏悔思想》、第十六章《“裕固学”与河西回鹘关系漫议》都是围绕回鹘文献展开的系统论述。作为全书的主要部分,这七章是杨富学先生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蒙古豳王家族、摩尼教、“裕固学”等议题近年来格外引人注目。
杨富学先生先后师从苏北海先生和郑炳林先生,系统学习维吾尔族历史与维吾尔语,一直从事敦煌吐鲁番学、宗教学、中外关系史、西北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正是通过学术上的辛勤耕耘,杨富学先生才能佳作不断。在《回鹘摩尼教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杨富学先生曾坦言:“回鹘摩尼教一直是我孜孜以求的研究方向之一,积三十年而未敢稍有懈怠。古人云‘十年磨一剑’,用以比喻治学的不易,铢积寸累,方可有成。本人不才,积三十年之功,始有一点点创获,尚不称意。治学之难,于此可见一斑,古人诚不我欺也。”自谦之余,杨富学先生对学术之艰难发出了由衷心声。摩尼教仅为杨富学先生众多研究方向之一,竟积三十年之功,其他领域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可想而知。
二
20世纪初在敦煌和西域曾出土大量文书和文物,国内外学界随之掀起利用这些出土文书与传世文献的研究热潮。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学者很难直接接触流散国外的文书,为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同时因为语言等障碍,国内学者仅囿于汉文研究或国内少数民族研究层面,在国际相关研究领域很难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敦煌民族史探幽》的出版正好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对国内学术界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在通读《敦煌民族史探幽》一书时会发现,杨富学先生在语言上具有一定优势,对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情况了如指掌,对其学术成果运用自如,在兼蓄诸说上得心应手。这不仅体现出作者渊博的知识,而且反映了其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强大能力。国外学者人数众多,领域广泛,主要包括德国学者缪勒(F.W.K.Müller)、茨默(P.Zieme)、葛玛丽(A.von Gabain)、勒柯克(A.von Le Coq)、哈密顿(J.Hamilton)、科林凯特(H.J.Klimkeit)、邦格(W.Bang)、沙德尔(H.H.Schaeder)、阿拉特(R.R.Arat)、文特(W.Winter)、威尔金斯(J.Wilkens),英国学者刘南强(Samuel N.C.Lieu)、克劳森,法国学者沙畹、德微里亚、哈金(J.Hacken),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W.Radloff)、马洛夫(С.Е.Малов)、季米特里耶娃(Л.В.Дмитриева)、奥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丹麦学者阿斯姆森(J.P.Asmussen),美国学者克拉克(L.V.Clark)、古乐慈(Zauzsanna Gulacsi)、孟赫奋,瑞士学者孟格斯,日本学者羽田亨、森安孝夫、松井太、田坂兴道,土耳其学者恰合台(Saadet S.Cagatay)、卡亚,等等。杨富学先生同样非常重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耿世民、彭金章、李正宇、刘玉权、史金波、牛达生、钱伯泉、才让、张铁山、谢继胜、段晴等学者给予广泛关注。杨富学先生在搜集材料方面做到了视野开阔与面面俱到,对前人研究成果和学术前沿动态并不简单罗列,而是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地加以综合引用。在论述自己观点时,杨富学先生对所驳对象表示出最大的敬意和尊重,坚持以史料说话,在批判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1.用突厥语解释“敦煌”、“莫高窟”
与以往学界根据东汉应劭《汉书·地理志》解释“敦煌”为“敦,大也。煌,盛也”和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之“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不同的是,杨富学先生根据钱伯泉先生《“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1]一文,进一步论证了“敦煌”、“莫高窟”名出突厥语的可能:“敦煌”为突厥语“dawam”(瓜)的音译,历史上的敦煌正是产瓜之地,曾一度被称作“瓜州”。武德五年(622)之后,正式改名瓜州。至于“莫高”,杨富学先生认为并不是“莫高于此山”,而是突厥—回鹘语“Bögü”(神圣)的译音,“莫高窟”即“圣山”。同时,杨富学先生还列举了“祁连山”(天山)、“合黎山”(黑山)、“合黎水”(黑水)、“温宿”(三)、“疏勒”(水)、“姑墨”(沙)、“黑龙江”(阿尔泰语系民族固有之称谓)[2]等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的地名。
2.“沙州回鹘国”
关于“沙州回鹘国”,我们有必要交代一下与之相关的回鹘与敦煌归义军政权。首先,回鹘由回纥改名而来[3]6124,时间为贞元四年(788)②。天宝三载(744),回纥可汗骨力裴罗在鄂尔浑河上游的杭爱山之北建立突厥汗国之后的又一漠北汗国,“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3]6115。开成五年(840),回鹘叛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③攻灭回鹘,“诛(杀可汗)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3]6130。回鹘部众一部南下至唐朝边塞,不知所终,一部西迁至中亚、新疆、河西等地分别建立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者曰喀喇汗王朝④,以高昌、北庭、龟兹为中心者曰高昌回鹘王国(西州回鹘)⑤,以甘州为中心者曰甘州回鹘⑥。其次,敦煌(沙州)归义军政权。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在瓜、沙等地的统治后建立敦煌(沙州)政权,被唐朝赐名归义军。张氏(张议潮、张议潭,潭子张淮深、潮子张淮鼎,鼎子张承奉)、索氏(张议潮婿索勋)、李氏(张议潮婿李明振,振子李弘愿、李弘定、李弘谏、李弘益)、曹氏(曹仁贵即曹议金,金子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忠子曹延敬即曹延恭、曹延禄,禄族子曹宗寿,寿子曹贤顺)等敦煌大族轮番执政⑦,上演了一段不为史书所载、被敦煌文书揭示的归义军史⑧。
杨富学先生在《敦煌民族史探幽》一书中认为,840年回鹘分崩离析后除在河西建立甘州回鹘外,还有以沙州为中心、统治瓜沙地区的割据政权——沙州回鹘国⑨,与曹氏政权存在紧密联系⑩。虽然元昊于1036年攻陷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地区,但在治平四年⑪(1067)北宋重占敦煌之前,西夏并未对敦煌实施有效统治[4]124-129。在李正宇先生的论述基础上[5]149-174,杨富学先生进一步对学术界关于沙州之“西州回鹘”⑫说进行了反驳与论证,其要点如下。
首先,假设“沙州回鹘”说成立,那么沙州必有回鹘军队存在,而且政权独立。杨富学先生指出,唐初就有回鹘别部——契苾部到过沙州,同时保有自己的部落组织——族帐。大约在10世纪初,沙州回鹘集团逐步壮大并控制沙州,1036年建立沙州回鹘国,成为抗击党项的主要力量。关于这一点,杨富学先生认同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说法,“至迟到11世纪早期,敦煌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回鹘团体,这个团体起初曾操纵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但是从1023年开始,回鹘取代了曹氏,1052年以后彻底统治了沙州”[6]21-35。但是,杨富学先生对森安孝夫的“沙州回鹘政治上隶属于西州回鹘”之说持否定态度。
其二,杨富学先生利用传世文献论证治平四年(1067)以前西夏未曾有效统治敦煌。沙州遣使向与西夏对立的北宋朝贡,被认为始自景祐四年(1037),即元昊击灭沙州归义军政权的次年,结束于皇祐四年⑬(1052)。沙州至少11次向北宋朝贡,使臣多为回鹘人。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与辽交往时自称“沙州回鹘敦煌郡王”[7]36,以讨辽朝后族回鹘述律氏[8]94之欢心,从而寻求辽的支持。与之相对,曹贤顺在与北宋交往时自称归义军节度使而不用“沙州回鹘”之号,反映了沙州相对独立的地位,奉行亲宋反夏的外交政策。杨富学先生利用《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文鉴》、《宋名臣奏议》、《武经总要》等当时的文献资料论证瓜、沙二州不属于西夏[4]126-127。杨富学先生通过敦煌石窟题记和出土文书,发现只有1036年至1070年间的北宋年号,却不见西夏纪年。莫高窟最早出现的有明确西夏纪年题记的洞窟是第444窟,时间为“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9]168。西夏统治瓜、沙地区的确切时间史无明载,杨富学先生根据《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10]一文,赞同李正宇先生“西夏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治平四年或此前不久,但不会早于治平元年”⑭的说法。
其三,杨富学先生对森安孝夫提出的“沙州北亭可汗”为高昌回鹘王国夏都“北庭”⑮、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沙州将军”⑯、因敦煌壁画供养人画像酷似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画像而得出“西州回鹘领有沙州”⑰等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北庭”说成立,那么“北庭”前面“沙州”二字应该做何解释?北庭为唐代方镇名称,回鹘一直以“biš balïq”(别失八里)称之,从未采用“北庭”这一汉名。回鹘文木杵文书写于土猴年(戊申年,即948年),时为沙州归义军曹元忠统治的繁盛期,据此认为西州统治沙州的说法与理不通。至于石窟壁画的相似性,杨富学先生以莫高窟第409窟为例,认为男性回鹘供养像服饰上有团龙纹图案,随从侍者所持团扇上也绘有双龙纹,明显受到汉文化影响。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图像中未见团龙纹或以龙纹装饰衣冠,肯定了贾应逸先生的说法:“莫高窟第409窟的回鹘王及其王妃的供养像与柏孜克里克……服饰制度差别很大……可以说明高昌回鹘没有统辖到沙州,高昌回鹘和沙州回鹘都是各自独立的政权。”[11]515-516另外,杨富学先生从语言学角度考证了“arslan”、“可汗”、“特勤”、“都督”、“将军”、“大市”、“副使”等称号,认为其反映了沙州政权的回鹘性质。
3.莫高窟第464窟与蒙古豳王家族的关系
通读《敦煌民族史探幽》一书,可以说第十一章是最为精彩的部分,最能体现杨富学先生的治学风格。这章的内容与其说研究的是第464窟与回鹘的关系,倒不如说“第464窟与蒙古豳王家族的关系”更能表达作者的言外之意。因为正是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沙州回鹘才能大规模修复洞窟。在这里,有必要简要阐述一下正、反两方的论点。
首先,张大千、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宿白、史苇湘、谢继胜、郑炳林、沙武田、谢静、梁尉英等先生多持“莫高窟第464窟为西夏窟”之说,尤以谢继胜先生为代表。刘玉权、关友惠、王惠民等先生持谨慎态度,没有明确说明第464窟所属具体朝代。杨富学先生通过彭金章、王建军二位先生的考古证明[12]54-56,认为“莫高窟第464窟原为北凉禅窟”,该窟前室与甬道为回鹘窟,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
其次,以谢继胜[13]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第464窟为西夏窟,主要依据为:第一,前室南、北壁有两则“大宋”游人题记。杨富学先生指出,若元昊于1036年统治敦煌,势力尚不稳固,怎会有余力和心思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石窟?若政权不稳,故未能对该窟壁画的重绘下大功夫,仅可在素面上重绘而已。战乱期间虔诚的西夏佛教徒可以做的佛事,何以至西夏统治稳固后却不能继续,以至于半途而废?第二,谢继胜先生认为第464窟具有比较典型的藏传佛教壁画特点。杨富学先生认为,这一说法在表述该窟壁画的时期上出现了自相抵牾的现象。第三,谢继胜先生认为第464窟后室南壁上师冠帽为宁玛派莲花帽,这是其立论的根本依据。杨富学先生认为这种莲花帽并非西夏所特有,同时列举了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宁夏山嘴沟石窟、黑水城出土唐卡、16世纪尼泊尔绘画等材料佐证说明。第四,谢继胜先生认为该窟后室窟顶藻井的大日如来像为藏传绘画风格。杨富学先生认为这种画法在藏传佛教艺术中一直盛行不衰,并非西夏所特有。
其三,针对第464窟的多处西夏文题记[14],杨富学先生认为硬物刻画文字不可能出自石窟创建者之手,多为后来朝山者所为。同时,他还对后室东壁甬道顶部梵文六字真言做了说明,指出其与壁画同属一个时代,应始于元朝[15]183-184。在为数众多的西夏时期藏传佛教画品中,六字真言迄今尚无所见。榆林窟第29 窟(西夏窟)窟顶藻井井心的墨书梵文六字真言,经研究实为元代之遗墨[16]260。
其四,杨富学先生对第464 窟前室西北角的“元代公主墓”[17]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与当时统治瓜、沙地区的蒙古豳王家族有关。
现将主要论述概括如下[4]273-280。
(1)豳王(驻肃州)。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晋封豳王,位列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同年由甘州移驻肃州,豳王乌鲁斯形成。天历二年(1329)十二月,出伯之子忽答里迷失袭封豳王,再传喃答失。
(2)西宁王(驻沙州)。天历二年(1329),出伯之子忽答里迷失改封西宁王,位列二等诸王,佩金印螭纽。天历三年(1330),出伯之侄速来蛮袭封,再传阿速歹。
(3)武威西宁王(驻哈密)。大德八年(1304),出伯获封武威西宁王,赐金印。元统二年(1334)五月,出伯之子亦里黑赤袭封,地位仅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
(4)肃王(驻瓜州)。天历二年(1329)八月,出伯之兄哈班的后裔宽彻获封肃王。位同豳王,位列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
杨富学先生根据与西宁王速来蛮有关的《六字真言碣》、第61窟外的皇庆寺[18]108-116等材料,推测第464 窟前室西北角之“元代公主”应为豳王家族成员。元代是回鹘在敦煌地区比较活跃的时期,因为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回鹘人在豳王家族支持下修复了第464窟前室和甬道现存壁画。
4.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现存壁画为元代遗墨
与莫高窟第464窟相似的是,杨富学先生认为文殊山万佛洞并非西夏石窟,而由元朝后期统治河西地区的蒙古豳王家族资助修复,并对以谢继胜、施爱民、陈育宁、王德政等学者为代表的“西夏说”进行了反驳。首先,杨富学先生从壁画中上师像的冠帽、衣装进行分析,认为莲花冠并非西夏所独有,西夏艺术曾受到唐宋、回鹘、吐蕃乃至瓜沙地方曹氏艺术的交互影响,特征不明显。其次,目前对于洞窟的分期还处于尝试阶段,尚难视为定论。其三,杨富学先生从历史背景因素对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石窟进行了说明,认定该窟在蒙古豳王家族支持下修复,文殊山万佛洞现存壁画为元代遗墨。
在《敦煌民族史探幽》第十六章中,杨富学先生详细论述了与莫高窟第464窟、酒泉文殊山万佛洞有关的蒙古豳王家族,这是其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与蒙古豳王家族有关的“裕固学”也是杨富学先生一直关注的课题之一,最终形成《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19]一书。
三
与所有精益求精的学术著作一样,《敦煌民族史探幽》一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但这并不会降低该书的学术价值。
第一,个别假设和论证依据不足。第一章第五节中出现的现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编号Or.8212-108的回鹘文《说心性经》,杨富学先生认为这是多种汉文禅宗文献的回鹘文改编本,值得商榷。另外,“月氏在东、乌孙在西”、“土著”、功德记、“蕃字”、“左衽”、“右衽”等提法也存在争议。
第二,杨富学先生在探讨第464窟等石窟的断代时多从历史文化背景因素入手,很少从石窟艺术角度分析,建议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
第三,几条该注却未注的引文。“沙州北亭可汗”、“前有裳无衽”、“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三条引文理应加注标明出处,方便读者查阅。
第四,个别论述未能保持一致。阔端与萨迦派宗教领袖班智达举行“凉州会谈”的时间,一处作1244年,另一处作1246年,实为1247年。第134页第四行和第135页最后一行的“柏孜柯里克”,应与书中其他论述中的“柏孜克里克”保持一致。第118页引用的李正宇先生的《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一文的题目,正文与注释不一致。
瑕不掩瑜,《敦煌民族史探幽》一书是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中外关系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一部具有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高水平专著,值得学界关注。
注释:
①桑原骘藏:《张骞远征》,《桑原骘藏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第274页。
②另有元和四年(809)说,此处以贞元四年说为主。参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③柯尔克孜族(或吉尔吉斯)、图瓦族、阿尔泰族和哈卡斯族的共同祖先。参王洁、杨富学《突厥碑铭所见黠戛斯与突厥回鹘关系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④1141年分裂为东、西汗国。东汗国依附西辽,1211年灭亡;西汗国先依附塞尔柱突厥,后依附西辽,1212年为花剌子模所灭。参魏良弢《喀喇汗王朝》,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⑤1346年为察合台后王秃黑鲁帖木儿所统治。
⑥1028年亡于元昊,后裔与河西蒙古经过长期融合形成裕固族。
⑦关于敦煌大族,参冯培红《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⑧关于归义军史研究,参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三秦出版社,2009年;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的历史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⑨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沙州回鹘研究之一》,《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49-174页;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9-21页。
⑩苏莹辉:《瓜沙史事丛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8-107页;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对于曹氏家族的族源,荣新江、冯培红二位先生认为是粟特后裔,参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⑪司马光:《司马光传家集》卷四十一《论横山疏》,原注:“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万有文库本。
⑫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山口瑞凤编《讲座敦煌2: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331-338页;《チべツト文字ご书かおウイグル文仏教教理问答(P.T.1292)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XXV卷,1985年,第1-85页;《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国》,《东方学》第74号,1987年,第58-74页;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劄记》(二),《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编》第32 号,2014年,第28-29页;钱伯泉:《沙州回鹘研究》,《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汤开建:《甘州回鹘余部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⑬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十九记载,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沙州最后一次朝贡,此后不再见贡事。
⑭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 页。日本学者认为“至迟于1073年,西夏即开始有效的统治了敦煌”,参冈崎精郎:《タングート古代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第274-275页。
⑮另有日本学者多持此说,参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三),《东方学报》(京都)第13卷1号,1942年,第70、74页;冈崎精郎:《タングート古代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第273页;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京都汇文堂书店,1955年,第490页。
⑯ F.W.K.Müller,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Klasse,Berlin,1915,S.4;森安孝夫《ウイグル仏教史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书》,《史学杂志》第83卷4号,1983年,第39-40页。
⑰另有岑仲勉先生、德国学者毕丽兰女士持此说。参岑仲勉:《吐鲁番木柱刻文略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 本),1947年,第117-119 页;Lilla Russell-Smith,Uygur Patronage in Dunhuang.Regional Art Centres on the Northern Silk Roa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Leiden/Boston,2005,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