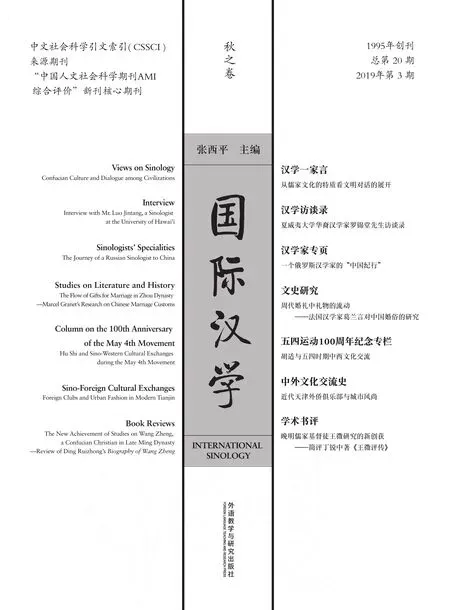编后记:从汉学家看汉学
2019-12-14任大援
□ 任大援
夏至之前,趁着天气还没有太热,我们又完成了一期编辑任务,要说几句编里编外的话。
“汉学一家言”作为一个固定栏目,已经办了多期。这一期我们刊登了景海峰先生的大作,由国内学者谈谈中国儒家文化,这似乎和“汉学”有一点儿不沾边,但是仔细一想,300多年前在欧洲知识界发生的“汉学”热,不正是由于“礼仪之争”所引发的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所致吗?“礼仪之争”中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一派允许遵行儒家礼仪的中国人加入信奉一神论的天主教,他们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和判断具有学理上的准确性吗?抑或只是一种误判或出于传教需要的权宜之计?这类问题直到今天仍然为汉学家所关注,因而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为从事汉学研究的人所关注。
“礼仪之争”在欧洲引发的一个客观后果,是汉学研究的队伍增加了“学院派”力量,并且后来居上,在欧洲高等学府占有一席之地,而后扩展到海外各国。汉学家因而被我们所关注。通过汉学家,我们可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汉学。
本期“汉学家专页”虽然只有两篇文章,却涉及了三位俄国汉学家,一位法国汉学家,十分有趣。李福清(Boris L.Riftin,1938—2012)是人们熟知的当代汉学家,他的文章讲述了近代俄国大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Vasiliy Aleksyev,1881—1951)在20世纪初在北京邂逅法国大汉学家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随后二人在中国游历考察的故事。他们一同攀登泰山,又一同浏览西安碑林,从历史记录和他们后来各自发表的作品和收藏,可看出两位大师相似而又迥异的学术旨趣。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阿列克谢耶夫关于民间风俗、神灵崇拜、民间艺术研究对李福清的重要影响。
《一个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纪行”》中对中国诗人与酒的关系的描写,不禁令我想起一件往事。1989年我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国,波恩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的汉学家庞纬(Werner Banck,1941—2002)托我带给李福清教授一本中国民间画册的书和一瓶白酒。我到莫斯科他的家中后,拿出随身携带的礼物,李教授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可是当他妻子进来的时候,他迅速地把酒塞进桌子的抽屉,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动作和表情令人忍俊不禁,至今难忘。现在读到李福清教授文章中对文人与酒的叙述,字里行间仿佛看到这位德高望重的汉学家一颗未泯的童心,这种真挚(对酒的真挚、为人的真挚与作学问的真挚结合在一起)应该说也是他汉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来源。
文章中提到阿列克谢耶夫与沙畹的学术旨趣之不同,仿佛是汉学中的“经院派”与“民间派”,这点值得注意。发生在汉学家身上的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对汉学的影响。
20世纪的汉学家中,还有另外一个类型。20世纪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居住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进入汉学研究领域,我们可称他们为“华裔汉学家”。他们长期在海外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绝大多数基本用西文写作。本期介绍了一位基本用中文写作和讲课的华裔汉学家罗锦堂先生,这在“华裔汉学家”中属于少数个案。罗先生是国际汉学界“元曲”方面的专家,他虽然在台湾拿到博士学位,与大多数“华裔汉学家”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不同,但是他随后在中国香港和日本的研究工作经历使他走入国际汉学界,最后落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东亚系,从事研究与教学达30年之久,成为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元曲专家。他在美国坚持用中文授课,这和他的研究对象有关。同时他又将美国汉学家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翻译成中文,以便学生参考。这说明他兼顾了“对象”(中文文献)与“方法”(西方观察角度)上的融合,为我们研究华裔汉学家提供了独特的鲜活资料,值得我们关注。
和华裔汉学家相对应的还有一类西方汉学家,他们用西方语言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虽然不讲中文,却也成为知名汉学家。本期刊登的有关耶稣会传教士与南明王朝之关系的文章,其作者柯兰霓博士(Claudia von Collani)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类汉学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是以西方语言为主体的非汉语文献。利用这些资料,他们同样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种情况,古来有之。例如17世纪编写《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的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18世纪编写《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等。这两位耶稣会士汉学家既不懂中文,也没有到过中国,却同样跻身于17世纪和18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之列。正如伏尔泰所说,杜赫德虽然不曾走出巴黎,不认识一个汉字,但是他借助教会同僚们撰写的相关报道,编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关于中国的佳作,堪称举世无双。当然,这类的成果的优劣和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有很大关系。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为杜赫德此书供稿且到过中国的传教士有27人之多, 并且能找到资料之间的对应关系。另外,对这些成果的评价,也要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这种研究方法流传至今,因为西方文字的汉学资料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早期时代,可以满足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需要。除了前面提到的柯兰霓博士,还有我们熟悉的汉学家高华士(Noël Golvers)、杜鼎克(Adrian Dudink)等,基本属于这类汉学家。他们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例如,他们的研究资料有些是档案和手稿,因此,他们一般具有较好的拉丁语言和多种古代欧洲语言的训练基础,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在当代,随着“汉学”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成为“显学”,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非汉语资料不断增加,在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的条件越来越便利了。就中国学者而言,西文的原始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资料,也越来越丰富了,这就为外语专业出身的学者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拓宽了学术研究的领域,由“语言、文学”的“汉学”,进入到“历史、哲学、文化”的“汉学”。这种情况,从我们投稿作者的情况便可看出——稿件的研究范围扩大了,材料丰富了。我们利用暑假开办的“国际汉学”研讨班,报名踊跃,也可说明这一点。 汉学研究成果的丰富和视域的扩展,对我们编辑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常有这种情况:关键词的选定、专业词汇的翻译,甚至一个外国人名或地名的汉译名,我们的编辑与作者之间都经过反复讨论才能确定。尽管如此,还是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例如,有的汉学家的名字,出现过八九种不同的译名,哪一个更准确?这些看似小问题,实际上都需要加以研究。
今年正值五四运动100周年,本期发表了欧阳哲生先生的《胡适与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通过胡适与五四时期来华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个案,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状况的丰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