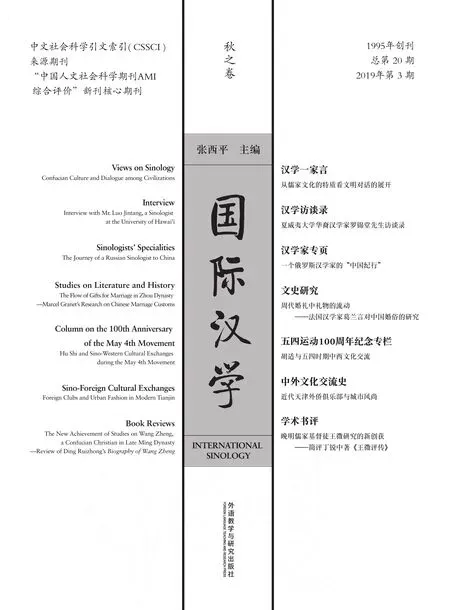《〈诗经〉翻译探微》述评
2019-12-14赵洪娟
□ 赵洪娟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浪潮推动下,典籍翻译及其研究层出叠见。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海外传播,开展各种典籍翻译的热潮中,我们不禁要问,典籍外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把中文典籍变成异语言所要达成的愿景是什么?由此总结出的典籍翻译的原则方法又是什么?对于上述疑问,李玉良教授的《〈诗经〉翻译探微》一书作了颇为深入的探讨。
李玉良教授从《〈诗经〉英译研究》之宏观视角探究,到《〈诗经〉翻译探微》(以下简称《探微》)之多译本、译家批评及《诗经》翻译的多角度微观分析,历时十载,朝乾夕惕,孜孜不倦。《探微》一书不但从翻译技巧方面给予了一定剖析,最主要的是通过方法论的阐述分析,在翻译思想以及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两方面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作者以许渊冲、汪榕培、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詹宁斯(M.A.William Jennings)、庞德(Ezra Pound,1885—1972)、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1844—1920)等中外译者《诗经》英译本为根据,对《诗经》名物翻译的文学性、《诗经》韵律翻译的价值规律、《诗经》意象翻译的可能与否以及《诗经》的修辞和题旨翻译等六个方面展开“中西会通的尝试”,①张西平:《〈诗经〉翻译探微·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并对典籍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规律、方法进行了颇有启发性的探究。
探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一定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要把典籍翻译“跳出简单的两种语言转换的层面,一定要把翻译的问题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社会背景之下,去审视、去思考”。②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东吴学术》2013年第2期,第47页。《探微》指出,经传、笺、疏、注得以实现,成为政教工具的《诗经》,对其开展的语内翻译实际上就是翻译《诗经》文化,而《诗经》文化就是《诗经》接受史,是其在传承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的深刻影响。③李玉良:《〈诗经〉翻译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8页。而对于《诗经》的跨语际翻译则不免要涉及翻译与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中国典籍翻译从译者到译本都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以译者为例,不仅有传教士、汉学家,还有大量的诗人、文学家也涌入到中国典籍翻译的浪潮之中;且在20世纪30年代,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和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相继在美国成立,美国的汉学研究一度展现了勃勃生机。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无论是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翻译,还是以西方读者的接受性为关注点的归化翻译,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的内部危机。正如周宁所言,无论是丑化中国形象,还是美化中国形象,其背后不变的是西方现代性构建中的话语构成原则,④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页。是出于要改造并完善自身文化的一种迫切需要。诚然,由于被翻译作品在译者的掌控下,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又会搭建出新的话语空间。因此,此时的典籍英译便成为解决西方文化内部危机的重要工具。以《诗经》为例,外国译者的典籍英译多是“因《诗经》之名,行创作之实”,①《〈诗经〉翻译探微》,第239页。借鉴别的民族文化来发展和完善本民族文化。
此外,由于文化交流的意义主要源于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因此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目的的典籍翻译,其译本都应忠实原作。以史为鉴,在侧重解读翻译文本的同时,要关注历史,探析源语在其历史语境下的意义。但实际上,要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让我们的“异文化”被认同和接受,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有自己的原有文化,需根据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选择恰当的文化传播和翻译策略。简言之,从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的综合角度考量文化传播和典籍翻译策略,这不免要涉及《诗经》的意象翻译问题。
何为意象?庞德认为意象是在一瞬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种思想,而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②同上,第280页。在20世纪初期,掀起了西方哲学、美学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危机进行批判的浪潮,为解决其内部文化危机,为西方文明探寻出路,诸多文人试图在东方国度的东方文化中寻找希望。庞德的翻译就是为了颠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寄希望于翻译活动创造出新的话语空间的一种尝试。庞德作为诗人,而非汉学家或翻译家,其尝试中国古籍翻译的目的就是“改革美国诗歌艺术形式,完善其于20世纪初所提出的意象主义诗学”,③同上,第240页。为西方文化服务。因此庞德用意象主义理论指导诗歌翻译,对《诗经》原意象的改变程度之大便可想而知。
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再叙事的体现。因“叙事是一个或数个叙事者向另一个或数个受众讲述一个或多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④Gerald Prince, The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p.58.《诗经》翻译作为文本叙事的一种,译作的失真、意象的扭曲以及内涵的缺失必为常见之事。对于意象翻译中存象失意的问题,《探微》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译者和原作者既不处于同一时代,又不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二者在意象寓意问题上不存在共有信息,因此对于存象失意问题不要过分归责于译者。此外,《探微》不但对有关《诗经》意象的文献史料进行了爬梳剔抉,而且对意象在西方文献中的意义进行了详细考证,对中西意象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探微》还指出,《诗经》中的原始意象多来自神话体系及具有隐喻性的周代民俗。而对意象的翻译问题,詹宁斯强调意象的文学特征,而许渊冲则认为其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传达最为重要,作者指出要实现《诗经》翻译的上述目的,最有效的操作方法就是在译文后面加以注释。诚然,若译者在正文翻译之外,多提供文化和历史背景信息,对典籍中所涉及的难以理解的物象做出面向当下的诠释,必能极大地促进读者对译文的接受。
实际上,要使《诗经》意象在语际翻译中得到有效传达,语内诠释是其必要前提和基础,因此需对典籍的训诂和阐释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所谓训诂,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整理及古籍文献的意义阐释。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训”之含义为“训者,说教也”,⑤(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3(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3页。班固《汉书》中提到“诂”的含义则为“师古曰:诂谓指义也”,⑥《汉书》,卷87(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4页。实质是指解释古代汉语之意义。由于典籍的英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古代思想文化的一种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必然要建立在合理的语内诠释的基础上,若语内诠释背离了古籍文献本意,那忠实可靠的异语翻译和文化传达便无从谈起。《探微》以“雎鸠”为例,指出不同译者对“雎鸠”理解不同,其英译亦多种多样,有些翻译完全相悖于“雎鸠”为性情凶猛的鱼鹰之本义。如理雅各和韦利将其译成“osprey”,庞德译成“fish-hawk”与“雎鸠”原意基本一致,而高本汉的“ts’u-kiu bird”翻译则不知其所云。此外,作者还指出英国阿连壁的《鹊巢》翻译基本是无视训诂,任意篡改字义之作,目的是为迎合英国读者的审美诉求。外译中出现此种意义背离,除了与译者的理解、翻译目的有关之外,概与译者所用的训诂译本有一定关联。因此在典籍翻译时,译者所使用的训诂译本应当选择善本。所谓善本应该是校勘缜密,讹误较少的版本。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认为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史越久远,古史中的人物就越被放大,顾先生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典籍的版本,越古老的版本越发可靠。
《探微》中特别强调了训诂的意义,认为重视训诂与注疏是翻译好《诗经》的第一法门。对于后人为《诗经》所做的《诗序》,其认可的翻译原则为正确的要翻译,错误的也要翻译,但一定要做出必要合理的说明。这种原则的坚持主要是从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的角度予以考量,因各种对《诗经》的传、笺、疏、注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创作和传播。因“翻译不仅赋有忠实于原作的道德义务,而且赋有建设本民族文学和文化,满足本族读者什么需求的道德艺术”,①《〈诗经〉翻译探微》,第30页。而且阐释是人对存在的理解,②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73页。所以对《诗经》传、笺、疏、注的语内翻译诠释和将其翻译成外文的语际翻译在建设民族文学和文化,满足读者的艺术需求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除具有五经之首、文学之源的地位之外,其独特的迭句、迭字、迭韵,适于吟唱的诗歌韵律表达方式亦彰显出其独到的魅力;而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表现手法,则刻画出了自西周到春秋时期生动的民俗生活画面。因此,《诗经》的韵律翻译规律和民俗事象也是《探微》一书探讨的重要内容。
在近代,西方传教士曾在中国进行过大量的文化交流传播工作,他们曾试图用中文写诗歌,或将其赞美诗翻译成中文。传教士在最初翻译基督教的赞美诗时,为符合中国的诗歌表达习惯,多用浅近的七字或五字文言进行表述,虽然这种翻译既不符合赞美诗的特点,也不符合赞美诗的音乐乐律,但他们认为这样的翻译更具接受性,更能被中国人所认可,如“行善修持品最高,随时检点用心劳。恶人道路休趋向,敬畏圣神莫侮污”等。③《养心神诗》第一首,无出版年月。《诗经》在古时为吟唱之歌,对韵律十分讲究,但对《诗经》英译时是否用韵,如何用韵的问题,学界争论已久。对此问题,我们在《探微》一书中找到的答案是:《诗经》译韵虽然难度较大,但并不能成为不进行韵律翻译的阻碍,《诗经》为诗歌,诗歌必有韵律;此外,因东西文化中诗歌韵律的差异和审美习惯的不同,译诗韵律当不必与原诗韵律一致,若《诗经》译文能为英语文学输入新鲜血液,并让译文读者了解《诗经》的本来面目,翻译的目的便就此达到了。
此外,典籍翻译要有跨学科的研究和思维方式,不能在增译、减译、正说、反说等翻译技巧方面过于纠缠,而是应该将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和方法融汇其中;在对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关照之后,从多角度解读文本,解除翻译仅是文字间的字面转换和对译的误解。《探微》立足于语料,通过多译本比较分析,既考量单个译本的独特之处,又对所有译本的共通点进行了细致分析,为读者了解《诗经》的翻译状况提供了非常综合而全面的分析。由于民俗文化是“民”的文化,最能真实地反应民众生活及文化习俗的内容,不论各国家民族在具体习俗习惯上有多大不同,其作为“民众”的一员,必具有“民”的共通之处。若在忠实翻译的基础上,较好地保有原文化的民俗事象和意象,不但能反映出译者的文化态度,而且更能为异文化读者所接受,更好地实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在《探微》中,作者指出韦利的《卫风》译文就是从民俗学的视角进行的阐释翻译,英国读者亦较为容易理解。从文化接受的角度看,这种考量、融入民俗文化的翻译,不但较大程度地反映了原文化,而对文本的塑造和异文化读者的接受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方式。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摸索中,《〈诗经〉翻译探微》一书的出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翻译能让读者接受,典籍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此前对《诗经》的翻译研究多注重从诗歌的韵律及诗学、美学等角度予以分析,而《探微》则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的外传问题,且在翻译策略上作者强调要尽可能地使用归化法和诠释法,最大限度地传播原语文化的同时,又要使译文具有较好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这一点与谢天振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要考虑“时间差”和“语言差”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今后《诗经》的翻译研究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探微》中提到的修辞、韵律、题旨、意象等内容的翻译问题,进一步思考典籍翻译处理策略的通用性问题?是否可以在系统梳理《诗经》翻译史的基础上探究《诗经》译作的海外传播情况?是否可以在传统文化走出去效果机制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完善“走出去”的文化策略问题,特别是典籍翻译问题?诸多问题仍待我们继续思考研究,在开展典籍翻译,推动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的道路上我们还需扎实、坚定地走下去,让世界真正地认识、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