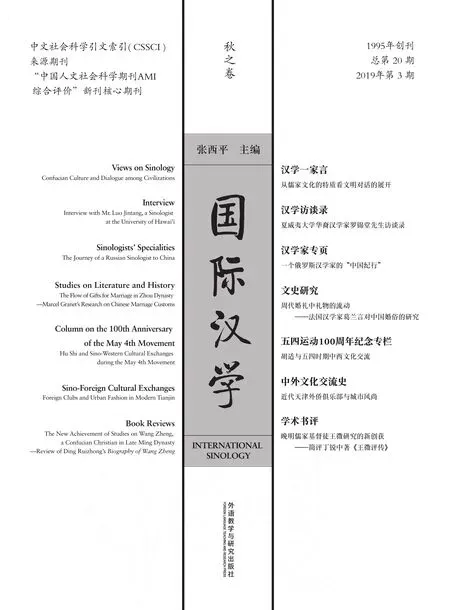晚明儒家基督徒王徵研究的新创获
——简评丁锐中著《王徵评传》
2019-12-14林乐昌
□ 林乐昌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皈依天主教后取圣名斐理伯(Philippe),卒后学者私谥端节先生。他是陕西西安府泾阳县人。明天启壬戌(1622)登进士第,历任广平、扬州司理、山东按察司佥事兼辽海监军。王徵一生喜读“奇书”,广交“奇人”,善制“奇器”,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科技发明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作为儒家基督徒与著名的“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一起被合称为晚明“四贤”,此外还有“南徐北王”之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30年代,自从陈垣先生撰写《中国基督教史》为王徵立传以来,对王徵其人其学的研究渐为学界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降,王徵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王徵研究的走向看,其间经历了从零星研究到局部研究,再到综合研究的过程。综合研究比较早的成果有毛瑞芳所著的《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①毛瑞芳:《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该书在晚明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对王徵接受和传播西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五年后,青年学者丁锐中在德国波恩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汉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了《王徵评传》②丁锐中:《王徵评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评传》)。《评传》与毛瑞芳所著书,都属于王徵综合研究的成果。由于丁著采用的是“评传”体例,因而完成的是一部具有评论性质的王徵生平和学术传记。就《评传》的内容看,其13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叙述王徵的生平经历,内容包括十上公车、领洗奉教、两任司理、守御乡里、监军辽海、逢赦归里、创办仁会、绝食殉国等,合计10章;第二部分深入评析王徵的学术思想,内容包括“资耳目”之学、“资手足”之学和“资心”之学,合计三章。纵览全书,有一条贯穿王徵生平经历和学术思想的主线,即儒、耶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学术融合。以下将参照这一主线,从三方面对《评传》一书进行评析。
一、就王徵违诫娶妾评析儒、耶文化冲突
王徵受洗奉教后,因娶妾违反了天主教的“十诫”。这在他内心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虽然以往学术界对王徵生活经历中的这一事件也曾有过评论,但《评传》作者因格外重视王徵的这段经历,特设专章展开评述。在《评传》第三章中,作者对王徵的这段经历所做的评析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事件原委说明清晰。据《评传》的说明可知,王徵受洗入教,约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46岁时。而王徵娶妾,则在他入教后的七八年,当时他大约54岁。早在万历十三年(1585),15岁的少年王徵便已娶妻尚氏。他中年娶妾之前,与妻子尚氏所生的几个儿子都先后因病夭折了,只剩下两个女儿。天启二年(1622),52岁的王徵登进士第。两年后,在其父的严谕和妻子尚氏等家人的哀求下,王徵未能坚守诫规,娶15岁的申氏为妾。
王徵娶妾发生的原委,既有其文化背景,也有其具体原因。就其发生的文化背景看,《评传》以“晚明纳妾制”为题,用一节篇幅做了说明。作者指出,“纳妾制是中国家庭婚姻制度的补充,绵延上千年,形成了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这种婚俗在传统社会是被法律伦理认可的”。①《王徵评传》,第33页。作者还指出,祖先崇拜是儒教信仰基础之一,而祖先崇拜必须由家族中的男性后代来完成。若缺少男性后代,则会动摇家族秩序。为此,《大明律》明确规定,凡男子年满40岁而无后嗣者,允准纳妾。因此,解决无嗣问题,便成为纳妾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文化冲突剖析到位。天主教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也主张男女婚姻平等。天主教“十诫”的第六诫是毋行邪淫。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在其《天主圣教实录》中指出:“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独得有二女乎?夫妇以相信故相结,信失而结解矣!况夫妇乖,妻妾、嫡庶争,无一可者。此所以有罪也。”②同上。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在其《口铎日抄》中也极力批驳纳妾的不合理。与此相比较,娶妾便成为当时中国士人受洗入教的最大难题。部分中国士人娶妾后却有受洗入教的意愿,由于这严重违背“十诫”,便遭到传教士的拒绝。
对于中西文化的这一冲突,《评传》的作者从多方面做了论析。首先,崇祯九年(1636),王徵撰写《祈请解罪启稿》,表示“惭愧之极,悔恨之极”,并立下誓言:“从今以后,视彼妾妇,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倘有再犯,天神谙若立赐诛殛!伏望铎德垂怜,解我从前积罪,代求天主之洪赦。”王徵作为天主教徒娶妾,到66岁时祈请解罪,违诫所导致的内心冲突困扰他长达12年之久。其次,王徵虽然以“祈请解罪”的方式使违诫问题得以解决,但解决冲突的方式当中也包含了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所做的调和。王徵以过继自己兄弟之子的方式解决了无嗣问题之后,为了不改变信仰,王徵与妾申氏解除了婚约,但二人死后却同葬于一穴。这种对文化冲突的解决方式,既未违背天主教教规,又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吻合。不难看到,作者的这些评析都是比较到位的。
第三,事件意义阐发深刻。《评传》虽然对王徵因娶妾违诫引发文化冲突这一事件的意义着墨不多,但所做的阐发却相当深刻。首先,作者正确地指出,传教士把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观念带入中国,是对中国妻妾婚姻制度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其次,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妻妾婚姻制度维护的是男子特权,这对妇女的尊严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而,在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的冲击下,王徵对娶妾的悔罪,可以视作对男女平等意识的呼唤,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二、就“资心”之学评析王徵对儒、耶学术义理的会通
在《评传》中,作者用一个章节的篇幅,研究和评析了王徵的“资心”之学。在王徵看来,“资心”之“心”,指精神生命,具体指信仰和道德。清初关中大儒王心敬曾正确地指出,王徵是“以畏天爱人为心”的。其“资心”之“资”,意思为“助”。据此看,“资心”之学是一种有助于精神生命成长的学问。崇祯元年(1628),58岁的王徵在扬州府推官任上撰写完成了《畏天爱人极论》一书。在《评传》第七章中,作者对王徵“资心”之学的评析,正是与其“畏天爱人”的为学主题结合起来进行的。《评传》第七章分为两节。
第一节的内容,主要是当代学术界对王徵“畏天爱人”之学的评述,包括对“畏天爱人”之学理论渊源的梳理。首先,关于当代学术界对王徵“畏天爱人”之学的评述《评传》引用了国内学者陈俊民、孙尚扬、林乐昌以及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从不同角度对王徵《畏天爱人极论》的评述。其次,正如钟鸣旦所指出的,《畏天爱人极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王徵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其他著作。例如,王徵在论述“畏天”“天命”等命题时,引证了不少儒家经典,包括《论语》《孟子》《尚书》等。此外,王徵还引用了传教士的宣教作品,包括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Dantoja, 1571—1618)的《七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等。在《评传》作者看来,王徵的《畏天爱人极论》对中外典籍和著作的大量引用,表明此书既有其儒家经典依据,又有传教士的著作作为其理论来源,同时还表明,《畏天爱人极论》是王徵与传教士对话的产物。①《王徵评传》,第108页。
第二节内容集中介绍和评析了王徵的《畏天爱人极论》一书。这一节是第七章的重点内容。首先,介绍了《畏天爱人极论》一书的结构特征。《评传》作者把王徵《畏天爱人极论》的内容,梳理为八次问答。这八次问答,分别讨论了王徵入教的原因、王徵信仰的几次转折、王徵对天主唯一性的论证、王徵对天堂地狱说的理解、王徵对来世利害的认识、王徵对灵魂不灭说的看法、王徵对畏天爱人价值取向的阐发以及发问者对王徵所述天主教义理的信服。这八次问答,尤以第二次问答和第七次问答最为重要。在第二次问答中,王徵回顾了自己信仰的两次转折,一是从佛教徒转而皈依道教,二是又由道教徒转而信仰天主教。《评传》作者认为,由于王徵把儒教的天命信仰与天主教的根本教义结合起来,从而使第二次问答成为王徵儒、耶义理会通的精彩部分。②同上,第110页。其次,评析了王徵在其《畏天爱人极论》一书中是如何会通儒、耶义理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其中的第七次问答为例。这次问答的内容,是王徵对畏天爱人价值取向的阐发。对此,《评传》作者做了十分详尽的评析。一是强调,王徵的“畏天爱人”总括了天主“十诫”之意;二是认为,王徵运用儒家之“仁”观,结合“畏天爱人”之说巧妙地进行了儒、耶会通;三是指出,“畏天爱人”之学的意义在于阐发信仰的突出地位,并强调切己践行的重要性。③同上,第116页
通过以上的介绍和评析,《评传》作者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王徵皈依天主教,并非从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转化”为天主教信仰,而是对天主教教义加以吸收“以补充儒教信仰的欠缺”;④同上,第108页。第二,“畏天爱人”是王徵对传统儒家“天人关系”的拓展,而《畏天爱人极论》一书则见证了王徵会通儒、耶的信仰追求。⑤同上,第117页。作者的这些评价具有总结性,是很深刻的。
三、就“资手足”之学评析王徵对西方科技的汲取与传播
中国古代把器物制造的学问称作“制器”之学,是从制作对象的客观角度界定的,而王徵喜欢把“制器”之学称作“资手足”之学,则是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加以界定的。“资手足”比“制器”的说法更贴切,也更人性化。据王徵的解释,他致力于“资手足”之学,是由于他“每叹人若畜”,对劳动者的工作要付出太多的体力深表同情,于是下决心帮助劳动者减轻沉重的体力支出,认为“资手足”之学是一种“大用”之学。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特别热衷于各种实用器械的研制,并力图“广为传造焉”。早在与传教士结交之前的青年时代,因受舅父张鉴的影响,王徵就开始迷恋于制器之学。王徵回忆说,当时“顾颇好奇,因书传所载化人奇肱,璇玑指南,及诸葛氏木牛流马、更枕石阵、连弩诸奇制,每欲臆仿而成之。累岁弥月,眠思坐想,一似痴人。虽诸制亦皆稍稍有成,而几案尘积,正经学业荒废尽矣。又性宽缓耽延,不即就铨,致弟友亲爱辈咸嗟怨刺讥不已。直至十上公车,始克博一第焉。”正是由于王徵特别迷恋制器,所以他对举业一直提不起兴趣,以至九次进京参加会试都落第而归,直至第十次会试才终成进士。这一过程整整经历了30年。
关于王徵对西方科技的态度,《评传》的作者是从汲取和传播这两个方面进行绍述及评析的。首先,关于王徵对西方科技的汲取。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西方科技著作的译绘以及受西方科技成果的影响自己独立撰著的科技著作上。天启六年(1626)冬,王徵为继母服丧期满,入京待补新职。在此期间,王徵有机会从外国传教士那里看到科技图书“不下千百馀种”,这让他兴奋不已。不久,在德籍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的指导下,王徵有选择地编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并摹绘了书中的配图,译绘成书。在该书中,王徵对西洋奇器的选录非常严格,明确提出了“三最”原则,即一选录其对民生日用和国家所需之“最切要者”;二选录工匠便于制作和不费工值之“最简便者”;三选录众多器械中之“最精妙者”。由于该书是依据这“三最”原则译绘的,故取书名为《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崇祯元年(1628),王徵将译著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三卷与自著的《新制诸器图说》一卷合为一帙,刊刻行世。《评传》作者参照学术界的相关成果,高度评价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科学价值。①《王徵评传》,第89页。王徵对西方科技著作的译绘,是他汲取西方科技的的起点。此外,王徵还独立撰著了若干科技著作,比较重要的有《新制诸器图说》。该书共收入九种器械:虹吸、鹤饮、轮激、风硙、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及兵器一种,即连弩。这些器械,可以运用于农耕、灌溉、运输、战守,其中有些是对前人发明的总结,有些则是他自己的创新。《评传》作者对这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第一部机械制造的专著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制器之学的总结,并指出王徵在该书中还阐述了一种爱护自然、珍惜资源、善求变法的新型制器观。②同上,第91页。其次,关于王徵对西方科技的传播。这既反映在上述王徵对西方科技著作的译绘,扩大其影响方面,也体现在他对接受西方科技影响的一系列成果的推广和运用方面。正如《评传》作者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既体现了王徵“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也体现了他的利民救世的实学愿望”。③同上,第103页。
综上所述,通过《评传》一书对贯穿王徵生平经历和学术思想的儒、耶文化冲突与学术融合的多方面评述可以看出,在王徵身上中西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融合,而融合往往多于冲突。《评传》作者所做的一系列评析,对读者不无深刻的启发意义。因而有理由认为,《评传》一书弥补了王徵研究领域一直没有评传类成果的缺憾,是对王徵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充分肯定《评传》多方面优长的同时,也应当指出,该书也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例如,作者若对王徵所谓“资心”“资手足”等说法稍加解释,可能更有助于读者对这两种说法的理解;又如,与《评传》一书的绍述文字相比,书中各章的评论文字则显得展开不够。这些不足之处,希望《评传》一书再版时能够得到修订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