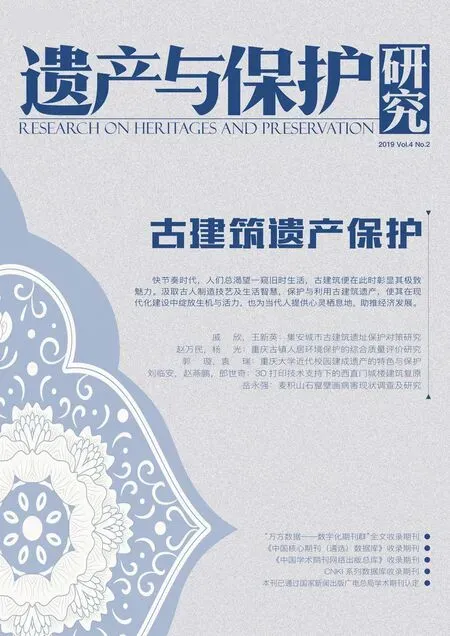遗产实践中的社区参与述评
2019-12-14
(浙江科技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对政府作为遗产的所有者和遗产实践主体来说,遗产所在地的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是遗产实践所不能回避的问题[1]。社区参与遗产实践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遗产认知发生转变。最初人们认为遗产是“纪念碑性质的”物质性遗产,代表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建筑价值或美学价值,这种遗产认知把遗产看作是过去历史的凝固,因此遗产保护和利用涉及专业性知识,是遗产专业人士、专家学者所关注的领域。然而,随着对遗产认知的加深,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或译为思辨性遗产研究)认为遗产是一种“社会过程”,强调遗产在认定、保护和利用过程中与人的关系,以及物质性遗产所承载的非物质性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强调作为过去历史传承下来的遗产与当下社会的互动,与认同、社区归属感等紧密相连,与社会融入、社区复兴、城市复苏等当下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此种视角认为不仅遗产相关专业人士应关注遗产保护与利用,遗产所在地的居民与遗产也紧密相连。因此,把遗产所在地的社区参与纳入遗产实践的决策、管理层面中,将社区居民对遗产价值的认知理解考虑进来,对遗产实践具有重大意义[2]。
虽然有研究认为,社区是否参与遗产实践对于遗产保护和管理来说并非完全必要[3];但是,在政府管辖权所允许的范围内,社区参与是文化资源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亦是遗产活化利用的重要资源。本文主要从社区内涵、社区参与模式、社区参与遗产实践的作用和我国社区参与遗产实践现状进行述评,以提供一个宏观视角深化认识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的社区参与,为我国遗产活化利用中的社会参与提供启示。
1 遗产领域中的社区内涵
社区,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社区,作为社区居民持久的生活空间,逐渐在遗产保护和利用领域引起重视。遗产领域的“社区”概念来自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ies),但是社区研究中的“社区”并没有统一的定义[4]。总体说来,理解社区概念需要注意3点:①社区概念兴起的原因,是由于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熟人关系网络构成的乡村逐步集中到城市,熟人社区逐渐解体,现代社会(society)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冷漠,因此早期的社区研究具有怀旧(nostalgia)情结,是对熟人社会的依恋,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能够构建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联系的诉求[5]。如Calhoun所说,社区会激发人的“在一起(togetherness)”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温暖和安全的关系,也表示某种特定模式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6]。②社区不同于社会(society)。滕尼斯认为,社区是老式的,社会是新的,两者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从另一种角度看,每个人都向往乡村生活,表明人们对强有力和富有活力社区的向往。社区意味着真实性、大家一起生活,具有持久性;社会是短暂的、流于表面。因此社区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而社会则是机械性的拼凑、人为的产物[7]19。③要成为社区必须符合两个标准:一是要在同一个地理区域范围之内;二是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网络[7]33。这两方面并非缺一不可,人际关系网络可超越地理限制,形成精神上的社区[8]。如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社区空间的建立,为在遗产实践被边缘化的群体提供了话语平台,可以参与遗产实践[9];社区精神可称为“社区意识(sense of community)”或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美国的遗产保护中,人们认为这种归属感可以治愈许多由于城镇化给人带来的痛苦和疾病[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公约对社区也并没有明确定义[11]。这是因为社区和群体是流动的,且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社区和群体的概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理解方式[12]。而且,对社区的理解是一种常识,“一提到社区,人们感觉温暖、有情感;在一些公共政策以及文化政策中,提到社区人们就想到是做有益的事情。总之,在社区里做有益的事情,对社区有归属感,人的感觉会非常美好”[13]。
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东京的一次专家会议对社区进行界定:社区是由人类构成的网络,在其共享的历史联系中生发出的认同感或归属感,源于该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传承。而这并未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官方定义[14]。可见,社区概念或许可以等同于遗产所处的景观、历史环境,包括遗产地所在的场所空间以及其中居民的故事、情感、经历和想法等,使人们具有归属感和亲密性。从这点来看,社区相当于2003年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产中提到的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文化空间内无形的文化遗产,在社区内一代代传承下来,并被社区居民不断创新创造,以呼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通过人与自然、历史的互动,促进文化认同感、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多样性、创造性。
2 遗产实践中的社区参与
2.1 遗产实践
本文所指的遗产实践,是就政府作为主导者的这一类遗产而言。国内外的遗产实践和研究大都将政府视为实践主体,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从本质上尊重政府、遗产专家学者作为遗产保护和管理者的既有主导性地位,研究和讨论遗产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如何被纳入主导性地位,以及如何发挥其从属性作用。
从国内外一些遗产实践案例看来看,除了政府,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遗产的私人拥有者,都可以是遗产保护主体。但是,这并没有成为遗产实践必须考虑或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中,多有社区参与、公众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字样,本文对这三者的内涵与差别进行梳理。
国际学者对于遗产实践中的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involvement)和公众参与(civic engagement)有不同认知。前者侧重遗产地所在社区的居民、非政府组织、社区内的个体或者群体;后者侧重非政府组织(NGO),较少涉及个人,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一定位于遗产地所在社区,亦可是由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环保主义者、历史学家组成的专业性遗产组织,这样的组织参与遗产实践往往具有较高的话语权。
维基百科对社区参与、公众参与和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ment)三者进行比较:公众参与主要指参与以公民社会组织为单位的政治性活动、成为其成员或者是志愿者组织;社会参与指参与一些集体性活动;社区参与则指为了社区长远的集体利益和未来发展,社区内的组织和个人建立长期的、不间断的联系①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_engagement[2018-10-12].。
英文表达中有“社区中的公众参与”(civic engagement in the community)一说,可见社区参与可以包括公众参与。社会参与更多指的是个人以个体的身份参与社会群体的活动(包括一些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注重的是活动、社会网络、社会群体关系,参与过程中个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尊重个人意愿而非强制,不涉及家族责任或者金钱等因素。
由此可见,社区参与、公众参与和社会参与可总结为:①公众参与和社会参与的目的性比较强,一旦实现既定目标,公众参与和社会参与可即刻撤出;社区参与的持久性更强,这是因为社区内部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性和凝聚力更加紧密。②社区参与和公众参与中常有强有力的组织,社会参与一般较少有系统的组织,通常是依照个体意愿的参与。③在以社区为单位的地理空间中,社会参与和公众参与可以涵盖进社区参与当中。
本文所说的社区参与,包含社会参与和公众参与。从《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社会参与的内容看,“社会”指多种社会力量,包括个人、企业、民间组织。
2.2 遗产实践中的社区参与
虽然理论界已认可社区参与遗产实践的作用,但在具体遗产实践中,遗产保护和利用一直都与“专家”有关,社会公众往往被排斥在遗产实践之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的社区参与差强人意[15]。或许正因如此,国内外许多遗产研究通过具体遗产实践案例来进一步探究社区参与遗产实践的意义,总结社区参与遗产实践的具体路径、经验和教训等,通过理论研究促进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利用的实际应用。遗产研究中认为,社区参与遗产实践有多种方式,比如作为观众收看遗产相关电视节目,接受遗产教育和提高遗产素养;作为旅游者到遗产地参观旅游,既能受到教育也是一种休闲消费;作为工作人员或非工作人员参加或组织社区内的遗产活动,如社区内考古遗址的挖掘、遗产博物馆和相关档案整理工作、遗产实践中政策发展和资源管理等[16]。可见,社区参与程度不一,参与方式、参与遗产实践阶段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在遗产本体价值保护的初期参与,有些是在遗产利用,尤其是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参与。总之,同一社区内,由于社区成员的共同利益、共同业及社区群体经历不断发生变化,社区内部成员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也是各取所需,有不同声音,也有不同利益诉求,社区参与呈现多样化[17-18]。
社区参与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top-down model或institution-led model)的模式,主要由政府机构主导。此种模式下,各种官方或者半官方的遗产组织成为社区参与的重要支撑,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在社区参与的大方向把握、领导人的选择及权力的施行上简单也富有成效[18];但是,社区参与在成效、与当地居民关联度,以及遗产实践可持续性、长期发展方面有局限性[19]。而且,很难把社区内每一种声音,每一个个体都纳入遗产实践话语体系中来。在既定目标达成后,社区参与的组织也随即解散。国际上大多社区参与都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由博物馆、官方组织或者半官方组织来进行组织,即使有社区居民、志愿者参与,然而参与流于表面,或是咨询性参与,或是在既有框架下的被动参与,而不是介入遗产保护的实际操作,与遗产保护主体不是平等合作的关系[20]。
相比之下,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bottom-up/grassroots model或community-driven model)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与社区居民关系的紧密度以及参与实践效果(如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改善环境,提高社会居民收入等[21])具有很大优势,尤其是博物馆、美术馆与当地社区团体合作,成效明显。但是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在前期组织和发展上、在相关政策实施上都比较复杂,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社区参与要达到理想效果,对组织社区参与的领导者的角色和功能要求相当高,他要具有多种专业技能和技巧,既能确保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的原真性,又能保证遗产项目能够顺利开展[22]。
国内外社区参与遗产实践,大都是自上而下模式,一些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政府或提供相关政策支持[23],或为相关民间组织提供部分资助[24-26]。虽然遗产叫作公共遗产(public heritage),在遗产实践中对历史、遗产的纪念碑价值和科学价值观的理解阐释,都是考古学家或其他遗产专家的“霸权式”话语,由于普通的社区居民缺乏遗产专门知识,缺少相关渠道,公众角色大都在整个遗产实践的末端,作为教育或信息的标准而存在,且常被排除在外。在整个遗产管理的过程中,公众的角色和功能并没有发挥作用,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参与度很低[15]。而且,社区内居民并非全是积极主动参与遗产实践,很多时候对政府主导形成依赖,除非公众认为遗产和他们的特殊利益、文化历史有直接关系,他们参与遗产实践的动机性才会非常强[27]。可以说,无论哪种模式,都是政府、民间组织、社区居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只不过在功能与角色上各有侧重。
社区参与遗产实践的作用在于:
(1)社区参与有助于人们了解其所在社区乃至国家历史文化的多样性。社区参与的主要领域是文化遗产管理和考古。在传统的考古学实践中,社区参与的水平随着考古学家和遗产组织许可度的扩大而增强,社区逐渐意识到过去历史留下的物质遗存的价值及复杂的身份认同和历史的关系。地方性知识和集体记忆与考古学和遗产专家的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遗产机构和社区从合作中获得收益。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理解遗产所在地方的历史文化多样性[28]。
(2)社区参与有助于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交流,消融矛盾,促进社会融合。遗产本身不可避免是政治的、具有竞争性,所以遗产实践过程中的冲突不可避免[29]。社区参与考古遗产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社区居民话语权,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和理解[30]。从物质性遗址点中获得对于过去历史的重新认知和解读,挑战了人们对于本地区既有的关于过去历史的认知,为当下人们对于历史的重新认知和身份认同建构提供重新商讨的空间[30]。这种对于物质文化的重新发现、文化遗址和景观地的解读和阐释,有助于社区居民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31],而且考古遗产可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能够从物质上证明社区与考古融合的一个过程[32]。
(3)社区参与有助于促进遗产认知多样性。公众对遗产的理解可能不同于专家、官方遗产实践者对遗产的理解。如公众更倾向于把遗产与信仰、价值观和共享的人生经验相结合,这与批判遗产研究中认为“所有的遗产都是无形的,文化意义才是遗产的本质”[33]的观点相同,可以与遗产的物质性、纪念碑性的理解互为补充和对话。
总之,遗产实践中政府和社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十分重要。其中,政府作为主导,有必要对社区参与在政策、遗产教育、资金上给予支持,这既有助于保证社区参与方向的正确性,也有助于社会共有共享遗产。一处遗产物质存在是否值得遗产保护,就要看他对国家、个人的关联性是否大,他的不可替代性和独特性在哪里。对于遗产管理者来说,要知道如何教育公众,对公众进行遗产教育,并且鼓励公众能够建立和遗产之间的个人联系,比如通过经历分享、故事讲述以及一些庆祝活动[2]。
政府的主导要具有开放性,接地气,能够把社区普通人的遗产认知融入到遗产实践。这需要社区居民积极主动,还需要遗产专家学者的桥梁作用。遗产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和实践,上联政府,下通社区,使遗产地所在社区居民有机会言说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过去,促进遗产理解和阐释多样性,实践中充分考虑社区居民有关想法,从而使公众的社区能够作为积极的遗产保护的贡献者而存在[2]。社区参与遗产实践有助于遗产的活化利用,使遗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种僵死的、只属于过去的历史,只是作为遗产旅游、博物馆消费。
3 我国遗产实践社区参与现状
我国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模式主要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意识到社会参与之于文化遗产实践的重要性,鼓励把文化遗产视作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明确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权利与义务。21世纪初,国家多次出台法律法规,强调社会参与遗产保护和共享保护成果,社会可以参与遗产保护对象认定、价值研究阐述、宣传、日常管理、监督和保护状况的检测、合理利用[34]。2018年10月,国家出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基本原则提出:要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坚持政府主导、多元投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但是,社会大众如何参与、从哪些方面参与,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操作指南。社会参与虽然是遗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具体遗产实践中可有可无;在具体遗产实践中,社会参与程度和范围有限[35];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大都依赖当地政府进行遗产实践;甚至社区参与被排除在一些遗产实践之外,社会公众无法享受遗产资源作为旅游开发带来的成果②如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实践中,当地政府通过拆迁方式获得遗产所有权。没有兑现给村民补偿金以及就业方面优先考虑的承诺,引起村民和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之间的矛盾。刘黎明.社区民众参与遗产地管理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7):61-64.。
我国社区参与遗产实践主要在遗产利用方面,尤其是遗产作为资源进行旅游产业开发以及遗产消费,在遗产治理方面参与相对较少,在遗产决策层面参与程度最小[36];同时,社会参与缺乏有效渠道和相应政策引导和法律法规保障[37]。国内社区参与遗产研究多以具体遗产实践为案例,或分析、总结遗产保护利用不同阶段的社区参与经验和教训;或探讨如何在法律制度建设上促进和保障社区参与遗产实践。
(1)在政府遗产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下,社区参与在具体遗产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许多研究以遗产实践案例为研究对象,指出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地方文化人士、遗产专家学者等全社会共同参与遗产保护的必要性,探索、研究和呈现我国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参与模式与具体实现路径[38-41]。
如袁奇峰、蔡天抒研究以广东民间文化保育组织作为政府和公众参与之间的第三方组织如何建构社区参与遗产实践网络,以及这个网络在推动历史文化保育实践中的影响力与局限性[37]。
喻涛以北京旧城保护为案例,分析总结以政府为主导,以NGO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遗产保护规划和设计中的经验[42]。
王美诗以南京博物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策展为例,呈现如何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构的非遗话语体系和我国传统文化语境对非遗项目的理解,打破由遗产专家为主导的策展传统,邀请非遗传承人和社区共同参与的新策展形式,使博物馆成为社区参与、非遗传承人的活态文化共同发挥作用和深度互动的文化传承空间[43]。
丁枫、阮仪三对扬州双东社区和浙江兰溪诸葛村的两个城乡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对比研究。前者是位于城市中的自上而下的社区参与模式;后者是在乡村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发现:①公众参与需要沟通和教育。公众需要了解一些专业知识,也是一个遗产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遗产专家的作用十分重要。②要有能够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人物。这里的人物应是公众组织的代表,具有公信力。③公众参与要能为公众带来切身利益。
(2)研究总结制定法律制度保障促进社区参与。遗产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规范标准制定有助于我国遗产保护[44],但是具体到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如马洪雨提出要构建保障公众知情权、受教育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法律制度,以确保公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45]。介绍地方已有的法律法规经验,如广东已出台法律条例社区参与遗产实践,包括在遗产教育、培训、基础研究方面有明确规定[36]。
国际学者研究社区参与角度与国内学者不同,更多关注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遗产实践的能动性。他们认为,社区虽然不是遗产实践主体,但并非被动接受政府主导,而是有选择性地发表意见,参与遗产保护利用不同阶段。主要表现在:①居民并不完全被动接受政府为主体的遗产实践及专家的意见和知识。如Oakes通过研究屯堡文化,发现村民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专家意见和知识,加上自己理解进一步强化,并在与专家和游客的交流中传播自身对遗产和屯堡文化的认知。面临政府为主导的遗产实践,居民将遗产所有权转让给政府,也是在自身利益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作出的主动性选择[46]。②社区居民参与遗产实践的阶段、程度多样化。如Su与Wall研究北京慕田峪村村民如何主动参与长城旅游开发并从中受益,得到当地政府和景区管理机构在政策和管理上的支持[35]。Chan研究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社区参与时发现,政府从宏观角度对梅家坞发展进行总体规划,但具体如何发展、怎样建设、如何进行旅游产业开发等,大多依靠村民自身的主动性和自发性[47]。Verdini等以江苏省双湾乡的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为例,认为社区参与虽然已经实施,但由于遗产经济话语占主导,社区参与缺乏有执行力的正式机制,加上社区组织松散,能否达到理想效果,还需长期观察[48]。
4 结束语
国内外社区参与遗产实践大都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遗产实践模式。此种模式下,政府的主导性地位和社区参与如何进行协调,允许社区参与到什么程度,参与遗产保护的哪些阶段等问题,都需要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效沟通与协商。
在每一处遗产保护和利用中,遗产本体、遗产所处历史环境及遗产地所在社区都存在着不同的情况,社区参与遗产实践呈现多样化态势,参与程度也因国家、地区、具体遗产实践而异。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遗产实践情况不同,更不能一概而论[49]。也正因此,在具体操作步骤上便很难对社区参与遗产实践进行整齐划一的设定。即便如此,各级政府仍可在制定社区参与政策、原则,以及相应法律法规上进行宏观引导、监督与规范,充分调动遗产保护利用的利益相关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实践中总结、积累经验和教训,促进地方经验交流等,以确保社区参与遗产保护能够取得积极、正向效果。
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和利用,有助于促进遗产活化利用方式多样化,使遗产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联系更加紧密,这有利于夯实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群众基础,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希望有更多学者和实践者关注这一领域,促进社会参与遗产实践,以缓和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精神需求,促进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