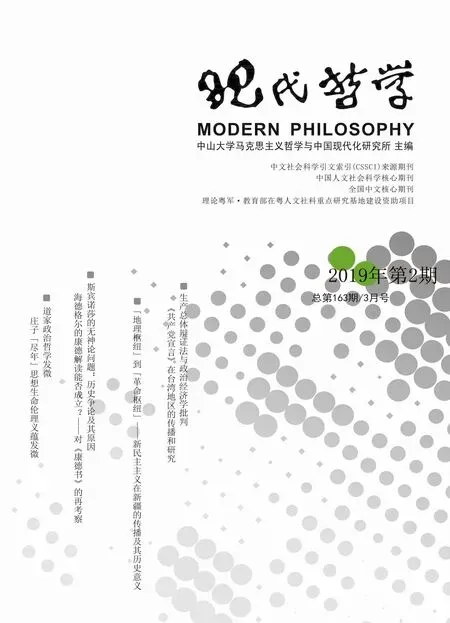庄子“尽年”思想生命伦理义蕴发微
2019-12-14罗祥相
罗祥相
当人碰到难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可否自主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非常难解的生命伦理难题,因其涉及对人生命所有权、自主权等不同的看法[注]关于自杀权利的争议,参考罗艳:《伦理视野下的自杀权》,《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60—66页。。对此,庄子“尽年”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人当自然地穷尽天赋之寿年,不中道轻生、弃生,明确反对人们自杀,实具有深刻的生命伦理思想意义。因此一思想在庄学中一直不受重视,故鲜有论者论及此一问题。本文拟揭橥庄子提出“尽年”思想的深刻缘由,以发微其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义蕴。
一、“尽年”之为生命在世伦理
《庄子》中多处论及人当“尽年”的思想。如《养生主》曰: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下引《庄》书皆只简标篇名)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在庄学史上常遭误解,笔者己作一辩证,故略而不论[注]参考罗祥相:《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思想新解》,《现代哲学》2016年第1期,第112—116页。。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此不仅主张身处乱世时,人当“缘督以为经”以保身、全身、养亲、尽年;而且将“尽年”与“养亲”这一在儒者看来身为人子必尽的义务并列而提,可知在庄子看来,“尽年”与“养亲”相似,同为人应尽的重要人生义务。
除“尽年”,《庄子》中还多次提到“终其天年”。如内篇: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人间世》)
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人间世》)
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师》)
《人间世》中,庄子以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因其能苦其生,楸、柏、桑等直木因具可用之材而恒被人斩用为例说明:在乱世中,人当如无材之散木以保身全生,努力“终其天年”,不中道夭于因材而取之祸患。同样,庄子对支离其形之妙用的赞赏,及其最后支离其德的主张,所为者乃“养身”与“终其天年”。《大宗师》中,庄子更是誉赞能恰知人之所为,“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为知之盛者,更可见其对“终其天年”的不舍追求。
外篇《山木》则直接载有庄子与弟子辩答何为“终其天年”之正道的故事: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木》)
由上可知,在乱世中,人当处材或不材之境地,以实现“终其天年”的人生目标,是庄子与弟子论辩之一大议题。同时,也反证《人间世》《大宗师》诸篇中反复申说的“终其天年”的思想,是庄子本人思想的直接反映。
常情而论,在一危惧的乱世中生存,人如不材之散木,以“无所可用”在世以“终其天年”应无大问题。然庄子故人家的两只鹅之遭遇:一只因有材能鸣,故在主人杀鹅享客时得保存性命;另一只因无材不能鸣,结果被杀为客人享;说明无论处材或不材之境地,均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患。故庄子弟子设问而难庄子,遇此两难之境地:“先生将何处?”庄子先以“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笑答,避免使自己陷入弟子设定的两难选择困境。但紧接着又以“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明确否定了先前给出的答案。
庄子指出,正确的做法是“乘道德而浮游”,即怀抱道德与时世变化相俯仰。庄子以“一龙一蛇”为喻,指出乘道德而浮游者,并不会让自己只依处于一种境地,只以一种处世原则专为;而是随时势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之方。然与时俱化,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丧失自己的道德原则。不仅“乘道德”说明在与世俯仰时,内心应始终怀抱道德,同时“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注]《礼记·礼运》“月以为量”,孔颖达疏曰:“量,犹分限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99页)。分限,即分判之度量、标准。成玄英疏曰:“言至人能随时上下,以和同为度量”([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69页)。也表明在随势上下时,应以与世相和作为自己的行事原则与度量。庄子指出,乘道德而浮游者能够“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能够优游于道,不为时势物势所物的人,自然不会让自己陷入前述的两难选择困境,为其所累。故《山木》中,庄子最终以“乘道德而浮游”的原则[注]张松辉曾认为,庄子在其“无用以保生”的原则受到了弟子的挑战后,“庄子不得不把自己的处世原则修正为‘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然这一原则更不安全……紧接着庄子提出‘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的主张”(氏著:《庄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将庄子最终的处世原则归为“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并不确当。因庄子最后提出的处世原则实为“乘道德而浮游”。若将之不当归为“一龙一蛇,与时俱化”,极易让人将庄子误解为乡愿主义者或滑头主义者。,教导弟子如何在混乱的时世中完成“终其天年”的人生责任。
此外,《天地》的“存形穷生”同样表达了人当“尽年”的思想: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天地》)
“穷生”,即穷尽天赋之生命,故“穷生”也即“尽年”。庄子以存形穷生,立德明道,为王者之大德,由此也可见庄子以“尽年”为人尽责修德之事业。
综合上述诸篇众多的“尽年”“终其天年”“穷生”等思想,可知庄子虽身处危险混乱的战国中期时代,却鲜明地提出了“尽年”的生命伦理原则:要求人们自然地穷尽天赋的寿年,不中道轻生、弃生;并认为“尽年”乃与“养亲”同等重要的人生责任。
二、“尽年”生命伦理的确立根据
身处困顿的生命境遇,遭遇难忍的劳苦悲忧等各种人生痛苦,为何人不能轻生、弃生以逃生之苦,还应努力地“尽年”?《应帝王》中,庄子曰: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应帝王》)
“尽其所受乎天”一句,在庄学史上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在庄子的生命哲学中,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它正解释了前述的问题:为何人应当“尽年”?因为“尽年”乃是在完成“尽其所受乎天”,这一在庄子看来每一个人都应尽的人生责任与义务。
“尽其所受乎天”,就其全部思想内涵来说,不仅包括“尽年”,即尽其天年,而且还包括“尽性”[注]易传《说卦》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向人们提出了“尽性”的要求。孟子亦有相似的“尽心”的主张。因孟子以心说性,心性一体,故其“尽心”也即“尽性”之义。可见,“尽性”乃先秦时思想家共倡的一种主张。,即尽其天性。因人之“所受乎天”者,不仅包括“天年”,还包括“天性”。在庄子看来,人不仅应当努力“保身、全身”以尽其天年,而且还应努力“致命尽情”,“达于情而遂于命”[注]《庄子》中,《天地》的“致命尽情”和《天运》的“达于情而遂于命”,即表达了庄子人应当“尽性”的思想。因“致命尽情”与“达于情而遂于命”二语中的情,乃性之义。《吕氏春秋˙上德》的“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顺情”,高诱注曰:“情,性也,顺其天性也”(见[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241页)。古代情、性互训。故“致命尽情”即“致命尽性”,“达于情而遂于命”即“达于性而遂至于命”。以尽其天性,如此才可谓完成“尽其所受乎天”的人生责任与义务。然问题的关键在:这一每一人都应尽的“尽其所受乎天”的人生责任与义务,是如何确立起来?
此问题关涉先秦时“天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先秦思想家普遍认为,人与天地间万物皆由天地阴阳二气和合而成,且皆由天地提供育养的环境与食物,故作为人与万物普遍意义上的化生者和育养者的天地,是人与万物之“父母”。如易传《说卦》曰: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周易·说卦》)
庄子亦曰: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达生》)
庄子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也是将天地视为人与万物普遍意义上的“父母”。《大宗师》的“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同样表达了天地乃人之“父母”的观念。因地乃阴之所聚,天乃阳之所汇,阴阳实为天地之异称。天地与阴阳非是异物,乃因异形、异态故而异名。
因天地乃人之“父母”,故每一个人皆禀受“天地之父母”之“命”而“生”。《左传》刘康公尝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左传·成公十三年》)
刘子以为,所谓“命”,乃人于天地之中禀受而来用以生存之物。即每一个人都是从“天地之父母”受“命”以“生”。每一个人只有从“天地之父母”禀“生”之“命”,如此才能在“生命”的基础上,展开各种“生”的实践活动,由此才有各种用以安定生命的礼义威仪之则。庄子与刘康公一样,也认为人皆从“天地之父母”受“命”以“生”。庄子曰:
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德充符》)[注]陈景元曰:“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见张君房本,旧阙”(氏著:《南华真经章句余事》,见《道藏》第1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05页)。可知此句原脱去七字,当从张君房本补。
松柏和尧舜皆是“受命于地”和“受命于天”。扩而言之,人与天地有“生”之物,皆是从“天地之父母”禀受“生”之“命”。
众所周知,若人从“上位者”,如君王或父母,禀受某一“命令”,那么此人对其“上位者”就负有完成这一“使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命令—使命”之间所存的内在伦理规定与要求。每一个人从有“生”开始,即从“天地之父母”禀受了“生”之“命”,故每一个人对赋予人以“生命”的“天地之父母”就负有完成“生”之“使命”的重要责任与义务。在庄子看来,“尽其所受乎天”即“天地之父母”赋予人的最为根本的“生”之“使命”。因这一人生根本“使命”的确立,乃奠立于人与“天地之父母”之间所存在的“命”之“赋予—禀受”的关系。自人从“天”之自然赋予中禀受其“命”开始生的那一刻起,就确立起了“尽其所受乎天”的根本责任与义务。故人只有在生命实践中“尽其所受乎天”,全尽自天所受的全部的事物——“天年”与“天性”,如此才算完成对“天”之所命授的根本责任与义务。
如果从父母和子女之间所存在的“孝”之伦理要求来说,因是“天地之父母”赋予人以“天性”和“天年”,故每一个人只有“尽其所受乎天”,才成其为听顺“天地之父母”的孝子;否则,就成为“天地之父母”的不孝子。在《大宗师》中,庄子就表达了人当听顺“天地之父母”之命的思想: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注]“父母于子”,宣颖曰:“倒装句法。言子于父母”(见[清]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子来,也就是庄子,在此提出,子女应听顺于父母的任何命令,无论是去东西南北,都应唯命之从。阴阳二气或天地与人之关系,无异于父母与子女之关系,故对“天地之父母”的任何命令,同样也应唯命之从。故当“天地之父母”命人“生”时,人应当听顺其命,“善吾生”;当“天地之父母”命人“死”时,人同样应听顺其命,“善吾死”。如果有人因“好生恶死”,只“善吾生”而不“善吾死”,则成为悍戾不顺“天地之父母”的不孝子。同理,如果“尽其所受乎天”是“天地之父母”赋予人的“天命”责任与义务,那么每一个人只有努力地“尽年”“尽性”,才成其为听顺“天地之父母”的孝子;否则,就成为捍抵不顺“天地之父母”的不孝子!
庄子在此把儒家的“孝”之伦理,由“人间之父母”推广到了“天地之父母”。不仅进一步拓展儒家“孝”之伦理的运用范围,还极大强化了“孝”之伦理对人的约束力。因“天地之父母”与“人间之父母”的不同之处在于:“天地之父母”是人与万物的“造化者”和“主宰者”,它掌管着天地间所有生命的存在权、所有权,以及这些生命存在的形式、样态、属性、特点等等。如果不听顺作为生命之“造化者”的“天地之父母”,则将会产生较之不听顺“人间之父母”更为严重的后果:天地自然将以主宰生命变化的形式,剥夺人之生命的有限使用权及全部存在权。
三、生命所有权视角下的“尽年”生命伦理
或有人以为,虽然是“天地之父母”赋予我生命,但在天赋予我生命后,生命的所有权就归我所有,故我有权自主处置自己的生命。故遭遇难忍的生命痛苦时,我有权选择轻生或弃生,不须完成所谓的“尽年”之责任与义务。然在庄子看来,“天地之父母”赋予人生命后,人只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的“生命使用权”,但并不因此而获得对自己生命的“根本所有权”。
庄子在《知北游》的“舜问乎丞”章中,就表达了对人之生命所有权的看法: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知北游》)[注]俞樾曰:“天地之委形,谓天地所付属之形也。下三委字并同”(见氏著:《诸子平议》,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65页)。孙子,当作子孙。王叔岷曰:“‘孙子’当作‘子孙’,成疏可证。《阙误》引张君房本亦作‘子孙’”(见氏著:《庄子校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15页)。
此章本是在讨论“道可得而有乎”的问题,但从中却可看出庄子对人的身体、生命、性命、子孙之所有权的根本看法。人若想得道,必须有用以得道的基础——人的身体。只有人从根本上据有了身体这一得道的基础,才可以通过修炼使自己获得“长生久视”等得道后的效果。然丞的“汝身非汝有”,却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得道进而有之的可能性。
为何说“汝身非汝有”?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之生命存在的基础——人的身体,乃由天地泄发阴阳二气,再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故本质而言,“身”只不过是天地之父母“暂时委付”给人使用的“人形”形体。当人的生命达到了它的寿限,人对身体这一“人形”形体的使用权也达到了它的最后期限,这时“天地之父母”就会将人之身体的使用权重新收归自己所有,将构生“人形”形体的基质重新转化为尘土,以塑造新的生命形式。因此,人的生命是一有“死”的存在物这一根本事实表明,人从未拥有过人之身体的“根本所有权”,人所拥有的只不是对自己身体这一“人形”形体的“有限使用权”。
庄子说,不仅人的身体,只是“天地之父母”暂时委付给你使用的“人形”形体;而且人的生命,也只不过是“天地之父母”暂时委付给你的一团“和气”;人的性命,也只是“天地之父母”暂时委付于你身体内部的理则;子孙后代,也只不过是“天地之父母”暂时委付给你的用以蜕化之物。因此,无论是人的身体、生命、性命,还是子孙,本质上都是天地之间强阳自动的元气,哪里可以让人执留而加以根本占有?
故从“天地之委”的角度而言,人只不过是借“天地之强阳气”来构生自己的生命存在。从所有权来说,“天地之强阳气”属天地所有,或从根本上属道所有。作为“天地之强阳气”之聚合体的人,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对它的所有权。故在此意义上,人之“生”实为“借物”而生,即借“天地之强阳气”而生。“借物”之行为所存在的伦理要求是:人对所借之物,必须珍惜之,爱护之,不敢将之有所毁伤,胡乱丢弃的行为更是绝对不允许;在使用完所借之物后,若原先委付给你使用的物之主人,要收回其所借之物时,人不能加以拒绝。
因此,如果从庄子的思想视角出发,就会发现前述认为“天”在赋予人以生命后,人之生命的所有权就归人所有,人有权自主处置自己生命的观点,其实是未达生命存在的本质真相,不知人之身体所有权的真正拥有者,认自己所有的有限的“身体使用权”为根本的“身体所有权”。其仅凭自己的意志就处置自己生命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僭越”自己权限的行为。因为如果人的生命并不归自己所有,乃归天道自然根本所有,那么人就无权仅凭自己的意志就此处置自己的生命;只有真正拥有它的根本所有权的天道自然,才拥有它的最终处置权限。人作为一个“借物而生者”,其实是必须对自己所借以生的身体,珍惜之,爱护之,不敢将之有丝毫的毁伤,更不敢将之胡乱的丢弃;等到天道自然赋予人身体使用权的最后期限时,将之完好无损地返还给天地,如此才算完成自己对天道自然所负有的根本人生责任与义务。
四、结 语
若将庄子“尽年”的生命伦理,与《孝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章》)的“孝”之伦理进行比较可知,庄子与孔子虽然出于不同的理由,提出了两种看似不同的伦理主张,却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孔子乃基于人之身体或生命的所有权,不归自己所有,而归父母所有,故要求人们不将受之于父母的身体发肤,有任何毁伤;庄子则是基于人之身体或生命的所有权,不归自己所有,乃归天道自然根本所有,人应“尽其所受乎天”,故要求人们自然地穷尽天所赋予人之生命寿年。两位先哲据以提出自己生命伦理主张的理由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要求人们珍爱、保护自己的身体,不随意地毁伤作为人之生命存在基础的身体,都反对人们随意仅凭自己的意志就处置自己生命的行为。
在当下因遭遇各种心理危机而自杀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庄子提出的“尽年”生命伦理,基于天赋我命,我负天责,即完成“尽其所受乎天”的人生根本责任,这对反对自杀及解决生命所有权争议等伦理难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现代价值,其丰富而深刻生命伦理思想义蕴值得进一步发掘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