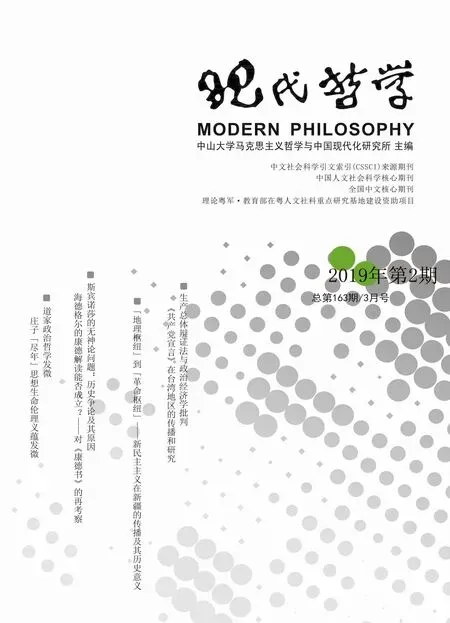海德格尔的康德解读能否成立?
——对《康德书》的再考察
2019-12-14江午奇李章印
江午奇 李章印
海德格尔《康德书》[注]这里的《康德书》是指《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主旨就在于,不是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纯批》)视为一部认识论著作,而是解释为一部为形而上学奠基的著作。对《康德书》的评价不仅事关海德格尔的康德解读,而且也涉及对《存在与时间》主导思想的评价,甚至还关联着如何看待康德哲学本身的问题。但在如何评价这部著作的问题上,至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早在达沃斯论坛上,卡西尔就已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提出反对意见。在《康德书》出版后,卡西尔又进一步撰写“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一文,更为系统地反驳海德格尔。[注]差不多同时,提出异议的还有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不过这些异议当时并没有公开。据Richard E. PalmerI说,胡塞尔于1929年夏天收到海德格尔寄来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并在页边写下了大量评注,这些手稿以及其它的研究成果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末被范·布雷达神父从德国带出,后保存在比利时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直到1994年在《胡塞尔研究》上发表。Richard E. PalmerI从胡塞尔的评论中提炼出六个主题,具体内容参见Richard E. PalmerI, “Husserl’s Debate with Heidegger in the Margins of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in Man and World, Vol.30 , 1997, pp. 5-28.此后,虽然也有肯定性的评价,但否定性的态度更占上风。而且在反对声音中,卡西尔的观点一直颇受重视,乃至被视为维护康德思想之正统的代表。卡西尔所认为的《康德书》的主要问题就是,“强迫作者说出某种他未曾说出的东西”[注][德]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海德格尔所谓的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也就失去其正当性。但问题也许并非如此简单。下面,我们将围绕海德格尔康德解读中三个争议较大的主题来对《康德书》进行再考察,并以此澄清康德是否为形而上学奠基以及海德格尔解读能否成立的问题。
一、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
在海德格尔把康德《纯批》解释为“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做法中,首先引起争议的是,把超越论想象力阐释为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卡西尔说:“康德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持有这种关于想象力的一元论,他坚持一种明确而彻底的二元论,坚持关于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二元论。”[注][德]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孙冠臣也认为,海德格尔在把超越论想象力阐释为感性和知性之根源的证明方面并没有成功,“虽然海德格尔在解释康德的过程中,正确地坚持了知识的条件必须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性,主张通过先验想象力把我们所有的认识功能联结起来,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想象力就是我们诸功能的共同根源。”[注]孙冠臣:《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那么,海德格尔是否意图发展“关于想象力的一元论”?“共同根源”又是何意?是海德格尔误解了康德,还是海德格尔被误解了?
实际上,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中并没有任何发展“想象力的一元论”的意图,“对于这种向着超越的本质源头的回溯来说,再没有什么是比对从想象力生出的灵魂的其他能力进行一元论的经验的说明更为不相干的事情了,”[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相反,回溯到作为感性与知性之根的超越论想象力,这说的只有一个意思:着眼于在奠基性的发问中所获得的超越论想象力的本质结构,不断地将超越的法相向着它的可能性的根据去重新筹划。奠立根据的回溯活动在‘可能性’的,即可能的使之可能〈mögliche Ermöglichungen〉的维度里进行。”[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显然,在海德格尔这里,所谓“共同根源”,并不是在“生产”意义上说的,而是指超越论想象力使感性和知性的运用成为可能。
我们首先看看超越论想象力何以使感性得以可能。海德格尔从感性的先天形式、即纯粹直观的本质特征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作为纯粹直观的时间和空间是“源生性的”,而“‘源生性的’这个术语源于‘intuitus originatius’〈源发性直观〉中的‘originatius’,它的意思是说:让……生发”[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即让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在我们之中以形象的方式给出外观(图像)。在此外观给出之先,有一种纯粹直观自身的源初“成一活动”,这种“成一活动”被康德称之为“综观”〈Synopsis〉(这种作用不是由知性带来的)[注]有关“成一活动”和“综观”的讨论,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4—135页。。纯粹直观貌似是纯粹接受性的,而综观却携带一种主动能力。这种主动力并不是由知性带来的,而是源于超越论想象力,构成纯粹直观之本质的这种综观“只有在超越论想象力中才是可能的”[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康德在《纯批》中说过感官或直观的作用是“对杂多的先天概观”[注]“概观”与“综观”的德文是同一个词“Synopsis”,邓晓芒教授译为“概观”,王庆节教授译为“综观”。此处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94。,在《康德手稿遗稿》中又进一步说“空间和时间就是在直观中的前象〈Vorbildung〉的形式”[注]转引自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前象”就是一种带有“综”之特质的形象活动。由于形象活动只有通过想象力才得以可能,所以综观必定是以想象力为先决条件的。故而,纯粹直观作为“前象”的形式,必定也是以想象力为其可能性条件的。由此,通过想象力,纯粹直观就不仅具有接受性,而且还具有自发性特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纯粹直观,究其本质的根基而言,也就是纯粹想象。”[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接下来看看超越论想象力何以使知性得以可能。海德格尔从知性的功用特质出发来阐释这一问题。在康德那里,知性是对感性杂多进行“规则的能力”[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126。,而这种规则能力就意味着:在我们对杂多综合之先,就有所表像地保持在某种统一性之中。[注]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因为对杂多的统一作用是通过范畴施行的,而范畴之施加到感性杂多之上又须通过纯粹统觉,这样,纯粹统觉在施行综合统一活动时就总是有一个先行的自发性“动作”,即先行把范畴带出来,然后再施加到感性杂多之上。进一步地说,纯粹统觉的这种自发的“先行”活动,意谓着某种表像活动,海德格尔称为“对统一性境域有所表像的前象活动〈Vorbilden〉”[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而纯粹统觉先行将范畴自发地形象出来,这又意味着知性范畴的图式化。由于“前象”作为一种形象活动,只有通过想象力才是可能的,故而这种图式化在根本上乃纯粹统觉借助于想象力而达成的。这样,纯粹统觉的综合统一活动,作为自发的、形象着的表像活动,首先就是超越论想象力的一种基本活动。不仅如此,知性作为规则能力还有接受性特质。因为统觉的表像活动不仅自发地将范畴形象出来,而且在将范畴形象出来进行规整活动时,规整活动是作为某种进行联结的东西在知性自身中进行的。也就是说,统觉“以某种领受活动的方式来进行表像”[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这种“领受”“必须源出于超越论的想象力”[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只有想象力才兼具自发性和接受性。
上述阐释表明,在纯粹直观和纯粹统觉的运用之先,都有“前象”这一环节。借助于这一形象活动,感性才对对象性的东西有其直观,知性才把范畴运用于感性杂多之上。这样,从直观和统觉的运用都离不开“前象”这一形象活动来说,超越论想象力使感性和知性得以可能的问题似乎就解决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第一版演绎中,康德将想象力与感性、统觉视为并列的三种源初知识能力,但在第二版演绎中,他把想象力仅仅解释为受先验统觉支配的、在感性和知性之间起“亲和”作用的中介。海德格尔指责说:“康德现在要把‘灵魂的功能’写为‘知性的功能’,这样,纯粹综合就被归附给了纯粹知性。超越论的想象力作为特殊的能力就变成可以舍弃掉的,而这样的话,那种恰恰是超越论想象力可能作为存在论知识的本质根据的可能性似乎就被腰斩掉了”[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在第二版中,超越论想象力只是名义上出现而已”[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对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这种指责,卡西尔也同样持反对态度。卡西尔的理由是,“康德对加尔伏关于 《纯粹理性批判 》 的评论的考虑,迫使他重新改写了该著作的第一版,他试图非常清晰而严格地将他的先验观念论与心理学的观念论区别开来。出于这个顾虑,康德不得不移动‘先验分析论’ 的重心……”[注]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
但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改写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心理学质疑,而在于超越论想象力威胁到了理性的地位,而且这种“改写”在维护理性至高地位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难题,使得感性和知性之统一的可能性成了问题。如果坚持先验统觉的统治地位,而它作为知性又与感性相互独立,且想象力又变成了某种从属知性的能力,那如何来说明知性范畴对感性之运用?其结果只能是知性通过从属于其自身的想象力来对感性施加综合作用。如果这样,知性似乎就直接应用于感性了,这与康德关于知性和感性相互独立的思想是不相容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坚持第一版演绎,即坚持把想象力作为与感性和统觉一样源初的知识能力,那么感性和知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在康德那里,直观不能思维,思维也不能直观,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使思维的概念成为感性的(即把直观中的对象加给概念)”[注]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51/B75。,另一是“使对象的直观适于理解(即把它们置于概念之下)”[注]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51/B75。。前者指的是赋予思维以直观(接受性)的特质,后者指的是赋予直观以思维(自发性)的特质。这两个条件表明,经验知识的形成要求二者的“融合”,而这只有通过超越论想象力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超越论想象力才兼具接受性和自发性两种特质。进一步地说,超越论想象力不仅是一种“中介”,它更是一种奠基性的力量。作为这样一种力量,在我们每一经验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它总是率先行动起来,以便使得感性和知性能够源发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越论想象力才被海德格尔解释为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
最后,海德格尔在《纯批》第一版演绎的基础上所表明的超越论想象力使感性和知性得以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根本不是什么“一元论”。“一元论”意味着某个根本性的东西是惟一的,其他东西都从这个根本性的东西里衍生出来。但在海德格尔这里,直观、统觉与想象力作为心灵的基本知识能力,早已经作为“潜能”内在于我们之中,超越论想象力并没有取代感性和知性而成为心灵的唯一能力。海德格尔只是认为,在这些基本知识能力的实际运用方面,想象力具有奠基性、优先性。它作为一种奠基性的力量,先行将潜在于我们的先天能力(感性和知性)源发出来而成为“现实”。海德格尔只是意识到,在康德那里,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不同知识能力之间的关系是成问题的,超越论想象力是他提出的一种调和性的解决方案。对此,王庆节教授也认为,超越论想象力作为“使……成为可能”的能力,是一种“‘奠基性的’力量或力道”[注]王庆节:《“先验想象力”抑或“超越论形象力”——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的解释与批判》,《现代哲学》2016年第4期。,而且“如果‘先验想象力’或‘超越论想象力’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就是人类知识力批判中所起的不仅仅是‘中介性的’、‘亲和性的’第三种能力的作用,而且更是更源初的‘奠基’作用、‘根柢’作用,所谓康德第一版中关于认知的‘二元枝干说’与灵魂的‘三分说’之间的表面不一致和对立就可能得到化解。”[注]王庆节:《“先验想象力”抑或“超越论形象力”——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的解释与批判》,《现代哲学》2016年第4期。由此,那种“想象力一元论”的指责就是站不住脚的。
二、源生性时间作为超越论想象力的渊源
虽说排除了对“共同根源”的误解,但海德格尔的解释还面临一个问题,即超越论想象力将感性和知性源发出来的那种“力道”来自何处?这一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前面的那种“化解”就依然是成问题的。海德格尔也意识到这种不充分性,“当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感性和知性的根源,这才第一次呈现出更为源初的阐释。在这里,这个结论还不起什么作用。”[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那么,如何给予“共同根源”以更充分的说明?海德格尔将目光投向了时间。他说:“相反,对综合之三种模式的内在时间特质所做的发掘工作,应当会对将超越论想象力……解释为两大枝干之根给出最终的和决定性的证明。”[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要从时间这里寻找超越论想象力借以把感性和知性源发出来的“力道”,就必须思考超越论想象力与时间的关系,就必须挖掘超越论想象力的时间特质。在康德那里,时间作为感性的纯粹直观形式,与想象力、统觉是并列的基本能力,康德似乎没有说过想象力具有时间特质之类的话。但康德说过,“我们的表象……都受到时间的支配”[注]转引自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亦可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98-99。,亦即我们的一切经验性的知识都要服从内感官的形式条件,即时间。这就意味着,直观中统握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和概念中认知的综合这三种综合,作为使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综合活动,必然要服从这一时间形式。又由于感性和知性最初层次的运用(前象)都是通过超越论想象力才有其可能的,三种综合活动都必须以超越论想象力为先决条件,所以,作为综合活动之形式条件的时间也就与超越论想象力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更为具体地窥见想象力的时间特质,我们需要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三种综合活动。
首先,纯粹直观的综合形象地关涉“当前”,直观中统握的综合使“当前”刺激我们感官的存在物之形象得以可能。由于“……在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对这杂多进行综合的能动的能力,我们把它称之为想象力,而想象力的直接施加在知觉上的行动我称之为领会”[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120。引文中“领会”的德文词是Apprehension,王庆节译为“统握”。 基于《康德书》的独特性,我们在文章中独立使用时采用王庆节教授译法。,所以,“在统握模式中的综合”就是“源生于想象力”的[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既然直观中统握的综合源生于想象力,那“当前”也必定是从超越论想象力这里获得其可能性的。
其次,再生的综合实即纯粹想象力的综合。康德说:“想象力是把一个对象甚至当它不在场时也在直观中表象出来的能力。”[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B 152。这意味着想象力是使“过去”之事物得以可能的条件,进而是使“过去”本身形象出来的条件。又由于“过去”实质上仍是“直观中统握的综合”的“当前”,再生的综合乃是对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当前”的二次形象,所以,再生的综合乃是“曾在”和“当前”的统一。[注]相关的讨论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最后,“如果一切表象,还有思维都应当听命于时间,那么,综合的第三种模式就必然‘形象’为将来。”[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康德认为,在三个综合过程中所思考的东西必须保持为同一个东西,“假如不意识到我们在思的东西恰好正是我们在前一瞬间所思的东西,那么一切在表象系列中的再生就都会是白费力气了。”[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103。康德的先验演绎又表明,在三个综合过程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某个持驻为一的意识或“我思”,“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识,把杂多逐步地,先是把直观到的东西,然后也把再生出来的东西,都结合在一个表象中”[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103。,而这又意味着“概念中认知的综合”在三种综合中占据首要的地位,因为那个“综合统一的意识”之综合,“它是导引着先前已经标画过的两种综合的首要的综合。它仿佛领先于后两者。”[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也就是说,这个意识在“直观的综合”时就已瞄准“直观”了,而它的目标是要在“认知的综合”中达到“概念”。因而在它这里存在某种先行的展望,即一种“将来的源初性形象活动”[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由此,第三种综合也具有时间特质,而且是以“将来”的模式体现出来的。
由于三个综合过程都具有时间特质,而此特质又是通过超越论想象力才形象出来的,故而超越论想象力本身就具有时间特质。进一步地说:“如果超越论想象力——作为纯粹形象的能力——本身形象为时间,即让时间得以源生出来的话,那么……超越论的想象力就是源生性的时间。”[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通过分析超越论想象力的时间特质,海德格尔进而把超越论想象力视为源生性的时间,这一点特别需要注意。在康德那里,作为先天直观形式而使对感性杂多的感受得以可能的时间、使杂多得以规整或序列化的时间以及三种综合的时间特质等都是序列意义上的,而超越论想象力则不同,它是使序列时间形式得以可能的知识能力,与三重综合之序列意义上的时间特质不同,其时间特质不是序列意义上的,而是更为源初的。
通过阐明超越论想象力的内在时间特质,海德格尔把一切知识能力都回溯到了源生性的时间这里。在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学者看来,这种做法正属于那种强迫康德说其未曾说过的话。卡西尔说,“如果海德格尔所说的解释要强迫作者说出某种他未曾说出的东西,而他之所以没有说,是因为他没能想到,那么,这样的解释难道不会沦为任意性吗?”[注][德]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确实,康德从未说过想象力具有内时间特质,但问题并不在于康德是否说过相关的话,而在于《纯批》是否蕴含了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东西。从前面的讨论来看,海德格尔的解释是以《纯批》为基础的,他是依循康德既有的东西而挖掘想象力的时间特质的。这就说明,海德格尔的解释不仅在康德那里是有根据的,而且也契合《纯批》本身的内在逻辑。对于海德格尔的前述解释,即便对《康德书》充满质疑的胡塞尔也没有在其“页边评论”中发表任何意见,Richard E. PalmerI也说,“我们在这两部分中没有看到胡塞尔有任何标记”[注]Richard E. PalmerI, “Husserl’s Debate with Heidegger in the Margins of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in Man and World, Vol.30,1997, pp. 20-21.。在我们看来,胡塞尔之所以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恰恰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解释有理有据。
但问题并未因此而完结,因为超越论想象力的内时间特质是海德格尔基于三种综合之时间特质与超越论想象力之关系而推论出来的,其真正的来源还模糊不清。而且,海德格尔也只是在超越论想象力使序列意义上的时间得以形象出来的意义上,认为“超越论想象力就是源生性时间”。那么,二者是否同一个东西?源生性时间何以是源生性的?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澄清思维或纯粹理性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海德格尔在讨论概念中认知的综合之时间特质时被搁置的一个问题。卡西尔的支持者海茵·布尔迪尼森也对此提出过质疑,即“康德不允许在‘我思’中、尤其是在一般理性中具有任何时间关系。”[注]Hein Berdinesen,“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Fundamental Ontology”, in Transcendentalism Overturned, eds. Anna-Teresa Tymieniecka, Analecta Husserliana (The Year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 108,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 51.所以,如果这一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海德格尔前面一系列阐释就都是不牢固的。
在《纯批》“概念分析论”第一章第三节的“纯粹的知性概念,或范畴”部分,海德格尔找到了解答上述疑难的“钥匙”。在那里,康德指出,时间和空间“任何时候也必定会刺激起对象的概念”[注]“任何时候也必然会刺激”中“刺激”一词的德文是“affizieren”,王庆节教授翻译为“激发”,邓晓芒教授译为“刺激”。此处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A 77/B 102。。海德格尔就此追问道:“时间激发一个概念,更确切地说,激发对象之表像活动的概念说的是什么意思?”[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按照他的解释,这个“时间激发”指的是“让对象化”,即时间自身激发着,以便让对象在时间中作为某种存在物来呈报。而且,在这种让对象在自身激发着的时间中呈报自身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一个统一的意识(纯粹统觉或我思)。这就意味着时间“隶属于有限主体的本质存在”[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因而“时间作为纯粹的自身感触就形象为主体性的本质存在结构”[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也就是说,时间与那个“统一的意识”是共属一体的。关于这种共属的自身激发,《纯批》自身也可以提供支持:“凡是能够在一切有所思维的行动之前作为表象而先行的东西就是直观……它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内心通过自己的活动、即通过其表象的这一置入、因而通过自身而被刺激起来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某种按其形式而言的内感官。”[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B 67-68。可见,时间作为内感官的形式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心”、即“自我”本身来获得那种“激发”。这样,“内心”或“自我”与时间就不是互不相容的东西。相反,它们共属一体。也即是说,“自我”具有时间特质。海德格尔进一步说:“凡是在康德振振有词地否认纯粹理性以及纯粹统觉的自我具有时间特质的地方,他都只不过是说,理性所听命的‘不是时间的形式’。”[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也就是说,正因为自我或纯粹统觉乃是时间自身,所以纯粹理性才不被作为时间内的东西来把捉。“自我”或纯粹统觉并不在序列意义上的时间中,也不是在时间之外的某种实体性的东西。对于纯粹统觉的这种时间特质,胡塞尔在对《康德书》的“页边评论”中也给予了肯定,他说:“一个内在的时间视野是必要的”[注]转引自 Richard E. PalmerI, “Husserl’s Debate with Heidegger in the Margins of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in Man and World, Vol. 30, 1997, p.22.。
实际上,不仅源生性时间与纯粹统觉或自我具有共属性,超越论想象力亦然。因为上文提到的“让对象化”实质上说的乃是让对象形象出来,即让形象化,而形象活动只能源出于超越论想象力,这就说明,在时间性自我的自身激发中蕴含着超越论想象力的形象活动。这样一来,不仅后者的时间特质源于前者,而且超越论想象力与源生性时间、纯粹统觉是共属一体的。这里的“共属”并不是指三个物件并列共存于某一统一体之中,而是指它们作为“潜能”构成心灵的本质结构。不过,就它们源发出来成为“现实”来说,源生性时间的激发活动具有优先性,即激发的原动力来源于源生性时间,而它所触发的活动首先表现为超越论想象力的形象活动。如此,超越论想象力将感性和知性源发出来的那种“力道”就来源于源生性时间的自身激发,存在论知识在根基上也统一于源生性时间,感性对杂多的直观和纯粹统觉对感性杂多的综合也都是在这种激发的力道中展开的。这样,超越论想象力之时间特质、存在论知识的本质统一性以及超越论想象力与源生性时间的关系问题就得到了根本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康德把“时间”视为先天知识能力,虽然他也探讨了时间与想象力、统觉的关系,并且也提到了时间的“激发”特征,但他并没有在这些方面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并没有发现在时间与想象力的关系中所蕴含的想象力的时间特质,并没有发现在时间的“激发”特征中所蕴含的源生性特质,他的“时间”主要是在序列意义上被讨论的。而海德格尔则发现了蕴含在康德时间学说中的这些未经言明的东西,并将之与超越论想象力和纯粹统觉(我思)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发掘出它们在根基上的本质统一性。时间之所以是源生性的,关键就在于它的这种自身激发本身乃是内心或自我的活动,“时间并不是作为这样的形象物〈Gebilde〉,而是作为纯粹的自我感触,才成为超越的更为源初的根据。”[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而超越论想象力之所以具有时间特质、之所以能够将序列意义上的时间形象出来,其根源也在于时间的自身激发。这表明,源生性时间的根就在《纯批》中。
因此,在解读康德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并不是把《存在与时间》中的东西强加给康德。超越论想象力、纯粹统觉与源生性时间的共属性关系以及后者在三者中的核心地位,作为涉及存在论知识之可能性的心灵之元结构的形而上学问题,对于康德来说,诚然有些陌生,但也并不意味着是强加给康德的。在直观、统觉和想象力的关系问题上,康德本身就持某种摇摆不定或不甚清晰的立场,因而给不同的解读留下相应的可能性。康德1772年2月21日写给马库斯·赫兹(Marcus Herz)的信也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在信中说,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即“那种在我们之中被我们称为‘表象’的东西与对象的关系的根据是什么?”[注]转引自Camilla Serck-Hanssen, “Towards Fundamental Ontology: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Reading of Kant”, in Cont Philos Rev, Vol.48, 2015, p. 220.,而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是打开“迄今为止仍旧晦暗不明的形而上学的整个秘密的钥匙”[注]转引自Camilla Serck-Hanssen, “Towards Fundamental Ontology: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Reading of Kant”, in Cont Philos Rev, Vol.48, 2015, p. 220.。如果康德在这里所说的“根据”指的是那些作为经验知识之可能性条件的先天知识能力,那么在这些“能力”身上就必定承载着某种形而上学的使命,如此也就可以说《纯批》乃一部为探索形而上学的秘密而奠基的著作。卡米拉·希尔克汉森(Camilla Serck-Hanssen)就认为,这与《纯批》要解决的先验的综合统一的可能性问题是一回事。[注]参见Camilla Serck-Hanssen, “Towards Fundamental Ontology: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Reading of Kant”, in Cont Philos Rev, Vol.48,2015, p. 220.另外,威廉·巴尔特(William Barrett)也对海德格尔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他认为,海德格尔的解释就是与过去思想家的对话过程,“也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一股思想之涌流从已逝去的哲学家那里释放出来,在当下重新变得至关重要。那些已逝去的思想家所努力着想要说的东西,那些他仅仅是犹豫不决地或不完善地、甚至是无意识地说过的东西,作为今天仍困扰我们且与我们相关的问题而鲜活起来。”[注]此处引用来自威廉·巴尔特为Charles M. Sherover《海德格尔,康德与时间》一书所作的导言。参见Charles M. Sherover, Heidegger Kant and Time, Bl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X .
三、将“理性的有限性”凸显为“人的有限性”
把一切知识能力都回溯到超越论想象力,进而又把源生性的时间阐释为超越论想象力之渊源,其结果就是,纯粹理性被解读为与源生性时间共属。这种“共属”不仅意味着“它们共同隶属在同一个本质存在的统一性中”[注]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而且还说明源生性时间构成纯粹理性的本质结构,后者的一切活动都以前者为条件。这就意味着,纯粹理性的这种本质同时也是它自身的限制。正是由于这种“共同隶属在同一个本质存在的统一性中”的限制性关系,才“使得人的主体性的有限性在整体上得以可能”[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理性的有限性被进一步凸显为人的有限性。
对此,卡西尔同样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理性的实践应用表明,自由的理念可以帮助超越感性和时间的限制,因为“‘目的王国’不再从属于这种想象力的法则,它不需要图型化 ”[注]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卡西尔的这种立场在后来尤其得到海茵·布尔迪尼森(Hein Berdinesen )的支持:“如同卡西尔在达沃斯所指出的,图式化不能运用到伦理学,康德是特别清楚的。”[注]Hein Berdinesen,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Fundamental Ontology”, in Transcendentalism Overturned,eds. Anna-Teresa Tymieniecka, Analecta Husserliana (The Year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108,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 52.“如果我们要解决康德从直观和知性的分析转进到先验辩证论的分析、以及更进一步地转移到实践理性的问题,那么海德格尔的解释以及对图型法的利用就会变得尤其充满困难。”[注]Hein Berdinesen,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Fundamental Ontology”, in Transcendentalism Overturned,eds. Anna-Teresa Tymieniecka, Analecta Husserliana (The Year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108,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 51.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想要表明,理论理性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实践理性的有限性,进而不意味着人的有限性。
从卡西尔、布尔迪尼森等人的反驳来看,他们显然误以为海德格尔要把图式化运用于实践领域。事实上,海德格尔很清楚,图式化乃衍生于源生性时间的时间图型,它仅仅适用于理论理性领域,而不能与实践领域发生关联。因而,他在《康德书》第30节“超越论想象力与实践理性”中所作的解释,实质上是以源生性时间为根据的,而非时间图型。在那里,他诉诸于“尊重”的“情感”来进行阐明。在康德那里,“尊重”是对道德律令的尊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注]参阅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77—97页。。在海德格尔看来,“尊重”作为一种对道德律的尊重之情感,是一种“感触”,其激发之力来自主体自身。也就是说,“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来自主体自身。一方面,出自于对道德命令的尊重,出自于对我自己的人格的尊重(把自己当作目的而非手段),我把我自己从这种情感的激发中公开出来(纯粹的自发性)。另一方面,对道德命令的尊重,在本质上乃是对我自己的纯粹理性的听命(纯粹的接受性)。在这个意义上,“尊重”就意味着接受着的自发性或自发的接受性。但这两种特质的结合只有通过超越论想象力才可能,也就是说,前述“情感”的自行“感触”与对纯粹理性的“听命”,在我们之中是源初地同根的。由于超越论想象力基于时间的自身激发,故而这种源初的“根”的源发力量,只能源出于激发着的源生性时间。而且,康德也曾明确,在我们之中只有一个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只是就其应用领域的不同而做的区分。因此,如果自身激发的源生性时间构成纯粹理性的本质结构的话,那么它必定也适用于实践理性。也就是说,源生性时间与纯粹理性的那种限制性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实践领域。
在卡西尔看来,海德格尔从“尊重”的“情感”来挖掘实践理性的超越论想象力根源是成问题的。因为,虽然康德确实从实践理性的动力方面谈到了“尊重”,但是这种尊重感是属于心理学的东西、属于伦理学的应用部分,而非从属于伦理问题的基础领域。而且,《实践理性批判》是对理性的考察,而非对人格、人性的人类学考察。在他看来,海德格尔诉诸于“尊重”、“人格”来阐明实践理性的超越论想象力根源,混淆了科学的界限。[注]参见[德]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他认为,“自由理念”才是构成伦理学的基础性的东西。
在我们看来,尊重感确实指向伦理的实践应用,但是尊重感本身并不从属于伦理学的应用领域。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尊重感意味着一种更源初的力量。既然康德从实践理性的动力方面来讨论“尊重”,那就说明“尊重”相对于实践理性的实际应用来说具有优先性和奠基性,因为在我们自身之中,尊重感作为一种自身激发着的行为,是使作为“潜能”的纯粹实践理性得以源发出来而成为“现实”的条件。因而,它是超越于实践理性的实际应用的。这就说明,尊重感并不是什么心理学的东西,而是道德主体自身颁布道德命令的可能性条件,它比一般心理学的尊重更为源初。设若没有这种道德情感的自身激发,又如何来说明道德主体之行为的实践动力?卡西尔只是从超越感性时间的“自由理念”、从科学的划界来反对海德格尔的解读,但对于“自由理念”如何给实践理性以动力,却不能给出合理的说明。[注]参见[德]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
关于“自由理念”,海德格尔也这样回应过,“自由的实践上的实在性。这种智性的东西恰恰在理论上无法把捉。”[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90页。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自由理念”之所以是“理念”,乃是因为它仅仅是作为调节性的东西而设置的,它的实在性并没有被真正把捉。而且,康德也这样说过:“意志尽可以是自由的,但这却只能与我们意愿的理知原因有关。因为,凡是涉及到意志所表现出来的现相,即行动,那么我们就必须按照一条不可违反的基本准则……永远如同对其他一切自然现象那样亦即按照自然的永恒的规律来解释这些行动。”[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 798/B 826。如果意志的自由并不能保证由它所表现出来的行动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不是可疑的吗?用它来反对人的有限性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且,“自由”在康德这里的这种窘境恰恰说明了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在康德那里,科学的划界仅仅是一种基于理性应用领域的不同而作的区分。实质上,知识论、伦理学与人类学不仅统一于先验哲学体系,而且在根本上统一于“人”本身。康德在《逻辑学讲义》中提出的四个问题正好能说明这一点。这四个问题是:“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4.人是什么?”[注]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玲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页。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四个问题恰恰表明,在康德那里,知识论、伦理学与人类学之间有某种必然的统一性关联,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人”本身也有着某种根本的统一性关联。他就此追问道:“为什么这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可以‘关联’到第四个问题?”[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05页。在他看来,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前面三个问题的关键词“能够”、“应当”和“可以”,即它们暴露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正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才会提出上述问题。在我们看来,由于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最终走向的是对“人是什么”的追问,因此,“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才是上述问题的核心,才是把握康德哲学的关键。再联想到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附录中的这句话:“《纯粹理性批判》本来应该是给形而上学找可能的。”[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7页。这样,从康德整个先验哲学体系来看,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就最终落在对“人”自身的追问上。因而对康德哲学的继承,首先就不是去探讨人类学问题,而是要对人的有限性进行发问,去思考关于人的形而上学问题。
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的反对者过于拘泥于康德的某一论点,比如图式化不适用于实践领域,从而误解了海德格尔,也曲解了康德。在海德格尔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图式化是否适用于实践领域的问题。他所关注的乃是先天知识能力在根基上的统一性问题。他对康德的解读实质上是要在更源初的意义上发掘理性之实践运用的可能性条件。他想强调的是,在康德那里只有一个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是同一的。所以,如果源生性时间构成纯粹理性的本质结构,那么它也就是实践理性的本质结构,实践理性正是从这里获得其在实践上的动力。“我能够知道什么”(理论理性)、“我应当做什么”(实践理性)、“我可以希望什么”中的“我”皆属同一个实际生存着的“我”,即“意志所表现出来的现相、即行动”的“我”。也就是说,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统一于实际生存着的人自身。故而,纯粹理性的有限性在根本上意味着人的有限性。当人们指认海德格尔忽视了“实践理性”之超时间的自由时,在坚持“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以及知识论、伦理学与人类学的区分时,却忽视了康德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摇摆性,忽视理性本身的同一性,忽视了康德的哲学问题在“人”这里的统一性以及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与人的根本性关联。
总之,那些康德已说的和由海德格尔所揭示出来的未说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远超“知识论”所能涵盖的范围,而且其中也确实蕴含着以“人”的研究为其方向的形而上学展望。海德格尔把《纯批》解释为“为形而上学奠定某种基础”这一立场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