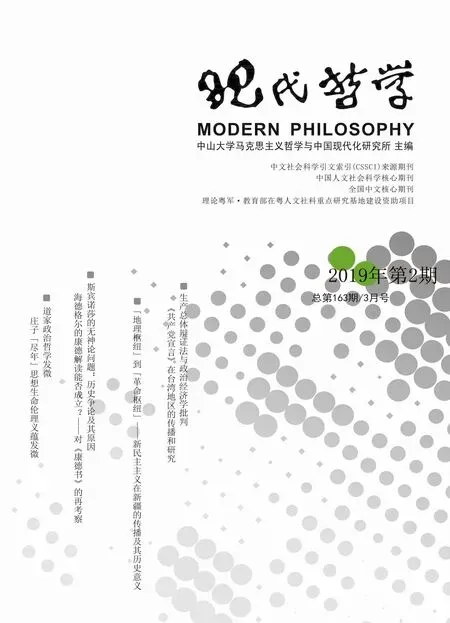“痛苦”的意味
——“动物解放”的价值论剖析
2019-12-14孙亚君
孙亚君
在诸环境伦理学派[注]这里,涉及到环境伦理学的边界问题。在狭义的语境中,道德地考量整体性的环境对象(如生态系统)往往被视为环境伦理学的题中之义。但是,如果将环境伦理学宽泛地定义为道德关怀对象不局限于人的伦理学,那么,这种“广义”的环境伦理学既包括Peter Singer(2009)的动物解放学说,也包括Tom Regan的动物权利学说。本文中所谓的环境伦理学即是广义的环境伦理学。中,以“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为标志的Peter Singer的学说是功利主义学派(或曰仁慈主义学派)的典型代表。自1975年初版以来,Singer的《动物解放》,既是西方近现代改善动物福利之社会变革的反映,又激励着动物保护运动的全面化与深入化。目前来看,在所有的环境伦理学派中,以废除动物实验与终止圈禁饲养动物为实践指向的“动物解放”理论具有最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也是第一个成功推动社会实践的环境伦理学派。例如,至1989年,美国的几大化妆品公司如Avon,Revlon等都已放弃或中止了动物实验,而以其它方式检验产品的安全性[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59, p. 247.。又如,瑞典于1988年7月通过的法规要求在10年内废除鸡笼实验,并要求奶牛、猪及毛皮动物都应该尽可能地在更为自然的环境中饲养[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112.。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现在都立法规定饲养肉犊(veal)需要保证肉犊有转身的必要空间,且给肉犊提供足够的铁质与粗纤维补充[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136.。应该说,这些蓬勃开展的“动物福利”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就在于Singer呼吁的“动物解放”学说。
另一方面,对于“动物解放”的质疑与批判也一直存在。这使得“动物解放”成为一种充满争议又影响深远的主张。无论是支持方还是批判方,都必须以正确理解“动物解放”的逻辑为前提。应该看到,“动物解放”不仅仅只是一种实践口号,而是勾勒了一种新的伦理学。以此,理解“动物解放”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其实践主张上,而是应该深入理解其价值论,后者是实践的根据。但是,在《动物解放》中,Singer并没有直接论述其价值论。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Singer关于“痛苦”与“感受性”的论述,来阐明作为其实践主张之根据的“隐性的”价值意味。进而,本文考察了这种价值论与实践主张之间的逻辑性与潜在的问题。这样,我们不仅能够看清“动物解放”的力量与不足,也可以更坚实地继续我们的道德实践与环境保护的工作。
一、痛苦的平等意味
在Singer看来,伦理学的精神是“平等(equality)”。这当然是现代主义的伦理学传统。在边沁那里,道德平等性体现为“每个(人)都算一个,而没有(人)多于一个(Each to count for one and none for more than one)”。当然,边沁主要是针对政治参与而言的。在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 p. 5.那里,这种平等性的内涵并不是平等的参与权,而是平等地被考量(equal consideration),后者并不意味着同等的对待:对不同个体的同等考量内在地要求可能的区别对待。这为将相关动物纳入道德考量之中作了铺垫。因此,道德平等性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实践“规范(prescription)”,后者以给予相关对象同等的道德关怀为题中之义,而不是事实“描述(description)”,如理性、才能等[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p. 4-5.。以此,在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p. 4-5.看来,道德平等性并不依赖诸如智力、道德感、体能、才能等所谓“优秀”的诸能力。如果这些特征可以左右道德考量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平等将变得不可能[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6.。
同时,平等的考量也需要一个构成平等的基石。在这个问题上,Singer又回到了边沁,并援引边沁的论述:“问题不是它们[应被道德考量的动物]能理性吗?也不是它们能说话吗?而是,它们能遭受痛苦吗?”[注]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9, Chapter 17.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7.可见,边沁将伦理基石建立在感受痛苦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之上。虽然边沁对动物是否应该受到伦理关怀作了建设性的展望,但边沁的伦理对象仅仅囿于人类。如果肯定非人动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的话,边沁的伦理基石与伦理对象之间并不完全相称,后者显得过份狭隘。特别地,在边沁[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10.看来,人类肉食的行为是应当的,即使相关动物将遭受宰杀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的程度往往要低于在纯自然环境中该动物因饥饿、疾病、以及被其它动物所捕杀而带来的痛苦。然而,边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如果有可能,道德主体应该避免将导致它者痛苦的行为,而非以一种痛苦代替另一种痛苦,即便前者比后者程度更轻;第二;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即素食主义对道德主体的完成而言是可行的。因此,边沁的伦理学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说是并不彻底的。
以实践而言,边沁伦理学主要的面向是政治层面,以此,“权利(rights)”成为道德考量的指向。然而,传统的权利主体要求具备维权意识,似乎很难与非人动物发生联系。因此,在传统的权利框架下,边沁也很难说清楚痛苦之于非人动物的具体权利意味。与边沁不同的是,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8.回避了“权利”,而将感受痛苦与快乐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 and enjoyment)作为个体“利益(interests)”的充分与必要条件。与蕴含主体需要自身维护意味的权利不同,相关个体的正当利益,是应该受到每一个道德主体所保护的。进一步地,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p. 8-9.以“感受性(sentience)”作为感受痛苦与快乐的能力的代名词,并成为它者(利益)是否应当受到道德关怀的判据:
“一个生命个体要有利益必须能够感受痛苦或快乐。如果一个生命遭受痛苦,在道德上就没有正当理由忽视其痛苦,或者不把这痛苦与任何其它生命相似的痛苦作平等的考虑。然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生命不能感受痛苦或快乐,就无须加以考虑。因此,划界的问题就是对我们认为的一个生命不能感受痛苦做出合理决定的问题。”[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171. [美]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第155页。
Singer通过将利益,而非权利,作为其伦理学的核心关注,更为自洽地衔接了功利主义的伦理本体,即“感受性”。这里,Singer告别了边沁的伦理划界的暧昧立场,从而肯定了伦理对象并不仅仅指向道德主体[注]在道德实践方面,Regan区分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受体:道德主体,或曰道德行为人(moral agent),是指具有运用道德原则以考量并实践的能力的个体,如正常的成年人;道德受体(moral patient),指的是缺乏道德考量与实践的能力,但应该受到道德关怀的个体。以此,道德主体不属于道德受体,但是两者都应该受到道德关怀,即它们之间不存在交集,但一起构成了道德关怀之对象的完备集。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51-152.或权利主体,而是指向所有具有“感受性”的个体,后者未必囿于人类。
二、动物的感受性
针对仅仅人类受到道德关怀的传统,Singer认为,我们需要改变对于非人动物的看法,因为人与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质的差别,而是量的差别。[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xiii.固然,人类具有非人动物所不具备的抽象思维、道德感等能力,但这些能力并不相关于作为伦理对象之判据的感受性。以感受性为判据,Singer伦理学的一个任务就是将道德关怀由人推向众多非人动物,后者同样具有感受性,因而理应成为伦理对象。但是道德主体不是非人动物,又怎么知道它们具有感受性呢?
在传统看来,无论是基督教将人视为造物主之形象的主流神学观,还是文艺复兴以来回归人是万物之尺度的人本主义,非人动物的感受能力显得无关紧要。作为基督教神学与文艺复兴思潮的交织产物,笛卡尔哲学将意识(consciousness)作为灵魂的判据,并由此断定(非人)动物仅仅只是机器或曰“自动机(automata)”,它们并无感受痛苦或快乐的能力。固然,笛卡尔的理论精妙地解决了一个神学难题[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01.,即没有(原)罪的动物何以要遭受无尽的“痛苦”,后者也无法在动物身上得到补偿(如人死后进入天国)?在笛卡尔看来,动物的“痛苦”只是有原罪的人的移情使然。然而,笛卡尔的逻辑并不严密,意识能力难道就等于感受能力吗?既然具备自我意识以具备感受能力为前提,我们应该承认无自我意识的感受之存在。显然,笛卡尔机械主义的解释并不能使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满意,因为这种解释使得动物身上的诸感官神经之复杂性显得多余[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02.。同时,人类任意折磨动物的行为也受到了批判。然而,无论是休谟的情感论还是康德的理性论,批判的目的,总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即残忍对待动物将有碍健康人性(或曰对其他人的态度)的培养,而人是惟一的目的。
在人与动物之间,似乎永远具有无法翻越的伦理鸿沟。真正对此信念构成挑战的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在达尔文(1871)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以演化机制解释了“人”的完成:人的身体构造、人的情感、人的理性、甚至人的道德感,都与其它物种一样,源于动物社群的适应性演化,因此人与动物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在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06.看来:
“达尔文学说革命在知识上是真正的革命。这时人们知道,他们不是上帝按神的形象制造、并与动物分离的特殊创造物,相反,他们终于认识到人类自己也是动物 ……人类的道德意识起源于动物的社会性本能,这种本能使动物喜欢与同类群居相伴,互表同情和互助服务 ……人类与动物的情感生活在很多方面十分相似。”[注][美]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第188—189页。
在继承达尔文学说的前提下,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15.通过逻辑类推肯定了非人动物的感受能力:如果我们相信其他人的感受痛苦的能力,我们就不该怀疑其它动物具有同样的感受性。在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171.看来,支持该信念的证据在于(1)它们遭受痛苦时的应激反应,以及(2)它们与人类相似的神经构造系统。如果语言未必可尽意或未必可尽信(一个保守却合理的前提),我们对其他人拥有感受能力的承认不也是基于上述两点吗?对此,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p. 12-13.引述了Richard Serjeant[注]Richard Serjeant, The Spectrum of Pain, London: Hart Davis, 1969, p. 72.关于动物感受能力的实证认知:
“实际证据的每个细节都支持这个论点,高等哺乳动物对疼痛的感觉至少与我们同样灵敏。……与今天的人类相比,这些动物更多地依赖于对险恶环境有最敏锐的意识。[注][美]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第12—13页。
可见,Singer的类推策略的合理内核不在宗教层面或情感层面,而在实证认知层面(不论是动物的应激反应还是它们的神经构造),从而在崇尚实证科学的当代社会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感。对于一个找不出推翻实证认知之充分理由的当代人而言,承认非人动物的感受性是一种合理的保守态度。进而,对于以感受性作为道德关怀对象之判据的功利主义而言,道德主体应当持有这种谨慎的保守态度以尽可能地避免无知之过。因此,非人动物应当作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关怀对象。
三、实践推论
Singer的道德实践是就事论事的。他并不在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实践原则,而更关注能切实减少动物痛苦的具体措施。特别地,在Singer看来,当代世界的痛苦大多数发生在动物实验与“饲养工厂(factory farm)”之中。因此,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19,p. s. 10.的道德实践的论述重点在于消除这两方面的痛苦,而非动物福利组织所关注的对于可爱宠物的同情。在实践方式上,Singer希望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禁止某些动物实验与饲养工厂的残暴行为。在此基础上,Singer也呼吁个人自觉地履行更高的道德义务,如素食主义。
Singer伦理实践的一条总原则是,所有具备感受能力的动物都应当享有伦理层面的同等的考量。逻辑上而言,承认非人动物的感受性并不必然地赋予它们道德受体的地位。我们似乎既可以承认非人动物的感受能力,并给予一定的道德关怀,同时又不全然地将它们视为与人相若的道德关怀对象,即,我们的道德关怀是可以分层的,由近及远地呈现由强及弱的变化。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依然可以将动物而非人类作为实验对象,将动物而非人类作为圈饲对象,因为其他人相比其它的动物个体与我的关系更亲近。古代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以及当代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派中J. Baird Callicott(1989, 1999)的伦理累积模式与Holmes Rolston(1988)的层次价值理论,不正是这种层次伦理学的体现吗?对此,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s. 19.认为,如果不同的社群圈真地具有伦理意义,就像Lewis Petrinovich所谓的“亲子、亲属、邻居、与物种”对应不同的伦理考量一般,那么,我们为何不在其中加入一个“种族”圈呢?因此,对于抛弃种族主义的当代人而言,这些层次的意味不应该是伦理性的。另一种契约伦理学认为,伦理源于互不伤害的契约精神,因而无法订立契约的动物就不能享有道德关怀,即道德主体对它们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对此,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s. 20.的反驳也是类推式的:如果上述原则是正确的话,那么理智不全的人士(如幼儿、智障人士、及未出生的后代)也应该排除在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外,即道德主体对他们也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显然,这个推论是难以被现代人接受的。现代主流伦理学的一条底线是,无论是否具备道德实践能力,每个人都应当获得平等的道德考量[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225.。可见,道德考量的判据无关理性与道德实践能力。
因此,如果我们接受(1)道德考量的基石在于避免痛苦;(2)每个人应该受到的道德考量是平等的这两条原则;那么每个具有感受能力的个体(不论是人还是非人动物)都应当享有平等的道德考量。质言之,Singer伦理学的核心在于对物种主义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像Tom Regan(2004)那样诉诸“权利(rights)”,而是一种类推的思辨,即物种的不同特征并不能作为对相关具备感受能力之个体的利益给予不同的道德考量的理由[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s. 24.,否则逻辑上将导致令现代人难以接受的谬论。以此,反对物种主义的实践也是一场告别各种“偏见”的社会进步运动,后者亦指向消除性别歧视与消除种族歧视[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21.。
四、问题讨论
与一般的伦理学不同,Singer并没有直接论述其价值论,这或许因为历史上内在价值论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联系。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只有“人”才具备受到道德关怀的资格。作为将道德关怀赋予非人动物的先行者,Singer似乎有意避免因涉及内在价值而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是,简单地认为Singer没有价值论考量,或者将他的主张解读为所有(感受性)的动物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的观点都是不恰当的。纵观Singer的“动物解放”,其根本目的不外乎“减免痛苦”。以此,Singer的伦理主张的价值论核心是“内在价值”,后者的基础是对于“痛苦”的感受性。另一方面,在阐述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时,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0.承认,否定物种主义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生命具有同等值得(equal worth)。特别地,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0.指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抽象思维、为将来谋划与复杂的交流活动等等能力的生命比一个不具备这些能力的生命更有价值,怀有这样的观点并不武断。”为什么这些能力(capacities)赋予能力主体更多的价值呢?这里,Singer闭口不谈这种“价值”对于它者的有用性。因此,这种价值不是工具价值。同时,对于Singer来说,这种价值又是可比较性的。这种“可比较性”又接近工具价值的特征。这种价值层面的“吊诡”同样地反映于Singer的道德实践。在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0.看来,若在一个正常人与一个智障人之间做选择:如果是挽救生命,则我们应该优先挽救正常人;如果是减免痛苦,则谁也不具有优先权。对此,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p. 20-21.给出的理由是:痛苦之恶是自身的恶,无关其它特征,而生命的价值(value)则受其它特征所影响。这里,痛苦的内在特征是符合内在价值之内涵的,而生命的价值应该不属于内在价值。进而,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21.关于生命价值的判断与实践也是物种中立的:当一个人比一个非人动物的相关能力更为受限时,该非人动物比该人的生命更具有价值,也具有更高的得到保全的优先级;即将同等的尊重给予人的生命与在智力上相当的动物的生命。可见,在Singer看来,个体生命价值的本质在于个体诸能力(capacities)的多寡。这里,生命价值的内涵与传统的内在价值的内涵(即苦乐感受)是有区别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种以诸能力表征的“价值”与以“感受性”表征的“价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感受性也是一种能力的话,那么,后者似乎仅仅是前者的一个部分。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感受性”只是一种潜在的感受能力,似乎不再具有以切身感受为面向的内在价值的意味了。不管怎样,在Singer的体系中,两种“价值”都具有价值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影响,即,它们都构成了Kenneth Goodpaster(1978)[注]Kenneth E. Goodpaster, “On being morally considerabl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5(6),1978, pp. 308-325.所谓的“道德考量性(moral considerability)”。如果Singer的“解放动物”的基础是以内在的感受性表征的价值(一如他表述的那样),那么Singer似乎面临着价值多元论的危险指控:以诸能力表征的“外在价值”如何能回到感受性之“内在价值”上来呢?另一方面,如果Singer的“解放动物”的基础是以诸能力表征的“价值”,那么,感受性表征的“价值”如何能作为“解放动物”的充分条件呢?如果具有较少能力的动物的痛苦换来了具有较多能力(例如理性能力)的人类的快乐,而这些能力都具有道德考量性的话,那么这种“交换”未见得是不合理的。然而,这种辩护下的人类中心主义似乎是合理的。更糟的是,这一进路体现的是现代主流伦理学避之犹恐不及的优等主义(perfectionism)的精神。这完全违背了Singer的主旨。因此,以Singer的整体构架而言,我们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并且我们愿意相信这种情况下的其它能力的道德考量性是一种特殊情况(如Singer所谓的在取舍生命时的考量)。无论如何,Singer对于这两种“价值”的比较与阐述是有待完善的。
在实践层面,以感受性作为实践判据的功利论也难以避免相对主义。对于Singer[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9, p. 16.来说,以感受性而非理性能力作为伦理对象的判据能够摆脱相对主义,如一个具有更高思维能力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具有特殊的痛苦感受能力,因而道德平等性对于所有的伦理对象是一视同仁的。但Singer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固然对痛苦的感受性在不同动物的不同个体间是同等成立的,但对痛苦的感受能力的强弱对于不同物种的不同个体也是同等的吗?如人类内部的不同个体对于痛苦感受的敏锐度就存在差异性。以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演化渊源关系为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对痛苦的感受能力的强弱对于不同物种的不同个体是不同的。以Singer类推策略的两个证据而言,这种感受性的区别同样可以在应激反应(强弱性)与神经构造(丰富性)两个层面获得支持。如果“感受性”在存在意义上的平等性意味着“动物解放”,那么,“感受性”在程度方面的差异性又应该落实怎样的道德实践呢?这里,Singer理论的一个逻辑缺陷是他将具有差异的感受性与没有差异的道德考量画上了“等号”,而这等号的依据并不比他所反对的将具有差异的理性与没有差异的道德考量画上等号更有说服力。
进而,Singer以“减免痛苦”描绘的“理想世界”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对痛苦的感受性是产生内在价值的前提,那么,不无讽刺的是,一个消灭了痛苦的世界似乎也就舍弃了内在价值得以“显明”的基础。这一推论并不符合价值论的应有逻辑。应该承认,痛苦本身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里,我们不妨引述Goodpaster(1978)[注]Kenneth E. Goodpaster, “On being morally considerabl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5(6),1978, pp. 308-325.对于功利论将感官功能作为道德考量之判据的批判,“生物学而言,感受性似乎是生命体的一种适应性特征,后者提供生命体更好的预感与避免对于生命的威胁的能力。这至少表明,当然,尽管它没有证明,受苦与享乐的机能并非依凭其自身而作为[道德]可考量性的入场券,而是附属于某种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比“感受性”“更重要的东西”未必是唯一的。从演化角度看,痛苦正是自然选择之于主体能动性的适应性调节信号,这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思路;以个体而言,痛苦的意义在于保全个体的生命,这为生命中心论敞开了维度。借用中国哲学中的“体”“用”关系,功利论中的痛苦是在“用”的层面上,而抛却“本体”的“用”是难以为自身辩护的。因此,Singer的“动物解放”的困境在于将“生命”解构为线性化叠加的诸价值合体的同时,却架空了“痛苦”的伦理基础。这也许是功利论伦理学的一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