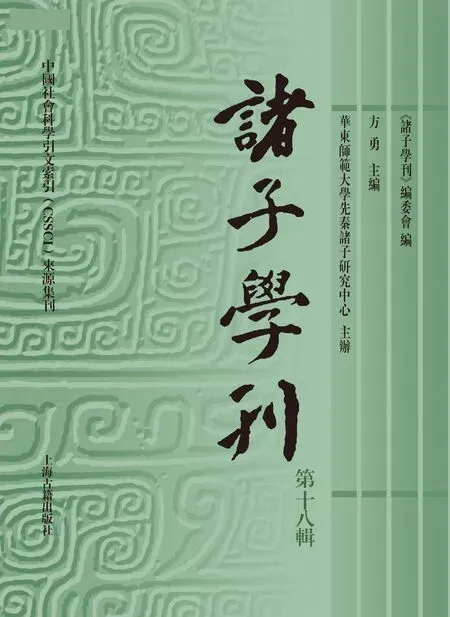賈誼與董仲舒禮學思想的天道論特色
2019-12-14臺灣賴升宏
(臺灣) 賴升宏
内容提要 賈誼禮學思想的研究多偏向其對漢初禮制的擘畫,以彰顯其思想先驅的地位,而較少探討其思想背後的天道論部分。本文乃析論賈誼“道”、“德”、“理”與“禮”等範疇内涵,明其“道”與“禮”之間的連結,以呈現其禮學思想的天道論内涵。董仲舒乃漢代大儒,其禮學思想的基礎在天人相應之説,本文由天人相應的角度探討董仲舒禮學思想的形上根據,並試圖説明二家禮學思想在天道論部分的特色與缺陷,進而一窺漢代禮學思想演變之一貌。
關鍵詞 賈誼 董仲舒 禮學 六理 六行 天人相應
賈誼(前200年—前168年),洛陽人,文帝時博士,漢初著名政論家。《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説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1)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版(據武英殿本影印),第1007頁。《漢書·賈誼傳》班固贊:“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黄,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夭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2)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臺北宏業書局1978年版,第2265頁。二書俱肯定賈誼對漢初國體禮制倡言改革之功,有著作《新書》傳世(3)關於《新書》五十八篇材料真僞問題,前賢辯之甚詳,多以《新書》材料爲可信。詳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中所載《〈新書〉的問題》一節(臺北學生書局1974年版,第112~119頁);王興國《賈誼評傳》第二章《著作的真僞與繫年》(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39~50頁);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中所載《關於〈新書〉的真僞問題》一節(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4頁)。。
一、 賈誼——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
(一) 道、德、理
《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將人性之内涵溯源於天道,以“性”作爲天人之聯結,但性與天人之間的内涵未詳述。孟子進一步云:“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盡心上》,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頁。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5)同上,第489頁。言仁義禮智内在於心,此爲孟子性善説之所據,並隱然指向性善之内涵本源於天,故“盡心、知性、知天”既有儒家道德之内在義,同時亦具宇宙本體義,但“天”之内涵爲何,“天”又如何賦予“性”,此中之聯結則未明確説明。
賈誼云:“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6)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第1009頁。天地造化以陰陽二氣,物之生乃氣聚成形,物之亡乃氣散而亡,實皆造化所生而無分貴賤人我,賈誼此説乃受莊學影響。《莊子·知北遊》云:“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7)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莊嚴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頁。莊子後學正是由氣之聚散論物之生死之氣化觀。漢初賈誼的氣化觀雖受道家影響(8)《道德説》一文,表明賈誼早期受道家思想影響比較深。可參王興國《賈誼評傳》第217頁。,卻以儒家仁義忠信的價值詮釋天地之道的内涵:
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道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9)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第327頁。
老子重“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10)河上公注《老子》,臺北五洲出版社1980年版(據明世德堂刊本影印),第34頁。强調道體之絶對與獨立性。賈誼論“道”,則重“德”與“理”,其云:“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有載物者,畢以順理適行。”(11)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第325頁。“道”爲無形、載物、順理適行之本體,“道”所載爲“德”。“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腒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12)同上,第326頁。“道”爲創生之本體,“德”爲道生物之内涵,“德”内涵在物中之表現曰“理”,故“德”發愛物養物之心曰“仁”,“德”具事理之宜曰“義”,“德”者養物而厚待曰“忠”,“德”者信固而不易曰“信”。故“道”爲本體義,“德”爲内涵義,“理”爲表現義,三者乃不同層次之概念。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内度,内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内,變流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律,故能合六法。人謹修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13)同上,第316頁。
賈誼論道之狀自“德”始,此或本於老子“道生之,德畜之”(14)《老子》五十一章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詳高明撰《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9頁。之説。“德”的内涵爲“六理”,“六理”爲“道、德、性、神、明、命”。此“六理”爲天地、陰陽、人物之内涵,此“六理”内在於陰陽則有“六月之節”,内在於天地則有“六合之事”,内在於人則有“仁、義、禮、智、信、樂”之“六行”。天地陰陽人物不失六行,方合六法,乃具六理之運,人則當謹修“六行”,乃上合“六法”、“六理”,是天地陰陽人物皆以“六行”爲備。
賈誼以“六”爲備,此説恐本於秦制(15)《史記·封禪書》云:“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詳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版,第120頁。,此由“六理”涵蓋天地陰陽人物之生,陰陽二氣稟“六理”而有節令,天地稟“六理”而生養運行,人道稟“六理”而爲“六行”,“六行”爲“仁、義、禮、智、信、樂”,乃人所當依循之道德價值,“道、德、性、神、明、命”的六理,落實於人而爲“仁、義、禮、智、信、樂”之“六行”,是由天地氣化之理以論人道之立。
賈誼論“六理”之内涵,“道”與“德”分屬生物與人物之本體義,“性、神、明、命”屬成物之内涵,人能行“仁、義、禮、智、信、樂”之六行方能彰顯“性、神、明、命”之價值,此曰“成德”,乃爲“合道”。
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16)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第326頁。
此論“性”之所生。蓋道體涵“六理”之德,能由“無”而之“有”,始可造物之生,物之所生乃合形與氣而成。性者乃神氣之所會,故可通行於外,對外物有所感而應之。故云:“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濼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17)同上。“神”者對天道而言爲道德造物變化之能;對人物而言,“神”與“氣”内具於人物之中,乃人物得感通内外之能。“性”者天之所生,合“神”與“氣”而會,“神”爲感官之能,“氣”爲所感而發喜怒之情,故曰“性生氣,通之以曉”。
“明”者爲知覺的能力,所謂“神氣在内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内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18)同上。。“神”與“氣”使吾人具感通之能,發喜怒之情,“明”則使吾人可作事理是非之判斷,此爲“知”,故“明”乃爲判斷是非之能力。
“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載於物形,故曰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19)同上,第326~327頁。。“命”者指人所受於道德之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即内、外、行、止各具其所宜之位分。
學者唐雄山將道、德到六理、六法、六術、六行的創生過程以圖示表示,以下簡列之:
道→德→六理超然於物外 具有本源性{道德性神明命→六法存在於物内 物的規定性{道德性神明命→六術
(内在形態){仁義禮智信樂→六行
(外在形態){仁義禮智信樂
(20)唐雄山《賈誼禮治思想的本源論》,《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唐氏分本體義之道與德,道爲無形天道創生之本體,德爲無形之造物内涵,道、德、性、神、明、命分物外之六理與物内之六法之别,六理乃物外之本源,六法乃物内之定性,仁義禮智信樂又分内在形態之六術與外在形態之六行,六術指内在之心性言,六行指外在之表現言,所論甚詳明。
對賈誼而言,天地爲“道”所造化,造化之内涵爲“德”,“德”的内涵爲“六理”,“六理”乃人、物之性之所由,“人性”的内涵爲“神”、“氣”、“明”、命”,包括人的感官之能、喜怒之發、道德是非之判斷及外在行止之所宜,由生理、心理、德性及外在表現之行爲,合而爲人之整體内涵,而此人之全體内涵又來自“道”與“德”之造化。故賈誼“道”、“德”、“理”之説正説明“天道”之内涵及如何賦予於“人、物”之聯結,並擴及“性”之内涵與“行”之實踐,以回歸於道德之理,其説結合道家、陰陽家及儒家道德價值而成。
(二) 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
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志,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内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修成則得六行矣。(21)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第316頁。
此由人道之生以論人教之設,人性雖有“仁”、“義”、“禮”、“智”、“信”、“樂”之内涵,卻“細微難識”,故先王乃設教教化天下,著《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藝之學,使天下人緣此以爲“六行”,以自修成德,是爲聖人立教之由來。
此説雖近於荀學而又有所差異。荀子云:“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22)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35頁。荀子以爲古之聖王爲人起禮義、制法度,乃矯人之性惡,以正情性,使天下歸於正。賈誼論聖人立教,與荀子論古聖王爲民立教之義相同,但二者之立基處有異,荀子以人之欲爲性,賈誼則以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樂”的内涵,較近孟子“性善”説,惟因人“細微難識”未能彰顯,故聖人立教乃使人能自覺性之六理乃而成德,故賈誼論人道之教之所生,則既有孟子“仁、義、禮、智”之性善内涵,又有荀子“聖王、師法”之教的外在規範,可謂孟荀之説的融合與創新。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2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22頁。賈誼之説更清楚地闡釋“性”、“道”、“教”的關係,由“六理”進而論“六經”的重要。其云: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人能修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内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24)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第327~328頁。
賈誼將儒家經典溯源於天道義的“道”、“德”、“理”,“六經”的根源是“道”,内涵爲“德”,“六經”所析論者是“道”、“德”、“性”、“神”、“明”、“命”的“六理”,《書》者“著德之理”,《詩》者“志德之理”,《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樂》者“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合則驩然大樂”。故《書》《詩》《易》《春秋》《禮》《樂》不再只是儒家之經典,其爲天道凝爲人道之經典,乃人文社會當依循之典籍,此提高儒家“六經”地位,“六經”乃提升爲人道所當依循之常道,人當依循六經以表現六理而成德乃合於道之善。學者徐復觀云:“(賈誼)他把道家的道與德的形上格架,加以詳密化,一步一步的向下落實,在落實的過程中,將道家的虚、静、明,將儒家的仁、義、禮、智,都融到裏面去,以完成天地人與萬物的創造,以建立六藝與形上的密切關聯。”(25)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170頁。論賈誼將儒道二家之説落實與相融,以提高六經地位的時代意義。
值得注意者,賈誼論“《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此説甚具特色。一者,“體德理”乃自天道義言,論“禮”者乃聖人體天道六行、人德六理而生,“禮”本源於天道六行、人德六理,此處賈誼非由“先王之道”(26)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詳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7頁。的三代文化傳承義論“禮”,乃由天道本體論“禮”之由來,表現漢初天人相應思想的特色。二者,“節文”乃由人性處言,此處可謂遠承孔子“克己復禮”(2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顔淵》,第181~182頁。之説,近承《荀子·禮論》“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28)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346頁。節制人欲以爲禮的思想影響。三者,“成人事”乃論“禮”落實在禮制的實踐,衍生而爲賈誼論國家制度、服色、官制、君、臣,甚至王位繼承人太子教育的主張。故賈誼禮學思想的天道思想,乃本於天道六行,據於人德六理,發而爲人情之節制與規範,最後落實爲國家禮制的規劃。(29)賈誼云:“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强弱之稱者也。”詳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第214~215頁。
二、 董仲舒——禮者,繼天地,體陰陽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廣川(今河北棗强)人,少治《春秋》,景帝時爲博士,武帝時以賢良對策焉,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班固以爲:“(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30)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2526頁。肯定董仲舒在漢代學術的地位。董仲舒其學以《春秋公羊傳》爲宗,倡“天人相應”説,影響漢代學術深遠。
(一) 禮者,繼天地
(1) 天人相應説。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回應武帝所問何以維繫五帝三王之道,何謂天命與災異之説。(31)“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没,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詳《漢書·董仲舒傳》,第2496頁。董仲舒提出“天人相應”之説: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32)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2498頁。
天人相應説爲董仲舒禮學思想基礎,國家失道,天將出災害以告,人君不知自省而改,天再出怪異以懼之,人君再不知變,則傷敗乃至,並舉周之興亡爲例:“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争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33)同上,第2500頁。商紂無道,天命乃棄,文王之德、武王伐紂乃受天命,人心所歸,是以白魚入舟、火復王屋流爲烏之祥瑞應之,至於晚周失德無道,廢德任刑,邪氣怨惡乃生妖孽,災異乃起,終於覆亡。此乃董仲舒天人相感相應之説。
關於天人相感,天降福禍之説,在戰國晚期以至秦漢間著作《管子》(34)關於《管子》一書的著作年代衆説紛紜,陳麗桂以爲:“《管子》的撰作時間非一時,約當戰國中晚期至秦漢之間,作者非一人,大抵是齊國稷下先生或管仲學派(齊法家)所作,地點在齊,而以稷下學宫爲中心,至其思想成色則以法家爲主(原十八篇)而參合各家,是黄老學派與法家結合的産物。”詳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黄老思想》第三章《〈管子〉中的黄老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版,第113頁。陳鼓應進一步分析説:“今本《管子》有些篇敘述管仲的遺説,成書較早(如《大匡》《中匡》《小匡》篇);本文關注的《管子》四篇成書當在戰國中期以後。有關四篇年代,筆者同意張岱年先生的看法,認爲其年代‘當在《老子》以後,荀子以前。《心術》等篇中談道説德,是受老子的影響;而荀子所謂虚一而静學説又是來源於《心術》等篇’(見張岱年《中國哲學史料學》,第581頁)。”詳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28頁。二説皆主《管子》當成書於戰國晚期。與《吕氏春秋》(35)《吕氏春秋》爲秦相吕不韋召集賓客所著,而成“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吕氏春秋。”詳司馬遷《史記》,第1014頁。等書已出現。《管子·四時》云:“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36)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四時》,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38頁。刑德合於時而施,則天降福,不合於時而施,則天降禍。《吕氏春秋·季春紀》篇末云:“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37)許維遹《吕氏春秋集釋上·季春紀》,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5頁。天人相感,禍福相應之説出現在戰國時齊、秦二國並非偶然,因爲齊、秦二國是戰國晚期二大强國,戰國以來群雄争戰不休,民心厭戰(38)賈誼云:“秦滅周祀,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向風,若是何也?曰: 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正,强淩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也。”詳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第13~14頁。,齊、秦二國是最有實力一統天下的國家,因應新的時局,需要有新的思想價值觀因應,因此天人相感、福禍相應之説,可對大權在握的君王有所約束與期許,此説由《吕氏春秋·序意》所云“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39)許維遹《吕氏春秋集釋》,第273~274頁。可證。
董仲舒提出天人相應説的用心,其吸收道家的天道觀、陰陽家的陰陽五行之説、《管子》《吕氏春秋》的祥瑞災異之説,實希望漢代帝王施政能够扭轉秦政之失,由嚴刑峻法轉向以德以仁爲本乃董仲舒的用心所在。故在賢良對策中,董仲舒再三强調:“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40)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2498頁。人君順應天命,便當强勉學問、强勉行道,使見博智明,修德立功,此皆藉天命之説以重建儒家立己立人、修德行道的價值觀。董仲舒又懲秦亡之教訓而對曰: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41)同上,第2504頁。
董仲舒一面以天降災異以警示人君,一面以秦政無道而失天下以告誡人君,其用心至明,借天命之威嚇,借歷史之教訓,使人君心懷戒懼而不敢妄爲。今漢繼秦之後,若仍一意孤行嚴刑峻法,則恐天將降災,終至失去政權,故董仲舒强調漢得天下,要與秦政有所别,當有所“更化”。“更化”正是董仲舒天人相應説的用心所在,“更化”不僅包含改正朔、服制之類,更有施政方向“重德輕刑”的轉向,最終目的是儒家價值觀的重建(42)林聰舜以爲:“雖然西漢罷斥非儒者並非發自董仲舒,但是他對‘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作出全新且整體的解釋,亦即他能以重新塑造的儒學‘更化’,建立以儒學爲主導的新統治秩序,使儒學能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這就標誌了儒學的新紀元。”詳林聰舜《漢代儒學别裁: 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40頁。,從董仲舒第三次賢良對策中提議罷黜百家的主張(43)“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詳《漢書·董仲舒傳》,第2523頁。可以看出。近代學者余英時以爲:“董仲舒以後,儒家多説‘天人相應’,……從文化史或廣義的思想史的觀點看,這種情形足以説明儒教在漢代是一個有生命的大傳統,因爲他真正和小傳統或通俗文化合流了。……陰陽五行説對先秦儒教的扭曲其實僅限於它的超越的哲學根據一方面,至於文化價值,如仁、義、禮、智、信之類,則漢儒大體上並没有改變先秦舊説。事實上,孝悌觀念之深入中國通俗文化,主要是由於漢儒的長期宣揚。漢儒用陰陽五行的通俗觀念,取代了先秦儒家的精微的哲學論辯,但儒教的基本教義也許正因此才衝破了大傳統的藩籬,成爲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道理。”(44)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3頁。余氏論陰陽五行思想是否是小傳統,尚待商榷。但董仲舒吸收陰陽五行思想建立“天人相應”説,表現漢儒適應漢代社會的轉化,以及維繫先秦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價值觀的苦心。
武帝建元六年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内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内者天災内,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45)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第1332頁。董仲舒借遼東高廟與高園殿遭火之事,認爲此非單純意外,乃天有意降災以示警,警醒武帝當留意漢沿秦政未改,以及皇親貴屬驕奢恣睢之問題,若不及早因應,恐釀更大禍事。據《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46)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第1277頁。此處可以看出董仲舒災異之説的用意,他藉由災異之説試圖勸諫武帝進行政治改革,削弱地方皇親諸侯的權勢,但也差點惹禍上身,所幸最後武帝仍然赦免了他,卻也從此不敢再言災異,此也看出董仲舒試圖影響帝王權力的微弱。雖然如此,由後世漢朝帝王每逢天災,往往下詔罪己之事(47)昭帝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罷中牟苑賦貧民。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虚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漢書·昭帝紀》,第229頁。)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托於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令三輔、太常、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詳《漢書·宣帝紀》,第245頁。來看,董仲舒天人相應説仍有其影響力。
(2) 王者受命應天,制禮作樂。
漢代秦而起,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張非始於董仲舒,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漢文帝時的賈誼便主張:“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説皆自賈生發之。”(48)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1007頁。惜因當時文帝謙惶,加上功臣嫉賢而未采用。武帝即位,天下承平日久,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再次呼籲朝廷要行改制之事,其云:
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49)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7~19頁。
賈誼站在朝代更替的角度,主張要“悉更秦法”、“改正朔,易服色”,惜功敗垂成。董仲舒提高到“天命”的高度,主張受命而王,受命於天,若一因前制,則無以彰顯天志,亦無以别新王。而所謂“改制”僅包括“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僅限宫室、稱號、曆法、服制,其餘“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即國家社會的倫常秩序、教化、風俗一如其舊,所謂“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此説其意爲何?
學者杜保瑞以爲:“其一,要求新朝君王承認異姓更朝是天意授予而非人力私爲之事,要求國君公開面對天下人,大張旗鼓,榮譽登場,並且要理直氣壯地要求百姓從此以後接受自己的照顧與管理。因爲天下是老天給的,並不是自己因私用武、用計就能奪得來的,而是天意讓自己推翻前朝而得的,因此可以公開地昭示天下。所以董仲舒是藉由‘新王改制’以給予新朝政權合法性,更進而藉由新王朝欲取得政權合法性的意圖,而要求其接受一套‘君權神授’的價值體系,從此一路董仲舒才得以在天意的要求下强將儒家價值意識轉爲約束君王的政治力量。”(50)杜保瑞《董仲舒政治哲學與宇宙論進路的儒學建構》,《哲學與文化月刊》,2003年第9期。杜氏以爲董仲舒藉由受命之君的君權神授説,提高政權的合法性,並藉由君權神授説以約束帝王的政治力量。故董仲舒此説,藉由“天命”强調“改制”的必然性,此説乃“天人相應”主張落在禮制上説,是將禮制的必然性提高至天命的層面;再則强調唯“受命之王”乃得改制的神聖性,是將“天人相應”主張落在帝王身上説,賦予新朝代的帝王以神聖性,其云:“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51)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三代改制質文》,第185頁。最後則爲化解“改制”的疑慮,故强調僅止於宫室、稱號、曆法、服制,其他如舊。這樣的説法,確實是漢武帝改新制的誘因。實則,新王改制,不僅止於改正朔、稱號、服制,還有制禮作樂。
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樂。樂者,盈於内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52)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楚莊王》,第19~23頁。
董仲舒論改制本於其“天人相應”之説,王之改制分兩部分: 應天改之,應人作之。改正朔、稱號、服制乃應天命之改而作,制禮作樂則爲應人心之動而作,王受命於天,民同樂於人心,故新制之生乃應天命之新,新樂之作乃順民心之樂而制,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皆有新樂以應新代,漢繼周而起,亦當製作新樂以應。
董仲舒藉“神權”加諸“王權”之上,有提高“王權”地位的意義,但另一角度來説,新王應天命而生,也可能應天命而廢,故也有借“神權”來壓抑“王權”的意義在其中。王永祥以爲“這顯然是説,天子雖爲天神所立,最爲天下貴,但卻不可任意胡爲,否則,天將會把他的王位奪去。這也就是要用神學的目的論來限制統治者對人民的壓榨,以防止激起人民的反抗和起義,危及封建政權。這顯然有着對孟子民本思想的繼承”(53)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頁。。天子之位原來自天命,天命的内容爲儒家推崇的仁義禮智之道,若人君勤勉行仁義之道則天降祥瑞應之,若人君違背仁義禮智之道則天降災異警之,若不知悔改,最後天命可能變易之,此見董仲舒雖是建立新的天人相應模式,但並不背離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價值觀。
此外,董仲舒論王者受天命,其目的則在“制禮作樂”,此可看出董仲舒是借天人相應之説,得到君王的接納與信任,其目的乃爲實現儒家制禮作樂,成就一代禮制的理想,此爲董仲舒建構天人相應新宇宙論的真正用心所在。
(二) 禮者,體陰陽
(1) 天者貴陽賤陰,政者任德不任刑。
“陰陽”與“五行”歷來研究頗多(54)梁啓超《陰陽五行説之來歷》,顧頡剛編《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頁。鄺芷人《陰陽五行及其體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陳麗桂《從循環、代勝到主從、尊卑——戰國秦漢陰陽五行説的緣起與演變》,《哲學與文化》,2015年第10期。,“陰陽”與“五行”本爲兩種詮釋自然的樸素觀念,並無神秘色彩。自戰國以來,鄒衍始將二者結合以詮釋政治之道,歷經《管子·四時》《吕氏春秋·十二紀》,以至於《淮南子》加以演繹擴充,遂建構成一套包含月令、天文、星象、干支、帝神、物候、音律、祭祀、災禍等嚴密的天人相感的施政藍圖(55)可參陳麗桂《從循環、代勝到主從、尊卑——戰國秦漢陰陽五行説的緣起與演變》一文。。
董仲舒吸收陰陽與五行思想主要不在繼續擴展上述所論天人合一施政的規模,而是直接由自然之道契入人倫政治之道。其賢良對策曰: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56)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2502頁。
陽居春夏,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居秋冬,以空虚不用爲處,此陰陽二性乃順先秦以來由陰陽消長詮釋四時更替之説。但董仲舒所重在陰陽二性所表現之德,陽爲德,以生養爲德;陰爲刑,主殺伐,天道以陽爲主,故任德不任刑。董仲舒又云:“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57)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陽尊陰卑》,第327頁。。”以陽氣爲暖、予、仁、寬、愛、生,以陰氣爲寒、奪、戾、急、惡、殺,説明天道大德而小刑,以德爲常經大道,以刑爲變通權用,值得注意者,“暖”、“予”、“仁”、“寬”、“愛”、“生”都是先秦儒家的價值觀,在上述所引《管子·四時》《吕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關於陰陽的看法,多爲相對平等,並無孰輕孰重之别(58)“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四時》,第838頁。)“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而復合,合而復離,是謂天常。”(陳奇猷《吕氏春秋校釋·仲夏紀》,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版,第255頁。)“古未有天地之時,唯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蒙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别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精神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頁。。
董仲舒雖吸收陰陽之説,卻是有意識地加以轉化,將其轉向儒家“暖”、“予”、“仁”、“寬”、“愛”、“生”之價值觀,於是“陰陽對等”成爲“重陽輕陰”,目的是轉向“重德輕刑”的儒家德治主張,以扭轉漢代承秦法以來的政治方向,所謂“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爲董仲舒其深意所在。
(2) 天有陰、陽之施,人有貪、仁二性。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59)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爲人者天》,第318頁。
董仲舒論人道本於天道,並將人之形體、血氣、德行、好惡、喜怒、受命皆比附於天地之象,其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60)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天副人數》,第354頁。此爲“天副人數説”。先秦儒家以人爲貴,孟子有“人禽之辨”(61)“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十三經注疏·孟子·離婁章句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版,第145頁。,强調人當存養四端之善性;荀子有“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62)“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王先謙《荀子集解·天論》,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4頁。,在形氣内涵上强調人之道德性。但由天以論人則爲《中庸》“天命之謂性”(63)“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十三經注疏·禮記·中庸》,第879頁。之説,言人當“盡性”、“至誠”以上達天道之德,皆屬道德性的感通以上達天道。
董仲舒“天副人數”之説,具體明確地指出人爲天之所生,由“數”的觀念比附天之道(64)張德文認爲董仲舒的數位系統爲:“一”乃指天地之氣,合而爲一;“二”乃指陰陽二氣;“三”指天、地、人三才;“四”天之四時,人有四肢;“五”天列五行,人有五臟;“十”十端,人懷胎十月;“十二”十二月,人有十二節。詳參《董仲舒的“天人關係”模式及其思維方式》,《中國文化月刊》,2000年第239期。,是以骨節象三百六十日、耳目象日月、五臟象五行、髮象星辰、鼻口呼吸象風氣、喜怒象四時。關於天人關係,董仲舒不僅止於道德的感受與創造,他在具體的形體、感官、喜怒之情中,將天與人作明確的比附,人之形體喜怒乃從天之四時、日月、風氣、星辰所化而來,由人身内在情性與外在感官肢體所透露的“數”去作連結的證明,反映的思想意義是董仲舒承繼先秦以來“以人爲貴”的觀念,只是他是以人身之“數”以對應“天道之象”以襯出人之尊貴。
董仲舒云:“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災疾莫能爲仁義,唯人獨能爲仁義;物災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65)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354頁。此明人之所以爲貴,天地由氣化以生物,人、物皆爲氣之所生成。人獨受命乎天,此或承《中庸》“天命”之説,但《中庸》以“性”爲天命的内涵,董仲舒卻吸收荀子之説,以人獨能知仁義而爲貴。人除能知仁義,更惟有人獨能“偶天地”,此乃董生“天副人數”之説,肯定人之爲貴的價值。由今觀之,“天副人數”不免有牽强附會之處,但由先秦儒家論“天人合德”的思想發展而言,董仲舒可謂將二者作了最具體的連結,人之内在與外在皆受天之特别造化,以明天與人確爲一體。
栣衆惡於内,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栣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栣。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66)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295~296頁。
董仲舒由氣化天道以論人道之心性,所謂“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道有陰、陽二氣,人身亦有仁、貪二性在其中,人之受氣善、惡皆在心性之内,但天道尊陽而卑陰,不免有時而月厭於日光,乍全乍傷,故人有時不得不損輟其情性,是皆應天之所爲,稟天氣化之自然,故人雖有仁、貪在性中,但亦具好仁惡貪之性向,所謂“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67)同上,第63頁。。故心性雖善惡在其中,但天道尊陽而卑陰,故人亦好善而惡惡,是以對董仲舒而言,人非“性善”,而是有“好善”的天性。
董仲舒論“性”較近於荀子,荀子云:“性者,本始材樸也。”又云:“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爲氣化材質義,“僞”乃是對“性”的人爲裁成義,“性”與“僞”本質上相同,只是在表現上不同,“性”乃自人欲發,“僞”則經過人爲的教化洗禮而發之禮義之行。只是荀子没有在天人氣性的連結上加以論述,而董仲舒則由天道氣化之“尊陽卑陰”下落於心性而論人心之“善善惡惡”,是其理論又較荀子嚴密。
(三) 禮者,體情而防亂
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争,流争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68)同上,第469~470頁。
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6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顔淵》,第181~182頁。“性與天道”孔子雖少言,但言“克己”則知性中自有私欲當克乃得“復禮”,“復禮”乃視、聽、言、動皆當循禮而行,始爲仁人君子,故孔子論“仁”由内在之克己,加上外在視聽言動之循禮而言。
董仲舒論“禮”言“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争,流争則亂。”可謂孔子“克己”内涵的闡發,好色之性、飲食之性當循禮而行,否則當流而爲亂,人世之紛争始起。此説與荀子論“禮”相近。荀子論“禮”自情欲之規範處言,所謂“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70)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禮論》,第346頁。的論點相同,荀子論“禮”自情欲之“性惡”論,乃由“防亂”角度論“禮”。董仲舒好色之性、飲食之性若無禮則流爲亂,正是自“防亂”角度論“禮”。
但董仲舒論“禮”的作用除“防亂”之外,還提出“體情”之説,因董仲舒人性觀不全然是好色、飲食之性,其人性内容有仁、貪二性,人性本好仁惡貪,由“貪”而言,所謂“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禮”固防亂也;由“仁”而言,則“禮”爲“體情”,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乃從人性之好仁、好義處發出,故“禮”非一味奪人之情,防人之性,其用意乃在因人之性以安人之情,故言“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
(四) 民受成性之教於王
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71)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深察名號》,第300~302頁。
董仲舒與荀子“性惡説”看法相近,基本上皆自“天生性情”處説性,即性是天生的氣質,本身不是“善”,“善”要經過後天的教化才能爲善,荀子重“化性起僞”,董仲舒曰“成性之教”,就重視後天教化而言,二説是相同的。對荀子而言,人性的内涵就是“食色之性”並無所謂善惡,透過聖人制禮義的實踐,透過“學”與“習”,“近師友”的“同氣相感”以變化氣質,使過與不及之欲,化作有節制且合理之禮法規範,此即“化性起僞”的主張。董仲舒則强調人性中有“仁貪兩性”且基本上人是“好仁惡貪”的,具備“好善惡惡”的傾向,即人性中有善質,因爲有善質,所以才有“教化成善”的可能性。董仲舒主張透過外在的教化,使“仁貪兩性”的心性論轉化爲善,但主導的不是聖人、亦非師友,乃轉向君王,君王除了是政治領袖,也是道德教化領袖,此爲董仲舒人性説的特色,將政治義的君王賦予更崇高的道德教化使命。
董仲舒由天道之陰陽以論人性之貪、仁二性,性非善,性須待教而爲善,天乃爲之立王以教民,使民爲善。故民受性於天,受教於王,王者承襲天意乃以教民爲善以爲己任。其云:“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72)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2503~2504頁。論人君施教於民之内容與必要性,古代聖王莫不以教化人民爲務,漢承秦而起,仍續秦法而嚴刑,無怪乎國不得治,故君王當改弦易張,以教化爲重,立大學、庠序以教化人民。而君王更當身自表率,其云:
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衣服容貌者,所以説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説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説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説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説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説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73)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爲人者天》,第320頁。
此論王教之内容,天以生物爲德,地以載物爲德,聖人以教化爲任,知王教乃具天人一體之必然性。董仲舒“聖人”乃指君王而言,所謂“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74)同上,第319頁。。君王不僅以威勢爲政,更有教化之使命,君王先之以博愛、不貴難得,則教民以仁、義、孝、弟也。君爲民之心,“心”者明辨是非之主,故君有教民之責,以爲民心之主;民爲君之體,民有從君之義。故君立身以孝悌好禮,重仁廉而輕利,躬親職於上,君立己以正民,則萬民從善於下。人君行之於身,所謂視聽言動合於禮,衣服中而容貌恭、言語順應、好仁惡薄、去鄙就善,合於耳目感官之悦,而爲民可樂可觀之身教也。此可謂董仲舒對孔子“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75)“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詳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顔淵》,第190頁。的影響力,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整合,成爲人君立身言行的準則,並賦予人君以立身言行爲教化人民的使命。
董仲舒“王教”有數義: 一、 董仲舒結合陰陽之説,由天道之陰、陽以論人性之貪、仁,天命乃立王以施教,此乃爲君王的成立建立權威與道德之根源義,君承天命而來,可謂董仲舒涵義的“君權神授”,但此君權非可一意孤行,當以人民之施教爲任,君王乃天命之君,且爲天命之師,亦爲教化之領袖,對推尊漢代君王之地位影響深遠。二、 董仲舒的主張實有所承又有所創新,承襲的是先秦儒家君王德治的理想,而關於君王德治思想演變,由孔子“君子之德風”,荀子“師法”、“聖王”之説,以至賈誼“君德”、“君行”、“君容”之説,可看出德治理想漸向推尊君王方向發展,至於董仲舒藉天道陰陽思想,遂達至君權與師道結合的巔峰。三、 董仲舒雖推尊君權,但已將儒家德治思想灌注其中,君王握天命之權威,但也不可任意妄爲,其有爲民表率的使命感。
結 論
(一) 賈誼禮學思想天道論的創見與缺陷
學者錢穆論及戰國末期以至漢世,秦漢儒者吸收道家、陰陽家之説,開創“新宇宙觀”的意義,其云:“惟自戰國晚世,下迄秦皇、漢武之間,道家新宇宙觀既確立,而陰陽家言又不符深望,其時之儒家,則多采取道家新説,旁及陰陽家,而更務爲變通修飾,以求融會於孔、孟以來傳統之人生論,而儒家面目亦爲之一新。……故論戰國晚世以迄秦皇、漢武間之新儒,必着眼於其新宇宙觀之創立,又必着眼於其所采莊老道家之宇宙論而重加彌縫補綴,以曲折會合於儒家人生觀之舊傳統,其鎔鑄莊老激烈破壞之宇宙論以與孔孟中和建設之人生論凝合無間,而成爲一體,實此期間新儒家之功績也。予謂此時期之新儒,以《易傳》與《小戴禮記》中諸篇爲代表。”(76)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年再版,第23頁。錢氏説明秦漢新儒吸收莊老道家、陰陽家新説,建立新宇宙觀的思想背景。但秦漢儒者是否求融通於孔、孟傳統之人生論,以曲折會合儒家人生之舊傳統,則值得商榷。
賈誼頗通諸子百家之學(77)“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吴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吴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1007頁。,其禮學思想的天道論可謂結合儒、道、法三家之説,所謂“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甚具特色。天地萬物始於“道”,論述卻以“德”爲主,“德”的内涵爲“六理”,“六理”爲“道”、“德”、“性”、“神”、“明”、“命”,人發而爲“六行”,即“仁”、“義”、“禮”、“智”、“信”、“樂”。故“禮”本於“六理”而來,“六理”則本於天道而生,“禮”本於天,乃成爲天與人之間的連結與表現,此可見賈誼吸收道家天道觀,以“道”爲禮之始源,但卻以儒家的價值觀“德”爲主體,以仁、義、禮、智、信、樂爲實踐,而以法家之規範以約束,表現漢初融合諸子思想的特色。
杜琦以爲:“賈誼的哲學思想積極吸收了道、儒、法三家思想之精華,他以道家的‘道’爲形上本體立基,通過‘道’‘虚’‘術’三者之間的關係,在‘道’的格架下融入道、儒、法的内容,把道家道的虚、静落實到了儒、法兩家的仁、義、禮、智、信、公、法上,把道家的抽象的道與儒、法的社會宗法人倫日用聯繫起來,貫通了道、儒、法三家的思想。他借用道家的‘道’,以道爲本體,由形上到形下,從虚無到實有,創生萬物,打通了陰陽、天地、人。其思想既有形上的建構,又有形下的完善,由此創造了一個完整的哲學理論體系。”(78)杜琦《淺論賈誼的哲學思想》,《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賈誼吸收道家的本體義,但不强調形上本體義,更重視萬物“德”之内涵,並以儒家“仁”、“義”、“忠”、“信”爲“德”的表現,是由陰陽氣化之道以論人道之禮的建立,吸收道家與陰陽家氣化思想,以補充儒家仁、義、忠、信之形上根源義,是將儒家的道德義賦予天道根源,反映漢初儒、道、法、陰陽思想合流的特色。
賈誼對“禮”的天道論思想,在理論上補充《荀子·禮論》的不足。荀子以“禮”乃是人性欲望的節制與合理分配的問題(79)“禮起於何也?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346頁。,欠缺“禮”的天道根源義,“禮”遂偏向於“法”,下開韓非、李斯之法家思想。賈誼由“道”下“德”而落於“禮”的理論模式,使“禮”的道德内涵在天道義上得到貞定,此乃賈誼之創見。
審視賈誼的禮學思想在天道論上的影響,卻没有董仲舒將“禮”建立在天人相應説來的影響深遠,何也?筆者以爲董仲舒以天子承天命制禮作樂,其云:“禮者,繼天地,體陰陽”(80)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奉本》,第275頁。將“禮”之形上根據於天地、陰陽理論,其天人相應之説簡捷明白。反觀賈誼所論“道”乃生物之始,“德”乃物之内涵,德有道、德、性、神、明、命之“六理”,其在人,發而爲仁、義、禮、智、信、樂之“六行”,故人當行“六行”以合“六理”,乃爲有德,乃合於天道之説,理論太過曲折,故賈誼之説有其創見,但影響力卻不及董仲舒天人相應説,恐是因其理論晦澀曲折,一般人不易瞭解的缺陷有關。
(二) 董仲舒禮學思想天道論的權威化傾向
董仲舒云:“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内、遠近、新故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寶。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内之心懸於天子,疆内之民統於諸侯。”(81)同上,第275~278頁。論“禮”由天地陰陽之序立論,順天道之序以立人道之位,以天地之序作爲人倫之序的禮制根據,强調人道的尊卑貴賤有序,尤其是君王的地位受到推尊,以其乃天之所命爲最高,其次乃公侯諸侯之尊,是由天道義之秩序以建立政治義的尊卑倫理基礎。
董仲舒此説其特色: 一是,不强調自然義的法天地思想,更偏向人道義的秩序根源的探討。二是,“禮”是天人相應思想在人世的表現,“禮”成爲天與人的連結,使禮制更具必然性與合理性。三是,天道以日月爲尊,人道以人君爲尊,進一步彰顯尊君思想。四是,人世之尊卑貴賤乃相應於天地之秩序而來,故建立禮制之尊卑貴賤有其必要性,人倫世界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乃成爲絶對性尊卑之規範。五是,其説簡潔明白,天地之序落實爲人倫之禮,君爲天子推爲至尊,因而得到君王的信任,儒家人倫之道也因而獲得支持,而得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先秦孔子論“禮”强調的道德化與相對尊重性,卻也大大弱化,漢代禮學思想至此表現越來越强烈的權威化與絶對化傾向。
學者董金裕以爲:“先秦時代的孔子、孟子等儒家宗師,雖然懷抱極大的理想與熱誠,想要得君行道,但終其一生,仍未能實現。直到兩漢初期,董仲舒才開始扭轉此一情勢,在獲得漢武帝的信任之後,將其所主張者化爲實際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取得正統地位,並且獲得部分實現,功績十分值得肯定。但是爲了迎合帝王及時代風潮,不得不糅合百家,並以陰陽家之説作爲推論方式,將儒者所强調的人的主體性,轉换爲具有權威性格的天,從而被統治者假借運用,難免也遭致批評。然而從儒者之目標乃在於由内聖以達外王的角度來看,如非董仲舒的極力推崇儒家,儒家是否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導的地位,並因而使儒家向來所主張的仁義之道,以及‘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民方式,得以在歷史上實現,則十分難以斷言。”(82)董金裕《董仲舒的崇儒重教及其現代意義》,《衡水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董氏對於董仲舒推展儒家思想的貢獻與流弊之論堪爲公允,董仲舒還是功多於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