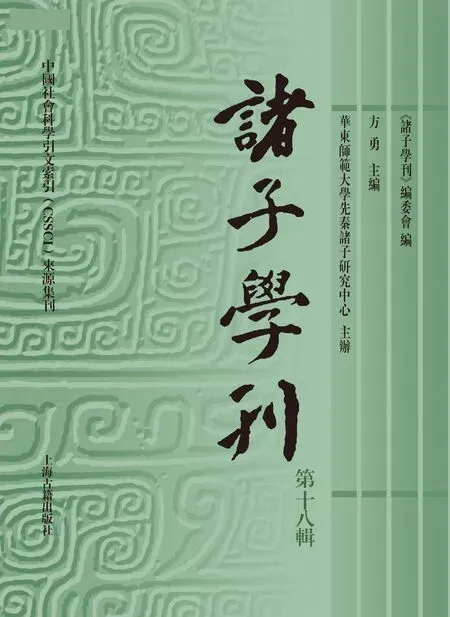儒 家 之 後
——韓非“權力經濟學”的源流、思維與進路
2019-12-14臺灣曾暐傑
(臺灣) 曾暐傑
内容提要 韓非是爲法家集大成者,歷來在儒家作爲主流的意識形態脈絡中,其思想往往被視爲刻薄邪僻。然而,韓非思想可以説是對當時作爲顯學的儒家與墨家的回應與批判,即指出儒、墨思想對於重建戰國時期社會秩序之無效性。本文則特别着墨於常被作爲儒、法關聯的荀、韓關係,藉此思考爲何在面對相同的時代與相同的問題時,儒、法兩家卻開出了截然不同的學説。可以説,荀子對於思孟學派的批判是儒學内部的轉向——從“道德形上學”到“倫理經濟學”;而荀子到韓非則是另一種轉向——就此轉出了儒家的脈絡,開出了不以道德爲基礎的“權力經濟學”。這個儒家開展之後的發展,是一個内在道德逐漸弱化、外在權威逐漸提升而漸次講求治亂的效率與效能的過程;韓非思想正是儒家之後對於人性論與政治論的修正與發展,具有其時代精神與意義。
關鍵詞 新子學 韓非 荀子 儒法 經濟學
前 言——“新子學”視域下的法家
集法家大成者韓非(1)韓非生卒年不可考,相關問題可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51~553頁。,歷來受到學者的批判與非難,言其嚴刑峻法,刻薄寡恩,與仁義相悖,成爲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反韓”現象(2)趙逵夫《應運而生的思想家——兼評〈韓非子的成書及其文學研究〉》,《諸子學刊》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頁。。如蘇軾即指出申韓所謂“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的謬論,是造成秦漢暴政的罪人(3)蘇軾《韓非論》,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頁。。方孝孺則説:“韓非、商鞅書……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4)方孝孺《與樓希仁》,《遜志齋集》卷十一,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版(據《四部備要》明刻本影印),第28頁左。張爾岐亦言:“申韓管商……最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慎也。”(5)張爾岐《蒿庵閒話》,臺北藝文印書館原科景印《百部叢書集成》1967年版,第21頁左。王船山更認爲申韓是一種“缺陷人格和病態文化”(6)王夫之《老莊申韓論》,見氏著《王船山詩文集》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7頁。。
甚至有如張鼎文者,直指李斯、韓非“不智”而“無術”,後或死於獄中,或車裂而亡,其不得善終實是“天道之報昭昭哉”(7)張鼎文刊刻《韓非子·校刻韓非子序》,嚴靈峰編《無求備齋韓非子集成》第七册,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5頁。,已落入用“人身攻擊代替説理”的邏輯謬誤(8)關於“人身論證”,請參蕭永倫《以〈孟子·告子上〉中的對話爲素材談論辯謬誤》,《哲學與文化》,2001年第8期,第742頁。,頗有幸災樂禍之戲謔情緒(9)宋洪兵《子學復興視野中的“韓非學”研究——以明清爲中心》,《諸子學刊》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頁。。而當代學者也多“照着”歷代學者講(10)“照着講”相對於“接着講”而論,是馮友蘭在《新原道》所作的區分: 前者指依着前人思想體系中的典範而論,後者則超出前人的典範進行新的體系論述與建構。參馮友蘭《新原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93~194頁。,把韓非思想視爲層次很低、深陷黑洞而難見天日的學説(11)陳拱《韓非思想論衡》,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35頁。——或如牟宗三言其是爲暗無光明的“黑暗密窟”(12)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版,第173頁。,或如勞思光直斥爲“罕見之邪僻思想”(13)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版,第344頁。,可能都有落入宋洪兵所指出的“充滿太多濃厚的主觀成見乃至偏見”(14)宋洪兵《韓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頁。,帶着儒學本位去評價申韓的危險。
但在現代甚至後現代的新時代脈絡中,文化的多元性乃是人們必然的選擇(15)方勇《“新子學”構想》,《諸子學刊》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頁。,乃至如王晴佳所説,當代多元價值體系下的經典詮釋應如“花園風景”(landscape),衆生喧嘩,而非尋求一把真理的金鑰匙(16)王晴佳《後現代主義與經典詮釋》,黄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臺大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 134頁。。應該如“新子學”所倡導之理念——在“經學”一元化的思維模式外,開展非“經、史、子、集”下附庸於“經學”的“子學”視野,强調百家争鳴下“諸子百家”之“子學”,回歸學術自身,承認多元世界的自在狀態,敢於面對紛雜繁複的現實社會,去尋求學派間的平等對話與争鳴。(17)方勇《再論“新子學”》,《諸子學刊》第9輯,第1~3頁;方勇《“新子學”構想》,《諸子學刊》第8輯,第 363頁。
當然,儒家本位的論述有其必要性與正當性——每個存有(Being)都有表達其信仰與價值的權力;但在新時代的脈絡下,堅持韓愈所謂“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18)韓愈《原道》,韓愈著、閻琦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頁。的道統思維,並將不符合孟學意識形態者皆視爲歧途或異端,或許並無必要(19)劉述先著,景海峰編《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劉述先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頁;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第315~316頁。。也就是説,從儒家“獨尊”的唯我意識中跳脱,將可以更真切地回到百家争鳴、共襄大業的學術現場,而以更公允的態度去發掘法家與韓非的學術價值(20)參何美忠《借力諸子開拓中國學術新途徑》,《諸子學刊》第8輯,第396頁。。
胡適説:“非儒學派的恢復是絶對需要的。”(21)胡適《先秦名學史》,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五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那能够讓人看見多元文化之間的張力以及子學的思維方式(22)李有亮《重返中國傳統文化最佳生態現場——對“新子學”的一點理解》,《諸子學刊》第8輯,第386頁。,讓人思考爲何法家會不滿於儒家而開展法家,進而能够藉由獨立與自由的精神理解原創之見(23)正如方勇所説,墨子不滿儒家而另創之墨家,莊子無所不窺而恢弘的道家,荀子的性惡論,爲何都不依傍前人而自成體系,都有其思維之奥秘與意義。參方勇《“新子學”構想》,《諸子學刊》第8輯,第362頁。。那麽就能够跳脱儒學傳統的神聖權威(24)正如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90—2002)所説“被奉爲傳統和習俗的神聖的東西都具有一種無名的權威”,是以作爲中國文化中“大傳統”(great tradition)的儒學,具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權威性,讓人不自覺地將之奉爲唯一真理而以此爲判準去評價他者。Refer to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7, p.265; Robert Redfield, 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89, pp.1~16.,甚至站在公正的角度去批判那些“陰用其術,陽斥其人”(25)蕭穆《敬孚類稿·汪梅村先生别傳》,黄山書社1992年版,第330頁。的“僞儒者”,而了解到韓非思想的生成必有其時代性的意義與價值。
一、 “權力經濟學”的源流背景
在“新子學”的思維與方法的指導下,我們應該嘗試重返傳統文化的生態現場(26)李有亮《重返中國傳統文化最佳生態現場——對“新子學”的一點理解》,第385頁。,正視先秦時代的“子學現象”——百家争鳴爲何而起?進而凸顯“子學精神”的意義之所在(27)方勇《再論“新子學”》,第1頁。。也就是説,法家因何而起,韓非爲何而發,其思想的出現在歷史的脈絡中必然有其意義與價值。正如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所謂“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28)[德] 黑格爾(G. W. F. Hegel)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1頁。,一個制度與思想的生發,必然有其緣由與背景,必然有一環境内部産生的推動力,促成一個思想體系的誕生,進而對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提供了精神的質素(29)李有亮《重返中國傳統文化最佳生態現場——對“新子學”的一點理解》,第386頁。。
(一) 經濟形態的轉型: 從“井田制度”到“私田買賣”
正如方勇所説,諸子學的興起無不是源自先秦時期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禮樂秩序的全面崩潰,封建體制的徹底解體(30)方勇《“新子學”構想》,第362頁。。亦即,百家争鳴之所以彼此攻訐,都是出於解決禮樂封建制度的瓦解與崩壞而發。孟子所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所言“君子必辯”(《荀子·非相》),都是出於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所説的“秩序至上主義”的思維(31)[美] 史華慈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頁。。但對韓非而言,當時的顯學儒、墨之説恐怕都是“好辯説而不求其用”(《韓非子·亡徵》),都不足以救亂世,甚至會造成國家的覆亡。
所謂的“用”即是理論在現實上是否得以施行,那麽在討論韓非理論的形成時,固然應該從禮樂制度的崩解來思考,而不能一味由儒家本位的仁義思維去理解,言其學説與仁義相背(32)趙逵夫《應運而生的思想家——兼評〈韓非子的成書及其文學研究〉》,第388頁。——認爲韓非將君臣與妻子皆視爲“我之賊”,是凶險惡毒的理論(33)張榜《韓非子序》,見陳啓天《韓非子參考書輯要》,中華書局1945年版,第112頁。。禮崩樂壞只是表面的現象,如果從更深層的脈絡去思考就可以發現,韓非之所以會如此建構其理論,關鍵在於禮崩樂壞背後所造成之經濟形態的改變。
(1) 井田回歸: 宗法制度中的孟子。
在孟子之時,雖然已是戰國時代,禮樂已然崩壞,但整個封建體制與經濟並未完全瓦解;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即在於貴族世襲的封地制度一息尚存,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左傳》昭公七年)的傳統——土地的所有權屬於天子,不得任意轉讓與買賣(34)趙海金《韓非子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69年版,第3頁;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頁。。然而,在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土地作爲主要生産資料,没有土地所有權的人民如何維生?關鍵即在於孟子所説的“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説,農民擁有“私田”得以耕種自足,但此“私田”是依附在“井田”制度中的(35)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第3頁。,農民並未有實際的“財産權”(property rights)(36)“財産權”的有無主要依據是否擁有支配物品或資源的權力來判定,亦即是否能够依照自由意志去分配該物品或資源所産生的效益流(benefit stream)與收入流(income stream)。而在井田制度中,農民必須依附在官方世族的井田制度之下,必須依據封建領主的意志去種植作物,亦必須根據一定比例繳交收成給貴族,因此可以説當時的農民並未擁有“財産權”。參高安邦《政治經濟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版,第31~32頁。。隨着戰國時代征戰日益頻繁,生存的資源日益減少。然而人口的壓力卻持續增張(37)如人口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指出,人口往往呈等比級數(geometric progression)成長,然而資源卻只是以等差級數(arithmetic progression)增加,是以資源提升所形成的供給永遠趕不上人口壓力造成的需求。是以儘管戰國時期鐵器農具的使用提升了農業的生産量,但依然無法負荷戰國時代人口的增加以及戰争所帶來的破壞。參曾暐傑《孟子之後——荀子“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及其儒學回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年,第86~87頁;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形成資源稀少性(scarcity)的問題(38)作爲“經濟財”(economic good)的資源是有限的,未必能够滿足每個個體的需求,是以面對無窮的欲望,如何分配與選擇便形成了“經濟學”的問題。可以説,經濟學(Economics)是建立在“稀少性定律”(law of scarcity)的基礎上的。參温明忠《經濟學原理》,新北前程文化2013年版,第3頁;高希均、林祖嘉《經濟學的世界: 上篇——經濟觀念與現實問題》,臺北天下文化出版1997年版,第69~70頁。——亦即“供給”(supply)持續緊縮,然而“需求”(demand)卻不斷提升,是以在供需失衡的狀況下,勢必要能够開源節流而尋求供需平衡(The supply meets the demand)(39)温明忠《經濟學原理》,第31~32頁。。
那麽,要達致供需平衡,基本上有二條進路: 增加供給或是減少需求。作爲儒家的孟子選擇了透過“仁義”與“良知”、“良能”的道德自覺與實踐來達致減少欲望的可能(40)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頁。——亦即在資源生産條件不變的狀況下,透過減少道德主體的欲望來降低需求。是以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透過道德的修養來達致“寡欲”的結果,那麽自然也就能够達成減少需求的期望(41)曾暐傑《孟子之後——荀子“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及其儒學回歸》,第203~204頁。。
甚至可以説,孟子是反對透過增加需求的途徑來達到供需平衡與建構社會秩序的可能。他説:“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上》)此處孟子提出了最應該被處以刑罰的三類人: 好戰之人、策動合縱連横戰争之人與開墾授田之人。一般認爲這是孟子的“仁政”思想,目的在於遏止戰争對百姓所造成的傷害以及殺人盈野的殘酷。(42)參傅佩榮《人性向善——傅佩榮談孟子》,臺北天下遠見2007年版,第320頁。從人文精神而論,這當然没錯,但其背後有個更關鍵的因素,在於這類人都是破壞封建制度和諧的亂源。
“善戰者”與“連諸侯者”製造邦國之間的衝突與戰争,破壞天下的秩序自然没有問題,但關鍵在於“辟草萊任土地者”——開發荒野林地以增加田地之人,何罪之有?爲了因應戰國混亂下供不應求的“封建失靈”(feudal failure)(43)因爲生産過剩或生産不足而造成的供需失衡情況,在經濟學上稱爲“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這時候就需要政府扮演一隻“看得見的手”去平衡此一困境,而不能任由市場中“看不見的手”自行發展。然而,在先秦時期尤其是孟子的時代,並無明確的“市場”,或許可以把這在禮樂社會下形成的供需狀態的失控稱之爲“封建失靈”——而諸子百家所扮演的角色即在於告訴君王應該如何扮演那隻“看得見的手”。關於“市場失靈”,可參高希均、林祖嘉《經濟學的世界: 上篇——經濟觀念與現實問題》,第227頁。,增加可耕地面積來提升農民的生産力以增加供給,不是應該值得鼓勵嗎?爲何孟子反而將其視爲罪大惡極的行爲?關鍵即在於由林地開發而來的田地成爲井田之外的私田,是動摇井田制度的關鍵(44)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第5頁。。
然而孟子畢竟是期望着能够恢復禮樂封建社會,並將井田制度中“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那樣先公而後私的倫理自覺視爲一種淳美之風,由此而能同尊周天子爲共主,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信念,達到供給與需求的穩定關係,進而能够保證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2) 私田興起: 封建瓦解下的荀韓。
然而,到了荀、韓之時,禮崩樂壞的程度似乎讓當時的思想家了解到: 回歸封建社會已不可能,應該致力於如何在由貴族政治轉向階層體制的威權統治中尋求社會秩序與供需平衡的可能(45)干春松《荀子與儒家在戰國政治轉型中的秩序安排——荀子與賢能政治》,《邯鄲學院學報》,2013年第 1期。——亦即他們都承認“新型國家”(46)許倬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4~127頁。的形成已成定局,是以預先肯定了君勢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並由此建構他們的理論(47)高柏園《韓非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頁。。而封建社會之所以已成了不可逆的過去,關鍵即在於井田制度的全面瓦解。商鞅變法後,廢井田,開阡陌,真正使井田制度走入了歷史(48)吴秀英《韓非子研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頁。。
而井田制度是周朝封建體制的基礎,也是藉由貴族與農民之間的“超穩定結構”(49)金觀濤指出,中國社會中有一穩定的階層體制,作爲穩固權力、社會與經濟的根據;而這樣的結構儘管也容易在亂世中瓦解,但總是能够在社會的動盪後再回到此一穩定的結構當中。參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 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197頁。作爲社會秩序與供需平衡的根據——貴族擁有封建領土,藉由公田與私田的制度,讓農民得以自給自足,同時也作爲供養貴族之所需,形成一種“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子·滕文公上》)的穩定關係結構。這種制度中,封建君王以宗法制度爲骨幹,以井田制度爲養分,所以井田制一旦瓦解,封建體制即失去了能量的來源,自然便無從延續(50)吴秀英《韓非子研議》,第27頁。,必然走向重視“力”與“利”的君主制度之新形態。
(二) 財産意識的形成: 從“關係導向”到“利益導向”
井田制度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使得人民的“財産權”意識被具體化——由“公私一體”轉爲“公私二分”,人民得以爲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奮鬥,支配自我財産所衍生的效益流,而不是活在貴族的陰影之下。由此,時代的經濟型態,便形成透過“力”去追求“利”的意識形態——擁有越多的資源與資本,也就能够創造越多“供給”來滿足“需求”。是以可以看見,當時井田制度崩解、私田興起的同時,還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志上》),推行農耕生産技術,有西門豹興修水利,在在都是企圖增加民生供給之作爲。(51)吴秀英《韓非子研議》,第28~29頁。
此外,荀、韓的時代重利思想也帶動了商業之興盛——子貢貨殖屢中,郭縱冶鐵致富,吕不韋以大賈之姿躋身卿相,巴寡婦清采礦致富,正所謂“庶人之富者累鉅萬”(《漢書·食貨志上》)。正因爲如此,當時手工業興盛,交通發達,商旅輻輳,秦之咸陽、趙之邯鄲、楚之郢都、魏之大梁、齊之臨淄皆以商業繁華之地聞名。(52)同上,第29頁。這點由《韓非子》中所説“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徒於越”(《韓非子·説林上》)的例子便可以了解到,當時手工業的興盛與商業貿易的移動頻繁而平常。
(1) 何必曰利——孟子的“道德形上學”。
其實在這樣經濟形態的轉型時代以及暴虐而争奪頻繁的現實中,孟子、荀子與韓非子皆看出了利益的動機是人行爲的動力;但他們選擇了以不同的典範(paradigm)與視野去面對這樣的現實。(53)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80頁。儘管孟子在時代中看見經濟形態不得不轉型,並了解到“利益”是作爲人行爲的關鍵,但他不願意由此來定義人並放棄封建社會的秩序。他説:
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孟子·梁惠王上》)
也就是説,孟子體認到了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所説的“動機階層論”(need-hierarchy theory)——唯有在滿足了最底層的“生理的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才有追求“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之可能(54)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4, p.411; Abraham H. Maslow: The Fa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2, p.423.。但是孟子卻在梁惠王問其“將有以利吾國乎”時,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堅持將人視爲“道德人”(moral man),企圖透過仁義的道德來馴服人對利益的欲求(55)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80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透過“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的工夫回復作爲“道德人”的本質,是一種“道德形上學”(moral metaphysics)的進路。(56)曾暐傑《孟子之後——荀子“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及其儒學回歸》,第57~95頁。
而孟子的政治理論,也是在此“道德形上學”的脈絡中建構,亦即“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蔡英文所指出: 孟子有着將“政治道德化”的特質。(57)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80頁。所謂的“政治道德化”,即是孟子所説“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將治亂的方法訴諸道德的自覺,並且認爲只要君王有此道德心,則天下的問題皆可以解決。
對荀子而言,這並没有真正論述政治的方法,而只是一種“没有政治論的政治論”,僅是用道德形上學涵括一切,將仁義與道德之心的有效範圍無限擴大到政治範圍之中的“政治道德學”(58)同上,第78頁。,並未説明要如何解決“無恒産”的問題,反而不斷强調“有恒心”則能“有恒産”。但“無恒産”的問題没有解決,又如何能有“有恒心”之人?在此處形成了一個論證的循環。(59)曾暐傑《孟子之後——荀子“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及其儒學回歸》,第192~194頁。
(2) 禮義養欲: 荀子的“倫理經濟學”。
是以荀子認爲,孟子這樣的進路是“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荀子·性惡》)的空談,因爲人本身並無任何力量來消除利益的欲求,而必須透過外在的力量來制約人性,進而達到治亂的可能。是以荀子强調以“禮”來化導人性(60)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86頁。,他説:
禮起於何也?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
這完全從欲望情性來定義“人”,而將人視爲充滿欲望的“經濟人”(economic man),並從中體現了在資源的稀少性下,人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必然會形成爲了生存資源而相互争奪的混亂,是以必須依靠“禮”來分配資源,進而使供需達到平衡,從而化解衝突。(61)曾暐傑《孟子之後——荀子“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及其儒學回歸》,第85~95頁。這顯然是以經濟爲基礎的政治理論,相對於孟子的“政治道德學”可説是一門“政治經濟學”。
(3) 計之長利——韓非的“權力經濟學”。
然而,韓非認爲當時的顯學儒、墨二家的理論皆是無效的立論,他説: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韓非子·五蠹》)
韓非的意思是: 古代與現今的制度不一,新舊時代的情況也不同,在面對今日那些充滿利己意識與欲望的人民,如果還要像從前封建時代,透過道德仁義去尋求供需平衡與建立社會秩序,那就好像没有韁繩和馬鞭要去駕馭野馬一般,没有績效可言。(62)謝雲飛《韓非子析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版,第63頁。
韓非在此處指出,過往西周時代的宗法制度所依靠的是“尊尊而親親”(《漢書·地理志下》)的思維,是以“關係導向”爲基礎。正如孟子所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上》),這是一種基於血緣關係的道德體系——内在的親屬關係透過嫡長子與階層制度(Hierarchical System)的確立,讓人能够安於道德秩序而彼此謙讓。(63)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頁。因爲有着天生而來的情感,是以能够自然而然地開展仁義,因爲那是建立在家族彼此的親情關係之中的。
然而隨着時間的遞衍,血緣關係會逐漸疏遠,那透過“尊尊而親親”的血緣關係所建立的向心力便會開始瓦解而轉爲離心力。當資源越趨稀少,人與人之間不再因爲血緣的緊密性而實踐“親親”,不再願意分享、禮讓,透過彼此的合作去達至供需平衡。相反地,在没有血緣親密性的基礎下,人與人之間會透過争奪來取得資源,而使得“關係導向”無從施展,進而使宗法制度崩解。
是以,韓非便不能再以“關係導向”爲基礎去建構社會秩序,而必須從“利益導向”而論。也就是説,整個社會之間的關係,必須從“利益”的角度去思考與開展,那是一種客觀的現實考量,用以取代“關係導向”中的“主觀性”情感連結。(64)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119頁。此即韓非所説:“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禄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韓非子·難一》)這樣的“利益導向”論述,的確十分現實而無情,但這其實正是面對儒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立論的無效性所作的辯駁。
儒家以親緣的關係强調推己及人,透過辭讓與關懷有血緣關係者,一層一層往外推,自然能够達到關懷天下人——即孟子所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或《禮記》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禮記·禮運》)。韓非認爲這樣的思想在封建社會下或許還可能爲之,但於戰國時期財産權的發生下,人性已然不同。封建井田制度下人民没有土地私有權,財富無公私之分,自然無利可争;然而在私田興起並得以買賣後,便形成了公私相背,以自利爲考量的“利益導向”思考。(65)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第68頁;趙海金《韓非子研究》,第58~59頁。
是以韓非舉了衆多的例子試圖證明:“親親”並無必然性,如果將“親親”作爲尋求供需平衡與秩序建置的基礎,完全無效而不可靠。(66)謝雲飛《韓非子析論》,第66頁。如韓非即言:
父母之於子也,産男則相賀,産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六反》)
就連有骨肉之親的父母與子女,都會爲了長期的利益而殺害自己的親生骨肉,又何況是没有血緣關係的君主、臣民呢?韓非就由此指出:“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韓非子·五蠹》)對韓非而言,“親親”的道德呼唤最不可靠,唯有以“法”爲標準去施行,才有治亂的可能性與必然性。(67)同上。
二、 “權力經濟學”的人性觀點
是以可以了解到,韓非企圖以“利益導向”去理解人,並由此建構秩序。可以説其觀念中的“人”是具有“理性”(rational)與“自利”(self-interested)之“經濟人”(homo economicus)(68)高希均、林祖嘉《經濟學的世界: 中篇——個體經濟理論導引》,臺北天下文化出版1997年版,第5頁;温明忠《經濟學原理》,第10頁。;而非孟子所謂“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孟子·公孫丑上》)的“道德人”。韓非即言:
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 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 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韓非子·外儲説左上》)
(一) 利益導向的人觀: 好利惡害的經濟人
可以見得,人與人之間的愛與不愛、怨與不怨,皆不是由“關係導向”來決定,而是以“利益導向”爲核心——只要是有利於個體的,即使是蠻荒之地素不相識的人,彼此也能和合而處;然而只要是有害於個體的,即便是親如父子也會視彼此如寇讎而相互疏遠。
進一步而論,夫妻之親密關係,相較於有血緣關係的父子之間,更是以利爲導向;在現實中並没有透過“關係導向”而保證了夫妻間的和諧關係。其言:“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韓非子·備内》)這即是韓非所觀察到的人性——以“利”爲出發點,即便父子夫婦之間也不能免。(69)趙海金《韓非子研究》,第56頁。
由此可以得見,韓非思想中的“人”是絶對的“理性”與“利己”的“經濟人”,是以“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韓非子·内儲説上》)。不僅充分體現了“利之所在民歸之”(《韓非子·外儲説左上》)的“利益導向”秩序,更是一充滿欲望的身體(70)或即伍振勳所説“自然的身體”——充滿欲望與衝動,未經教化的人性原始狀態。參伍振勳《荀子的“身、禮一體”觀——從“自然的身體”到“禮義的身體”》,《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1年第19期。——是以有“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韓非子·備内》)之情況,“關係導向”完全被擱置。
其實,將人視爲“經濟人”的表述在荀子的脈絡中即已展現(71)曾暐傑《孟子之後——荀子“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及其儒學回歸》,第55~116頁。,這點可説是韓非對於荀子“性惡論”的吸收。(72)趙逵夫《應運而生的思想家——兼評〈韓非子〉的成書及其文學研究》,第388頁。然而,《韓非子》全書未明言“性惡”,這是荀、韓走向分歧的關鍵。荀子從禮教作爲判準將人性中“利己”的傾向稱之爲“性惡”,表示其思考與論證中藴含着道德的内涵,人性之價值並未喪失。(73)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版,第273頁;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96~97頁。韓非雖言“利己”,且所言説之案例較荀子更爲極端,但卻不言此爲“性惡”,正因爲韓非完全肅清了道德的素質(74)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96~97頁。,没有禮義作爲道德的判準來定義人性——利己就是利己,無所謂善惡。這是“實然”(is),而無討論“應然”(ought to be)的必要。
(二) 道德真空的政治: 刑賞威嚇的經濟人
儘管韓非所言之“人性”與荀子極爲類似,但不能逕自將其稱爲“影射性本惡之觀念”、“肯定人類‘自利’的劣根性”(75)吴秀英《韓非子研議》,第68頁。,或言其理論皆是從“人性本惡的基本觀點出發”,韓非不言“性惡”有其關鍵性意義,否則便無法解釋爲何他會走向與荀子不同的政治道路。
對韓非而言,只要把握“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韓非子·姦劫弒臣》)此一人性的事實,並利用此特質來建構經濟秩序,而不須如荀子一般强調“化性而起僞”(《荀子·性惡》),企圖將“自然的身體”轉化爲“禮義的身體”(76)伍振勳《荀子的“身、禮一體”觀——從“自然的身體”到“禮義的身體”》,《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1年第19期。,因爲韓非認爲“人性”不可化也不必化。他説:
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韓非子·顯學》)
説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能有“不忍人之政”,那是“先王”有之,並不代表今人亦有之;大力地鼓吹先王的“仁心仁政”,不會讓今天的人性變得更好,不會使人成爲“先王”。這就好比再怎麽跟醜人宣揚毛嬙與西施的美,也不會使醜人變美女。重點是要用胭脂水粉來化妝,使醜人變美;而就現實“利己”的人性而言,“刑賞”就是最好的化妝品。
是以可以了解到,荀子雖然也將人認定爲“經濟人”,但是他並未放棄“禮義”作爲道德價值的判準;也就是説,其“經濟人”仍然是被置於“關係導向”之中來思考,是以言“性惡”——因其有“道德感”故須以“惡”言之,韓非將“道德”擱置、反文化教養(77)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114頁。,是以不必言也不能言,僅僅在“利益導向”中建構秩序。
也就是説,荀子理論中的“經濟人”是必須在儒家傳統的“關係導向”中轉化的,如荀子言: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荀子·性惡》)
荀子的確指出人性原初“利己”的傾向,但其建構秩序的方法,仍然是從“關係導向”中與父兄之倫理關係來規範,企圖透過禮義將人由“利己”特質中開出道德意識,進而符合“關係導向”中的倫理。
三、 “權力經濟學”的政治實踐
那麽在現實“利己”的人性中所造成的供需失衡,作爲統治者要如何形塑一個制度來解決這個困境,這即是先秦諸子不斷在思考的關鍵問題。孟子認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用道德良知的自覺去減少人的需求,進而達到供需平衡的可能;而其所據以規範人以減少“需求”的是一種“道德權威”的隱性規範——所依靠的是人性的自覺,因此可説是一種“政治道德學”。(78)曾暐傑《孟子之後——荀子“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及其儒學回歸》,第191~199頁。
而荀子據以協調人與人之間因争奪資源而産生衝突的關鍵在於倫理,其制度亦由聖王根據禮義來規範,所謂“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惡》)。這是透過聖王的權力去推展以“關係導向”爲核心的禮義倫理,屬於一種“禮教式的顯性規範”,聖王的權力僅僅是手段而非核心,關鍵還是在以德性意識型態的化導,是以在“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時,荀子説: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荀子·儒效》)
他雖然不否認“利”,也不否定君王的權威,但關鍵在於是否能够利用這個勢位去運用有德之人以倫理的意識形態去化導人民,可稱之爲“政治經濟學”(79)同上,第200~214頁。。
而韓非則完全是憑藉着國君的“勢位”,依靠强大的意志力與法令規章來進行秩序的建構。(80)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113~114頁。他放棄道德與倫理的判準,以絶對的效率與效能去思考如何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益與秩序的安定。這是一種利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而開展的“規訓式的顯性規範”(81)[法]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年版;賴俊雄《暴力經濟學: 倫理、法律與正義》,《文山評論》,2007 年第1卷第6期。,可稱之爲“權力經濟學”(Economics of Power)。(82)曾暐傑《孟子之後——荀子“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及其儒學回歸》,第246頁。
(一) 强國利民: 國家本位的零和博弈
但是所謂的“權威”未必是負面的,在當代社會對於“權威”似乎有種負面的刻板印象,那是在經歷二戰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提出“集權主義蔑視法律和合法性”的論述,使當代人對此有所警惕(83)[德]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林驤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頁、408頁。。但必須强調的是,韓非所倡行的是“集權主義”——將政治權力集中於中央君主而不將權力分散出去,以達到穩固而有秩序的國家,而非無限上綱的“極權主義”(84)金觀濤《永不放棄的追問——寫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成書六十年》,收入[德]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林驤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第11頁。。
强調“權威”未必是不好的,而端看此一“權威”的目的爲何,而韓非强調君主的權勢其目標即在於創建一個强而有力的統治權去形塑出安静、穩固而具有凝聚力的政治秩序,並藉此來達成國家的富强。(85)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22頁。正所謂“賞罰不阿則民用。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强,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韓非子·六反》)。由此可知君王的霸業取決於國富兵强,而國富兵强此一背後的深層理路正是“國家至上論”的終極目標。(86)同上,第28頁。
這樣的“國家至上論”强調的是耕戰,這與孟子將“善戰者”、“連諸侯者”與“辟草萊者”視爲罪人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孟子的脈絡在於回歸封建制度之下“親親而仁民”的思想,避免衝突與相互包容,以減少百姓受到殺戮的悲劇。然而韓非卻説:“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韓非子·八説》)强調必須開地增加耕作産量,攻伐他國增加土地與資源。論者多以此辯難韓非——這難道不是陷人民於水火之中嗎?
其實不然,韓非是站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的攻伐之困境而論,他的理論與儒家以“天下”爲訴求標的不同——不同於荀子所言“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 夫是之謂大形”(《荀子·君道》)。將天下視爲身體,各國如同軀幹與四肢,是以任何一個國家的攻伐與搶奪耕地,在以天下爲視角、視天下爲一體的儒家論述中是没有意義並會造成自身傷害的。
因爲如何攻伐與搶奪,都是“己身”,傷害的也是自己的“軀體”,是以儒家尋求的是在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亂,亂則窮”的困境中,不是靠着彼此的攻伐來達到需求的滿足,而是尋求適當的分配——“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亦即孔子所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依靠分配來形成一種“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的結果(87)荀子的“天下從之如一體”之概念應該是導向和平的共贏概念,而非如“中研院”人社中心蔡英文所説是與韓非一致又開展出極權統治的根源。參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第106~107頁。另“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請參[美] 威廉·龐士東著,黄家興譯《囚犯的兩難: 博弈理論與數學天才馮紐曼的故事》,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頁。。
韓非認爲天下已分裂,各國的兼併争戰中,没有所謂非零和博弈的可能。在資源供給固定的情況下,他者多獲得一分供給,我必然少一分供給;而我多一分需求,他者必然就要少一分需求。他是以“國家本位”的視野去强調耕戰,我國多一塊田畝,供給就多一塊田畝的産量;我國多攻伐下一座城市,就多一座城市的資源。這是透過增加自我供給來滿足自身需求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88)正如趙逵夫所指出,韓非的思想並非萬世不變的金科玉律,也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是專門爲了單一國家能够統一、强大而獲得更多的資源供給以帶來人民安定富足的理論。參趙逵夫《應運而生的思想家——兼評〈韓非子的成書及其文學研究〉》,第389~390頁。
(二) 階級鬥争: 人民至上的貴族批鬥
由此可以了解到,韓非子强調君王的權威、强調使人民耕戰,是爲了國家的富强,而國家的富强是爲了人民之利,此並非爲了一己之私,正如韓非所説“聖人之治民……期於利民而已”(《韓非子·心度》)。法家之所以辟草萊、廢除井田而開放私田買賣,即是以君主的權威力量去爲人民争取更多的資源供給,因爲當時阻礙生産力提高的,正是那群身爲井田主人的封建貴族——上欺其君、下壓其民,是以試圖以君王的絶對權威去化解這股勢力。(89)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第144頁。這樣的思維與作爲頗與列寧(Владмир Ильч Ульнов, 1870—1924)所謂“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争,政治就是反對世界資産階級而争取解放的無産階級的關係”(90)[俄] 列寧(Владмир Ильч Улья’нов)《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頁。有着類似的概念。
而“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91)同上,第381頁。,是以韓非極爲重視人民與國家的生産供給與需求的滿足。而古代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産來源即是土地,是以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指出: 幾乎所有的古代社會鬥争,最終都可以歸結於土地的擁有權與使用權。(92)[德] 韋伯著,康樂譯《經濟與歷史: 韋伯選集IV》,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頁。是以須瞭解到,私田買賣制度的興起,是法家爲國家人民提高資源供給量的鬥争,是從未馴化的原始野性過渡到野蠻的過程中,使有閒階級的井田主逐漸浮現,是在人民習慣温順於貴族壓迫的生活習慣中,轉變爲好戰的生活習性的形成。(93)Refer to Thorstein Veblen,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p.7.
是以可以説,韓非法家的初衷不僅不是極權主義,不是壓迫百姓、宰制人民千年的邪僻思想,更非“視萬民若芻狗”的君權維護者——那是儒家本位與被扭曲的法家形象所塑造而成。韓非就曾明確地説:
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韓非子·備内》)
法家認知到重徭役會造成民間疾苦,而一旦人民苦痛,貴族階級就會趁勢而起去收攏民心,如此貴族階級便借機拔升爲主導階級,取得主導地位,形成一新的宰制人民的勢力,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當然這之中或許藴含着確保君王權勢的優越性,但不能不説這是運用單一權威去追求利民的可能。(94)正如李景鵬所説,政治的過程中,各種政治關係呈現交錯的狀態,政治主體與政治客體是錯綜複雜的;君王與貴族可能是政治主體與政治客體的關係,然而貴族與人民又是另一政治主體與政治客體的關係,如何在此之中尋求平衡,是一重要課題,否則就容易落入韓非此處所説的惡性循環。參李景鵬《權力政治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頁。
作爲法家的韓非,此是打破固有井田制度中的供需關係——企圖破壞放任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之情境,而試圖從國家的角度去追求集體利益(collective good),重新建構家國社會結構中的供需關係(95)經濟學家約翰·偉克斯(John F. Weeks)就對於使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經濟制度感到不滿並進行批判,認爲那是須要受到破除與改變的。參約翰·偉克斯著,張嘉文譯《爲1%的人服務的經濟學》,臺北商周出版2014年版,第25~26頁。。這是從少數人手中奪取財富,還富於國家的政治鬥争,這也才是李斯遭致車裂的關鍵因素——而非張鼎文所説“天道之報”。韓非與先秦法家的勇氣不容抹煞,不當幸災樂禍。
(三) 苦民長利: 需求導向的刑賞權威
正如宋洪兵所説,應該避免僅僅將韓非與商鞅等法家思想作爲反面教材,提示人們刻薄寡恩之害,藉此來凸顯儒家王道政治的可欲性;(96)宋洪兵《子學復興視野中的“韓非學”研究——以明清爲中心》,第340頁。其實所謂的刻薄寡恩,是站在儒家“仁心仁政”的角度而論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禮記·大學》)。其實此處前後兩句没有必然關係,而應該將“民之所好”區分爲“短期愉悦”與“長期愉悦”(97)人類有着“需求當下”與“需求未來”的能力,當能够思索未來時,即便當下得不到滋養,人們也會甘之如飴。但大部分的人都未能有這樣的前瞻能力。參[德] 尤阿希姆·鮑爾(Joachim Bauer)著,王榮輝譯《棉花糖的誘惑: 從腦神經科學看自制力》,臺北商周出版2016年版,第117頁。。正如韓非所説: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韓非子·顯學》)
人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他們就像嬰兒一樣,僅有短期欲望的視野而無長期欲望的遠見,是以不能人民喜歡什麽、想要什麽就順着他們。苛刻的法,對於人民當下來説或許苦不堪言,但對長期而言卻是有利的,正如韓非所言:
今家人之治産也,相忍以飢寒,相强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韓非子·六反》)
“法”雖然要人節儉以“節流”,使人當下得不到完全的滿足,甚至要人服兵役,忍受軍旅中的艱難與危險,但那是透過攻伐爲國家“開源”的大利。雖然人民當下不喜歡,但是對於他們而言卻是具有長期利益的。韓非認爲,儒家的仁義之道雖然當下讓人民感到快樂和諧,但以長期來説,不開源、不節流而僅强調非零和的分配,終將淪爲窮苦之中。
這也是爲何韓非要强調君王的“權威”,爲何要特别凸出政治支配的强制性而發展一强而有力的“權力經濟學”(98)李景鵬《權力政治學》,第80頁。——關鍵即在於没有此一强制勢力,如何讓人民忍受短期之苦而獲取長期之樂,致使國家富强?這在民智未開、教育未普及的古代社會,不是一種霸權,而是一種“利民”的手段。就連近代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也指出,人民通常不知道什麽東西對他們是好的,所以統治者必須幫他們決定,這就與韓非有着相似的概念。(99)[法] 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48頁。
結 論——韓非形象的重構
是以韓非站在富國的立場、處於利民的角度,特别强調經濟上的開展,將“權力經濟學”充分體現了列寧所説之“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總而言之,韓非的政治經濟理論,面向極廣,在開源、節流與分配上都有着深刻的表述與理解。(100)吴秀英《韓非子研議》,第124頁。韓非基本上把握了經濟人“利己”特質,利用此一人性來開展所謂“實用”而可施行的經濟理論。
在“增加供給”上,韓非强調了耕戰,這是開源最重要的基礎,也是爲何法家要辟草萊、興私田的依據,故其言“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 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曰: 可得以貴也”(《韓非子·五蠹》)。正因爲在戰國時代的亂世,國與國間處於非零和博弈,唯有透過開闢農田、攻伐城鎮,才能獲取更多資源,來達至供需的平衡,這也是爲何韓非會説“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争於氣力”(《韓非子·五蠹》)。在零和博弈中没有絶對的軍事能力,就没有資源——“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韓非子·顯學》),是以由孟子的“道德形上學”到荀子之“倫理經濟學”,再到韓非的“權力經濟學”,有其時代的必然性與必要性。
在“減少需求”上,這點是頗具有人文精神的,而非過往刻板印象認爲勤儉是“儒商”的專利。事實上,儒家反而反對節用,而强調分配,是即孔子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點由荀子所説“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説不免焉”(《荀子·富國》)可以了解到。對儒家而言,“節用”不是問題,因爲儒家認爲“萬物得其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何患乎不足也”(《荀子·富國》)。相反,韓非特别强調人欲無窮,必須加以節制——“治人事天莫如嗇”(《韓非子·解老》),“力而儉者富”(《韓非子·顯學》),“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韓非子·解老》)。
就“資源的分配與正義”而論,法家與韓非不但不是壓迫人民的極權主義,反而是强調階級鬥争,禁奢於貴族階級而還富於家國百姓。就基本的政策而言,是透過税賦的政策來達到財富分配的均衡,即所謂“論其賦税以均貧富”(《韓非子·六反》)。更進一步而言,韓非子認爲奢侈品應該有所管制,故其言“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韓非子·難二》)。韓非認爲應該要“禁淫奢”,是以外來的奢侈品皆不得入關。
韓非此等“利民”思維,只要能够從“新子學”的視野,跳脱儒學本位去重新釐清與定位,便能化解過往對於法家與韓非的誤解與非難,甚至是人身攻擊式的謾駡,而見其思想之時代性與意義。當然,此並非要揚法而抑儒。不可否認,韓非的理論亦有其時代的限制性與可商榷之處,甚至不能躲避此套理論一旦失控便會造成可怖的後果,但又有何種古代經典與學説能够不經轉化即可置入當代脈絡之中呢?又有何種思想不會在臻於極端之際走向崩壞呢?或許,良知的失控所帶來之災難,並不亞於君權的失控所帶來之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