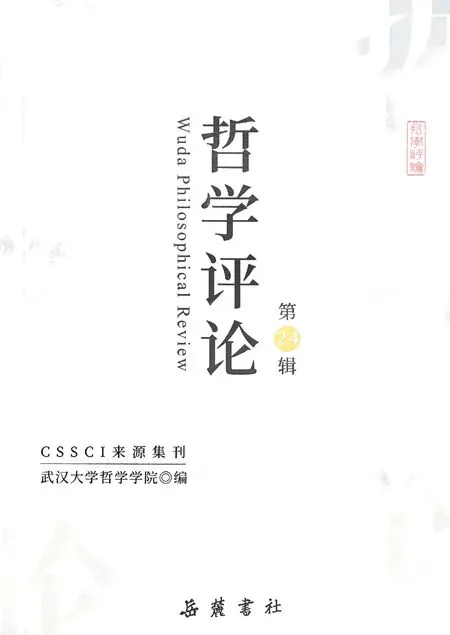生命与惩罚
——青年黑格尔论犯罪与刑罚
2019-12-14王兴赛
王兴赛
在西方刑法哲学(尤其是刑罚理论)发展史中,黑格尔与黑格尔学派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仍有影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这从德国当代著名的刑法学者和法哲学家帕夫利克(Michael Pawlik)教授的一系列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比如他在《人格体 主体 公民:刑罚的合法性研究》(Person, Subjekt, Bürger: Zur Legitimation von Strafe)一书中就借鉴黑格尔的刑罚理论资源批判预防论,并提出一种新版本的报复论:“刑罚是要制裁公民的不法,并且通过正是履行忠诚义务与享有自由之间的相互性,得以将法作为法进行恢复。”(帕夫利克:《人格体 主体 公民》,谭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作者指出,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刑法学界出现了报复论的复兴,黑格尔的刑罚理论是这股复兴潮流中得到借鉴的重要传统资源。对此,德国和英美学界多有阐述,国内学界的相关阐述相对较少。[2]德语学界关于黑格尔刑罚理论的重要研究文献,请参见帕夫利克:《人格体 主体 公民》,第34页注释3,第45页注释4。英美学界的相关研究,可参见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18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黑格尔刑法哲学的研究大部分是从黑格尔成熟时期的法哲学著作入手的。众所周知,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90—103 节(“强制和犯罪”)与第218—220 节。最能体现黑格尔犯罪和刑罚理论特色的莫过于他对犯罪和刑罚之本质的阐述。黑格尔强调犯罪的本质在于对法本身的破坏,而非对社会(或他人)的危害。这决定了刑罚的本质就在于法本身的恢复,而不在于对罪犯的矫正、预防犯罪、威吓、儆戒等等。在黑格尔看来,人只有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接受惩罚。而且人只能是目的。只有如此,刑罚才是正义的。黑格尔的刑罚理论常常被称为“报复论”。他所谓的刑罚正义就是报复(Wiedervergeltung)。[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4页。报复不同于同态复仇(Rache)(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报复主要是从普遍的价值方面来确定,而非局限于被侵害的东西的质和量。报复与复仇在内容上是一致的,都是正义的。但在形式上,复仇因为是主观意志或特殊意志的行为,这不免就会超出罪刑适当原则,成了一种应受刑罚的新的侵害,因此是不正义的。[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7页。而报复则是客观且普遍法律所规定的行为,即用法院审判的方式实现刑罚正义。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认为刑罚正义表现为法律同自身的和解以及罪犯与自身的和解。[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0页。
其实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1793—1796)就对犯罪与刑罚制度感兴趣。在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当他刚开始构建其观念论体系时就尝试着从统一哲学方面去探讨犯罪与刑罚,这算是黑格尔正式对犯罪与刑罚进行哲学讨论,有些想法一直延续到《法哲学原理》中。在耶拿时期(1801—1806),黑格尔在新的哲学体系中不断更新和加深对犯罪与刑罚问题的讨论(如《论自然法》和《伦理体系》)。本文着重探讨的是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的犯罪与刑罚思想,首先分析黑格尔阐述犯罪与刑罚思想时的历史语境与哲学前提,然后重点分析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对犯罪与刑罚问题所做的哲学分析。最后,本文将联系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的犯罪与刑罚思想进行比较和反思。
一、青年黑格尔刑罚思想的历史语境与哲学前提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开头曾描述了1757年3月2日在法国实施的一场公开处决的场面,其后又引述了1837年左右一处监管所的监禁规章,他通过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欧美当时刑罚思想和制度的重大变革:“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整个惩罚体制在重新配置。这是传统司法‘丑闻’迭出、名声扫地的时代,也是改革方案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时代。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有关法律和犯罪的理论,一种新的关于惩罚权利的道德和政治论证;旧的法律被废弃,旧的惯例逐渐消亡。各国各地纷纷酝酿或制定‘现代’法典:俄国在1769年,普鲁士在1780年,宾夕法尼亚和托斯坎尼在1786年,奥地利在1789年,法国在1791年、共和4年、1808年和1810年,这是刑事司法的一个新时代。”[1]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版,第7页。关于福柯所说的“一种新的有关法律和犯罪的理论,一种新的关于惩罚权利的道德和政治论证”,他并未明说,对此,罗森(Rosen)在《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第十九章中曾加以概述,即“18 世纪后半期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哲学思考的发展,重点是孟德斯鸠、贝卡里亚与边沁的著作……把这些重要思想家的哲学观点与那些更为现实的讨论,主要是在英国进行的讨论联系到一起,这些讨论涉及废除死刑以及诸如流放和监禁等各种替代惩罚方式”。[1]《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主编,刘北成、马万利、刘耀辉、唐科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27页。显然,罗森所考察的孟德斯鸠、贝卡里亚和边沁等人的刑罚思想应该属于福柯所说的新理论和新论证。它们的共同之处或可概括为“将个人自由问题作为立论的基础”,并强调“惩罚的确定性要比严厉性更重要”,以及“罪罚相称的观念或惩罚分级的观念”。[2]《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主编,刘北成、马万利、刘耀辉、唐科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31,541,543页。当然这些思想家之间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仍具有很大的不同。在新时代,就像福柯所洞见到的那样,“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3]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版,第7—12页。
显然,这也正是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这种变革自然就构成了他思考刑罚问题的历史语境。正如福柯所描述的时代转变一样,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就开始关注“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思考监禁制度,关注普鲁士刑罚制度的改革。在对《卡特密信》的翻译和评注中,黑格尔曾就书中提到的某些刑事制度做了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比如针对瓦特和本邦德语居民部分实行不同的刑事制度,黑格尔强烈批评了那种刑事审判权由政府掌控的情况,他强调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立的必要性。黑格尔还针对当时刑事讼诉程序上的一些不正当表现作了批评。[4]见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薛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在大约1795年,黑格尔从福斯特(Forster)的《来自莱茵河下游的观点》(Ansichten Vom Niederrhein)中摘抄过福斯特对于监禁制度(Gefängnißwesen)的看法。福斯特强调,“人格的自由”(die Freiheit der Person)比单纯活着更重要,前者才无可争议地是“与人的规定不能分开并因此不能转让的善”,监禁(甚至终生监禁)的初衷是对犯人进行道德改造,使他们悔罪等,但实际情况是它往往并不能达到这些目的,因为在监禁中,人格自由被压制了。[1]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3, hrsg.von Friedhelm Nicoli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1) , S.217, 293-294。根据罗森克朗茨的记载,黑格尔曾对普鲁士邦法改革中的监禁制度表达过一些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下这段话:“隔绝和人交往是正当的,因为罪犯已把自己孤立起来。用冷冰冰的理智,把一些人时而看作能劳动和能创造的东西,时而又看作须得改良的东西,并且指令人们这样做,这会成为最可恶的暴政,因为整体的福利作为目的如果并非是正当的,就对这些人是异己的。”[2]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薛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2, hrsg.von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4) , S.586。不能确定黑格尔的这个片段是写于伯尔尼时期,还是法兰克福时期,对此见S.663。黑格尔在这里似乎表明了监禁的某些正当性,但他否定从手段方面来理解人,相反要从人是目的这个方面来理解刑罚的本质和目的。黑格尔还专门写过关于公开实施死刑的思考片段,他反对基于预防犯罪和教育民众的刑罚理论而为公开实施残暴的死刑辩护。他最后强调,如果公民拥有正当的权利,那些因不公开实施死刑而引发的不安(如法官实行不法)就会消失。[3]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2, hrsg.von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4) , S.602-604.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论述集中体现在《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二卷Text 55,它是所谓的《基督教的精神》(Text 52—Text 60)这组文本中的一篇。构成这组文本的哲学基础的其在伯尔尼后期和法兰克福初期从康德式主体哲学所转向的统一哲学(Vereinigungsphilosophie)或生命哲学,这主要表现在《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二卷Text 40—Text 42 以及Text 49 中。一般认为,黑格尔之转向统一哲学与荷尔德林以及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有密切关系。[4]参见朱学平:《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青年黑格尔思想的形成与演进》,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4—75页;罗久:《黑格尔论命运与惩罚——早期文本中的康德批判与同一哲学的构想》,《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 期,第107页。值得注意的是,荷尔德林在1795年初也写作了一个与惩罚有关的片段,即《论惩罚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Straffe)。黑格尔对犯罪与刑罚的论述或许也受到了这个断篇的影响。简而言之,这种统一哲学强调存在一个“先于意识和自我的统一”,这种统一先于一切对立,它是一种源初的统一,它也被称为“存在之一般(Seyn schlechthin)”,这是一种本体论原则。反思或判断(Urtheil)[1]在司法中就表现为审判。意味着源初统一性的分裂,即主体和客体的分裂。[2]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 卷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为了克服这种分裂,我们要“倒回去设定一个更高的统一性”。[3]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 卷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0页。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和费希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就是分裂的表现。为了克服这种分裂,黑格尔提出“爱”的概念和生命哲学体系:“只有在爱里面人才是同客体合而为一的。”[4]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2, hrsg.von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4) , S.9;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4页,译文稍有改动。在生命哲学中,生命“从这种未经发展的合一出发,经过曲折的圆圈式的教养(Bildung),以达到一种完满的合一。”[5]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9页。根据这种统一哲学或生命哲学,康德所谓的道德法则和法律(包括司法审判和刑罚处罚)在本质上就不是源初的统一或生命的统一,而是内含着对立的统一,即对立面在一个概念里的统一,因此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对此,黑格尔提出用爱来扬弃道德和法律。由此,黑格尔直接推论出用爱来扬弃刑法和刑罚的主张,并提出作为命运的惩罚的概念。
二、爱对犯罪和刑罚的扬弃
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在《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二卷Text 55中直接针对了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部分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思想。[6]康德于1797年分别出版了《法权论之形上学根基》和《德行论之形上学根基》,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根据罗森克朗茨的报道,黑格尔从1798年8月10日开始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作了评释,于是可以猜测,黑格尔在这里对刑法和刑罚的批判针对的是康德该书《法权论》第二篇(“公法”)第一章(“国家法”)中的“惩罚的法权与赦免的法权”。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惩罚的法权与赦免的法权”中首先对惩罚的法权与犯罪(Verbrechen/crimen)作了定义,并区分了私人犯罪(Privatverbrechen)与公共犯罪(öffentliches Verbrechen)——前者是对私法的违反,后者是对公法的违反。[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343页。原文参见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Bd.6, hrsg.von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4) , S.331。康德还区分了司法的惩 罚(Richterliche Strafe)与 自 然 的 惩 罚(natürliche Strafe)。[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013年,第343页。司 法的惩罚不能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而使用,而只能因为有人犯了罪,因为人不能是手段,而只能是目的。因此惩罚只能来自刑法(Strafgesetz)所规定的“应当”。对于刑法,康德强调,它是一项定言令式。因此它是普遍的、确定的、必然的。刑罚正义就在于刑法本身的满足,即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处罚,其他任何试图免除刑罚或减轻刑罚的行为都是不正义的。康德进一步指出,刑罚的原则是对等(Gleichheit)原则,即罪犯给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他自己就要受到同样的伤害。就此而言,“只有报复法权(Wiedervergelgungsrecht/ ius talionis [罪罚相等的法权]),但听好了,是在法庭面前(而不是在你的私人判断中)的报复法权,才能明确地规定惩罚的质和量;其他一切法权都是摇摆不定的,而且由于其他种种干预性的考虑,不能与纯粹的和严格的正义之判决相符合”。[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013年,第344页。康德尤其强调要对杀人犯判处死刑,“在此并无任何替代物可以满足正义”——但要禁止任何形式的虐待。[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页。他批判了贝卡利亚基于人道的同情性伤感而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
在Text 55 中,黑格尔也首先讨论了犯罪与刑法。从字面来看,犯罪(Verbrechen)行为当然就是指违反了法律(Gesetz)规定的行为,或者说做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杀人违反了“不要杀人”这条法律,偷窃违反了“不要偷窃”这条法律。很明显,犯罪行为损害了法律的内容,并因此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针对犯罪行为,为了补救法律的统一性,也为了对受害人进行救济,法律往往都作了相应的刑罚规定,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最古老的同态复仇规定。这种针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就是“刑法”(strafendes Gesetz)。[1]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9页;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2, hrsg.von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4) , S.182。本文按一般理解将“strafendes Gesetz”译为“刑法”,或许将其翻译为“惩罚法”更好一些,因为它既包括客观的、实定的惩罚法,也包括主观的“愧悔的良心”(böses Gewissen)。即使仅就实定的惩罚法而言,它也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刑法。黑格尔在这里似乎没有区分现代意义上的侵权与犯罪,而只是强调应对犯法者给予何种惩罚以及给受害人何种救济。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使用的“strafendes Gesetz”类似于罗马法中的惩罚法,对于后者可参考王华胜:《罗马法中的“刑法”与“惩罚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 期。但在Text 55 中,黑格尔似乎主要是就杀人这种最极端的犯罪行为来讲述惩罚与命运的,因此将其翻译为“刑法”也有道理。
与一般的法律一样,刑法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必然性和强制性。对于个人而言,在他未犯罪时,刑法主要是一种恫吓性、警告性的存在。当他犯罪后,刑法既不能赦免罪行,也毫不留情,否则它就把自身给取消了,因为这是与它的性质相悖的。[2]黑格尔还曾形象地指出,罪犯以为破坏了刑法的内容后,他就成了法的主人,但因为刑法的形式仍旧存在,所以刑法现在就按照规定对罪犯施加刑罚,此时刑法变成了惩罚人的具体行动的形式,即刑罚,而不再是恫吓的静止形式了。(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页。)根据对等原则,罪犯所受的刑罚就是“丧失同他由于犯罪而损害别人的权利相等的权利”。[3]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3页。把罪犯施加给别人的伤害同等地返回到他自己身上,这就是法律上的公平和正义。黑格尔还指出阻碍刑罚正义实现的几种可能性,比如刑法本身仅仅是一种概念性规定,所以它仅仅还只是一种应然状态,为了使惩罚成为现实,刑法必须与享有权力的执法者(Exekutor)和法官(Richter)等有生命者联系起来,而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使刑罚正义的实现成为偶然的。[4]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3—394页。
很明显,黑格尔上面关于刑法的性质以及刑罚正义的实现的论述,与康德关于刑法的性质、对等原则和刑罚正义的讨论差别不大。但黑格尔下面就开始从统一哲学角度直陈刑法、刑罚和正义本身的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之道:爱一方面扬弃刑法的形式,另一方面扬弃它的内容,即刑罚和正义。
黑格尔强调,刑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使得和解成为不可能:不论是罪犯与受害者或复仇者之间的和解,还是罪犯与刑法之间的和解,都不可能。具体来说,对于罪犯而言,客观的、实定的刑法是异己的力量和敌对的存在。刑罚的实施并不代表罪犯与刑法的和解,它只能使刑法得到满足。在这之后,刑法就仍旧返回到它一开始针对所有人的恫吓形象,而没有成为友好的东西。[1]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4—395页。就此而言,惩罚之前、惩罚过程中和惩罚之后,罪犯与刑法一直处于对立、敌对状态。在刑法面前,罪犯就只是罪犯,是罪恶的存在,是孤立的人,似乎与人类无关,这个孤立的人受到刑罚就是事情的全部。
对此,黑格尔指出,只有从生命、命运和爱等角度来理解犯罪和刑罚,才能有和解。从统一哲学或生命哲学来看,在犯罪行为之前,不存在分离、对立和统治他的东西。[2]黑格尔强调,作为全体和统一的生命既不由法律所调整,也不是不法的(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7页)。犯罪就等于脱离统一的生命、杀害生命。比如,杀害了别人的生命并不是指把别人的生命变成无,而是指整体生命的分离(Trennung),把生命变成自己的敌人:“生命是不死的,生命被杀害了的它就表现为它的可怕的鬼魂,这个鬼魂要维护生命的每一方面,报复任何仇恨。”[3]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7页。最后一句直译就是:“这个鬼魂要使它的一切方面都是有效的,抛弃它的仁慈。”(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2, hrsg.von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4) , S.190)比如在《麦克白》中,麦克白谋杀了班科,但班科并不因此不存在了,他作为恶的鬼魂重新出现在麦克白的宴会上,宣告麦克白的命运。[4]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7页。参见莎士比亚:《麦克白》,第四场第三幕。
从统一哲学或生命哲学来看,“生命不与生命相区别”,所以罪犯对异己生命的杀害就是罪犯对自己生命的摧毁。他摧毁了生命的友好性,生命成为他的一个敌人或异己的力量。[1]换一种说法就是,犯罪是对本性(Natur)或统一的破坏,就此而言,侵害者与被侵害者所遭受的破坏同样多。这就是命运或作为命运的惩罚。被伤害了的生命作为一个反对罪犯的敌对力量,虐待罪犯,就像罪犯之前所做的一样。就此而言,作为命运的惩罚就是罪犯本身的力量反作用于自己。
但与刑法上的惩罚不同,命运或作为命运的惩罚能够得到和解,因为“命运是在生命的范围之内发生的”。[2]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7页。作为生命、统一整体的分离,命运或作为命运的惩罚是人对自身的侵犯,因此可以返回到自己的生命和爱。用更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生命可以重新医治它的创伤,使分裂了的敌对的生命重新返回到自身,并且可以扬弃犯罪行为的罪过、扬弃法和惩罚。”[3]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8页。具体说,在作为命运的惩罚中,罪犯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摧残,这也是对被摧毁的生命的感觉,这种生命感就是爱。罪犯重新认识到生命,因此罪犯对那业已失去了的生命产生一种渴望(Sehnsucht),即渴望返回到生命本身。只有通过“愈益强烈的爱”,犯罪行为引起的命运才能停止。[4]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6页。这就是命运在爱中的和解。
就此而言,对命运的恐惧是对分离的恐惧,是对自己本身的害怕。而对刑法中惩罚的恐惧,则是对一个异己的东西的恐惧。[5]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8页。同时命运的和解意味着罪犯的矫正(Besserung),因为命运的惩罚让罪犯产生对生命之丧失的感觉,使他认识到,丧失了的东西是生命,是一度对它很友好的东西——这种认识本身就是生命的享受本身。而刑法的惩罚并不能使罪犯有所矫正,因为刑罚对罪犯而言仅仅是一种受苦,让他产生一种无力感。[6]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9页。
三、比较与反思
与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的刑罚理论相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论述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所阐述的刑罚理论具有更多类似性。首先,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和康德都强调意志自由(个人自由或主体性)是刑法和刑罚强制之正当性的前提。其次,刑罚的目的仅在于恢复受到侵害的法,刑罚的本质规定是报复。而在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作为其刑罚理论前提的不是意志自由,而是生命的源初统一。粗略而言,意志自由对应着主体性,生命的源初统一对应着实体性。从这种实体性原则出发,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就强调,以主体意志自由为基础的刑法及其规定的刑罚在本质上内含着对立、分裂和强制,刑罚正义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幻象。为此,他才提出一种没有强制的惩罚,即作为命运的惩罚。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让犯人产生一种内在的悔恨和对恢复统一的渴望。只有这种惩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
这也表明,虽然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批判了康德的刑罚理论,但他后来其实在某种程度又回到了康德。一般认为,黑格尔到了耶拿后期才重新以康德式的主体性或意志自由作为其法哲学的基点。[1]朱学平:《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青年黑格尔思想的形成与演进》,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258页。这说明,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囿于一种源初的实体性原则之中,还没有把主体性原则作为其体系的出发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黑格尔此时并不像后来那样是在法哲学意义上来讨论刑罚问题的,而是在宗教意义上来论说的。简而言之,在《基督教的精神》这组文本中,黑格尔写作的思路是“德行—爱—宗教”,即德行、法律(包括审判和刑罚)被爱所扬弃,然后爱与反思综合到宗教之中。这种思路决定了黑格尔此时不可能在一般法律意义上来讨论刑罚问题。也就是说,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把爱和法律以及道德和法律混在一起,而到了成熟时期才对它们进行划界。
虽然成熟时期的黑格尔与康德在刑罚的前提和本质问题上具有诸多类似之处,但不可否认,两人在论述上仍有一些差别,而这些差别可以部分追溯到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的讨论。一方面,与康德不同,黑格尔非常强调刑罚所具有的和解作用,即通过刑罚,被破坏的法同自身得到和解,犯人同自身得到和解,而和解正是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从爱、生命和统一出发所特别强调的。另一方面,在《法哲学原理》中,在论述完强制和犯罪后,黑格尔就从抽象法过渡到道德上去,而这与康德的叙述方式显然不同。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或许也与他在法兰克福时期的刑罚思想相关。在法兰克福时期的文本中,黑格尔将刑法规定的刑罚转变为作为命运的惩罚后,外在的强制就转化成了内在的悔恨。后续在谈到如何面对侵害时,黑格尔提出了主动放弃权利并退回自身的“灵魂之美”(Schönheit der Seele)。[1]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2—403页。这似乎类似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到的从犯罪向道德(主观领域)的过渡——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是从意志自身的发展来论述这种过渡的。
虽然黑格尔很快就否弃了从统一哲学或生命哲学出发对刑罚的讨论,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些讨论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意义。一方面,如何克服法律本身的强制性,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在中外法学理论史上不断出现。就西方法学理论而言,爱和法律常常被对置起来加以讨论,这说明了用爱来克服法律的强制性并非仅仅是青年黑格尔自己的主张。这种回答的经典版本当然就是黑格尔此时所借用的耶稣之爱对犹太律法的克服,这个版本也一再被拿出来加以运用,黑格尔所做的只不过是给这种回答赋予了生命哲学或统一哲学的论证。另一方面,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示,黑格尔正生活在欧美刑罚思想和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的刑罚思想或许可算作是对这场变革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虽然不同于康德、贝卡利亚和他后来所强调的自由意志、刑罚确定性和罪罚相称原则等,但它似乎也符合福柯对这场变革的判断,即刑罚对象主要不再是肉体,而是转向了诸如权利和灵魂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