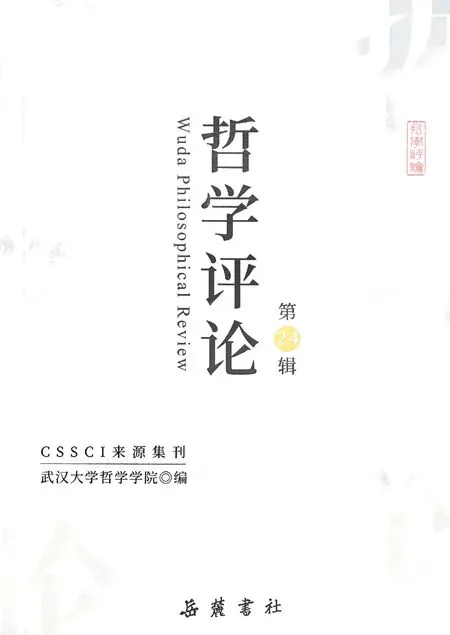胡塞尔意识概念的多重意蕴:意识、前意识、无意识
2019-12-14陈志伟
陈志伟
一、导 言
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哲学,从总体上看,可以被看作为是意识哲学。意识,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核心范畴:意识是现象学的研究起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范围、研究的最终归宿和目的。胡塞尔一开始的就通过悬置的方法将外在世界的自在存在的问题悬置起来而存而不论[1]胡塞尔说道:“为了对抗这类谬误,我们必须坚持依靠在纯粹体验中的所与物,并将其置于明晰性的范围内,正如它所呈现的那样。于是“现实的”客体应被“置人括号”。”,明确的表示,只有在意识范围之中意识现象才是现象学所关心的问题,所谓的外在世界的
HUSSERLIANA BAND III,1,S .187; 中译文参见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4页自在存在的问题要被最终还原到意识范围的内部,即外在的事物最终被还原为先验自我在意识范围之中所构造出来的“看起来”外在的事物,其所谓的“外在性”本身只不过是意识构造的一个特点,意识将之构造为显现地外在于意识,但是其终究还是内在于意识范围之中的。可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所研究就是意识范围之中的意识现象。意识是现象学的原起点,“现象学”这个名词中的“现象”所标识就是意识现象。而胡塞尔所进行的现象学的研究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构建起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为人类的知识在意识中找到最终的奠基点。因此,称他的哲学为意识哲学、关于意识的哲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我们知道意识哲学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从古希腊以来就有关于努斯(Nous)的探讨,进而又有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对于“心灵”的探讨,以至于伯格森的绵延、尼采的权力意志、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等等,无不是对于意识领域的哲学探索。那么,胡塞尔的意识哲学相对于历史上的这些意识哲学有何独到之处呢?他是否对意识本身有什么新的发现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哲学史上似胡塞尔早有定论,即胡塞尔对于意向性以及本质直观的方法的发现等等。萨特说道在《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一文中说道:“这种意识作为对与自我不同的东西的意识存在的必然性,胡塞尔称之为意向性”,海德格尔说道:“关于现象学的决定性的发现,我们要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意向性,第二是范畴直观,第三是先天的原本意义”[1]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页。。然而,不管是萨特还是海德格尔都是从一个特定的意识角度来谈论胡塞尔的意识的,即对象化的意识的角度。在这里,他们并没有从总体上对胡塞尔的意识进行仔细的区分,他们对胡塞尔的意识这种评价还仅仅停留在静态现象时期的对象化的意识的范围之中。实际上,进入到发生现象学时期的胡塞尔对于意识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发现,重新发现了意识所具有的更深层次的新的维度,而且,正是这种新的深层次的维度才为表层的对象化的意识奠定了最终的基础。胡塞尔对于意识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发现了意识当中的意向性。具有意向性的意识仅仅是意识的第一个层面即对象化的意识,在对象化的意识之下还有前对象化的意识以及更深层的无意识。只有借助于发生的视角,进入到胡塞尔的前意识和无意识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清晰的看到胡塞尔的意识理论的进步意义。在笔者看来,这种进步的意义首要的是从发生的维度中彰显出来的。其从发生的角度对于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发现和探讨,或许具有相对于静态的现象学时期的意向性更大的意义。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在对对象化的意识进行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到对于前意识和无意识的论述之中。意识的三种维度中的后两者,前意识和无意识将是我们所着重论述的,是我们分析的重点。这一方面是因为,哲学家和研究者们过分的偏重于第一个的层面的意识,而忽略了最后两个层面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因为,如果我们从发生的角度去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处于底层的前意识、无意识是表层的对象化意识的最终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前对象化的意识的基础上,对象化的意识才最终的得以可能,才最终能够成为“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一、对象化的意识
在此,首先需澄清的是,胡塞尔自己本人并没有在专门的意义上将意识划分为三重的维度: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这种划分,是笔者在仔细阅读胡塞尔自身的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在此笔者仅仅是抛砖引玉,至于这种划方式是否合理,还有待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不过,虽然胡塞尔本人并没有在他的书中明确的提出这种对意识的三重的划分,但是,如果我们从发生的角度对其意识思想进行仔细的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他本人确实在这三种意义上展开对于意识的讨论。当然,最为熟悉的首先是意识的最表层的、最明显的第一个维度,即对象化的意识的维度。这种意识的维度指的是:对象化的意识,即按照“意向行为——意向对象”的认识模式所进行的,对于某个特定对象的认识。胡塞尔关于意识的论述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关于这种对象化的意识的论述。尤其是在静态现象学时期,这种对象化的意识一直都居于主要的地位,虽然在其中也有一部分关于前意识的论述。在从《逻辑研究》到《观念I》的静态现象学时期,胡塞尔所认为的“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就是对于这种第一层次的意识的核心的概括和描述。其中的某物,指的就是意识所意向的对象,而对这个某物的指向行为则是意识行为。也就是说,这种意识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结构特点就是意向性,也即意识行为总是指向某个对象。这种层次上的意识是我们所最为熟悉的,也是最为容易理解的。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意识所遵循的依旧是主体、客体的模式,意识只不过是主体对客体的指向。《逻辑研究》中对意识的探讨总体上所遵循的模式就是:立义——立义内容的模式,而这模式背后所隐含着的依旧是主体、客体的区分。而在《观念I》中,胡塞尔对于意识的探讨,则总体上采用的是意向行为(Noesis)——意向相关项(Noema)的模式。同样,在这种模式背后所隐含着的依旧是主体、客体的区分。而且,甚至在“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发现上,胡塞尔也并不是第一人。
那么,在对象化的意识的这个层面,胡塞尔的进步的意义在哪里呢?他是否对意识有所推进呢?在笔者看来,尽管此时他仍旧处在主客体的传统的思维模式之中,但他仍旧在意识领域之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种突破的意义首先在于:主体和客体不再是分属于两个领域中的不同事物,主体和客体都处在同一个领域之中,即都处在意识的领域之中。由此,也就避免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主体意识如何超出意识自身的范围而通达到意识范围之外的客体对象。实际上,由于意识领域和非意识领域的区分和它们之间的异质性,要想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关联,进而使得非客体的意识能够“认识”客体本身,是非常之困难的,甚至是西方几千年以来的认识论所一直难以回答的难题。[1]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的考察这个难题的前提的话,就会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难题就是因为意识中的主体和非意识的客体之间的本体论上的区分。因此,关键不在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在于对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的前提条件的考察。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重要的不在于问题的回答,而在于问题的化解。对于这个问题,现象学给出了不同的回应:在胡塞尔那里,通过悬置的方法,而将意识之外的客体悬置起来,将客体还原到意识范围之中,进而把问题转换为主体在意识之中对客体的构造;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个问题则完全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Dasien 的存在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Dasein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Da,一个境域、一个缘在场,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之点,Dasein 从源头上就存在在一个因缘关联体之中,并对这种关联性有着存在论上的最本源的领会。因此,认识论上的问题本最终要还原到存在论的基础上,并在基础存在论中得到了化解。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所谓的认识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在存在论上定错了方向。在胡塞尔那里,问题变成了:意识如何构造出意识对象。进而,胡塞尔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沿着意向性的角度对意识的意向性结构和构造的功能进行探讨。意识的对象本身就处在意识的范围之中,并且,是意识的构造活动的产物,因此,在二者之间当然不存在者所谓异质性的鸿沟的问题。意识不需要超出自身去认识在自身之外的某物。对于认识何以可能以及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问题,胡塞尔的所采取的思路是:先验自我通过本质直观的方法在具体项的基础上,构造出不同层级的本质范畴(形式本体论和区域本体论),并把这些本质范畴以及其中的公理作为认识先天条件来指导认识,进而形成普遍必然的本质知识。
关于胡塞尔在意向性上所做的推进,已经有了非常之充分的论述,在此我们不想再做重复工作。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意向性的结构隐含着的前对象的、前意向性的因素。根据胡在《观念I》中的论述,意识的基本结构可以展现为: 意向行为——意向内容。而这种意向结构相对于《逻辑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中的意向内容这个环节也具有了其自身的结构——对象本身(X)、内核、晕圈。而且,意向行为对于晕圈的指向仅仅是一种附带的指向,它同意向行为对于意向对象的指向在本质上不同。实际上,它是一种前对象化的指向。另外,意向行为本身对其自身也有着一个基本的的体验(erleben),这种体验也不同于对于一个对象的指向,这种体验并不是一种对象化的行为,而是一种前对象化的行为,因此也以归到前意识当中。在此,我们仅做简单的提示,在下文中将做出具体的论述。
二、前意识
所谓的前意识指的也就是前对象化的意识,在对象化之前的意识。胡塞尔自己本人并没有经常的使用前意识这个词语,但是,在胡塞尔那里有前对象、前自我、前意向、前谓词等类似的表述。在此,我们暂且使用前意识这个词来表示尚未进入到对象化层面的,处在对象化之前的意识。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看,严格意义上的、与自我相对应的对象,是有着其漫长的发生历史的。从最初的被动性的、处在发生的最低层的内时间中的感性材料(尚没有对象和自我的区分)到自我通过主动的意向行为所明确的指向的对象,需要经过众多的发生性环节,如,内时间意识——原联想(Urassoziation)——凸显(Abhebung)——触发(Affektion)——朝向(Zuwendung)——注意(Aufmerksamkeit)——朴素的把握和观察(说明性观察、关系性观察)等众多的环节,意识的构造过程同时涉及到被动性与主动性,“在横向上,‘构造’涉及被动性领域和主动性领域的动态关联方式。”[1]韩骁:《胡塞尔“构造”概念的三种图式》,《云南大学学报》,2018(6)。。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告诉我们的是,在对象化的意识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的、更为深层的前对象化的意识。正是这种前对象性的意识才从发生学上为对象性的意识奠基了基础,使得对象性的意识得以可能。
在此,笔者试图结合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和静态现象学中的相关论述,对之从总体上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并尤其注重突出发生最底层的内时间意识的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从两方面对之进行介绍:对于晕圈的附带的意识、意向行为的自身体验。
(一)对于晕圈的附带的意识——以《观念I》为例
在此,我们以胡塞尔自身的一段话来开始我们对于晕圈的附带的意识的论述。胡塞尔说道:
“作为一种感知活动的严格意义的感知中,我朝向对象,(例如)朝向那张纸,我把它把握为这个此时此地的存在物。把握行为(Erfassen)是一种选出行为(Herausfassen),任何被感知物都有一个经验背景。在这张纸周围有书、铅笔、墨水瓶等等,这些被感知物也以某种方式在“直观场”中被感知为在那儿;但当我朝向这张纸时,我一点也未朝向和把握它们。它们显现着,但未被抽出,未因其本身之故被设定。每一物感知都以此方式有一背景直观的晕圈(或“背景看”,如果人们已在把被朝向物包括进直观中去的话),而且这也是一种“意识体验”,或者简单说,“意识”,特别是“关于”一切事实上存于其一同被看的客观“背景”中的意识。但是显然,我在这样说时并未谈论那种应在可能属于被看背景的客观空间中被“客观地”发现的东西,也并未谈论有效的和向前涌进的经验可能在那儿发现的一切物质物和物质事件。”[1]HUSSERLIANA BAND III, 1, S .62; 中译文参见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9—120页。
在这段话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的几点:我对于一个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当下的朝向是感知[2]在胡塞尔的理论体系中,对于对象的朝向、把握的对象化的行为可以分为感知、回忆、期望、想象等行为,其中感知居住最为主要的地位,因为在感知中可以获得最为充分的对象物的“被给与性”。因此,前对象的前意识是完全不同于感知、回忆、期望、或者想象等对象化的行为的。;而感知对象必然的处在一个背景域中;这种背景域或者晕圈虽然显现着,但是却并未被抽出,也就是并未被对象化;对于这种背景域的意识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体验”;对于背景域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意识,进而晕圈也非客观物。显然,通过对于上面的这段话的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对于晕圈的意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于对象化行为的,它不同于感知,也不同于想象、回忆等对象化的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一种像感知行为那样的朝向、指向、把握的行为,“我一点也未朝向和把握它们”,对于晕圈的意识并非是对象化的意识。于此相应,晕圈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象,它还处在对象之前,还没有被对象化,“它们显现着,但未被抽出,未因其本身之故被设定”。在此,有必要专门的对“体验”进行一个简短的说明。在《观念I》中的体验,可以分为意向性的体验(即对象化的意向行为)和非意向性的体验(前对象化的意向行为),或者分为实显的体验(也即意向性的体验)和非实显(非意向性的体验)的体验,而且这两种体验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对象性的体验必然的伴随着前对象性的体验。胡塞尔说道:“非实显的体验的晕圈围绕着那些实显的体验;体验流绝不可能由单纯的实显性事物组成。正是这些实显物在与非实显物对比时,以最广泛的普遍性(这可能超出了我们例子的范围)决定着“我思”、“我对某物有意识”、“我进行着一种意识行为”这些词语的隐含意义”[1]HUSSERLIANA BAND III,1,S .63; 同上, 第121页。、“连续不断向前的思维链索连续地为一种非实显性的媒介所环绕,这种非实显性总是倾向于变为实显样式,正如反过来,实显性永远倾向于变为非实显性一样”。[2]HUSSERLIANA BAND III,1,S .64; 中译文参见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2页。
不同于在《逻辑研究》中对意向行为和意向内容之间的简单的区分,在《观念I》中,胡塞尔对意向内容的结构作出了卓越的洞察:意向内容本身也具有自身的结构,意向内容的内核必然的被晕圈所环绕。这也就意味着,对象必然伴随着前对象的东西,而对象化的行为也必然的伴随着前对象化的行为。因此,从静态现象学时期开始,前对象性的意识也即前意识已经是一个必然性的环节了。但是,在此需注意的是,作为对晕圈的附带性意识的前意识,还仅仅是对象性的意识行为的附带物,它还是从属于对象化的意向行为的,而并非居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而晕圈以及对于晕圈的意识最终还可以转变为意向对象和意向行为。另外,从篇幅上讲,胡塞尔在大观念中对于晕圈的论述也仅仅出现在35 节、67 节等少数的几个章节中,并非是论述的主要的主题,胡塞尔此时关注的重心无疑还是在对象化的行为上面的。
(二)对于意向行为自身的体验——以《逻辑研究》为例
对于意向行为自身的体验,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领域,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了意向行为所指向的意向对象上了,而对于指向意向对象的意向行为本身却缺乏关注。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在看的电脑的时候,我不但看到了电脑,同时也知道“我在看”,即我对我的“看的行为”有一个基本的体验,虽然这个体验还不是一个对象化的体验(我尚未将我的“看的行为”当作一个主题对象进行反思,主题是看的对象)而仅仅是附带的体验,但是,它却不可或缺地必然的伴随着我的任何的一个意向行为。因而,完整意义上的意向性的结构不仅包括意向行为对意向内容的指向,即意向行为——意向内容,而且还包含对于对意向行为的自身的体验。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对意向行为的自身体验和对意向对象的指向,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前意识(前对象化的行为),一个是对象性意识(对象化的行为)。
在此,我们依旧从胡塞尔自身的文本出发。下面是从《逻辑研究》中可以找出的,能够最为清晰将这种差别展现出来的一段话:
“感觉以及对它进行“立义”或者“统摄”的行为在这里被体验,但是它们并不对象性的显现出来;它们没有被看到、被听到,没有被带着某个“意义”被感知。另一方面,对象则显现出来,被感知,但它们没有被体验。不言而喻,我们在这里要排除相即感知的情况。”[1]E.Husserl: LU II/1, A363/B1385.中文版参看,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良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第451页。
在这里,处于描述现象学时期的胡塞尔所使用的术语同先验构造现象学时期的所使用的术语略有不同,大致而言,前者的立义——立义内容同后者的意向行为——意向内容相互对应。这段话中所说的“立义”或者“统摄”的行为实际上也就是意向行为。其中,在这句话中,我们要尤其注意胡塞尔自己所加的带有着重号的地方,实际上,其中蕴含着如下的逻辑关系:“意向行为、被体验、前对象性”——“意向对象、显现(被感知)、对象性”。也就是说,意向行为只能被体验,而不能被感知、或者显现,因为它是前对象的,而这里的体验行为也是一种前对象性的行为;意向对象只能被感知或者显现出来,而不能被体验,因为它是对象性的,而感知、显现等则是对象化的行为。
也就是说,通过对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这段话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意向行为自身的体验是一种前意识,完全不同于作为对象性意识的感知、显现等。而且,这种前意识的行为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甚至于比对象化的行为还要普遍。我们所进行的任何的一个意识行为都伴随有对于这个意识行为本身的体验,因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我们在进行着某种意识行为。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我进行了某种意识行为,但是我对这种意识行为的进行却一无所知。如果我对某种意识行为的进行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种意识行为是“我的”意识行为。但是,却可能存在着没有特定的对象的意识行为。例如,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可能会感到莫名的忧伤、突然的喜悦等等,在这些意识行为当中并不存在着特定的意向对象。胡塞尔说道:“似乎并非每一个欲求都要求一个与被欲求之物的有意识的关系,因为我们常常活动于一些含糊的要求与渴望之中,而且,追求一个未得到表象的终极目标;并且,尤其是如果人们指明那些自然本能的广泛的领域,这些本能至少在原初时缺乏意识的目标表象”[1]E.Husserl: LU II/1 , A373/B1395.中文版参看,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良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也就是说,胡塞尔自身实际上也是承认存在着没有特定的意向对象的意识行为。但是,即便对于这样的没有特定对象的意识行为来说,我们对这种意识行为本身也是有着体验的,例如,我知道我在感到莫名的悲伤,虽然我暂时还不知道我到底为何而悲伤。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作为意识行为自身的体验的前意识有着更为广泛的普遍性。
但是,在此我们紧接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将这种没有特定对象的意识行为也看做是前意识,甚至是前意识的重要的一类呢?在此,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实际上,此种意义上的没有特定对象的意识行为可以看做是变样了的对象化的意识行为,它同对象化的意识行为处在同一个层面上。严格来讲,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意向行为所意向的对象,而是在于是否意向着一个明确的、特定的对象。实际上,二者都是意向于某个对象的,只不过一个是泛泛的指向,一个是明确的指向。我之所以莫名的忧伤,总是有所原因的、有所指向的,虽然我暂时还不明确的,但是,它总是指向“某”物,而不是无所指。对于这一点胡塞尔自身也有着明确的认识,胡塞尔说道:“或者我们说:这里所涉及的虽然是意向体验,但这些体验[应当]被描述为具有不确定朝向的意向,在这里,对象朝向的‘不确定性’不具有匮乏的含义,而是必然标志着一个描述性的特征,亦即一个表现特征”[1]E.Husserl: LU II/1 , A373/B1396.同上,第462页。,“而这个”不确定性“在这里属于这样的一些意向本质,这些意向的确定性恰恰在于,表象一个不确定的某物”。因此,虽然此种行为所意向的对象是不确定的,但是这种对某物的意向却是确定。这种没有特定对象的意识行为从本质上仍旧可以被认为是属于对象化的行为的。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意向行为自身的体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现象学之能够成立的基础。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对意向行为的体验,那么,对我们将无法知道我们具有意向行为,从而我们也就无从知道我们的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无从知道Neosis-Neoma 中的Neosis。在此我们仍旧有必要出一个严格的区分:对意向行为的体验不同于对意向行为所进行的反思。当我们要对意向行为进行研究的时候,必然要对之进行反思,但是此种反思的行为已经是一种对对象化的行为了,是一种指向意向行为的行为(对意向行为的反思以意向行为为对象)。而意向行为的自身体验却没有指向任何的对象,处在任何的对象化之前,“它们并不对象性的显现出来”。
三、无意识
(一)对无意识的界定——以《被动综合分析》为例
在上文中,我们从意识追溯到处在意识之前的前意识,但是以上的意识都是“清醒的”“明亮的”意识。对象化的意识自不用说,它必然是清醒的意识;前意识虽然处在对象化之前,但是,它依旧在某种程度上是清晰的、明亮的。例如,就对晕圈的意识而言,而然它并不处在最为明亮的核心,但是,作为环绕核心的周围区域,它仍然被附带的“照亮”,并且可以转变为对象化的意识,从而被完全的“照亮”,这个过程,我的意识也始终都是清醒的,自我始终都是清醒的自我;对于意向行为的自身体验来说,它也总是清醒自我的体验,我可以明晰的知道“我在看”、“我在听”;对于内时间意识中来说,其中的处在当下视域中的“滞留—原印象—前摄”也必然是“明亮的”、“清醒的”,因为,在“原印象”中具有最高的“触发性的活力”。但是,如果我们去追问,不断沉降下去的滞留的链条,不断进入到越来越深的过去中的滞留是否还是清醒的呢?其是否能够一直保持为“明亮的”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意识不可能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明亮的,而自我也不可能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清醒的,胡塞尔说道:“在我们的心灵生活的过程中,清醒的生活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除了这种类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一种类型,即深度的无梦睡眠,无意识(Unbewussten)。”[1]HUSSERLIANA BAND XI, S.362.
过渡到发生现象学时期的胡塞尔已逐渐的将无意识的领域纳入到他的视野当中,胡塞尔自身明确的承认存在着无意识的领域,并且认为有必要对并对无意识展开了它的现象学的探讨。胡塞尔说道:“不用我说,这些我们所从事的探究的整个领域都可以被冠之“无意识”的著名标题。因此,我们的思考相关于一个所谓的无意识的现象学”[2]HUSSERLIANA BAND XI, S.154.。而胡塞尔对于无意识的探讨,实际上是顺着对内时间的探讨而来,可以说,无意识是对于内时间的探讨的必然的延伸。具体而言,就是在内时间中的滞留链条随着向着过去的维度的不断的沉降,会经历连续的变样,从滞留转变为滞留的滞留、再到滞留的滞留的滞留,等等。而随着这个过程的持续,滞留会逐渐的沉入到昏暗的领域当中,最终以至于陷入到完全的黑暗之中,而这个黑暗的领域,也就是无意识的领域。
关于无意识,在胡塞尔的语境中,有很多相同或者相近的表达方式,如:背景意识、零度区域、沉睡的意识、零度意识等等。在此,我们从胡塞尔自身的文本出发,去澄清无意识的准确的含义。胡塞尔说道:
存在着一个活力等级,而且这种区分依旧在注意的范围之内。这种等级决定着某种意识和意识等级的概念和与相应意义上的无意识的对立。而无意识所指的也就是意识的活力的零点,而且就像将要表明的,它绝不是一个无。仅仅就触发力而言、就那种恰好以一个正值的触发性为前提的成就而言,它是一个无。因此它无关于那种质性要素的那种零强度式的零,例如声音的强度上的零,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声音的完全的停止。[1]HUSSERLIANA BAND XI, S.167.
在这里我们尤其需注意的是,无意识中的“无”应当如何来理解——无意识的无指的仅仅是意识的触发力的无,而并不是指意识自身的无、意识内容的无。按照胡塞尔的触发力的理论,触发力在当下中达到了它的最高值,当下的意识具有最大的活力,但是,此种活力会随着当下中的原印象向滞留的转变而逐渐的减弱,当滞留过渡为滞留的滞留,随着滞留的链条的不断的向着过去的维度的延伸,这种触发力会越来越趋向于无,当这种触发力完全的没有、成为无的时候,也即跨越过了触发力的零点而进度到触发力的零度区域中的时候,也就进入到了无意识之中。但是,此时的意识虽然完全丧失了触发力(只要有一点触发力就不是无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完全的消失,相反,这种沉睡着的意识还依旧保留着被唤醒的可能性,而它之所以可能被再次唤醒,就是因为它并没有消失——意识当中的意义积淀依旧被保留着,胡塞尔说道:“但是首先:唤醒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被构造的意义实际上还暗含在背景意识当中,被暗含在被称为无意识的非—活跃的形式当中”[2]HUSSERLIANA BAND XI, S.179.。被构造出来的意义在无意识当中依旧得以保留,虽然是以一种不再具有活力的零触发力的方式被保留着,但是我们依旧可以通过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联想综合而对之进行重新的激活。例如,我可以通过主动的回忆来把它重新回忆起来,或者,某一天它突然自己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来等等。在此,无、零点、零度区域等等用来刻画无意识的词汇都是而且仅仅是从触发力的角度而言的,而并非是从意识内容的角度而言的。而这一点也将无意识和被动性区分开来。无意识的区域虽然是被动性的区域,但是,被动性的并不必然是无意识的,在被动性的领域当中依旧可能存在着多多少少具有触发力的意识,例如,可能存在着这种情况:一个意识内容有触发力(不属于无意识),但是这种触发力的强度又没有足够大,没有大到可以对自我极施加足够多的刺激,进而使得自我极朝向并注意它(没有自我极的主动的朝向,因而依旧属于被动性领域)[1]胡塞尔说道:“感觉材料仿佛会对自我极(Ichpol)发出一股刺激性的力量,但是如果这种力量还仅仅是处在一种微弱的状态之中,那么它也就不能够到达自我极(Ichpol),因而,这个刺激对于自我来说并没有起到唤醒的作用。”HUSSERLIANA BAND XI, S.149、“一个旋律虽然响起,但是却并没有对我们造成触发力。”HUSSERLIANA BAND XI , S.155.。
同样,从触发力的角度对无意识的严格的界定,也可以把它同佛洛依德的无意识区分开来。虽然,从表面看来,二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使用的是同样的词汇——无意识。佛洛依德的无意识是一种被压抑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又可以以某种拐弯抹角的方式绕过意识的审查,以一种伪装的方式而逃逸到意识,例如,做梦、口误、丢东西等等。通过对它们分析,则可以窥探到无意识的领域。它之所以被压抑,往往是因为它不符合意识的规范,不为意识所接受,如违背道德的恋母情节等等。胡塞尔虽然也会说到一个意识对于另外的一个意识的压抑或者遮蔽,但是,这的压抑仅仅是指触发力的强的一方对触发力弱的一方的遮盖而言。例如,当下意识的触发力最强,从而它对自我极的刺激和吸引最大,最能够引起自我极的朝向和关注,于此同时,也使得自我极忽略掉了对过去的意识,也即压抑了过去的意识。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意识是随时都可能被重新唤醒的。总之,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论无意识的,虽然二者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
(二)无意识是否可以还原为对象化的意识或者前意识?
在上文中,我们从触发力的角度对无意识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在胡塞尔的语境中,无意识指的就是触发力为零的意识。这种意识丧失了活力的,对自我极不再施加任何的刺激、不能对自我极产生吸引并使得自我极对之具有兴趣并进而朝向它。无意识是没有触发力的黑暗的、沉睡的区域。
在此,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将无意识单列出来作为意识的一个层次,是否是合理的呢?它能否能够作为意识的一个单独的层次呢?对于以上的问题,我们在此将之区分为以下的几个层次:首先,无意识也是一种意识,它处在广义的意识范围之中;其次,无意识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而不可还原到对象化的意识或者前意识之中;无意识可以通过被唤醒而转变为对象化的意识或者前意识。
首先,从广义上讲,胡塞尔的整个的哲学都是对意识现象的探讨,他并不考虑处在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说的,通过悬置、还原的方法,胡塞尔从一开始就已经将自在之物的问题进行了排除和还原。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胡塞尔对无意识领域的探讨也必然属于广义的对意义领域的探讨。另外,在此我们可以从意识的时间河流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如果从发生的角度去考察,就会发现所有的对于意识现象的探讨其实都可以最终回归到对时间河流的探讨上来。例如,所有的对象性的意识都以及对意向行为的自身体验、对晕圈的附带的指向[1]由于对意向性为的自身体验和对晕圈的附带的指向都是必然的和对象化的意识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同时发生和结束。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讲,二者虽然是前意识的,但总是附属于对象化的意识,因而,总是同时间河流的横意向性必然的关联到一起。都可以回归到时间河流的横意向性上来,而内时间河流的自身意识则当然地归属于纵意向性。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无意识,实际上也必然的同意识的时间河流关联在一起,其本身就是丧失了触发性活力的沉降下去的时间河流的滞留链条。因此,它也是可以还原到意识的时间的河流上面去的,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它当然也属于广义的意识范围。
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清醒的、明亮的意识,相反,它已经丧失了全部的触发性的活力,而处在沉睡的、黑暗的区域之中。因而,它不可以还原到清醒的意识当中。而所谓的清醒的意识,在这里也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对象化的清醒的意识、前对象化的清醒的意识。对于上面所说的意识的第一个层面的对象化的意识来说,它是一种主动性的对象化的行为,这种意识意味着自发性的自我通过意识活动对于意向对象的明确的指向,因而,它必然是清醒的意识。而与之伴随的对意向行为的自身体验和对晕圈的附带的指向,虽然是前对象的,但是,对意向行为的体验意味着我总是清醒的知道我在进行的看、听等等的意向行为;而对于晕圈的附带的指向虽然并不清晰和明确,但是,这种附带的指向也总是清醒的自我的附带指向,而且,所附带指向的东西也随时可以进入到晕圈所环绕的内核之中,进而得到明确的、清晰的认识。因此,沉睡的无意识自然无法还原到这些清醒的意识上面去。最后,在内时间意识当中,按照胡塞尔的说法,触发力在当下中达到它的顶点,当下视域是时间河流中最为明亮的区域,这也就意味着,只有环绕着当下的时间河流的区域才是所谓的清醒的意识,而处在触发力的零点之外的滞留链条,则必然的与之相区别,而属于沉睡的区域,也即无意识,因而它必然不同于明亮的当下区域,也无法还原到其中去。但是,不管是对象化的意识、前意识、还是无意识,都可以在时间意识河流中得到解释,都可以最终还原到作为整体的时间意识河流之中(既包含明亮的当下视域,也包括黑暗的零度区域)。
另外,就无意识与对象化的意识和前意识的关系而言,无意识却可以通过重新被唤醒而转变为对象化的意识或者前意识。这是因为,无意识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时间河流的无活力的意义积淀,此种意义在原初形态上(处在当下视域中的时候)可以是对象性的意义也可以是前对象性的意义。随后,这种意义在无意识当中得到了保存。而当它们被重新唤醒的时候,从原则上依旧可以保留着其对象性或者前对象性的特征。
总 结
实际上,不管是意识、前意识还是无意识实际上都可以统一于内时间意识。内时间意识当中包含着前意识、包含着对象性意识,也包含着无意识。下面,我们就对之进行阐述。
内时间的基本的结构就是:滞留—原印象—前摄。滞留、原印象和前摄构成内时间的明亮的当下视域,原印象是这个当下视域的核心,而前摄和滞留则作为晕圈而环绕着这个内核。[1]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内时间的这种视域结构同感知的视域结构具有非常大的类似性。二者都是一个视域,而且都具有一个内核和环绕着内核的晕圈。但是,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感知的行为来说,其所感知到东西总是“外在”的空间事物,因而它是超越的(空间事物总是有着尚未显现的背面),但是对于内时间的这种由滞留、原印象、前摄所构成的当下视域来说,它是内在的。但是,从原则上讲,依照现象学的原则,所谓的外在的东西也都是可以还原为内在的,外在性最终还是在内在中构造出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感知的视域完全可以还原到内时间的视域当中来,感知行为本身也必然是在时间过程之中得以展开的。其中,原印象不断地转变为滞留,而滞留则不断地转变为滞留的滞留,形成一个滞留的连续统[2]在这个滞留的连续统中存在着纵意向性和横意向性。。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滞留、原印象还是前摄,三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向行为,虽然在protend(前摄行为)和retend(滞留行为)同intend(意向行为)之间存在着词源上的关联,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意向行为只能是对象化的行为,而内时间中还远远谈不上对象或者自我,滞留、前摄、原印象也完全是前对象的,其所涉及到的仅仅是一些感性材料,赋予这些感性材料以最初的合规律性,这些感性材料还远称不上是对象。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明亮的当下视域中的滞留、前摄和原印象是前意识。而滞留本身则不断的滑入到过去之中,变为滞留的滞留,成为滞留的连续统。而随着滞留向着过去的不断的沉降,它自身触发性的活力也在不断的丧失,当这种触发性的活力降为零的时候,它也就变成了所谓的无意识。这一点是比价容易理解的,我们在上文中也已经做出了交代。
接下来,我们从内时间意识当中的横意向性与纵意向性的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知道,任何的意识行为都是在时间当中发生的,不管它是对象化的行为还是前对象化的行为。超越的、实在的东西,总是可以还原到内在的、实项的时间意识河流当中。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笼统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细致分析,必然要求我们回溯到在内时间中所存在的两种基本的意向性中:横意向性与纵意向性。其中,对象化的意识所对应的就是横意向性,而前对象化的时间河流的自身意识,所对应的而是纵意向性。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滞留的双重意向性与意识流的构造》这一小节中说道:
因此,在这条唯一的河流中有两个不可分离的统一的、就像一个事物的两面一样互相要求的意向性彼此交织在一起。借助于这一个意向性,内在的时间构造起自身,它是一个客观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在它之中有延续和延续者的变化;在另一个意向性中构造着自身的,是这个河流的各个相位的拟—时间编排,这条河流始终并且必然具有流动的“现在”—点,具有现时性相位,并且具有前现时的相位串和后现时的(尚未现时的)相位串。这个前现象的、前内在的时间是作为构造着时间的意识之形式而意向地构造起自身的,而且是在此意识之中构造起自身的。[1]HUSSERLIANA BAND X, S.436,中文版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良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0页。
下面,我们就通过这这段话,来开始我们对时间河流中的对于横意向性和纵意向性的分析(尤其注意其中的:“内在的”、“客观的”与“拟—时间”、“前现象”、“前内在”之间的区分)。在胡塞尔看来,在内时间的河流的滞留链之中,同时存在着两种意向性,[2]“每个‘滞留’类型的意识映射都具有一个双重的意向性:一个是为内在客体的构造、为这个声音的构造服务的意向性,即我们称作对(刚刚被感觉的)声音的“原生回忆”,或者更清楚的说是这个声音的滞留。另一个是对在河流中对这个原生回忆的统一而言构造性的意向性。”HUSSERLIANA BAND X, S.434,同上,第128页。胡塞尔在此使用了“目光”的比喻[3]“目光可以穿越那些在持续的河流进程中作为对声音的意向性而彼此“相合”的相位。但目光也可以朝向这河流的,朝向这河流的每一个片段,朝向这个流动的意识从声音—启动到声音结束的过渡。”HUSSERLIANA BAND X, S.434,同上,第126—128页。, 朝向着在河流的每一个瞬间中所构造出来的客体的目光,也就是所谓的横意向性,而朝向着河流自身的过渡、自身的统一性的目光也就是纵意向性。例如,我在听一段旋律的过程中,既可以把我的目光朝向我所听到的作为客体的旋律,也可以朝向着我的意识河流自身的流动过程。前者是横意向性,而后者是纵意向性。然而,虽然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表面上的简单的区分,但是,在此我们不想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简单区分上面,而是试图深入的分析着两种意向性的本质差别所在。在此,我们要着重回溯到上面所列出来的那段话中。如果我们去仔细的阅读这段话的话,就会发现,胡塞尔从本质上做出了如下的区分:纵意向性、前客体、内时间——横意向性、客体、内在时间。其中,我们使用“前客体”这个词汇来对应胡塞尔所说的“前现象的”、用“内时间”来对应胡塞尔所说的“前内在时间的”。也就是说,在纵意向性和横意向性之间所隐含着的是根本性的差别,一个是前对象性的意向性,另外的一个则是对象性的意向性,虽然二者不可分割的统一在一起,“就像一个事物的两面”,但是在此我们却必须注意到这个“两面”是性质不用的两面,分属于对象化的意识和前意识的不同的领域之中。纵意向性是时间河流的自身体验,胡塞尔说道:“以至于在它之中还能够必然有一个河流的自身显现,因而这河流本身必然是可以在流动中被把握到的。”[1]HUSSERLIANA BAND X, S.437,中文版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良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1页。纵意向性是时间河流对时间河流自身的自我显现,它决然不是一种对象化的意向行为,并不是对象之外的自我通过意向行为对对象的指向。在这里,指向者和被指向者是同一个东西,它是一种“自体验”,自身对自身的前对象化的原意识,“这个河流自身显现并不需要第二条河流来,相反,它是作为现象而在自身中构造起自身的”[2]HUSSERLIANA BAND X, S.381,同上,第485页。。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通过这种前对象的时间河流的自身体验——纵意向性,胡塞尔才成功地避免了时间意识中所可能隐含着的无穷倒退的悖论。如果套用对象化的意向行为——意向对象的模式来探讨时间的话,就可能会面临着如下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到时间,是因为我们对时间的意向行为,而这种指向时间又处在时间中的意向行为本身,则又必然的要求具有另外的一条更高层次的时间河流来指向它,而这种高层次的时间河流又会同样的预设更高层次的时间河流,如此倒退以至无穷。但是,如果对河流的指向是一种前对象性的自身体验,则可以成功的避免这种悖论。而且,纵意向性的意义不仅局限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时间河流的自身呈现,使得我们得以“知到”我们是有时间的,进而,使得对时间性本身的反思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关于时间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而时间河流的横意向性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横意向性的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到对象化的行为是如何奠基在内时间之中的。通过横意向性,我们的“目光可以穿越那些在持续的河流进程中作为对声音的意向性而彼此‘相合’的相位”,进而看到被构造出来的对象。在时间河流的瞬间中,我们通过横意向性而指向着看起来“处在时间河流之外”客体,但是,这些客体又都可以最终的还原到时间河流中的对客体的构造过程之中。任何的客体,都通过时间河流的横意向性而显现出来,并在时间河流的过程中而被构造出来。任何的客体构造的过程,都必然的是一个时间中的过程,任何客体的显现都必然是在时间之中的显现[1]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构造的结果的客体,必然是在时间中的,例如,作为观念、本质的构造物就是超时空的。。
总之,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澄清胡塞尔的意识哲学之最为重要的概念——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总体上理解胡塞尔的意识哲学,看到他的意识哲学的不同的维度。从对象性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不同维度的视角出发,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的理解胡塞尔从描述的现象学、先验构造的现象学最终到发生的现象学的过渡,也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胡塞尔意识哲学的意义所在:胡塞尔哲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现了对象性意识中的意向性或者本质直观的方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前意识、无意识领域的开创性的探索。正是沿着这种“前”、“无”的维度,才有了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优越性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象化的意识,而是进入到了“前”意识、“无”意识的维度。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此在突破了胡塞尔的对象性意识,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胡塞尔的“前意识”和“无意识”。而萨特推崇“反思前的我思”,认为“正是非反思的意识使反思成为可能:有一个反思前的我思作为笛卡尔的我思的条件”、“反思一点也不比被反思的意识更优越”[2]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页。,这种观点也完全可以用胡塞尔的前意识、无意识的来说明,实际上萨特也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胡塞尔的“意识”理论。至于梅洛—庞蒂的前反思的身体现象学等等,也都可以用胡塞尔的多重意识理论来解释。然而,由于胡塞尔的意识的第二重、第三重的维度没有被充分的彰显,当提到前反思、前我思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想到的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而非胡塞尔。在此,希望通过本文的对于胡塞尔的意识的多重揭示,可以使得我们意识到: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家对于存在、前反思、身体等领域的探讨,在胡塞尔的意识哲学那里已经有了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