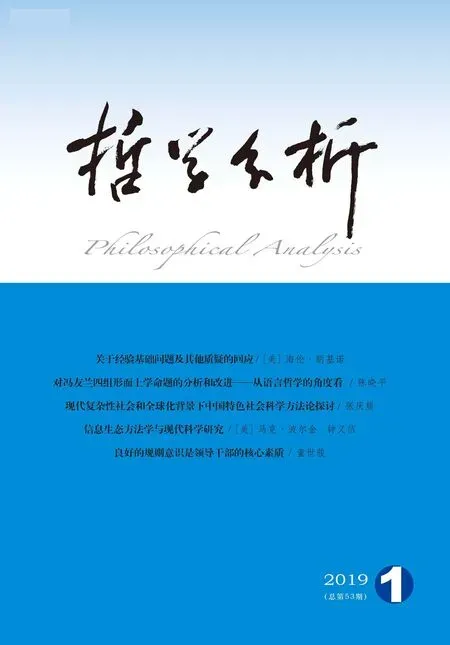“七八个星天外”
——追念韦尔默教授
2019-12-14应奇
应 奇
从国内的某公众号辗转得知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教授仙逝的消息时,我正结束在闵行公寓一天的劳作,从学校北门外喝了两杯德国啤酒于踉跄中回到宿舍。说来也是“冥冥中”有“巧合”,我为之伏案一整天的正是主要由自己编译的韦尔默那部文集《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中的两篇文字:《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和《民主文化的条件: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而之所以重温这两篇文字,乃是为了准备2018年9月底到柏林自由大学参加一个政治哲学会议的发言稿。据同样要与会的知情人士此前告知,韦尔默退休前任教的自由大学哲学系的同事本来还打算邀请2018年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老教授与会。闻听这个消息,从来没有机缘见过韦尔默本人的这位译者竟也一度开始“憧憬”起在柏林见到他的作者的场景,甚至颇欲事先就将之归为将要开始的柏林之行的最大“收获”,而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成为徒然的梦想 了!
得知讣闻之日仍在研读的《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是我接触到的韦尔默的第一篇文字。应该是整整20年前的1998年春夏之交,为了撰写台湾扬智文化公司所约的《社群主义》一书,我在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按照事先所做的功课,我按图索骥地复印了曾任《哲学杂志》编辑的凯利(Michael Kelly)所编《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解释学和批判理论》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in Ethics and Politics,MIT,1990/1991)一书。这个包含哈贝马斯、沃尔泽、赫勒、麦卡锡等名家的文集最后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并给我此后的学术生涯带来磨灭不去印记的却是我事先并不知其名的韦尔默的这篇宏文。我不但把他在此文中的基本思路运用到《社群主义》一书的尾章“两种自由的分与合”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写成的《论第三种自由概念》一文之中,而且在数年后与友人编译《第三种自由》和《公民共和主义》两书时,又分别译出了前述两文。至今犹记的是,我是通过童世骏教授的老师、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的介绍,取得了《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一文之作者授权的,那还是2003年底的事;转年六月,为了取得《民主文化的条件》一文的作者授权,我开始与韦尔默本人联系并从此得到了他一路的支持,包括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编译《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并请作者为此书撰写中文版序言,以及此后翻译《伦理学与对话》时,把我在纽约旧书店中得到的一本文集中的《交往与解放》一文作为附录增补到此书的中文版 中。
这个既顺利又曲折的编译历程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件小事是:2007年3月,我正在台湾佛光大学客座,《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一书的责任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吉人先生希望我能提供韦尔默的照片——这是纳入此书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的惯例,在尝试其他方式无果后,我只好再次求助于作者本人,最后韦尔默在他的女儿的帮助下寄来了后来放在此书扉页上的那帧哲学家的玉照。在收到照片数天后,我与从柏林自由大学博士毕业的林远泽教授从台湾的东海岸一直转到台北的草山,当远泽兄听闻我与韦尔默的“交往”时,不禁感叹了一句:“韦尔默待你不薄 啊!”
所谓“不薄”之语固然不无笑谈的成分,其实韦尔默之待我“不薄”当然不只在于从邮件上给出他的文章的授权许可,也不在于发来他的照片,甚至不在于为中文版撰写序言,而是在于他实际上亲自参与到了《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这个文集的编辑中,他不但认可了这个事实上以他已有德、英两版的文集《残局》为底本的“新”文集的新名称,而且特意推荐了他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斯宾诺莎演讲”的两个文本《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和《人权与民主》加入这个文集;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作为权利主要归属者的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s)才破例同意以这样“挑三拣四”的方式编译出版他的文集。而这个工作之所以能够侥幸地由我来完成,根本之点还在于作者本人原则上同意我从英文翻译他的文章,要知道苏尔坎普出版社原来是“理所当然”地坚持所有文章都必须从德文翻译 的!
我们的编译方案从《残局》中“剔除”了四篇文章,补入了韦尔默本人推荐的“斯宾诺莎演讲”以及我作为“编者”加入的《理性、乌托邦与启蒙辩证法》和《主体间性与理性》两文,总的篇目仍然是13篇,表面上看差别并不大,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变动,至少从“表面上”给出了一个了解和把握韦尔默哲学理路的可能路径。这只要对照一下《残局》对文章的“分类”和我的编排方式就能略窥端倪:前者把所有文章分为“消极的和交往的自由”“后形而上学视角”和“时间的想象”三个部分,而我按照“理论创造的准备稿”“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政治向度”和“思想语境”三个部分重新编排所选的13篇文字。虽然这种学案体的编排方式很难说有多大创意可言,但是至少这个编排方案是经过作者本人过目并同意的。至于这种方式是否真正符合作者的“原意”或者有助于读者理解作者的“原意”(如果有这种实际上已经被否认存在的东西的话)这个终极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到韦尔默思想本身的“难解性”,这个疑问本身的尖锐性就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 和。
《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一书出版后,至少它在表面上的“影响”似乎没有我预计的那么大,回想起来,这当然有文本固有的原因,前述“难解性”是一个方面——作者基本上是在哈贝马斯的范式下作业,如果对于哈贝马斯庞杂的工作没有比较精到的了解,实际上我们很难精准地把握韦尔默工作的方向和力度。其实我自己对于韦尔默的理解也极大地受制于这个“短板”。对此当然除了加强基本的功课之外别无偷懒之途。但是如果我们试着宽松些地从“语用学”的角度,从“运用”韦尔默的思想的角度来看待这件本来艰难的——再说世上本来又有哪一门学问不是艰难的呢,情形似乎会变得稍微“乐观”一些。例如韦尔默对于《法哲学原理》与《论美国的民主》之“同构性”的阐发,就是一个似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细节论证适当“脱钩”并加以“运用”和“发挥”的洞见。就我自己而言,锚住这个洞见不放,再细读他的文本,我在前些年曾经“提炼”出“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和“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这对概念,并把它们与哈贝马斯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和“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这对概念关联起来加以阐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勉强可以说是一种“语用学”的践履 吧!
如果放长一些时段看,特别是从近些年的情况观察,主要以《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一书为媒介的韦尔默思想的影响似乎呈稳中有升之势。早些年曾有国内的新锐学者向我表述阅读其中关于阿伦特的两篇文字后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最近以来又有更为年轻的学者试图从自然权利理论的角度深挖韦尔默的相关论述——请不要忘记,正如雷蒙·阿隆及其学派在法语世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就开始反击自然权利理论上的“逆流”,哈贝马斯和韦尔默也在约略同时展开了这项艰巨的工作,这些工作预示和提前呼应了在美利坚学院中以罗伯特·皮平为代表的重释德国观念论以回应保守主义挑战的事业和雄心。它们在当前中文世界的意义更是值得深长思之,而且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 分。
所有这些方面中似乎最不值一提的是从事韦尔默论著的编译之于我个人的沾溉。毫无疑问,我把《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与《第三种自由》和《公民共和主义》称作个人编译生涯中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产品,其中尤以《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为最,当年那种“心神以赴”甚至“欢会神契”的感觉如今想来可谓既记忆犹新,又恍如隔世。我大胆地相信,这种状态当然也体现在了译文的品质和质量上,我的一位学生曾说这部书的翻译是他老师的所有译品中最为精到的。2018年7月,我应邀在北大暑期学院的课堂上讲授以韦尔默为主的新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同样从柏林自由大学留学归国的一位年轻的主持人在谈到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时称它是近十几年国内的西学译品中翻译得最为“流畅”的,并感叹与此书之“相见恨晚”。面对来自后学晚辈的这类“称道”,也许我应当回应的是,我感到汗颜的与其说是这种“美誉”,还不如说是我在韦尔默思想的研究和阐发方面实在是做得太不成比例了!仔细想来,制约这种工作之展开的,除了所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能够切实地把《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中的认知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与《伦理学与对话》中的伦理现代性和《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中的审美现代性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把握和融通。这一方面制限了以往的工作,另一方面又预示了未来的方 向。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一文最后如是说:“哈贝马斯认为,审美体验、基于实践经验的阐释和规范期待并非彼此独立,当然这也就是说,审美话语、道德—实践的话语和有关‘事实’的话语并非被一道深渊彼此分开,而恰恰相反,它们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交叠在一起,无论人们用多少形形色色的有效性范畴来表述一种审美的、道德的和真实的有效性,而这些形形色色的范畴总是无法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有效性范畴。在这里讨论的并非是‘语言游戏’的和解,而是各种话语的相互渗透:在多种理性的范围内对单一理性的扬弃。”从长时段来看,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地位当然应该是无法与德国观念论相提并论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哈贝马斯和韦尔默仍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道出了那个根本的洞见。“星丛”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最为哈贝马斯所称道的、也影响过韦尔默的阿多诺的一个重要概念,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重要的德国观念论研究和阐发者的迪特尔·亨利希也曾经用“星丛”来形容和刻画德国观念论者构成的群像。在一种似乎显然不那么对等的尺度和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诸公也可谓构成了这样一个“星丛”,那么就让我借用这个“星丛”中刚刚逝去的表面上似乎不那么闪亮的这颗星的一句话,来试图表达这个洞见于万一,并表达我对于这颗星的一万分的追 念:
无可否认的是,没有道德上的侵害,特殊性在普遍性中的“扬弃”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有这些都表明,随着向世界主义法治国家的过渡,黑格尔所谓“伦理生活的悲剧”将在全球规模上重新出现,因为特定的文化传统的相对化也意味着它们的转型和局部的失效。这是现代性的代价;但对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人来说,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唯一仍可选择的是,特殊性的这种相对化在一种自由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世界文化的安定空间中是否会成为富有成效的,或者,富裕国家的防御性反应或感到他们的集体认同受到威胁的那些人的侵略性反应是否将导致全球内战或自由主义民主制的毁 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