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风骨,国士无双
2019-12-10钱虹
钱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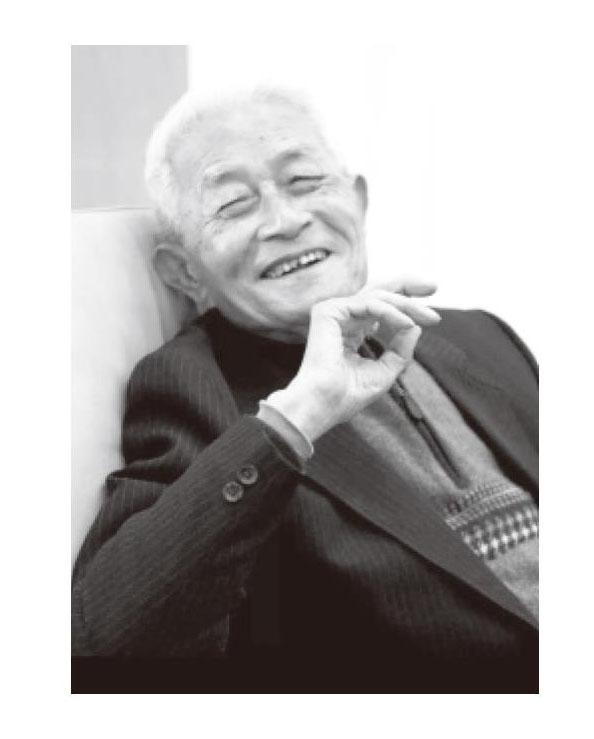


今年6月25日凌晨3时35分,走过人生105个年头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语文教育家、原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徐中玉先生驾鹤西行,离开了让他牵肠挂肚而又使他欢喜使他忧心的世界。噩耗传来,先生的亲朋好友和众多学生,无不唏嘘惋惜。6月28日,徐中玉先生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大厅内悬挂的挽联,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徐先生的一生总结:“立身有本,国士无双,化雨春风万里,何止沪滨滋兰蕙;弘道以文,宗师一代,辞章义理千秋,只余清气驻乾坤。”数百多名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生前友好、各届学生等汇聚成悼念的人流,为徐中玉先生送行。数不清的花篮和挽联从大厅一直排到门厅外,绵延不绝,表达着亲朋好友和他的学生们的无尽哀思。为徐先生送行的那天恰逢期末考试周,我有监考任务,分身乏术,只好在追悼会召开前夕,连夜代表任职学校起草唁文,并委托母校中文系代订花篮,以寄托心中的敬意与哀悼。
徐中玉先生是一代真正的知识人的典范。在超过百年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中国文论和文学的标杆,历经磨难而以民族、国家大义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为己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身处逆境而沉静,面临危局而敢言;兢兢业业俯首工作,甘于清贫埋首学问——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人生楷模与精神遗产。他的一生,端端正正地写好了一个大写的“人”字,成为我们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徐中玉先生毕生投身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乃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语文教育家,享有“大学语文之父”之盛誉。他在鲁迅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以及大学语文教育等领域成果丰硕,享有崇高的威望。先生一生成就卓著,品格高尚,高风亮节,为世人所景仰。他为推动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大学语文教材和课程建设等方面作出了世所公认的重要贡献。
初见先生,运筹帷幄
我最初见到徐中玉先生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当时填报的高考志愿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文革”期间,上海的几所文科院校如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等校合并,统称为 “上海师范大学”。不过,我接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明确写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所以我一入学就到了位于中山北路3663号的华东师范大学。当时中文系位于丽娃河东面靠近校门口的三幢庭院式的平房内,三幢平房都有着长长的走廊,系主任办公室、系资料室以及中文系的各个教研室都各据其间,穿过走廊透过玻璃窗总可以看见每间屋子里的情形。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徐中玉先生。他当时坐在中文系系主任办公室里,靠窗的办公桌前总是堆着一叠叠文件或书籍。他那时大概六十岁出头,国字脸方方正正,穿着朴素的灰色或藏青色中山装。平日里总是夹着一只黑色公文包,走路速度很快,讲话的语速也比较快。
平房前面就是三层楼的文史楼,从前是我们中文系和历史系学生上课的地方。文史楼正门有着四根罗马式大立柱,气势恢宏。这里或许正是茅盾先生在《子夜》中写到的“丽娃丽妲”,主人公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瑶、林佩珊姐妹上过学的地方,当年是从圣彼得堡流落到上海滩的白俄贵族开设的一所女校。文史楼是典型的方正恢宏的俄罗斯建筑风格,楼顶是一个大大的可以举办舞会的露天平台。我们77级入学后曾在露天平台上举办过活动,后来因为年久失修而漏水,露天平台就被关闭了。
那时,百废待兴,华东师大中文系首届通过高考的150多位大学生进校,集合了12年历届从66届高中生到76届应届生的1977级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该如何教学,如何引导?加上仅隔半年之后,1978级150多位学生又紧跟着入学,作为系主任的徐中玉先生,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然而,他却用四两拨千斤的非凡领导力,很快就使华东师大中文系这两届学生在全国的文学界、语文界有了较大的影响。
谆谆教诲,学研并举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后来会选择现代文学研究作为终身职业,是和徐中玉先生、导师钱谷融先生的教誨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徐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中文系鼓励学生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学术氛围分不开的。我考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不久,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给77级学生合开了一门“文艺学专题”课,我是选修者之一。当时因为年龄小,上课不是很专心,所以两位先生具体的讲课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两位先生在课堂上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却如雷贯耳,至今回味无穷。最难忘的一番话,就是写评论文章一定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真切感受,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一味吹捧。当时《上海文学》上登了一篇小说《阴影》,我就尝试着写了一篇2千字的评论,当作课堂作业交了上去。没想到过了几天徐中玉先生上课发还作业时跟我说:你很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试试投稿。在他的鼓励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就把它投给了《上海文学》编辑部。更没想到的是,我这篇课堂作业竟然以标题为《对小说〈阴影〉的一点意见》,在做了一定删节后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上,这对一个大二女生而言不啻是一个极大鼓舞。
此后,我一发而不可收,大三至大四期间在《百草园》《语文函授通讯》《萌芽》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谈谈〈草原上的小路〉中石均的性格塑造》《试论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创作》《刚刚入伍的未来将军——评〈萌芽〉复刊以来的短篇小说》《雾,在她的笔尖缠绕——王小鹰和她的创作》等评论文章。本科毕业论文后来分别以《论庐隐的早期思想和创作》和《论庐隐的后期创作》发表于《福建论坛》(双月刊)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为我报考钱谷融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看到现在有些写徐中玉先生的文章或报道,往往称颂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独开风气,允许有创作才华的学生如赵丽宏、王小鹰等人以诗集和长篇小说代替毕业论文,因而造就了令全国瞩目的“丽娃河作家群”的繁盛景象,甚至于有论者以为徐先生偏爱创作而鄙视“论文”,这无疑是片面的。其实,作为资深学者,徐中玉先生对于中文系学生在学术方面的鼓励和举措更为突出,例如,与我同班的一位学养深厚的男生,在“现代汉语”课后写了一篇讨论“词的重叠”的作业,任课老师觉得他写得不错,徐先生听说后立刻表示,应该推荐到学报去。不久,“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刘大为”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这篇论文的发表,当时不仅在中文系、历史系、政教系等文科院系学生中引起了极大反响,而且在中青年教师中引发了不少震撼,因为届时大多数中青年教师都还未曾在学报发表过论文。
此后,仅就中文系1977级中,就有夏中义、宋耀良、方克强等一批本科生的学术论文,纷纷登载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中文系学生的学术名声鹊起,就连“物质利益”也收获颇丰:当时在学报发表一篇论文的稿酬,几乎相当于大学青年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更为重要的是,在徐先生的主持下,1977级毕业留校的学生数前所未有,用时任系副主任齐森华老师的话说“是史无前例”的:仅我所在的77级4班,直接留校和考取研究生后再留校的学生,就有11人之多,占了全班四分之一以上,并且很快就成为中文系各门专业课程的教学骨干,从现代汉语到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到外国文学。以致有人戏称:1977级的留校学生,几乎就能开出中文系的主要专业课程。这也直接造就了华东师大中文系1980年代的生机勃勃的学术风貌。
一身傲骨,敢说诤言
徐中玉先生与导师钱谷融先生,生前一直是挚友加至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院系调整而由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等校合并组建为华东师范大学始,徐中玉先生从沪江大学,钱先生从上海交通大学,几乎同时调入新组建的华东师大,两位先生经历了近70年华东师范大学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他们的身上几乎贯穿着一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史。我在母校从本科读到博士、从毕业到执教的20多年里,常在丽娃河畔的华师大校园内看到两位先生几乎形影不离的身影。2014年12月,德高望重的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同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跟随钱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在中文系执教,期间以及后来在其他场合都亲耳听到钱先生十分敬佩地说起徐先生,“他实在是又能干,又肯干,敢作敢为,只要义之所在,他都会挺身而出,绝不瞻前顾后,不像我这个人,又懒散又无能”。
确实,徐中玉先生爱憎分明,敢怒敢言。曾听钱先生说起过一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施蛰存先生曾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粗暴对待和批判,旁人皆噤若寒蝉,唯有徐中玉先生挺身而出,为他辩解,结果自己不仅也遭到批判,还和施蛰存先生、许杰先生等一起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后才恢复名誉。对此,徐先生无怨无悔。施蛰存先生复出后,给我们77级开过一门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时年75岁。这是他复出后给本科生亲自讲授的唯一一门大课,他以深厚渊博的学术功底、风趣生动的讲课风格赢得了77级学生的好评,有不少同学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热爱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
可惜施先生在授课结束不久,即检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后就在家只给研究生授课了。2003年,恰逢施蛰存先生百岁和徐中玉先生九十寿辰,母校中文系为他们祝寿,著名诗人王辛笛先生为两位寿星分别写了旧体贺诗。就在这年下半年,施蛰存先生最后一次入院,徐先生去华东医院探望他,此时施先生已无法说话,但他却听出了徐先生的声音,向这位曾患难与共的老友用手招了一下,发不出声音来。徐先生在失语的施先生病榻前坐了一个多小时。次日凌晨,施先生就离开了人世,等徐先生再次赶到华东医院时,已是人去床空,但是徐先生坚信:“他的各种贡献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留给后世。”一生坎坷、历经磨难的一代文学大师施蛰存先生,有徐中玉先生这样的挚友与至交,也应该是一生无憾了。
九旬主编,彪炳史册
也正因为徐中玉先生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崇高威望和人格魅力,不久对推荐我申请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的录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我打算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如许地山、戴望舒等在香港期间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有许多重要的文学史料都收藏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内,所以想申请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但这需要有两位学术推荐人,所以我就找到了徐中玉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小思)教授,他们很快为我写了推荐信。寄去不久,我就收到了香港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录取通知书。虽然后来港大一再给我延期就读的机会,但由于当时赴港的种种限制,我未能如愿进入港大就读博士学位。不过,徐中玉先生为我这个学生亲自写推荐信和对我的关爱和支持,我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我出国回来,已过了当年报考博士生的时间,他和钱谷融先生又推荐我回母校先旁听后参加考试,次年我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后,提前一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还有一件事也是难以忘怀的,就是我2002年底之所以离开母校调入同济大学,其实也是受到了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此前,我与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吴启迪教授在一次活动中相识,她告诉我同济大学正在恢复筹办中文系,力邀我作为引进人才前去助阵。我就把此事对两位恩师讲了,征求二老的意见。徐先生对我说起了往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在沪江大学执教,时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先生曾请他去同济大学兼职开课,“那时,同济大学是上海高校中学科门类最多的一所国立大学”,医、工、理、文、法,学科门类齐全,可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搞“院系调整”,把同济大学完整的学科体系全打乱了,医科连根移植去了武汉,即如今的同济医科大学;文科、法学等全部并入复旦大学;而又抽调其他院校的土木工程、建筑等系科并入同济大学,结果使得同济大学成了一所纯粹的理工科大学,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国豪校长重新执掌同济大学后才又开始恢复综合性大学的建校方略。“真是可惜啊!”所以,徐先生对我说,你如去了同济大学,还可以去见见同济大学民盟的主委江景波教授,他也是前任同济大学校长。2013年10月,同济大学中文系终于请来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出席会议。这时,徐先生已是虚岁99岁,钱先生95岁,两位手捧鲜花的高龄老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仿佛岁月已在他们身上停留。
就这样,在徐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就从母校调入了同济大学,正好赶上了同济大学中文系挂牌。离开母校之后,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仍然经常鼓励我教学之余在学术上不懈努力,所以我自觉比较像样的论文,也会拿给徐先生看。有些他认为可以发表的就留下来,我有几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徐先生主编的一级期刊《文艺理论研究》上,如《海外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开端与突破》(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等。当时,年届九旬的徐先生除了担任由他主持创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学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三大全国性学术社团的名誉会长外,还担任他主持创办的《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主编,他主持创办的还有《词学》《中文自学指导》(今改为《现代中文学刊》)等一批学术刊物,从而使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无论是挂靠的全国学术社团还是学术刊物数量,都稳居全国第一。这些学术共同体的资产,确保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传承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徐先生担任刊物主编,并非像某些印在期刊扉页上的只是挂名主编而已,他是实实在在的终审主编,每一期数十万字的终审稿,都是他亲自审阅和把关的。试想,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孜孜矻矻伏案审读每一期稿件,需要怎样大的毅力和精神呵!
最近几年,已过百岁的徐中玉先生日渐体衰,尤其是患上了失忆症,严重干扰着老人的记忆力,使他陷入了认知障碍。我每次去华东师大二村看望钱谷融先生,也想去看望一下徐中玉先生,可是钱先生告诉我说,他已经很多人都不认识了,所以我只好打消了去看望他的念头,只在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安享晚年。2017年9月28日,99岁的钱谷融先生与世长辞。当电视新闻里播出钱先生的生前照片时,徐中玉先生突然清醒了,指着钱先生的照片说:“这个人,我认识的。”如今,比钱先生年长4岁的徐先生也走了,他与钱谷融先生、施蛰存先生,还有许杰先生等生前曾经患难与共、相知相交的挚友,终于可以在天堂相聚了。
或许,已经走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他们,会用这样一幅长长的对联来赞许徐中玉先生的人格与才干:
运筹帷幄,八面经营,三学会,十学刊,澤被岂止中文学科;
仗义执言,一身正气,仰对天,俯对地,彪炳何须官宦汗青。
在我们后学的心目中,无论怎么形容,徐中玉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