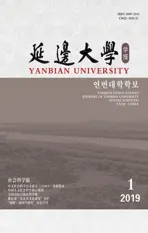人与自然融合的神性书写
——论红柯《美丽奴羊》的艺术特色
2019-12-09王启东
王 启 东
著名作家红柯原名杨宏科,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人。曾先后获得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等多项大奖,是西北作家群第三代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美丽奴羊》曾经获得1997年全国十佳小说奖、1997年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2002年吉元文学奖最佳作品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但目前针对这篇短篇小说的研究比较少。红柯挟着西北草原特有的牛羊腥膻和牧草、牛粪气息,骑着新疆伊犁骏马,闯进了当代文坛。他在短篇小说《美丽奴羊》中以刚健、清新的写作态度,借助于草原上的屠夫、牧人、大学生和美丽奴羊,点染出西部草原神秘玄妙的精神和气象,并思索着天、地、人三者之间合理的存在方式。他笔下的大自然是远远超出人的智慧与支配能力的,是高高地在人之上的神性存在,人只能借助自然之神的精灵——美丽奴羊的心灵关照,感悟、融入自然的神性,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他的小说倡导把人从外在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使生命回归自然的怀抱。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可以为红柯作品乃至西北作家群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有力的佐证,以进一步确立红柯在西北作家群中的独特地位。
具体来说,《美丽奴羊》的艺术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意象的奇妙呈现
红柯的小说意象多选择那些与自然有着共同灵性的载体,以表现他对自然神性的歌颂,这些意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屠夫与羊的意象分析
红柯的小说创作不重技巧而重感觉、意象,《美丽奴羊》就是各种奇妙、丰富而饱满意象的结合。凶悍的屠夫凭着自己高超的杀羊绝技,甚至不把连长放在眼里,连长给他敬烟,他只是朝连长点点头。这样一个“很牛皮”的“狠汉子”一连杀了14只羊,宰羊剥皮快、准、狠,不要别人帮忙。这个不同凡响的屠夫甚至都没放过其中一只“绝顶聪明的”跪下乞生的羊,他只愣一下,就把神收住了,毫不留情地照杀不误。而“一般屠夫遇到这种场面,便会丢下刀子,扬长而去,另谋职业”。[1]这样一个残忍的屠夫失掉了作为人最基本的善良、慈爱的人性,他所追求的是杀戮动作的快捷连贯,杀戮数量的庞大,和旁观者对他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的漂亮身手的感叹与赞美。他已经迷失在与羊这个假想敌发生冲突并取得完全杀戮胜利的无穷快感中,他“早已习惯这种哀号组成的乐曲”,[1]羊死亡过程的悲壮只能增加他对杀戮的兴趣。
美丽奴羊是自然之神的精灵,它不惧怕死亡,它用“清纯的泉水般的目光凝注牧草和屠夫,屠夫感到自己也成了草。人跟草一样,即使在寂静中,也会有一种内在的旋律在回荡”。[1]是美丽奴羊的神性感化了屠夫,使他参悟:那是只杀不了的神羊,是令人敬畏的自然之神的化身。人与草是本质相同、形式各异的平等的生命,同样吸取着自然的精华,感受着自然的伟大与自身的渺小,生命的价值在于回归自然的怀抱,被自然之神垂青。
红柯对屠夫杀羊的描写也可以看成另一个意象:屠夫杀羊技巧娴熟,“连羊自己也想不到屠夫对它这么熟悉,比它自己还要熟悉这美妙的身体”。[1]而这种杀戮也是屠夫和羊之间的深度交流,屠夫和羊共同演奏了一曲“弥漫于天地间的音乐”——天籁之音。红柯写出了在人与自然相冲突而又融合的时候,生命灵性的复苏与对自然的膜拜有机地结合,透视出人在物的世界中那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以及相通相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更深入地思考了人类在自然中的生命状态、存在价值等隐性的终极追问,这无疑是原生态的西部草原风情小说中值得重视的思想。
(二)牧人与羊的意象分析
“圣湖赛里木乌伦古博斯腾就成了草原人一年中最向往的地方。牧人必须在鲜花盛开牧草青翠的时候,把牲畜赶到那里。他就是在赶往赛里木湖的途中把羊弄丢的。”[1]他失魂落魄地骑着马在辽阔的荒原上到处找羊,呜呜咽咽地吆喝着羊,蜷缩在马背上,处于冥想状态,他听到羊咩咩的叫声便以为是他的羊回来了,丝毫未察觉狼跟在他身后。他太爱他的羊了,当他回到自己的帐篷,女人却告诉他羊没丢,可他却确信羊曾经丢过:“我把羊找回来了。”牧人放了一辈子的羊,却让羊给放了一回,不是他蠢笨,而是他虽然生活在大草原上却没有融入大自然的神性。
羊是真主的神物,大自然宠爱的精灵,它承担着自然的灵动、生气、活力,最能领悟大自然的神性,就连牧草也在一种甜蜜急切的期待中,出乎本能地闪射出纯朴和温情,将它的青春激情与魅力主动奉献给羊。羊与牧人是平等的,甚至在感悟自然方面羊强过牧人,比他更多几分灵性与深刻。“一个到不了圣湖的牲畜,不是它自己不行,是它跟错了主人。”[1]说羊放牧人,其实是让牧人感受自然犹如母性一般养育世间一切的丰厚伟大、慷慨无私,它孕育万物、滋养万物,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卑微渺小、孱弱无力的。牧人“不敢抬头,他知道脑袋四周大得没边边,旷野无边无缘,你简直没办法”。[1]大自然深广辽远,“别说几只羊,几百只几千只几万只,撒在准噶尔,跟撒一把沙子一样”。[1]放了牧人一回之后,羊又乖乖地跟着他走上去圣湖的路,此时的牧人已经进入与自然相通相融的天人合一境界,是能把羊带到圣湖的真正牧人了。
(三)大学生与羊的意象分析
来自江南的文弱书生“刚进疆就被马颠到地上”,[1]“除了读他随身所带的两箱子专业书,就是在牧场周围转悠”。[1]但是场长那句“能徒步穿越大戈壁的汉子就是天山的主人”的话感动了他,经过两个多月,他已经融入了天山圣地牧民们的生活,浸泽了西域绝地的神性。“大学生勒马于天山之巅,呼吸着一种英武豪迈的王者之气。”[1]大学生骑着伊犁马,从山顶直扑进紫泥泉草原上的黄泥小屋,在马鞍上一本接一本地阅读着马嘴衔起来递给他的书。一个完全领悟了天山绝域自然神性,周身洋溢着磅礴王气的大学生,“马为它强悍的主人感到自豪”,[1]“手里的书也发出咩咩羊叫”。[1]美丽的女记者被他身上的氤氲神气、磅礴王气所征服,“竟然鬼使神差又回到紫泥泉”,[1]成了他的好妻子。正如努尔江所言:“世间最好的东西来自人的生命。”[1]儿子和美丽奴羊便是大学生神性复苏所创造的美好意象。
紫泥泉是“生殖力最强的地方”,像个美丽而性感的女人。苏联专家没能培育出新品种是因为这些外国人根本无法融入紫泥泉的自然神性,就像他们的苏联羊,“体大膘肥,毛儿细长,一身的贵族气派,但只能呆在栅栏里,无法在天山落脚;一到山野里就呆头呆脑,胆小如鼠,山上滚下一块石头,哈萨克土羊毫无惧色,轻轻躲开,苏联羊则浑身发抖,等着挨揍”。[1]而大学生不仅在紫泥泉落了脚,还像雪莲一样扎根天山,呼吸着天山的神气,征服了像紫泥泉一样的“世间最美的女人”,创造了“世间最好的东西”——美丽奴羊。
红柯在《美丽奴羊》中描述了屠夫、牧人、大学生和美丽奴羊之间情节简单而意蕴深刻的故事。美丽奴羊作为大自然之神的精灵,以不同方式引领着他们发掘自身与自然相匹配的神性,带领他们以真正的自然之子的身份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感悟着自然的伟大,人类的渺小,生命的灵动。屠夫、牧人和大学生虽然身份不同,但都在美丽奴羊的关照下对自然母亲产生了由衷的虔诚之情,并且从这种虔诚构筑的母子关系中汲取了生命力量,焕发了勃勃生机与充沛活力。
二、多种手法的独特运用
(一)简单的叙事风格
红柯的小说淡化情节、淡化叙事,在对自然景物和生灵的描写中显示出其简单的叙事风格。《美丽奴羊》中屠夫杀羊本应是写实性极强的描写文字,但红柯却打破平俗的风格,以浓墨重彩的写意挥洒出有声有色、有缓有急的人羊共鸣、共奏华章的精妙画面。《牧人》中,红柯把苍茫的草原风光、羊吃草的情态、牧人对羊的热爱、牧民的风俗习惯、狼的尾随及少年杀狼等一系列的西部草原风景图用解构了的牧人寻羊的故事串联起来,犹如一串精美绝伦的钻石项链,每一颗璀璨的钻石都蕴涵着一个美丽的世界。《紫泥泉》中叙述大学生培育美丽奴羊的过程也是幻化奇特的抒情写意风格。“大学生勒马于天山之巅,呼吸着一种英武豪迈的王者之气”,[1]当他体会到了“科学不喜欢顶礼膜拜的人,它钟情的是强悍的王者”,[1]领悟到了大自然的神性时,“儿子和羊羔是他伸向大地的双臂”。[1]儿子和羊羔都是大学生感应到自然神性后的杰作,两者在他心中的地位相当,彼此幻化,妻子分娩后他将刚出生的孩子像刚出生的羊羔一样,抱到紫泥泉汇入马玛拉斯河的地方用冰凉的天山雪水冲洗一下,并抱着一只漂亮的羊羔来到妻子身边,以至于妻子也“以为自己生了双胞胎”。[1]红柯要表现的正是简单的西部生活中那种原始神秘,充满野性神性的精神,这种大气、广博而又缥缈的精神是很难精描细画的,但红柯做到了,他让这“诞生过柯尔克孜人伟大史诗《玛拉斯》的地方”[1]成为美丽奴羊和他孩子的精神家园,使羊、人、世界的神性精神融为一体。
红柯《美丽奴羊》中的人物大多没有名字,主人公是屠夫、牧人、大学生,每个人的称呼都没有任何修饰包装,出现的角色该是什么身份就称呼他什么。在西部自然世界里,人是简单而渺小的自然存在之一,因此作为类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异的。红柯就是要通过简洁“类”化的称呼回归到表述最自然的状态,并通过原生态写作表达西部自然世界里人与物的平等地位以及自然伟力不可超越的观念。
(二)大气的环境描写
绝域产生大美,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必然产生生命的大气象。红柯超越当今小说中的浅白、世俗、沉闷,以真挚的感情审视和描写西部的辽阔荒凉、富饶美丽、诗情画意与神圣庄严……,在他的笔下,西部是独特而鲜活的。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括山、石、草、木、牲畜在内,都具有灵性、神性,在长期的岁月凿刻雕琢中,散发着诗意的光辉和哲理的光芒。西部土地既为其他生命的存在提供背景,又与其他生命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如《屠夫》中这一段的描写:“麦种已经发芽,地皮还那么嫩,跟处女的肌肤一样,可它们不是处女地了,被开垦了许多年,撒了一茬又一茬种籽,一次又一次怀孕,生长成熟,收割耕耘,但铧犁翻起来的总是湿嫩细腻的处女的面孔。一溜羊蹄印非但没有损伤麦地,反而使地显得平和绵软而高贵。”[1]人在西部土地上开发耕耘,生命血脉已经同这块土地和其他赖以生存的生物融化在一起,顺着天山雪水流淌延伸。红柯笔下的草原风光巨到“一片铜色的原野”,微到一片草叶“潮润的汁液”,广袤西部草原上的万事万物无不入他的笔端,在他的描绘中散发着生命的热力。
(三)蕴蓄的抒情方式
红柯像一株生长在戈壁滩上的红色植物,深深地扎根在西北的草原上。十年的新疆生活,那里广阔的土地、呼啸的风沙、异域的文明使他深深陶醉,奔涌的生命激情让他激动不已,他热情讴歌、大胆赞颂,西部的天地使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飞扬灵动的才情与崭新、深邃的思想,他笔下的西部世界不是荒凉沉寂的,正如他所言:“不再是群山戈壁荒原,而是一种精神,一粒砂一棵草也充满着神性。神性的世界必然挣脱物质的桎梏,凌翔于生命的天空”。[2]《美丽奴羊》凝聚着红柯浓烈、深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是流于文字表面的,而是深藏在字里行间,读者在看似平淡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对西部草原的热爱与赞美,尊重与敬畏。这种意蕴深刻而含蓄的抒情,折射出西北人热烈、奔放而内敛的性格,与西部人们的精神气质相协调。红柯热爱西部草原广阔的天地,但他从不红头涨脸、声嘶力竭地叫喊,而是以细腻的笔触精细描画西部一草一木的美,让人从中体会到他对这片土地爱得热烈而深沉。红柯以其热烈绚丽、深沉厚重的抒情,奔放开阔的姿态,形成了其独特、浪漫、鲜明的特色,蔚然屹立于文坛西北一隅。
(四)别致的修辞方法
人们对于西部原始蒙昧的自然世界的理解领悟程度始终都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性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红柯以他年轻张扬的生命,身体力行的写作态度,在作为自然精灵的动植物身上感受着对自然的领悟和挚爱,因此,红柯笔下的人、动物、植物、景物和自然现象之间相互交往、揣摩、感受,他们在个体上是平等的,都是有鲜明的精神和气质个性的。这不是形而上的、玄妙不可解的神秘过程,而是一种独特的西部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在现实的西部人生活中也处处可见。红柯令人称道的想象力便来源于他对西部精神的领悟,他自己也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思想方式,对世界有了看法,这个看法是独特的,不是学别人的,是自己生命里的东西”。[3]
红柯的想象力是直接的,在《美丽奴羊》中这种直接式的想象力凝结在语言中就成了卓尔不群的比喻和比拟。“瞧他的嘴巴,蓬着黑糊糊的胡子,就像牧草里的石头。长这种嘴巴的人就该当屠夫。”[1]简单的比喻十分形象、深刻,用草原上茂密的牧草里坚硬的石头比喻屠夫蓬着黑胡子的嘴巴,本体和喻体都是人们熟知的草原上的事物,再贴切自然不过了。“原野空荡荡,但原野硬朗,平坦,辽阔,跟航空母舰的甲板一样。甲板底下汹涌着万顷波涛,但甲板是平稳的。”[1]西部广袤富饶的原野表面看来是安静、平稳的,但下面奔涌翻腾着如石油般原始而新鲜的生命动力,只要凿开一个井眼,便会奔涌而出,汩汩不息。“月亮一点一点升起来,像一只明亮滚圆的羊,雍容华贵,仪态万方,走过来,一直走到这个沉睡的男人身边。”[1]用美丽奴羊绵白柔软、肥胖圆滚的身躯比喻皎洁的月亮,它温顺柔和的脾性、灵性高贵的气质也同月亮一般无二,再巧妙地将喻体比拟成一个高贵的女人,眷顾醉酒沉睡的西北汉子,比喻十分奇特、巧妙。
红柯描绘西部的笔触细腻、别致,即使是没有思想感情的动植物也感情丰富细腻,好似恋人间的亲昵,《牧人》中羊吃草一段的描写称得上是经典:“羊黑黝黝的嘴巴碰一下叶子,脑袋一偏,黑嘴巴热乎乎跟烙铁一样把草苗条的身形全熨出来,草就软了,颤巍巍靠在羊犄角上,螺形大角是按河流的波浪线长出来的,比草的线条更曲折更流畅,草不由自主地淌起来,跟羊犄角上的旋涡搅在一起,死心塌地不惜一切。羊嘴巴便咬住草的纤腰,咂它的汁,越咂越多,像是从地底下伸出来的绿管子”。[1]羊类似于人的温柔、亲昵的动作熨出草纤细的腰身,草便瘫软在羊犄角上,心甘情愿地奉献它积蓄了很久的纯朴与温情。被羊连根吃掉本是草噩运的降临,生命的结束,在红柯的妙笔下,羊却成了欣赏草的青春激情,发掘草的精魂魅力的知音,草是情愿将自己的美好奉献给羊、回报给羊的,如同知音般互赠互酬。多么富有暖暖的人情味的比拟!
(五)深刻的象征手法
象征是红柯《美丽奴羊》中运用的一个突出哲理化的表现手法,他在文中设置了一些具有复杂抽象的思想内涵的具体形象,读来虽美好却不轻松,它可以让人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等深邃悠远的问题。在《美丽奴羊》中,我们几乎可以探究出每一个人与物的象征意义,他们都是大自然造物和人文精神融会贯通产生的复杂体。如果仅仅意会《美丽奴羊》这篇小说的表面文字,那么就会流于肤浅,只看到如照片般平面式的草原物象,而远非它们所承载着的,作者所崇拜并意在张显的生命意识。这种西部民族所具备并钟情的“生命意识”,正是我们从红柯小说中汲取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红柯对于自然神性的顶礼膜拜使他的文章有着极深刻的象征含义,呈现出许多象征意象。羊、草、人已经不仅仅是这些称呼本身所具有的原始意义,他们被红柯赋予了超越本身的神性力量和深刻的生命存在涵义。
三、简明结构的精心架构
《美丽奴羊》由三个若即若离的小短篇组成,它们各自独立又联系紧密,“美丽奴羊”是三个短篇衔合的链条。整篇小说结构单纯明晰,自然流畅,不绕弯子不设悬疑,拒绝戏剧化,与自然生态、自然状况融为一体,读来清新明朗,耳目一新。
《屠夫》《牧人》和《紫泥泉》各有其性格迥异的主人公和独特的故事情节,但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辽阔壮美的西部大草原,故事情节都离不开美丽奴羊。三个短篇反映的主题不尽相同,但又共同描画了西部大草原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所以三个短篇是形散而神聚、貌离而气合的。这样写既增加了小说的阅读视野、内容涵盖面,又深化了主题,扩充了旨趣。
小说以美丽奴羊为主要书写意象,西部草原的美丽生灵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熏染为主题,用三个不同主人公的小故事作为主体意象的稳定架构,从屠夫、牧人、大学生的精神洗礼中展现西部草原神性对人的精神改造,从而突出表现美丽奴羊神秘灵动而令人向往的特质。小说的三个故事各成一体又殊途同归,指向简单而又展现了西部草原的鲜活生灵的代表,人物多样而主题同一,结构散而不乱,分而稳固,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感受到草原文化丰富深邃的内涵,在明澈的感情浸染中得到精神升华。
《美丽奴羊》三个短篇中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都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凶狠残忍的屠夫因受美丽奴羊凝视的感化而放下屠刀,找回本真的他;原本仅有身份而并未有精神实质的牧人被羊放了一回之后,成为带领羊群奔赴圣湖的大自然之子;羸弱而书生气十足的大学生因美丽奴羊美妙名字的吸引与召唤,被天山气脉熏染、陶冶成壮硕强悍的西北汉子,征服了女记者,收获了爱情和事业的结晶——儿子和美丽奴羊。这三个人物精神世界的转变,都以美丽奴羊的心灵关照为过渡,人物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前后形成了鲜明对比,强化了主人公的形象,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美丽奴羊》的文章结构是火车车厢式的,全文分为《屠夫》《牧人》《紫泥泉》三个车厢式的小短篇。每个故事就是一节车厢,一个文章载体,故事中作者有意无意间穿插附带的草原景色、羊吃草的情态、少年杀狼、大学生吃馍等画面,就像车厢内坐席上的乘客,他们的故事内容十分丰富。乘客充实着车厢,内容充盈着文章载体。它们紧密连接,成为一个共同体,推动着《美丽奴羊》号这列轰隆隆地喷吐着西部生命豪情的火车向前驶进。
作家大胆设计,从容着笔,将本来就以短小精悍为特征的短篇小说再拆分成三个故事,用老练的文笔徐徐铺开绚烂的叙述。三条故事的彩线连接成西部草原美丽风光的观光线路,风景各异而又互为补充,主线清晰又不失美景纷呈,让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横向延伸的多彩无边的锦绣美景,又可以看到纵向深入的深刻明丽的璀璨光环,有铺陈,有宗旨,看似简明的结构,实际上是精心的架构,让人拍案叫绝。
四、精彩语言的个性表达
红柯小说的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清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简洁传神的语言运用
红柯携着古朴豪迈、粗犷强悍的大西北旷野之风,给当代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刚劲的阳刚之气。他的西部小说充满了新鲜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当今文坛迎着西北风沙招展的一面旗帜。
红柯的《美丽奴羊》语言质朴、简洁、清爽干净、蕴涵深厚,具有独特的语言表现力、舒畅俊逸的风格和来自大自然的清新气味。如《屠夫》中“那么白的羊那么绵的羊,不跑也不闹,静静地呆在林带里,像树梢挂住的一堆白云”。[1]作者只用了“白”“绵”和“白云”三个简单的词,就把如白绒球般的羊温驯的性情表现了出来。再如“麦地那边的草被割光了,草茬的皮已经枯黄,心还是暗绿色,还可以看见潮润的汁液。牲畜的粪便干硬发黑,踩上去很脆,像木柴片。高草全长在靠近河滩的地方,那里全是大石头,草从石缝里渗出来,遮住了石头,割草人不会在这种地方挥大撒把”。[1]平实朴素的语言将西部特有的草原风光尽现眼前,不是雄浑壮阔的奇丽景象,而是清秀、恬淡的牧场秋天景致。“草从石缝里渗出来”,一个“渗”字足见红柯炼字的本领,石头也阻挡不了草旺盛的生命力,勃发的生命汩汩地从石头缝中涌出,无止无息。
红柯还擅长用短句来干脆、明晰地表达自己对草原的认识与感受。《美丽奴羊》通篇都是短小、平实而隽永的短句,就连人物对话也干脆利落,意味深长,这不仅体现了红柯简练、深刻的文风,也符合西部地域人们含蓄而内敛的性格。“很牛皮,对大家连看都不看,连长给他敬烟,他只朝连长点点头,然后吸烟”,[1]技艺高超的屠夫目中无人的傲气尽现读者眼前;“丢了羊,丢了多少,不清楚,反正把羊丢了”,[1]简单句的反复突出、强调,表现出牧人“丢”了羊紧张焦急的心情。
红柯的小说不太注重故事本身,而是注重叙述语言,他的语言表达极为准确到位,这使得其小说语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审美对象,十分传神、精致、漂亮。屠夫杀羊一段描写得酣畅淋漓、入木三分:“屠夫把羊拎到广场的矮桌上,起手一刀,羊脑袋拎在手里,羊身子瘫在屠案下。屠夫丢下羊脑袋,抓起羊后腿,用刀尖一挑,羊皮就开了,很低沉地哗那么一声,刀子从脚跟蹿到大腿上,再用劲,从肚皮到脖子拉开一道缝,整个羊全开了。……刀子又轻又快,羊皮发出嗞嗞啦啦的响声,跟扯布一样。刀刃像哨子,在屠夫手里响着。……刀子左右飞动,越飞越快,整个羊发出骤雨般的轰响,仿佛两架钢琴在里边演奏”。[1]“羊身上像有一道尼龙拉链,屠夫一拉就开了。”[1]在红柯十分简明、形象、老道的语言描写下,屠夫简直就是一个高明的艺术家,他庖丁解牛般娴熟的杀羊技能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二)诗意化的语言运用
写小说之前红柯曾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也是他诗意迸发的另一种形式。他的《美丽奴羊》中,少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叙述,少有细致描绘的人物形象,他更多的是用充满灵性的语言为读者呈现诗一般的抒情韵致,浓得化不开的情绪。如:“他对这只羊特别精心,动作慢了许多,刀子的响声又细又长,跟小提琴一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屠夫和他的刀子一下又一下,每下都是他杀生生涯的绝活,都是天籁之音,那刀刃仿佛游动于苍穹和地心,当羊皮摊开时,弥漫于天地间的音乐一下子从赤裸的羊身上涌流而出。”[1]本来,屠夫杀羊是充满血腥和恐惧的事情,而红柯所描绘的杀羊场面却如同小提琴家演奏一般,优美而灵动,是一种身心交融的享受,令人陶醉其中。
红柯在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摆脱诗人的写作方式,他总是精心雕琢语言,努力用诗一样的语言展现他独特的感觉。“他看到美丽奴羊特有的双眼皮,眼皮一片青黛,那种带着茸毛的瞳光就从那里边流出来,跟泉眼里的水一样流得很远很远。”[1]其实,美丽奴羊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妙的名字,让人联想起温柔圣洁的天使。即使是再凶悍残忍的屠夫,被美丽奴羊“清纯的泉水般的目光”[1]凝视,也会放下屠刀,甘心做一株被它垂青的牧草。这种诗歌般美妙灵动的句子,与徐志摩的“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在内蕴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了红柯小说语言的优美、纯净、精致,灌注了作者强烈的感情。西部草原人粗犷、刚健的力量被大自然的精灵——羊,那温柔、细腻的神性目光融合,既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又合情合理,透射出西部精神的神秘和伟大。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红柯笔下诗意化的句子如泉水般流淌,绵延不绝,浸润了草原的一株株牧草,绿化了一片片土地,使荒凉粗犷的西部草原有了生机与灵气。
(三)哲理化的语言运用
红柯的小说极富诗韵,但他写下的不是浪漫轻柔的抒情诗,也不是曲折蜿蜒的叙事诗,而是涵义深刻的哲理诗。他的小说不引导人们关注日常现实,而促使人们萌生对自然的神往,对日常琐碎生活的超越的想法。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灵性融合的思考,对自然界里一切包含勃勃生命力的赞美和歌咏。“美丽奴羊就用这种清纯的泉水般的目光凝注牧草和屠夫,屠夫感到自己也成了草”,[1]“他栽倒时手和膝盖着地,刀子扎进沙土,连柄都进去了。他望着比他高的羊”。[1]那只地地道道的新疆美丽奴羊毫不惧怕死亡,它清澈如水的目光卸去了屠夫手中的刀子和心中的杀气,它大自然神物般的高贵和神圣,使屠夫拜倒在它脚下,仿佛虔诚的信徒。这只具有灵性的美丽奴羊给予了屠夫对生命全新的思考与感悟,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牧人》这则故事比《屠夫》的哲理意境更加深远、渺茫。老牧人把牧人失魂落魄地寻找其实并未丢失的羊解释为“放空羊”,“不是白跑,是牧人让羊放了一回,放了一辈子羊,羊嘛也要放他一回”。[1]在羊与牧人的关系互换中,红柯将牧人爱羊似乎到了疯狂的冥幻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现实而言,这种关系并不荒诞,羊人合一的魅力完全来自于红柯对草原牧人心灵的体验。“草原的青春激情与魅力全被化解在羊优雅的举止和细腻的动作里”,[1]“草发芽长叶吹风淋雨晒太阳,就是为了让羊热乎乎的黑嘴巴轻轻地碰一下,狠狠地咂一下,细细地嚼一下。草的魂儿都出来了”。[1]羊以其自然的生命方式和思维方式理解感悟着自然,比牧人更多几分灵性和深刻,并让牧人在和羊的心灵沟通中变成自然的一部分,和羊一样成为自然的神灵。
五、结语
红柯的《美丽奴羊》以其丰富深刻的象征意义,复杂多样的表现手法,简单明晰的文章结构,简洁、清新、传神而又极富诗意和哲理的语言来揭示深邃的主题意蕴,这些精熟的技巧使其小说《美丽奴羊》显得精巧雅致、淳厚质朴、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美丽奴羊》中,人与物相互敬畏,启迪着生命灵感,张扬着自然生命力,他把对自然神性的认识与生命力的体验和感受融入进诗一般的语言之中,“他将对生命力的体验渗透到小说的字里行间,使我们从生命的自由舒展中获得了存在的意境与快意”。[4]在当代诸多描写西部美丽世界的作家中,红柯展现出他独特的文笔与清丽的风格,确立了他无可替代的文学地位。可以说,红柯以他十数年新疆生活的沉潜为底蕴,用优美独特的文学笔触,展示出一个特立独行而又温情脉脉的观照世界的文学空间,表现出一个优秀作家的潜质和能力。虽然他已长眠于西部的莽莽山岭,但他留下的浩瀚阔大的文学抒写却注定会让无数的读者流连忘返,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