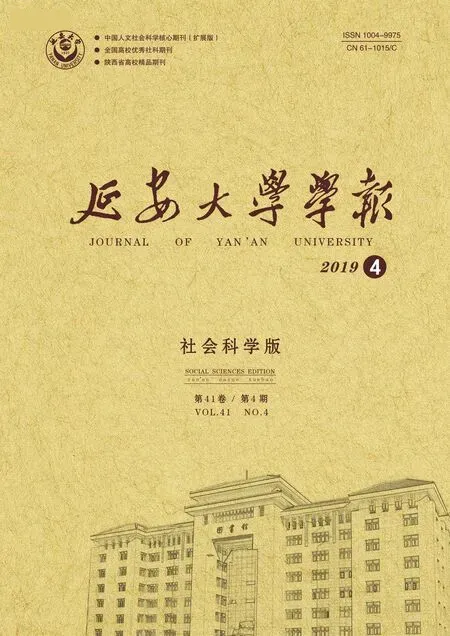比较法视角下的有限自治
——论我国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的限制规则缺失
2019-12-08徐秉鹏范书江
徐秉鹏,范书江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陕西西安710122)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7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该规定在法条的结构逻辑上,允许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定置于首要原则性地位,将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置于补充性地位。这说明我国对于涉外动产物权的适用法律规则完全开放了意思自治选择法律适用。在比较国际私法视角下观察,有别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国际私法给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一个十分显著的突出地位,同时在广泛的领域内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1]物权冲突法中是否规定意思自治原则主要考虑一国立法对于物权法性质的定性,如果私法自治空间在物权法有所体现,即在物权法中有一些任意性的立法规定,则在任意性法律规范的涵盖范围内允许意思自治是符合物权法性质的。[2]然而不论是运用以比较法方法为基础的对比分析,还是通过以我国物权法为基础的法律价值一致性的理论推导,都充分显示出涉外物权领域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只有极其有限的适用空间,如果控制不当,任意扩大适用空间,则会造成以偏概全的不合理状态发生,对于司法实践以及理论明晰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种开放性的体现显然是过度的。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不可或缺,目的是梳理清晰法律整体的逻辑,将合理的意思自治空间准确地体现在涉外物权适用规则领域。
一、比较国际私法角度的分析参考
(一)《罗马Ⅰ规则》关于合同中意思自治限制问题的评述
从《罗马Ⅰ规则》关于合同之债的准据法规定,可见欧共体国际私法的最新发展状况,它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私法的合同领域中得到了最广泛的运用和承认。不论是早期的《罗马公约》亦或是如今的《罗马Ⅰ规则》都赋予合同当事人有选择适用准据法的自由,此项法律选择自由构成了关于国际合同的整个法律适用规则体系的基石。[3]相比于物权领域引入意思自治,合同领域则表现的更加理所应当。因为在实体法层面各国立法对于合同的规定都采取开放的态度,合同双方依据意思表示达成合意应当被保护是毋庸置疑的公理。但即使是在涉外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开放,也不是丝毫没有限制。《罗马Ⅰ规则》第三条采用四个款项对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合同准据法做出合理的边际限制。
其一,第3条第2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随时变更合同准据法;他们可以随时约定合同原先所适用的法律以外的另一法律支配。但在合同订立后进行的一切有关准据法的变更,不影响合同的形式有效性,且不妨碍第三人的权利。合同之债在一些情况下不仅涉及双方利益,根据不同形式的合同内容也会牵扯到第三人利益,例如,在债务承担合同和债权转移合同或第三人保证的法律关系中就涉及到第三人承担责任的问题。此时对第三人利益进行保护十分必要,因为出现的利益第三人无法预见合同双方选择准据法的合意目的,公正合理的做法理应保护第三人利益,规定当事人双方选择的准据法不得对抗第三人。
其二,第3条第3款规定,如果在法律选择时,情势的所有其他要素均位于被选择的法律所属国之外的另一国家,则双方当事人的法律选择不得妨碍另一国家法律中的那些不得以协议方式加以损抑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这一规定很有效地防范了当事人之间通过协议达到法律规避目的的情形。也可以排除掉合同法律关系适用中一些虚假的涉外适用法律问题。同时给与法官在合同问题上一些自由裁量权,当情势的主要因素集中在该国时,适用法律不会破坏该国的强制性规范。
综上两款合同选择准据法限制规定的分析,必须注意到动产的选择适用准据法其实更加容易出现利益第三人的情况,并且由于物权的对世性及绝对性的特征,第三人往往不特定。所以原动产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则不得对抗第三人利益的做法是合理的。同时要限制自由选择准据法的范围,防止出现法律规避和虚假冲突。
(二)《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关于动产权利的评述
通常情况下对于美国冲突法中关于财产权的准据法适用问题有一个笼统的认识,即就是不存在关于财产的特殊连接点,统一适用与该物及当事人有最重要联系州的法律。[4]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作为指引冲突法实践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实是根本性的基石原则。美国冲突法重述第220条总则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当事人对物的权益,依在该特定问题上按照第6条规定的原则与当事人有最重要联系的州的法律或本地法。但是最密切联系原则不是没有任何限制而片面地适用。相反第九章财产权对于各种财产权利做出了明确的划分。事实上,不难发现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动产物权领域的诸多权利是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约定适用法律,并不是单一的由最密切联系原则来指导。例如,动产权益转让的有效性和效力、以动产中利益为担保的有效性和效力、担保权益的执行的回赎,行使经双方同意而产生的权力等四个方面都有允许当事人约定适用法律。只是这种约定不能与原则性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过分抵触,在实践中主要是给与法官自主的裁量空间,符合普通法国家的司法审判传统。
具体而言,第24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未作有效的法律选择,确定准据法时,对动产转移时的所在地,较之其他任何联系,将予优先考虑。第246条第2款规定,如当事人未作有效的法律选择,确定何州法律适用时,担保权设立时动产所在地,通常较之其他任何联系,将予优先考虑。第25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未作有效的法律选择,确定适用何州法时,担保权益设立时的动产所在地,通常较之其他联系将予优先考虑。第256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未作有效的法律选择,确定适用何州法时,转让时动产的所在地通常较之其他任何联系将予优先考虑。当事人有约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当事人约定,无约定情况下物之所在地法才被优先考虑。而最密切联系原则贯穿适用准据法的整个过程。这种方式适合美国司法体制合理消化。这种规制方式虽不适合我国国际私法规范的具体情况,但具有借鉴意义。同样是允许当事人对物权约定适用准据法,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情形限定为四种情形,并没有过分放大。例如,在动产权益是否因行使依法创设的权力而发生转移,以及被转移权益的性质的认定上,并不允许在当事人意思选择适用,规定由依法行使该权力时动产所在州的法院将予适用的法律。例如,转让对转让前既有动产权益的效力同样不允许约定。这种约束限制可以防止自治权利乱用的情况,当然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官自由裁量的判断,在发现不合理的自治约定出现后,可以利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否定诸如法律规避,虚假冲突的产生,这是美国冲突法在设计之初的特有优势。在国际私法的发展中,德国法也试图吸收这种最密切联系原则并扩大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46条规定:“一国的法较之依本法第43条至第45条的规定本应适用的法与物权事件有密切得多的关系的,适用该国法。”[5]总而言之,动产适用意思自治方面,美国冲突法重述的态度也是开放的,但同样做出了动产类型上的诸多限制。目的为了防止自治权利过大产生的不合理情形。
另一方面,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对动产变动及相关物权效力问题中可能出现第三人的情况也进行了合理的限制。第247条规定,动产权益,不得仅因其移至另一州而受影响。但是在该另一州就此项动产所进行的交易,则可能影响此类权益。第252条规定,仅将动产移至另一州,既不取得也不丧失动产担保权益的有效性。但在该另一州就此项动产进行的交易则可能影响该动产的担保权益。
该两条规定首先对机械地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进行了否定。动产上所拥有的权益不因其转移至另一州而产生影响。实际就是物上的权利不因物的所在地而必然产生本地法的支配效力。若当事人之间对于物的权益已经约定适用某州法律,即使该动产被运到任何另一州,当事人在物上的权益也不会因地点的变化而损益。动产移动范围变大和移动可能性变强在如今交通发达及贸易沟通频繁的情况下普遍存在。不因动产转移而影响物上权益的规定是合理可行的做法。以上情况的限制规定在法律规范的后半段说明,在另一州发生交易则会影响原有物上的权益。笔者认为该规定虽然没有提到第三人问题,但是对实践中物上可能出现第三人权益的情况的一种考量。物上可能仅有个人单独的权益,也可能因交易、租赁亦或担保抵押而产生双方分别对于物具有的相应权益。若动产转移在另一州因交易产生其他法律关系,则可能会在物权上产生新的第三人的权益。一方面因交易活动,物上权益与物之所在地法会发生实在联系而受到该法律的支配。而物上原有权益就可能受到此种第三人权益的影响。在法律适用方面受原权益支配的法律将会让位于发生交易的物之所在地法支配。在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层面事实上产生了作用。但具体会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还是原约定适用法律,还会由法官再去结合第六条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裁量如何适用。不过这一参考规定已经体现出对可能出现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动产物权适用法律的认识方面有很高的可参考性。一方面在动产权益的几个领域范围内,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体现出开放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配合着原则性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把这种自治性扩大的弊端缩限在符合法院认定的利益之下。另一方面规定也否定了僵化单一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做法,对于会出现第三人新交易的适用法律方面也有所保护。[6]
(三)瑞士国际私法中关于动产物权引入意思自治的评述
瑞士国际私法法典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国际私法制定法中最为详备的一部国际私法法典。它借鉴了欧洲当代国际私法的各种学说、判例、立法和国际条约中很多先进且合理的解决思路,所以立法水平和质量很高。[7]在物权领域,瑞士国际私法首先做出突破。传统而言,动产物权法律适用指向的准据法是物之所在地法。而该法为了打破统一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刻板僵化,将动产物权的取得和丧失所适用法律与动产物权的内容和效力所适用法律划分为不同的适用选择。在动产物权的取得与丧失即物权变动方面允许当事人有限的法律选择作为物之所在地原则的若干例外情形。[8]第104条规定,对于动产的取得与丧失,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货物发送地国家的法律、货物送达地国家的法律,或者适用调整基本法律行为的法律。并在该条第2款说明,此种选择不得用以对抗第三人。
笔者认为,瑞士国际私法对于物权引入意思自治的尝试和限制规定都具有示范意义,并且逻辑明确,立法目的清晰。首先,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入涉外动产物权的适用问题,最容易考虑到的就是会否出现与实体法当中的物权法定原则相抵触。而该法的规定是将动产物权的变动效力与内容效力分开讨论,仅允许在动产物权变动效力进行有限的意思自治。而一般意义上的物权法定是针对物权的内容和种类加以严格的法律限定。所以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也并没有被允许自由创设物权内容,只是在动产物权变动上加入了有限自治。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不会与物权法定原则相抵触,并且与实体法保持立法目的的一致性。而这样开放自治的目的在于,将同一关于物权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准据法适用和物权准据法适用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避免分割适用的弊端。其次,当事人只能在发送地国家或目的地国家的法律和物权的取得丧失据以发生的法律行为所适用的法律当中进行选择。这样会进一步缩小当事人自治的范围,只能在与物权法律行为有密切联系的几个连接点范围内进行选择,同样有利于防止法律规避或是虚假冲突的恶意自治的情况发生。最后,在第104条第二款规定了此种法律选择不得对抗第三人,因为第三人通常总是可以从他们已经依物之所在地法而确定的权利中谋取更大的好处。[9]153该款规定旨在对物权中可能出现的第三人加以保护。
综上所述,瑞士国际私法中对于动产引入意思自治的开口相当有限,甚至可以看作是给予当事人一种对于连接点的选择权,且仅适用在动产变动领域并不涉及物权的内容,同时不能忽略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保护。相关规定逻辑脉络周延,参考价值丰富。
二、我国涉外物权领域引入意思自治的空间及限制方法
通过分析对比具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私法规范,可以看出涉外物权领域引入意思自治必须有限制性规范伴随。重点限制的部分包括:一是把动产适用缩限在物权变动方面;二是要考虑到不特定第三人出现时的抗辩效力。围绕这两方面的限制,完善我国涉外关系法规定的不足,满足理论的一致协调,提高司法实践的操作水平。
(一)缩小限制动产物权适用的领域
从比较国际私法的角度去看各国的立法规定。《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作为法律行为标的之财产的所有权与其他物权的产生与消灭,依法律行为实施地法,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摩尔多瓦共和国民法典》第1602条规定:作为交易标的之物的所有权与其他物权的取得与消灭,依照适用于该交易的法律确定,当事人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1194条规定:构成法律行为对象的财产的物权的产生和消灭,由该法律行为实施地国法支配,但当事人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亚美尼亚共和国民法典》第1277条规定:作为交易标的的财产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产生与消灭,依照适用于该交易的法律确定,当事人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1108条规定:作为法律行为根据的财产的物权的产生和消灭,依该法律行为完成地国法,但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
上述国家在涉外动产物权的适用上都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但是规定中仅仅涉及动产物权的变动方面,即标的物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取得和消灭。这个范围不能再扩大,只能针对物权变动方面。而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7条将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法律的任意性规定适用于整个动产物权领域。对于动产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作为我国《物权法》的强制性规定是不能适用意思自治的,因此在内容范围上应该限制为动产物权的变动方面,以动产物权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取得和丧失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适用选择法律的范围。
(二)增加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从比较国际私法的角度,各国涉外动产物权领域引入意思自治的同时都考虑到需要兼顾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瑞士国际私法》第104条规定:对于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与丧失,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动产物权的取得与丧失,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发送地国法律、目的地国法律或者支配致使物权取得与丧失的法律行为的法律。此项法律选择不得对抗第三人。这项规定经常被认为过于刻板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变得稍微灵活了一些。同时,依照第104条第2款的规定:此种法律选择不得用以对抗第三人,因为第三人通常总是可以从他们已经依“物之所在地法”而取得的权利中谋的更大的好处。[9]156除此以为,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210条以及《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章国际私法第1.49条、第1.51条都有关于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规定。
在动产物权法律适用中不论是适用选择的法律还是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律,都很难照顾假设会出现利益第三人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涉外动产的跨国变动相对复杂、流通性强。但是从民法中物权的性质去分析,考虑到物权的对世性和排他性,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同时保证第三人不受物权效力存在瑕疵时的影响,又不得不兼顾第三人利益出现受损的情况。在涉外关系适用法方面,表现为第三人可能并不知道当事人双方协议适用法律的内容,一旦约定适用的法律与第三人默认发生法律关系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这就造成了第三人利益的损害,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为了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这一弊端,所设定的限制应当是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能对抗第三人。此情况仍然适用原则性的物之所在地法。这样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对于第三人利益损害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维护同一涉外物权关系上各利害关系人的公平一致。
三、结论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7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法律的适用方面确实过于宽泛,其打破了物权领域引入意思自治的限度,易于造成理论上的混乱。笔者建议可以在未来将要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明确限制该条内容的适用。具体解释内容可以规定为:当事人可以选择动产物权变更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不得对抗不知情的第三人。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如此一来,意思自治在涉外动产物权上的适用可以被限定在更加合理的空间范围内,有利于发挥这一规定的创新优势。最后还应说明,我国涉外物权方面的开放性是超前的,我国物权冲突法引入意思自治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物权法任意性规定与物权法定主义缓和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各编的起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习惯法的相对承认与物权法定主义缓和的扩大是必然趋势。相应地,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体现也会不断巩固。国际私法领域应当重视民法领域新的理论变化,及时思考调整本领域的发展走向,以便梳理两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基本一致的立法价值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