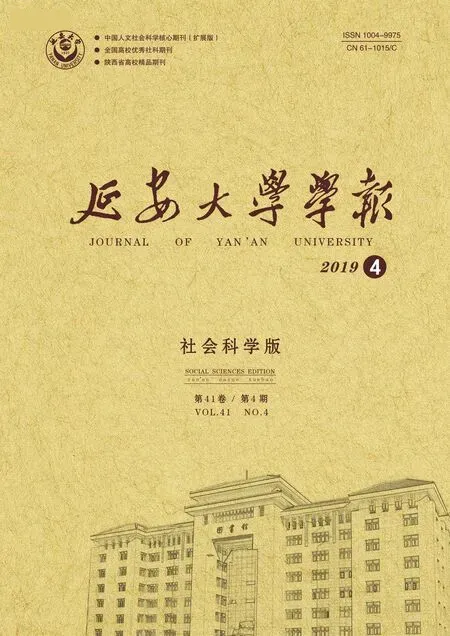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苏区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探析
——以《西行漫记》为中心的考察
2019-12-08刘新全
刘新全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枣庄277160)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当地群众对其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如何动员群众并取得他们的支持,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引导、整合和动员作用。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主张与陕北地区群众所熟知的传统文化具有质的差异,故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何种工作措施和机制,来实现民众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国记者从“他者”的视角来观察和解读这个问题的案例。
《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over China),是斯诺基于1936年6月—10月在陕北苏区考察和访谈的资料而写成的。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各界轰动,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往对《西行漫记》的研究多集中于报告文学、新闻学和历史学等视角,对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动员与工作问题没有展开系统论述。事实上,斯诺陕北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深入到中国革命的基部——普通的革命群众中,以此了解中国革命并预言它是否会取得胜利。[1]斯诺对中共领导的政权和军队如何组织、教育和动员民众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述,探求“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农民支持它吗”等问题的答案,这其中包含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的论述。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研究较为全面,但基于实地考察的素材进行案例式的解读却几为空白。为此,本文基于《西行漫记》的相关记叙,对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苏区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进行探析。
一、阶级建构与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工作前提
恩格斯认为:“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个人接受某种思想。”[2]463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民众并不必然予以认同,特别是对当时生存于封闭落后的陕北地区民众而言,更是如此。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更好地利用意识形态来引导和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是所属阶级身份的认同。作为表征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中的结构或位置的概念,阶级身份蕴含着忠诚、认同的内在依据。[3]如果这些依据发生变动,成员的忠诚或认同基础就发生了变化,新的身份与意识形态认同也可能因此而生成。传统上,农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4],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5]这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内涵相悖,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主张。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是由社会通过一系列的知识教化和权力惩罚机制而建构的。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现实存在的“贫富”差异予以解构,穿过日常生活的经验层面,与更为宏大和基础的“阶级”联系起来,指出这种差异的根源——“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差异,并对“被剥削”阶级予以扶助和解放,对“剥削”阶级予以抑制与剥夺。如果农民认知到自己“被剥削”的身份,那么就会从生活经验层面来提升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主张的认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470在《西行漫记》中,斯诺注意到,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把农村人口划分为这几个阶层:大地主、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流氓无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6]174并认为:“这种划分不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政治上的划分。”[6]174这种身份建构使民众熟知的“穷人”“富人”身份认同转化为具有政治属性和道德意蕴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身份归属,而中国共产党作为“解放者”的身份,其意识形态作为谋求“解放”的理论,自然能够获得被剥削穷人的认同。斯诺观察到这种“身份”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他们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当然,他们对红军的政纲是很少有什么概念的,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6]156显然,当红军成为“穷人的队伍”,苏维埃被视为“我们的政府”,就意味着贫苦农民认同党和红军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解救者的身份,其所主张的意识形态自然也获得了认同。
“身份”建构除了重构农村社会结构外,还辅之以对新身份“话语”的广泛宣传。意识形态总是以特定语言为载体,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特定话语交往和思考,这表征他认同并接受了这种话语蕴含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话语转换具有如此功效,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建构身份认同时,通过识字、戏剧、演讲等形式将“话语”渗透进受众生活世界中,使民众从接触、理解,到逐渐认同并日常使用,从而达到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在访问时,斯诺常惊讶于10多岁的孩子随口说出马克思主义词汇。[6]268书中记述,斯诺曾对孩子口中说出的“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6]51参加苏维埃和红军“是爱国行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6]196等话语和认识表示了极大的感慨。
二、利益给予与物质扶助:意识形态工作基础
任何意识形态教育的对象都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首先考量的便是其现实生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是谋求全人类的解放,这内在包含着被解放对象的利益满足问题,因此在动员农民认同意识形态、支持革命时,也必须强调物质利益许诺与实现问题。米格代尔(Joel S.Migdal)认为第三世界的农民革命运动“必须向农民个人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8]199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调物质利益给予的基础作用,在于“从多年的革命活动中,中共领导人懂得了对于农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谋生的问题。任何动员农民的努力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中共党人不是抽象的救世主,革命要发动起来首先得满足农民的具体需要”。[9]1934年,毛泽东就强调不能疏忽、看轻群众需要的满足问题,认为这对发动和组织群众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解决和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0]137在陕北苏区,斯诺注意到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对群众利益扶助与给予方面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对意识形态认同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要真正了解农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必须记住它的经济基础。”[6]176-177陕北人民之所以支持红军,共产党之所以在陕北地区受到群众拥护,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苏区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对贫农低利或无利放款等解决了“农民的当前问题——土地和租税”,[6]173“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农’成分的处境”。[6]177
如果说前文中的阶级建构和身份认同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情感的亲近,那么利益给予与物质扶助则提供了情感亲近的物质基础。这种通过利益认同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做法,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原则。正如毛泽东强调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接受我们的政治口号。”[10]138
三、组织嵌入与网络覆盖:意识形态工作依托
马克思曾经评价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农“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11]762之所以如此,在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而且这种隔离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11]762当时陕北地区的农民也处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也同样交通不便和处于贫困。显然,这种“一个个马铃薯”的分散状态不利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开展。米格代尔认为,决定农民参与革命运动可能性大小的因素之一是能通过招聘和吸收农民加入革命来扩大革命力量的革命组织的出现。[8]198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具有广泛覆盖性的组织网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依托。
以组织网络及其约束力为依托展开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做法。1925年,中共中央就提出团体应该群众化,力求通过组织去接近群众,以利于其宣传工作的开展的要求。[12]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群体中建立的各种组织印象深刻,“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6]175除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等传统组织外,还有外围的少年先锋队、儿童团,将大部分青少年都纳入其中;同时还将妇女们通过共青团、抗日协会、幼儿园、纺纱班、耕种队组织起来,成年的农民则组织在贫民会、抗日协会中,“甚至哥老会这个古老的秘密会社,也让它参加到苏维埃生活中来,从事公开合法的活动”。[6]175这些组织和委员会“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6]175“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6]176这些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广泛参与的群众团体的建立,一方面以制度化、规范化的组织为网络依托,为常规的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可靠媒介;另一方面使得意识形态可以转化为组织规范,利用组织的集体氛围和群体压力对成员加以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约束,并辐射到周围群众。
四、生存感受与价值共鸣:意识形态内容铺陈
“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理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13]但理念的未来趋向并不代表着只要宣传美好的未来,意识形态就会被受众所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认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1]152现实生活以及基于现实的主观体验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切入点。相对于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普通农民更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中,对个人生存构成现实影响的事物。如果这些事物引发农民内心深处的价值企盼与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相契合,那么就产生价值共鸣,从而推动认同、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在陕北苏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内容都是围绕着农民现实生活及其生存性感受而铺陈的,现实生活框定了意识形态内容的铺陈宽度,而生存性感受则限定了内容铺陈的深度。正如斯诺所评论的,虽然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共产党有可能组织大大地超过社会主义经济初生时期的政治体制……在此之前,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当前问题”。[6]173
(一)生死存亡的抗战意识
1936年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毛泽东在同斯诺访谈时指出:“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6]66因此,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唤醒关系民众生死存亡的抗战意识。在苏区考察期间,斯诺看到了围绕“民族危亡”展开的紧张宣传活动,其中以“人民抗日剧社”影响最大。该剧社的主要活动就是巡回演出,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6]82斯诺曾观看剧社表演的短剧《侵略》,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对沦陷区人民的奴役,包括日军把中国人当椅子坐,侮辱中国人的妻女,强迫农民购买毒品,吃完东西不付钱,乱杀无辜,以及最后村民群起反抗等情节。[6]84显然这些节目的编排都是围绕群众的生存感受而展开的,并蕴含着万众一心奋起反抗的全民族抗战主张。为了让民众强化民族危亡和抗日意识,报纸公报、群众大会、示威、群众讨论等各种宣传方式都被充分利用起来,宣传内容甚至加入了对法西斯侵略他国的介绍。对于陕北民众而言,这些全方位的、浅显易懂的宣传使得日本侵略成为一个与自己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斯诺发现,甚至在穷山僻壤之间的农民们也知道德意法西斯侵略的一些事实。他评论说:“共产党的宣传已造成普遍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们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险。”[6]196
(二)生产合作的经济意识
陕北地区地处偏远,土地贫瘠。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普通民众来说,衣食住行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斯诺注意到,苏区一方面强调发展生产,政府积极组织农民从事耕种,发布许多命令要求积极垦荒、改良作物、增加产量,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6]176另一方面也在生产过程中添加合作化和集体化因素,使发展生产与集体合作的新经济意识结合起来,“合作化运动在大力推广,其活动已超过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而扩大到像集体使用牲口和农具……这样新奇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组织劳动互助组方面的合作”。[6]178斯诺认为“苏区合作社运动的倾向显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6]181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强迫民众参与,而是通过对合作化运动好处的宣传、教育和奖励来推动。对此,斯诺评论道:“这里,共产党在播下集体劳动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种子——为将来实现集体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6]178
(三)当家作主的政治意识
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在当时特定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动员人民参加革命。因此,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要群众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治意识。这种新政治意识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一贯主张;另一方面也使苏区人民感受到自己“主人翁”的身份,从而更为积极地响应动员,参与革命。斯诺曾考察苏区的政权建设,看到政权结构自下而上设计,体系完善,目的是造成“‘农村无产阶级’的某种民主专政”。[6]174“代议制政府结构是从最小的单位村苏维埃开始建立的,上面是乡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最后是中央苏维埃。每村各选代表若干人参加上级苏维埃,依此类推,一直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凡年满16周岁的,普遍具有选举权……”。[6]174对于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农民而言,民主政治以及政治参与是一个新事物,需要一定的训练和适应过程。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政治动员的方式。斯诺写到:“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6]89这唤起了中国农村中亿万人民的主体意识。
(四)平等团结的民族意识
由于陕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红军也面临着与西北马家军作战的任务,正确的民族意识与党的政治和军事密切相关。因此,党和红军展开平等团结的民族意识教育。陕北苏区的民族意识教育以民族平等与团结为原则,将民族问题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范畴,利用宣传队、军队剧团、政治教育等形式,在红军和农民中间进行宣传。斯诺曾访问回族红军战士,战士回答说:“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都属于大中国。我们的共同的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剥削者、日本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革命。”[6]160对此,斯诺评论道,回族红军“看来已经有了相当的‘阶级觉悟’”,民族宿怨“正在逐步蜕化为阶级仇恨”。[6]260
(五)现代文明的生活意识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先进的理论体系,其内容不止经济发展、政治参与,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新生活方式。基于陕北地处偏僻,民众保守落后的现状,中共及其政权致力于在苏区推广扫盲识字、禁除鸦片、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缠足溺婴、人口买卖等新的生活方式。斯诺看到,苏区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年龄阶段普及文化教育,苏维埃、军队和共产党各级组织都兴办各类学校;不论儿童,青年人和中年人,都参与到识字活动中。识字运动对于意识形态工作意义重大,因为“识字的行为成为一种启蒙的、象征的仪式,这一仪式所完成的,既有对于阶级身份的指认,又有对于构造了语言文字的意识形态的认同”。[14]斯诺在苏区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乞丐,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彻底革除封建的结婚、离婚、遗产、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等糟粕法律和习惯,推行婚姻自由、提高婚龄、禁止彩礼等新规范。对此,他认为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6]179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苏区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受众的接受能力和知识基础,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诉求与民众的现实生存结合起来,富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五、生活世界与潜移默化:意识形态工作方式
中国共产党在设计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时,充分考量到陕北地区民众的意愿和接受能力,不单采用简单的理论说教,而是将意识形态寓于受众的生活世界之中,融于日常学习、艺术和娱乐之中。这种潜移默化的工作方式,一方面使得群众更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教育也因根植于群众的生活世界而得到受众的理解和认同。
(一)寓宣传于娱乐活动之中
在《西行漫记》中,随处可见对苏区娱乐活动的描写,斯诺也注意到这些娱乐活动蕴含的意识形态内容。他认为红军剧社是有力和巧妙的宣传武器,剧社节目更新快、题材新、方式幽默,赢得了不易轻信的农民的信任,“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争取人民的信任”。[6]87-88“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6]86“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6]88虽然斯诺认为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6]88但却满足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众的需要。通过寓意识形态宣传于娱乐活动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民众的宣传与教育,而民众也在娱乐中受到了教育。尽管道具粗糙,节目简单,但斯诺也肯定了这种形式的有效性,因为“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清界限的。惟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6]88
(二)寓思想于读书识字之中
陕北地区长期封闭落后,文化水平低下,正如徐特立所说:“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6]188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苏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以读书识字等活动承载意识形态。斯诺注意到,苏区教育在内容上着眼于政治方面,包括阶级斗争、红军英勇作战、新社会美好未来等方面。教育的“重点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6]189社会教育亦是如此,“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开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6]190在学习中,“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6]190斯诺的这番评论可谓切中了苏区识字教育的精髓。
(三)寓教育于军队工作之中
由于红军主体是由农民组成的,所以其文化、政治和军事素质都需要提高。因此,当时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对红军进行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教育。红军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十分健全,其中开展政治讨论、理论学习和娱乐活动的机构通常是“列宁室”。斯诺注意到,“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这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6]229虽然当时条件简陋,但是列宁室却是部队营房中最好的。列宁室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十分简单,就是“它们的全部生活和活动,必须同战士的日常工作和发展联系起来……必须简单和容易了解。必须把娱乐同关于军队当前任务的实际教育结合起来”。[6]230在一军团二师二团的一个连队的列宁室里,斯诺看到了“绿色的松柏树枝”[6]234“纸制的大红星”[6]234“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6]234“淞沪战争英雄蔡廷锴将军和蒋光鼐将军的照片”[6]234“俄国红军在红场集合庆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6]234等富有政治象征意味的符号。很显然,这些符号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要素,也与当时的抗日局势密切相关,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意识形态诉求。斯诺曾经评论红军中的政治教育“很生硬地带有宣传性的味道,这甚至有点传教的味道,但它的效果很大,这一点是很明显的”。[6]235
(四)寓道理于事实对比之中
除常规教育形式外,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还包括对群众的错误观点予以及时批驳,通常这种批驳都是建立在事实和道理的基础上,从而使得错误观点在事实批驳面前毫无说服力。斯诺在去前线的路上曾与苏区农民聊天,当有农民抱怨苏区物资短缺时,陪同翻译的傅锦魁随即反驳说:虽然苏区条件艰苦,但不用缴纳苛捐杂税,不会失掉房屋土地,而且“我们的生活和你们一样苦,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6]194一个赤着脚的十几岁少年在反驳一个老大爷的错误观点时,也是通过摆事实的方式:“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之前咱们听说过世界新闻吗?……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之前有过合作社吗?……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6]196当听到傅锦魁和这个少年的批驳后,“一切抱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意见是一致的”,[6]194“几个别的农民也连声说是,他们大多数人都面露笑容”。[6]196
透过《西行漫记》,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斯诺对陕北苏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符合当时实际的考察,使我们也能透过这一案例式的样本,从微观上观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举措和效果。从总体上来看,此时意识形态工作已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作体系,通过严密准确的基础铺垫、贴近受众现实需要的内容设计、细致入微的教育方式,绵密的依托网络与组织嵌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陕北苏区的有效整合和动员。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陕北地区特殊的民情和中国共产党特殊的生存境遇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斯诺不止一次评论当时陕北苏区意识形态工作粗糙、重视现实功用等问题,但考虑到陕北地区封闭落后、中国共产党立足初稳、苏区初立、红军西进东征、国民党封锁与进攻的紧迫局势,中国共产党出于政治动员和现实生存的考虑,意识形态工作具有上述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