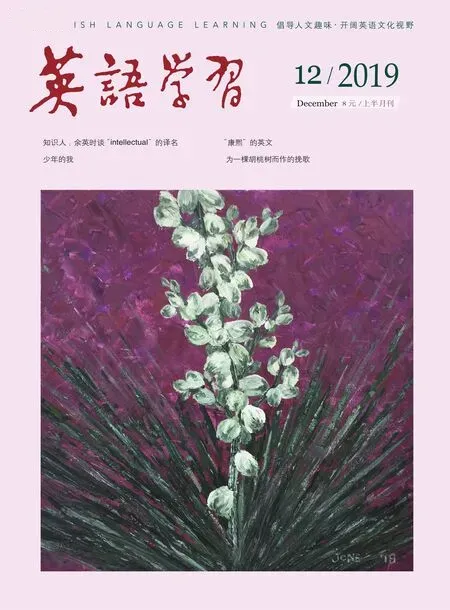I Northern Pike1
2019-12-07JamesWright
James Wright
All right.Try this,
Then.Every body
I know and care for,
And every body
Else is going
To die in a loneliness
I can't imagine and a pain
I don't know.We had
To go on living.We
Untangled the net,we slit2.slit:撕裂,切开。
The body of this fish
Open from the hinge of the tail
To a place beneath the chin
I wish I could sing of.
I would just as soon we let
The living go on living.
An old poet whom we believe in
Said the same thing,and so
We paused among the dark cattails3.cattail:香蒲,长在水边的草本植物。and prayed
好吧,这么着吧。
那么多人,我认识的,
我不认识的,我在乎的,
我不在乎的,都终将
死去。那孤独
我不敢想象,那痛苦
我也未曾知道。只能
这样活下去。我们
解开网,剖开鱼肚,
刀口从鱼尾一直拉到
鱼嘴。我真希望
我能歌唱,如果我能
让生者生。这话,
一位受人敬仰的老诗人也说过。
茫茫香蒲间,
我们停下动作,祈祷。
For the muskrats4.muskrat:麝鼠,北美洲一种半水栖的老鼠。,
For the ripples below their tails,
For the little movements that we knew the crawdads5.crawdads:即crayfish,龙虾。were making under water,
For the right-hand wrist of my cousin6.cousin:未查到此处cousin究竟指诗人的哪位亲戚,但正确地翻译为“亲戚”未免离原文太远,且失了诗味,故权且处理为“表弟”。who is a policeman.
We prayed for the game warden's7.game warden:渔猎巡警,负责保护野生动物,打击偷猎者。blindness.
We prayed for the road home.
We ate the fish.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very beautiful in my body,
I am so happy.
为水边的麝鼠祈祷,
为它们泛起的涟漪祈祷,
为水中的龙虾祈祷,
为我表弟的右手腕祈祷,
他是一名警察。
我们祈祷管理员不要发现我们,
祈祷回去的路上一切顺利。
我们吃了那鱼。
我体内有了什么美丽的东西吧,
我真开心。

这首诗进入得相当突然(正如我们这篇文章),上来就是“好吧”,可见诗人在前面已经经历了一番挣扎,最后才痛下决心:就这么着吧。而下决心的原因,则是因为人人都会死的,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在乎的不在乎的,最后都会在无以名状的孤独和痛苦中死去。
是什么样的事,会让诗人联想到生死,陷入这么悲观的状态呢?往后看,我们发现,原来只是杀鱼而已。区区一条鱼,就能想到死之必然与生之必须;仅仅是杀鱼这个动作,都要痛下半天决心。这样的人,内心一定十分敏感吧。所谓不敢想象的孤独和未曾知道的痛苦,大概是因为孤独过,痛苦过,才不敢再深想。
接下来我们看到,杀鱼的过程写得非常详细。为什么呢?因为在乎。诗人几乎是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虔诚地观察着这一幕。他要把每一帧画面都刻在脑海里,他要为这条鱼的每一次痛苦而哭泣,而歌唱。
可是他不能歌唱,因为他杀了这条鱼——“我真希望我能歌唱,如果我能让生者生。”想让生者生,多么单纯而美好的愿望啊,可是他不敢承认,只能假托前人之口。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吧,心怀善意,反而怕被人说“傻”,说“不切实际”,说“异想天开”。坏一点,丧一点,倒像是给自己掘了一个安全的窝:反正我已经这样了,谁还说得着我?于是诗人只能假装不经意地说出这个愿望,然后用更多琐碎的细节掩盖内心的波动。
他为麝鼠祈祷,为龙虾祈祷,甚至为表弟的手腕祈祷。这碎碎念之语,多么像海子的“关心粮食和蔬菜”“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细到不能再细,因为刚才那句大而化之的话,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勇气。诗人提到表弟的时候,语气多么生疏啊。他明明可以假装听者都知道此人,唠家常一样地说出这句话。可是他不,他一定要郑重其事地加上“他是一名警察”,和读者的距离一下就拉开了。仿佛在说,“我讲的人,你自然不认识,我还是解释给你听吧”——那么陌生,那么疏离。
有人说,自1963年出版诗集《树枝不会折断》(The Branch Will Not Break)后,詹姆斯·赖特(1927—1980)的诗色彩变得明亮了。这个明亮,得看怎么理解了。就像高音也能唱出哀婉的曲调,寒冷的白雪也能让人眼前一亮,意象再温暖,底色还是悲观的。他小心翼翼地去寻找生命中的可爱之物,每找到一处就欣喜若狂。不知道是尝过多深的苦,才能对一丝丝的甜念念不忘。
赖特的另一首诗《赐福》(“A Blessing”),写的是诗人在公路旁与两匹马驹的相遇。它们是那么欢快,那么温柔,清风和畅,万籁俱静,小马驹沉静细腻的触感让他感动不已。他真想此刻就跃出身外,绽放成一朵漂亮的花。多么容易满足的可怜人啊。面对时人过度的解读,他一再强调这首诗“只是描述而已”。可他的心分明早已沉入了景中,那朵花是苦痛生活中的意外之喜,是一朵绽放在绝望中的花。这样的诗再好,我也不愿读。我宁愿幸福的人强说愁绪,也不愿欢欣下埋着痛苦的灵魂。
相比之下,伊丽莎白·毕晓普的《鱼》可以算得上是气势如虹了。她上来就说,“我抓到了一条大鱼”(I caught a tremendous fish)。然后她开始打量这条鱼——它的颜色、它的腮、它的眼睛——那是一种征服者的凝视。鱼是她的战利品,是她光明磊落、通过正当竞争抓到的。她没有什么对不起鱼的,她强于鱼的地方,就在于她那无所畏惧的生命力。她最后放走了鱼,因为她已经赢了。
可是赖特做不到。他是和同伴一起来钓鱼的,他先是拿不准要拿那条鱼怎么办,拿不准就杀了呗(也有可能不便与同伴争),杀了就吃了呗。可是他又放不下,又说服不了自己。多大点事儿呀,但他一定要赋予吃鱼这件事更多的意义,他要让自己相信,这条鱼吃得值。所以在诗的结尾,他强行让鱼成为美好的化身,强行让自己高兴起来。这哪里是人吃了鱼,简直就是鱼吞走了诗人那颗小小的、脆弱的心脏。
赖特和毕晓普的缘分还不止于此。1979年10月,毕肖普去世后一周,哈佛大学举办了悼念她的诗会,赖特也出席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读诗,他又读了《赐福》。1965年他就读过这首诗,1968年又读过一次。11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珍视那个动人的瞬间。他的声音很紧,常常颤抖,还不时清清嗓子,像是咽炎很严重的样子。然而那不是咽炎,是喉癌。几个月后,喉癌带走了他的生命。两年后,他的妻子安妮(Annie)出版了他的绝笔之作《旅程》(“This Journey”),诗中写道:“总归,美好还存在于这世间。”(Still,/ There are good things in this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