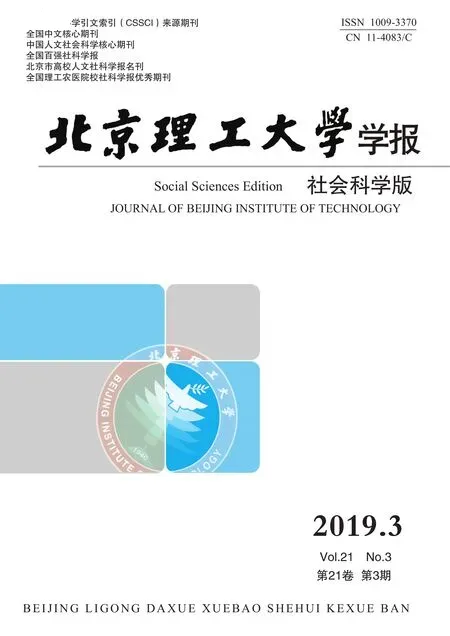《编珠》编纂与流传考
2019-12-04刘全波何强林
刘全波,何强林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南北朝时期,编纂类书成为一时之风气,上至梁武帝,下至一般士人乃至高僧高道都热衷于类书编纂,并把类书编纂当成一项重要的事业,于是相继出现了多部著名类书,《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经律异相》《无上秘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进入隋代以后,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同时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加速,国家开始致力于文化建设。《隋书》中虽说,隋文帝“素无术学”[1]54,但隋炀帝却被公认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隋炀帝有大量的作品传世,更重要的是,隋炀帝好撰集。《资治通鉴》卷182“炀帝大业十一年”条载:“春,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2]5694在隋炀帝的领导下,大隋文士共同编纂了多部资料丰富的各式典籍,以类书的编纂为例,短短几十年间,不但编纂有大型官修类书,中小型类书亦是多有出现,且质量较高。“隋代享国之年甚短,但在类书史上却占一个重要的位置。”[3]76“隋朝虽享国时短,却编了不少类书。”[4]47“隋代编撰的类书也很多,例如《长洲玉镜》四百卷、《北堂书钞》一百七十卷、《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桂苑珠丛》一百卷、《四海类聚方》二千六百卷、《四海类聚单要方》三百卷等。”[5]4-6《隋代的古籍整理》一文对隋代编纂的《玉烛宝典》《长洲玉镜》《玄门宝海》《编珠》《桂苑珠丛》《北堂书钞》6部类书做了介绍:“类书的撰集,是对古籍的一种综合性整理。隋代在书籍数量空前增多和科举取士制度产生以后,为了供帝王阅读和士人临文寻检之用,编纂类书的风气很盛,不仅种类较多,而且内容丰富,卷恢庞大,价值较高。”[6]3-15诚然,有隋一代,编纂了多部十分重要的类书,如《长洲玉镜》《北堂书钞》,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类书史的重要典籍。纵观隋炀帝时代编纂的这些类书,资料丰富毋庸置疑,但卷帙浩繁,实在是不便于翻检记忆,隋炀帝“每繁阅览”[7],而好作诗的隋炀帝迫切需要一部篇幅小而又能提供作诗素材的新型类书,《编珠》便应运而生。“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繁阅览,欲其故实简者,易为比风,爰命微臣编录,得窥书囿,故目之曰《编珠》。其朱书者故实,墨书者正义。时大业七年正月,奉敕撰进,勒成四卷。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臣杜公瞻谨序。”[7]《编珠》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隋炀帝准备诗材,由此可知,《编珠》的编纂质量肯定是可以信赖的,质量不高皇帝会不满意;再者,由于是供隋炀帝作诗使用的“随身卷子”,恐怕其他人不会很容易见到此书,这或许就是后来《编珠》流传不广的原因。
历代学者对于《编珠》的直接研究比较少,最先关注《编珠》的是胡道静。在《编珠残二卷引书考》中,胡道静对《编珠》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考证,主要内容后来收入《中国古代的类书》之中[3]78-85。孙丽婷《〈编珠〉残卷研究》从文献学角度对《编珠》作了比较全面的考证,作者以辨别《编珠》的真伪为基点,对编纂体例、所引诗赋类作品以及地记类作品进行了考证,在考证中又以其独有的文献价值来证明该书的真实性[8]。总之,以上研究加深了学界对《编珠》的认知,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对《编珠》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视之为伪书,故很多史实仍然不够明晰。
一、《编珠》的编纂
关于《编珠》的编纂者,在历代书目中均著录为杜公瞻,史书中关于杜公瞻的资料很少,杜公瞻《隋书》无传,在其叔《杜台卿传》后面有对他父子三代的简单描述。《隋书》卷42《杜台卿传》载:“有兄蕤,学业不如台卿,而干局过之。仕至开州刺史。子公赡,少好学,有家风,卒于安阳令。公赡子之松,大业中,为起居舍人。”[1]1421可见,杜公瞻曾任安阳令,而在《编珠原序》中,署衔是隋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可见杜公瞻一生做过著作佐郎、散骑侍郎、安阳令等官。《元和姓纂》卷6《杜》亦载:“魏仆射杜畿,后家中山,裔孙弼,北齐徐州刺史。生蕤,隋治中御史(岑仲勉考证隋无“治中御史”,当为“治书御史)。生公瞻,隋著作郎。”[9]934-935很显然,《元和姓纂》对于杜公瞻官职的记载与上文有异,《编珠原序》说其官职为著作佐郎,而此处却成了著作郎。《隋书》卷26《百官上》载:“秘书省置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谓之大著作,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领之。又有撰史学士,亦知史书。佐郎为起家之选。”[1]723可见,著作郎之地位明显高于著作佐郎,故杜公瞻编纂《编珠》时的官职应该是著作佐郎而不是著作郎。根据《编珠原序》可知,杜公瞻做过隋炀帝的“侍读学士”,可见隋炀帝对他的宠信,作为“侍读学士”为皇帝编纂一部作诗用的“随身卷子”,自然也是职责所在。杜公瞻在《编珠》之外,还著有《荆楚岁时记》二卷。《旧唐书》卷47《经籍志》载:“《荆楚岁时记》十卷,宗懔撰。又二卷,杜公瞻撰。”[10]2034应该是杜公瞻对宗懔原作的补撰或续作。
杜公瞻少好学,有才华,有家风,而其才华与家风必然是隋炀帝宠信他的主要原因,也是令其编纂《编珠》的原因。《太平广记》卷174《阳玠》载:“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台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谑。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11]1284-1285阳玠是著名才子,从这条笔记来看,杜公瞻与阳玠为友,学问应亦是不弱,可惜杜公瞻流传作品较少。杜公瞻今可考存诗一首,见于《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题名为《咏同心荷花》:“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引绿,双影共分红;色夺歌人脸,香乱舞衣风;名莲自可念,况复两心同。”[12]667宋本《初学记》作“松公瞻”,字之误也,应作“杜公瞻”。
关于《编珠》的编纂完成时间,根据杜公瞻《编珠原序》所载可知,当为大业七年(611)正月完成。而《编珠》的开始编纂时间史书没有记载,参考同类类书的编纂时间,《编珠》作为一部卷帙不大的小型类书,编纂时间必定不会像《华林遍略》《长洲玉镜》等类书一样,要花费上较长的时间。而“皇帝在江都日”是一个可以考察的时间段,查考《隋书》,隋炀帝“在江都日”在大业七年之前的共有大业元年八月,大业二年三月,大业六年到大业七年3次,而这其中,大业元年和大业二年可以很容易地排除,故《编珠》开始编纂时间是在大业六年(610)。根据《隋书》卷3《炀帝上》载:“六年……三月癸亥,幸江都宫。”[1]75可见,《编珠》的开始编纂时间在大业六年三月之后。
杜公瞻祖父杜弼,史书记载他“少好学”,在北齐任官时,多与邢邵、魏收等交游,曾与邢邵“共论名理”。《北齐书》卷24《杜弼传》载:“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13]348-349唐长孺:“杜弼是北朝仅见的玄学家,并非经师。”[14]235据《北齐书》记载,杜弼有四子,其中杜台卿和杜蕤皆“有学业”。杜蕤即为杜公瞻的父亲,杜蕤在仕途上很有一番作为,但是文名不显,没有著作传世。《北史》卷二十四《杜弼传》载:“蕤,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开皇中,终于开州刺史。”[13]354杜蕤在北齐时任大理少卿兼散骑常侍,曾作为使者出使南陈,而能够作为使者出使南朝陈,本身就是对杜蕤之能力与才学的肯定。
杜台卿是历仕北齐、隋的名臣,《北齐书》《隋书》《北史》有传,他的任官经历比较复杂,“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合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北齐灭亡之后,隐居不仕,“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在隋朝建立之后,应征出仕,“历中书、黄门侍郎,兼大著作、修国史”,后来因“聋疾”放归[1]1421-1422。杜台卿著有《齐纪》20卷,更为重要的是,杜台卿早年曾任职文林馆,参与过《修文殿御览》的编纂工作[15]39。后来杜台卿还编纂了一部《玉烛宝典》,其残卷流传至今,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偏爱采用谶纬之说。张重艳《从〈玉烛宝典〉看杜台卿的宗教思想》言:“卷四正说在《玉烛宝典》中比较特殊,在所有卷的正说中,篇幅最大,约3 000字。正说中引用了佛经、伪佛经、伪道经以及纬书,等等,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宗教思想。”[16]93-96杜台卿《玉烛宝典》偏爱采用谶纬书,而杜公瞻在《编珠》中也引用了很多纬书,如《河图括地象》《易纬》《易飞侯》《京房易飞侯》《春秋元命苞》《易通卦验》《孝经援神契》等,或许就是受杜台卿《玉烛宝典》之影响。
杜台卿曾经编修过《韵略》,陆法言等人在编修《切韵》时就利用了杜台卿的这一著作,杜氏家族在音韵上的造诣必然使得杜公瞻编纂《编珠》时更加考虑声律的作用,这在同时期的其他类书中是罕见的,《编珠》的编纂特点就是两两相对,彼此之间声律和谐。邓嗣禹说:“是书……凡十四门,门各有类,惟取其事之切于用,故实简而易为比风者编录之,以四字(如:天柱地轴),六字(如:树上日,井中星),或八字(如:桥势如星,沙形似月)标题;然后援引古籍以释之,皆甚简赅。”[17]2可见,《编珠》的编纂特点很鲜明,并且在隋代,此种体例虽不是首创,也是具有极大的创新性的。类语体类书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产生,如朱澹远的《语对》《语丽》等,但那时的类语体类书肯定没有达到《编珠》的高度,而杜公瞻所编纂的《编珠》对类语体体例有了大发展,此体例被后来的诸多类书与蒙书效仿,所以说《编珠》在类书发展史上,尤其是类书体例演进方面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二、《编珠》的流传
《编珠》问世以后并未大范围流传,《隋书·经籍志》中没有记载这本书,新旧唐书《经籍志》《艺文志》,也均没有记载《编珠》,这很让人怀疑《编珠》是伪书。但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并不代表《编珠》在唐代没有流传,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有:“《编珠录》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年代不可考,但可确定约在9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唐昭宗时期[18]4。《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对《编珠》的记载非常重要,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著录《编珠》的官修目录,证明尽管《隋书·经籍志》、两《唐志》没有著录《编珠》,但是《编珠》在隋唐时代,确确实实有过流传,甚至经由遣隋使遣唐使之手远渡重洋去了日本。但是《编珠》为何被著录为《编珠录》?再者卷帙为何由4卷变成了3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载《编珠录》可能是《编珠》的节抄本、缩略本。
与唐代不同,在宋代的书目中,已经有多部目录著录《编珠》。王尧臣《崇文总目》子部类书类载:“《编珠》五卷。杜公瞻撰。”[19]177郑樵《通志·艺文略》类书类载:“《编珠》五卷,隋杜公瞻撰。”[20]1733《宋史》卷207《艺文六》子部类事类载:“杜公瞻《编珠》四卷。”[21]5293很显然,《崇文总目》与《通志》所载《编珠》为五卷,与上文《编珠原序》所说不同,而《宋史》所载为四卷,与《编珠原序》所说相同,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在宋代《编珠》有四卷本和五卷本两个系统在流传。宋尤袤撰《遂初堂书目》亦载有“《編珠》。”[22]25但很可惜,《遂初堂书目》的记载很简单,没有记载《编珠》的卷帙等信息。宋代以后《编珠》在书录中逐渐不见著录,元代和明代的书目中大都没有记载,只有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编珠》,应该是焦竑采自前朝目录,或许并未见到原书。《国史经籍志》载:“《编珠》五卷。隋杜公瞻。”[23]511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言:“杜公瞻自序及目录具作四卷,《宋史·艺文志》亦作四卷,《崇文总目》及《通志·艺文略》作五卷。其篇目分为十四部,为:卷一《天地》《山川》;卷二《居处》《仪卫》《音乐》;卷三《服玩》《珍宝》《缯彩》《酒膳》;卷四《黍稷》《菜蔬》《果实》《车马》《舟楫》。 体例乃事对式。 自序云:‘其朱书者故实,墨书者正义。'故实即事对,正义即出处,与《初学记》中‘事对'部分相似。”[18]1159-1160《编珠》卷帙的不同,说明《编珠》在流传中,出现了变化,再者《编珠》一直是以抄本传世,或许是在传抄的过程中,有人对卷帙做了分合。
清康熙年间,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重新发现了《编珠》残卷,但是一直有人怀疑高士奇发现《编珠》残卷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四库全书总目》卷135《类书类一》载:“《编珠》二卷,旧本题隋杜公瞻撰。《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则国朝康熙戊寅詹事府詹事钱塘高士奇所辑也。案《编珠》,《隋志》不载,《唐志》但有杜公瞻《荆楚岁时纪》一卷,而无此书。《宋志》始著于录。然世无传本。始出于士奇家。其《序》称于内库废纸中得之,原目凡四卷,佚其半,遍觅不可得,辄因原目,补为四卷,又广其类之未具者为二卷。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称奉敕撰进,其结衔题‘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又有徐乾学序,称杜公瞻无所表著,《谈薮》载隋京兆杜公瞻尝邀杨玠过宅,酒酣嘲谑者,即此公瞻无疑。今观其书,隶事为对,略如徐坚《初学记》之体。但前无序事,后无诗文。原目分天地、山川、居处、仪卫、音乐、器玩、珍宝、缯彩、酒膳、黍稷、菜蔬、果实、车马、舟楫。所存者音乐以上五门而已……以其采撷词华,颇为鲜艳。士奇所续,亦皆取唐以前事,较他类书为近古。故疑以传疑,姑存以备参考焉。”[24]1499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作了考证:“考《内阁大库书档旧目》(此目凡二十种,皆清代内阁典籍厅收掌之档案,近始自内阁大库检得之,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次印行。)第七种,内有《编珠》一本,不全。此目虽不著时代,以其所收书考之,当编于康熙二十年以前,(详见原目卷首方苏所撰叙录)而徐乾学之序末题康熙三十二年。高士奇之序《编珠》纪年为戊寅,乃康熙之三十七年也。然则士奇所言之内库,即指内阁大库,而其所见之《编珠》佚去二卷者,即此目中不全之本,盖可知也。以此相证,知士奇之本,确得之内库矣,非士奇及朱彝尊之所依讬也。”[25]953余嘉锡从《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考证,得出其确实曾经有《编珠》一书,则高士奇从其中得到《编珠》残缺二卷,便不是空穴来风,而且内库中残缺二卷的《编珠》不仅高士奇见过,朱彝尊、徐乾学、王士禛3人也都见过。再者,修《四库全书》的清儒,虽然对《编珠》的重现表示了客观的质疑,但是很显然,四库馆臣对《编珠》也是很厚爱的,不然为何将之置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之首,《艺文类聚》之前,这个行为毫无置疑的展现了清儒对《编珠》的认可与肯定,而能够被收入《四库全书》的《编珠》之身份地位亦是毫无置疑地得到官方的确认与保护,遂能再次公开流传于世。
三、《编珠》的刻印与版本
高士奇发现残本《编珠》二卷以后,依据残存的《编珠》类目,仿照原书体例,从传世的六朝隋唐典籍中抄撮材料,进行补遗工作,补了两卷,凑足了原来四卷之数,再后来高士奇对《编珠》作续修,又编成《续编珠》二卷。所以目前所见的《编珠》共有六卷,前两卷主要是杜公瞻原本,再两卷是高士奇依据原目所作之补遗本,再两卷则是高士奇续修本。《编珠》补遗工作完成之后,高士奇请自己的姻亲徐乾学、好友朱彝尊作序,然后在康熙三十七年刻印行世。根据高士奇《编珠序》载:“曩直大内南书房奉命检阅内库书籍于废纸堆中,得隋著作佐郎杜公瞻《编珠》一册。原目凡四卷,遗其半,遍觅不可得,因手钞之,藏笥箧间。己巳归寓平湖,端居多暇,出而校雠,爱其精粹,辄因原目补为四卷,又广其类之未具者为二卷。其于著作撰述,本旨未知何如,乃其书则不致以残缺为人所弃矣。”[7]
高士奇校雠残缺的原本《编珠》以及为其续补工作开始于“归寓平湖,端居多暇”时,根据《清史稿》,康熙二十八年(1689),高士奇、王鸿绪等因为结党营私遭到弹劾,高士奇被迫回到浙江平湖家中,一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才重新被启用,则高士奇完成校书、续书,应当指的就是这一时期。则高士奇校雠以及续书时间应在康熙二十八年到康熙三十二年之间,高士奇得到《编珠》本子,则应该在康熙二十八年之前。从文政十二年刊本每卷末尾“男高舆、轩仝校字”或者“男高舆、轩仝校”可知,高士奇的两个儿子高舆和高轩也参加了《编珠》的校雠工作,为《编珠》的刻印作出了贡献。
关于《编珠》的序,有高士奇序、徐乾学序与朱彝尊序。高士奇在自序中说最为欣赏《编珠》的原因是“爱其精粹”[7],可见《编珠》作为一部提供作诗素材的小类书,在千年之后,还是很受文人青睐。但是高士奇对于杜公瞻最初编纂《编珠》的宗旨,并未作深入探讨,“未知何如”,只是抱着“其书则不致以残缺为人所弃矣”的宗旨才将其补续刻印。在高士奇心中,最初只是想把《编珠》作为秘不示人的秘籍来赏玩,之所以刊行,是因为一位友人的建议,“友人谓是编宜公同好”,这位友人是谁?极有可能是徐乾学。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南北党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一起遭到弹劾,高士奇被迫辞官返乡,徐乾学也于康熙二十九年辞官回乡,则这个“友人”应该就是徐乾学。徐乾学是康熙朝名儒,也是官书编辑大家,他与高士奇还是姻亲,高士奇续修《编珠》后,曾专门找徐乾学作序,故高士奇极有可能是在徐乾学的建议之下将《编珠》刊行的。
徐乾学虽然也承认《编珠》“考隋经籍唐艺文二志并无此书,他书录亦皆不著”,但是他的结论是此书不伪,只是失传久矣,“盖凋零磨灭久矣”[7]。为什么徐乾学会认为《编珠》不是一部伪书呢?《清文献通考》载:“士奇偕乾学奉命校勘阁中书,得之。已逸其后二卷,士奇博采故实,以补其阙,又广其门类之未备者。”[26]367可知当时徐乾学与高士奇是同奉康熙皇帝的命令去整理内阁书籍的,正是高士奇发现《编珠》二卷残本的见证人。对于《编珠》的评价,徐乾学认为《编珠》是沧海遗珠,因为大量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类书失传了,而此《编珠》却能独存,绝对一大幸事。徐乾学说:“自魏晋以逮,南北朝君臣宴集,每喜征事以觇学问,类书于是渐多。然今世传欧阳询、虞世南、徐坚所排纂,皆唐初时人,而志所载隋以前书,如《皇览》《类苑》《寿光书苑》《华林遍略》等书,当时极贵重,其卷帙颇繁,今皆无一简存者。即如戴安道、颜延之之《纂要》,沈约之《袖中记》《珠从》,其书不过一二卷,亦尽已散逸,独《编珠》犹得其半。”[7]
除了高士奇和徐乾学,朱彝尊也曾经为《编珠》作了一篇序,朱彝尊是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朱彝尊与高士奇曾同在南书房共事,相互之间比较熟悉,高士奇曾经因为嫉妒有过打击朱彝尊的举动。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载:“泽州语予曰:‘当日潘次耕、朱锡鬯在南书房,与高澹人不过诗文论略不相下,澹人便深衔之,一日语予曰:‘如此等辈,岂独不可近君,连翰林如何做得?'予曰:‘如此等人,做不得翰林,还有何人可做?次耕略轻浮些,至朱锡鬯还是老成人。'高往年还在监中考,为吾所取,称老师。是日,便无复师生礼,忿然作色曰:‘甚么老成人!'将手炉竟掷地,大声曰:‘似此等人,还说他是老成人,我断不饶他。'”[27]758可见,高士奇与朱彝尊之间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冲突,所以在高士奇康熙年间刻《编珠》时,没有收入朱彝尊为《编珠》所作的序,而在日本文政十二年刻本中,日本学者则从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中找出该序,并将之放在卷首。
朱彝尊为《编珠》作序是应高士奇之请求而作的,并且朱彝尊作序在徐乾学作序之后,由于朱彝尊名气较大,所以高士奇很重视朱彝尊,在徐乾学作序后,高士奇又嘱咐朱彝尊为《编珠》作序。朱彝尊在其序中敏锐的注意到了《编珠》在类书史上的意义:“予惟类书始南北朝,当时文尚骈俪,学者争以洽闻周见相高。如朱澹远有《语丽》,又有《语对》,徐僧权有《遍略》,顾其书皆不传,论者遂以《修文殿御览》为古今类书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台卿所撰《玉烛宝典》十二卷,见于连江陈氏《世善堂书目》,予尝入闽访陈后人,已不复可得,则类书当首公瞻。”[28]朱彝尊在当时明确指出杜公瞻《编珠》是当时可见最早的传世类书,并且朱彝尊以其经学家的敏锐发现了《编珠》所保存的大量谶纬书的价值。他指出虽然史书中说隋代严禁谶纬之书,“隋禁七纬,发使四出,凡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但是观察《编珠》,却“仍取《括地象》《通卦验》《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并且查考《北堂书钞》,“永兴虞氏《书抄》成于隋秘书省之北堂,亦采及诸纬”,由此朱彝尊得出结论:“然则史固有不足尽信者与,或当日所焚,不过《王明镜》《闲房》《金雄》等记,而非概畀之炎火,斯乃《乾凿度》《礼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28]。可以说,朱彝尊所作《编珠序》是最有学术价值的一篇序,由于后来高士奇与朱彝尊交恶,康熙三十七年(1698)高士奇刻印《编珠》时,便没有采用朱彝尊这篇序,只采用了徐乾学和他自己的序。后来的文政十二年刻本补用了朱彝尊序,文政十二年本后来在日本流传非常广,可以说,是得益于朱彝尊的这篇序。
现今留存的《编珠》主要有3个版本系统,第1个是康熙三十七年清吟堂本。清吟堂是高士奇的书斋,又称朗润堂,清吟堂本《编珠》9行16字,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内封题“吟堂秘本”,每卷末刻“男高舆、轩仝校字”,“弘”“丘”皆不避讳,当是高士奇在补完《编珠》之后的初代刻本。于今可见的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亦有藏本。高士奇的儿子高舆是当时的刻书名家,康熙朝编纂的大部头类书《渊鉴类函》高舆也曾刻过清吟堂本,高舆精于刻书,所刻印书籍,质量都比较高。《编珠》在光绪年间由甘泉宣哲用铅字又排印了一次,称光绪甘泉宣哲铅字排印本,这次排印本主要是根据康熙三十七年高士奇的本子刻印的,内容没有变化。
《编珠》的第2个版本系统是翰林院本。翰林院本即是《四库全书》本的来源,两者大体上是一致的,是一个系统的本子,翰林院本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上有扫描版,善本书号13728,封面有“隋杜公瞻编珠四卷有翰林院典籍厅官印”的题名,抄本,10行21字,无格,内题“钦定四库全书”,共4卷。翰林院本中“弘”字避讳,应为乾隆时期的抄本,但是这个本子有些混乱,比如“天地部”之后清吟堂本有“增补十四条”的小字标注,在翰林院本中却漏掉了,但是有些部类的后面,依然有着与康熙年三十七年本相同的小字标注,写明了高士奇增补多少条,而且翰林院抄本没有徐乾学序,也没有朱彝尊序,有“钦定四库全书”的题字于卷首,可能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一个抄本,这个本子的底本应该就是康熙年三十七年清吟堂本。《四库全书》本有四库馆臣序,徐乾学序,以及高士奇清吟堂序,《四库全书》本还有一个缺点是其与清吟堂本与文政十二年本相比,在每个部类下面注明的高士奇增补情况比较混乱,所以其校勘价值要远远小于其他两个本子。
《编珠》的第3个版本系统是文政十二年和刻本。文政十二年即道光九年(1829),这个本子共6卷,是较晚出的刻本,书内“弘”“丘”皆缺笔,可见的本子很多,主要有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与静嘉堂藏本。文政十二年本的创新之举是补入了朱彝尊序,故文政十二年本与清吟堂本与翰林院本相比较,价值小于清吟堂本而优于翰林院本。
除了上述几个版本系统,《编珠》还有抄本流传,如清嘉庆杨超仁抄本等,但是这些抄本流传较少,不如刻本的流传广泛。其实,在高士奇刻印之前,《编珠》便有抄本流传,根据王士禛所见池北书库本《编珠》可知,之前抄本多谬误,以至于王士禛根据抄本中“隋皇”断定高士奇所得残卷为伪。后来的抄本,很多是根据高士奇刻本所作的抄本,抄本总体上价值不如刻本大。
四、结语
《编珠》本是给隋炀帝作诗用的“随身卷子”,质量是不容怀疑的,并且杜公瞻家族有着良好的家学传承,这也保证了《编珠》的编纂质量,杜台卿等人对音律的熟稔,必然使《编珠》在音律等方面有突出表现,这样才更加有利于隋炀帝的作诗之用。作为隋炀帝“随身卷子”的《编珠》在后世流传不广,但是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代表的图书目录的著录,证明了其流传情况,虽不广,但余脉未断。高士奇在康熙年间重新发现了《编珠》残卷,并为之补遗续撰,六卷本《编珠》遂再次流传开来,甚至于日本亦有和刻本出现,不可不谓之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美事。清代部分学者或言《编珠》为伪书,但《四库全书》将之收入子部类书类,并且排于诸类书之首,又可见清儒对《编珠》的认可与厚爱,后来学者更从多个侧面为《编珠》证明清白。《编珠》的体例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之所以被人重视,主要是因为体例,此种体例极便于作诗作文之用,这也是千年之后高士奇爱其精粹的原因,敦煌文献中的《语对》《籯金》也是这种体例,但《语对》《籯金》肯定是《编珠》的“子孙”,肯定是《编珠》影响之下的新作,所以《编珠》对中国类书发展史是有贡献的。后世学者以“编珠”为名的著作有《仙苑编珠》,这是道士王松年编成的一部记载神仙事迹的类书,编排形式一仍《编珠》,四字为对,其取“编珠”为名,亦可说明《编珠》在唐宋时代知识人中间所具有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