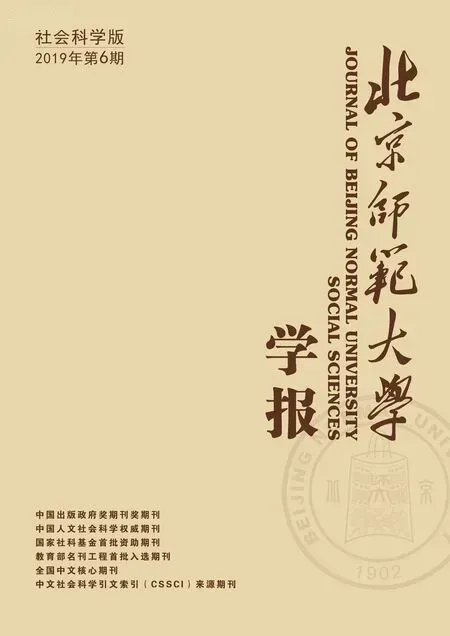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相关概念及发展阶段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2019-12-04田建民
田建民
(河北大学 文学院,保定 071002)
我们平时在阅读或写作中经常遇到或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五四高潮期”、“五四落潮期”、“五四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等概念,如谈到鲁迅的《呐喊》,我们会说那是五四高潮期为文学革命先驱者“呐喊”助阵的,谈到《彷徨》与《野草》,就说其表现了五四落潮期鲁迅的寂寞与彷徨。可是,到底“五四时期”、“五四高潮期”、“五四落潮期”都是具体指哪个时间段,各时期区分的标志是什么?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哪里?专业的学者似乎认为这些概念都是约定俗成、不言自明的。偶尔有研究者对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及起止时间进行界定,或是过于笼统而缺乏学理的研究与论证,或是武断地加以界定而存在诸多常识性的错误,或是以政治的视角与标准来评判文化的运动,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实际的历史情况不相符合,致使一些人对这些概念经常是“模糊”使用,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本文旨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相关概念进行学理性的厘定,并从文化的视角具体分析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各阶段的不同特点。
一、相关概念的厘定
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什么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定义。至少它们的异同,各自的起止时间,就没有准确的界定。还有的,一说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1)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全新修订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确实,目前学界对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相关概念及运动的起止时间节点等还缺乏权威的、学理性的界定和说明。一些研究者尽管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说明或界定,但或是过于笼统武断,而缺乏学理的深入研究与论证,或是因为用政治的视角与标准来评判文化的运动从而得出与实际的历史情况不相符合的结论。比如,有研究者依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周策纵教授在其1960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止时间的划分,断定周策纵在本书中认为“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他把五四运动的终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
新文化运动终止的时间,应当比这要晚些。”(2)④ 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全新修订版),第17页。这里首先出现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是在1915年9月,就是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也是在1916年9月,将其说成是1917年,这显然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两个概念混淆了。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研究的重点是1919年爆发的这一特定政治意义上的五四运动,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第二章的标题是“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1915—1918)”,第三章的标题是:“运动的开始阶段:初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3)〔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可以看出,周策纵是把1915—1918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视为促成五四运动的原因,把1917—1919年的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视为五四运动的开始阶段。这里周策纵所说的起止时间应该是特指的政治上的五四运动,而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外,美国学者格里德尔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提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12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1915年到1927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在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的旗帜之下。”(4)〔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可以看出,周策纵研究的着眼点是政治上的五四运动,所以他所给出的起止点根本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止点。而格里德尔明确划定的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止点,虽在时间段的划分上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大致吻合,但他把1915年袁世凯称帝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而不是把《青年杂志》的创刊作为标志;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作为新文化运动终结的标志,而不考虑新文化阵营的解体。所以他划分的着眼点同样是政治的变革而不是文化的运动。受周策纵与格里德尔的影响,有研究者提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我以为,还是将一九一七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较为恰当。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杂志总部迁到北京,到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十年的时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④我们说,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首先,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1915年的什么“节点”,即以什么为标志,没有说明。其次,说1917年“《新青年》杂志总部迁到北京”这种表述是不恰当的,因为当时的《新青年》没有“分部”,所以也谈不上“总部”,因为在1918年前《新青年》的前3卷18期是由陈独秀自己办,很难说有所谓“编辑部”,更何谈什么“分部”和“总部”。而且《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怎么就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呢?难道《新青年》批判旧文化,宣传新文化是到北京才开始的吗?再次,界定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1915年还是1917年,其评判的价值标准是不一样的。
以上所举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与起止的界定上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代表了学界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倾向。即笼统地以政治的视角判定文化的运动。如有研究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看法。狭义的时间节点是从1917年到1921年。广义的时间节点是从1915年到1923年。”(5)陈少雷:《古今中西论争: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文化思潮及其启示》,《探求》,2015年第2期。这种界定就显得简单笼统而缺乏论证。只给出了新文化运动广义与狭义的两个起止的时间节点,却没有加以论证和说明。而且一般讲,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为什么说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其依据是什么?这些都是应该论证和说明的,否则会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两个概念的混乱。再如李蓉女士例举的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从1915年至1922年中共‘二大’成立。以《青年杂志》创刊为兴起标志,以中共‘二大’成立为新文化运动结束。……有学者认为,1917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才应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因为陈独秀此前曾声明不参与政治,这时才明确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一种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大体上说,到了1924年,就进入它的后期了。”(6)李蓉:《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0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这三种观点更是典型的着眼于政治而不顾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发展变化的划分。第一种观点以中共“二大”成立为新文化运动结束的标志。(此话有语病,应该是中共“二大”召开,不能说会议“成立”)好像一个刚刚成立的政党的12个代表开一个会,新文化阵营就解散了,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就完成了。作者可能认为中共“二大”确立的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和建立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已经超越并可以取代五四的思想启蒙了,所以新文化运动就结束了。这完全是把政治逻辑强加到思想文化运动上来的不符实际的想象。第二种观点以1917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欲革新政治不得不革新文学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这种观点也是以政治为衡量文化运动的标尺。其误点有三:一是把文学等同于文化;二是认为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前没有进行思想文化启蒙;三是认为陈独秀此前不参与政治。其实,文学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陈独秀是参与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这些实际政治的,他是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了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所以才创办《新青年》掀起旨在思想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其在《文学革命论》中只不过强调了革新文学对于思想启蒙的重要性而已。第三种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这更是为强调政治而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因果关系及前后次序给颠倒了。
笔者认为,既然我们谈的是新文化运动,所以要把着眼点放到文化上,把文学与政治上的变革视为思想文化革新在文学与政治上呈现出的成果。即先有思想文化的启蒙,后有文学与政治的革命与运动。也就是说,是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并进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革新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相反。下面我们就以这样的原则来对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概念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的界定。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指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猛烈抨击旧文化,大力提倡新文化所形成的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文化启蒙在文学领域和政治领域取得的成果。“五四文学革命”特指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胡适和陈独秀分别于1917年1月和2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由此掀起的一场批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批判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的文学革新运动。“五四运动”则特指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政治上觉醒了的青年学生,于1919年5月4日带头发起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爱国政治运动。由于这是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一场运动,是思想启蒙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所以“五四”成为具有标识意义的一个概念。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冠以“五四”两个字,是指整个新文化运动并强调其思想启蒙的意义与作用。而“五四时期”,广义上是指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狭义上则指政治上的五四运动时期。同样,“五四高潮期”、“五四落潮期”也均可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但一般人们谈到的五四高潮期与落潮期是指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在文学研究界更是这样。
以上,我们从文化视角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的概念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界定。下面我们将重点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发展与落幕几个阶段的节点及各阶段的特点。
二、发起期的时间节点与特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期或说早期的时间节点是从1915年9月至1916年12月,即从《青年杂志》创刊到第2卷4期。这是《新青年》的上海时期。此时期的特点是专注于批判封建专制文化和迷信思想,宣传民主精神与科学理性。“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参与革命的一批革命党人流亡日本,其中就有陈独秀和被视为“民初头号政论家”的章士钊。章士钊于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邀请陈独秀协助编辑。虽然章、陈两人早在1903年合作办《国民日日报》时就建立了友谊,又都是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同道,但二人此时在政治理念上却出现了分歧。章士钊大力宣传“调和立国论”的改良主义的政体变革,而陈独秀则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政治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救国不能只凭一腔爱国热情,也不能只靠政治上的政体变革,而根本的在于提高国民的“自觉心”。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感情与智慧。而“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7)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东京)》,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正是以启发和培养国人的“自觉心”为鹄的,陈独秀于1915年6月回国,9月即在上海创办了旨在对国民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新青年》)。在作为本刊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即站在民主自由与平等人权的立场上,号召青年脱离奴隶道德而树立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他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他把传统所尊奉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斥之为奴隶之道德。认为“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他批判封建迷信思想说:“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与《敬告青年》同期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中,陈独秀提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8)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他以西方民族文化为参照,批评东方民族文化以安息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指出“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9)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在这些文章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其“科学与人权并重”的科学理念与民主精神的指向却是非常明确的。这是近代以来批判封建奴隶道德、提倡民主人权的最强音,为批判封建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调。
在批判封建旧文化时,陈独秀认识到儒家学说是宗法制度与奴隶道德的文化根源,其批判的锋芒开始集中对准以“三纲”为核心的礼教道德观。他首先站在立宪政治的立场,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角度,对儒家的所谓“三纲”批判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0)陈独秀:《一九一六》,《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认为,所谓共和立宪,只有少数政党主张是不行的,必有待多数国民的觉悟才能够成功。多数人的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代庖。认为实现立宪政体的惟一根本条件就是多数国民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这样所建立的政府,才能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宪政。如果立宪政治不是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国民“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袁世凯称帝前即大搞尊孔祭天,发表“尊孔令”,甚至强行在“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康有为也授意学生陈焕章等组织孔教会。在袁世凯死后,康有为致书继任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对此,陈独秀连续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等直接批判孔教的文章。提出儒家之礼教是我国伦理政治之根本。所以必须废除。批判康有为等人的尊孔言行是湮塞人智,其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认为“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2)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康有为等认为由于孔教废弛导致世道人心坏到不忠不孝,男不尊经,女不守节。陈独秀评判说:“然是等谓之不尊孔则可,谓之为风俗人心之大坏,盖未知道德之为物,与真理殊,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尔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勿依违,勿调和,依违调和为真理发见之最大障碍!”(13)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把思想文化的启蒙看作政治改革的根本。他说:“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14)陈独秀:《袁世凯复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这些批判传统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宣传独立人权、民主精神与科学理性,旨在启发国人的“自觉心”的文章,是近代以来批判封建奴隶道德提倡民主人权的最强音,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为批判封建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调。
当时和陈独秀并肩作战的是高一涵。在谈到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之外,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吴虞、鲁迅等活跃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的人物,而忽略了在新文化运动发生期就非常活跃的高一涵。其实,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吴虞等都是直到《新青年》第2卷才开始在《新青年》正式露面。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则更是到第4卷时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而高一涵在《青年杂志》时期是仅次于主编陈独秀的重要撰稿人。他连续在该刊发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1卷1号、2号、3号连载)、《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1卷2号)、《民约与邦本》(1卷3号)、《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1卷4号)、《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1卷4号)、《自治与自由》(1卷5号)、《戴雪英国言论自由之权利论》(1卷6号)等重头文章。在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对新文化的倡导上,如果说陈独秀偏重于伦理道德方面,那么高一涵则重在体制与制度方面。其《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即在启发青年对于国家之自觉。文章在比较专制体制与共和体制的种种区别的基础上,强调共和国家的兴衰隆替系于国民之全体。因为共和国本是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共和体制下国民的第一天职,是在本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 will),以决定国家的政治。共和体制的实质是“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而发表国家意思,则为人民之任。”(15)②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而要真正能够造成负起国家责任的国民,则需要青年摒弃旧的道德而养成新道德。而所谓新道德,一是摒弃传统的不问其理之是否合于现世,但问其例之有无的惟先王之道是从的道德观,而树立遵天性、贵进取、启发真理,楷模将来的道德观。因为道德之根据在天性,天性之发展恃自由,自由之表见为舆论。“共和国家之本质,既基于小己之言论自由。……专制国家之舆论,在附和当朝;共和国家之舆论,在唤醒当道。专制时代之舆论,在服从习惯;共和时代之舆论,在本诸良心以造成风气。”②其二,要取自利利他主义。即“应以谋社会之公益者,谋一己之私益;亦即以谋一己之私益者,谋社会之公益。二者循环,莫之或脱。损社会以利一己者固非,损一己以利社会者亦谬。……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16)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高一涵比较西方国家从专制到宪政发展的历史,批判封建守旧思想时说:“回顾吾邦,事事反古,出死力以排除近世国家原理,似惟民主义能行万方者,独不能行于吾国。非持数千年前陈言古义,逆系人心,则其群必将立涣。凡其制为吾史乘中所未经见,即当视作异端左道,百计驱除。一若国国皆循进化大势以前趋,独吾一国必遥立于天演公例而外,逆进化之大势而退转?自由平权、人格权利,在他国视为天经地义,倾国家全力以保护之者,在吾国必视为离经叛道,倾国家全力以铲除之。他国已入于一治不乱之时者,吾国必永罹一治一乱之劫。犹曰此吾国历史之特征也,此先王之微言大义,深入人心也,此亚洲民俗不能强合欧美也。囚心于虞夏商周,定睛在三皇五帝,迷身于一朝一代历史现象之中,举其比例参堪观察会通之官能,屏而不用,则迷于一国史迹,更何待言?”(17)高一涵:《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他以卢梭的民约论思想,阐释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即政府为受人民委托执行人民意志的机关,人民的意志或主权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由此,“人民对于国家,可牺牲其生命,捐弃其财产,而不得自毁其自由,断丧其权利。国家对于人民,得要求其身体,不得要求其意志,得要求其人生,不得要求其人格。……盖意志乃自主权之动因,所以别于奴隶牛马者,即在发表此意志得以称心耳。一为政府所夺,他事不可知,先令失其自主权矣。自主权失,尚何人格之足言,人格丧失,宁非耻辱之尤者乎?愚民之政,固令人痛恶不堪,辱民之策,尤令人愤恨莫忍。天下难忘之事,孰有过于耻辱?”(18)高一涵:《民约与邦本》,《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认为“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国家得要求于人民者,可牺牲人民之生命,不可牺牲人民之人格。人民之尽忠于国家者,得牺牲其一身之生命,亦不得牺牲一身之人格。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无权利则为禽兽为皂隶,而不得为公民。”(19)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高一涵这些运用政治学原理,在对国家体制、国家与个体关系剖析的理性层面批判封建专制、倡导人权、人格的文章,与陈独秀从伦理层面批判旧道德倡导新道德的文章,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想启蒙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在读了《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等文章后,知高一涵在东京,“访问半年余”,始与高一涵在东京所租居的房屋见面。随即两人“‘纵谈国事,所见无不合,遂相交’,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20)高大同:《高一涵先生年谱》,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陈独秀与高一涵之外,当时参与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还有汪叔潜、李亦民、高语罕、易白沙、刘叔雅、吴稚晖等。由此可知,《青年杂志》在创刊之初就激烈地抨击旧文化、倡导新文化,并很快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旨在启蒙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所以,把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合于历史实际的,而一些学者把这个开端推迟到1917年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三、高潮期的时间节点与标志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的时间节点是1917年1月至1920年9月。此间《新青年》自2卷5期出版至7卷6期,即《新青年》的北京时期。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期的标志有三:一是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二是掀起了文学上的革命运动;三是掀起了政治上的五四运动。新文化阵营的形成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进入高潮期。而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是思想启蒙在文学与政治领域取得的成果,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峰。
先看新文化阵营的形成。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重新召集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中华民国表面上又回到了民主政治的轨道。由此,因反对袁世凯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当年7月,范源廉出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范源廉曾与蔡元培一起共事。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范源廉即出任教育次长。范源廉出任教育总长后,随即举荐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于是,教育部发电给时在法国的蔡元培,促他回国赴任。由此蔡元培于11月由法国回到上海。随后即赴北京了解北大的状况。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向他推荐陈独秀做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与陈独秀曾一起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对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及做事的毅力与责任心早已了解。而此时陈独秀正办《新青年》,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尤其是其在《青年杂志》第2号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革新教育须从教育对象、教育方针、教育方法三方面下手。认为教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了解人生之真相、了解国家之意义、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与之相应,其教育方针应该是:1.现实主义;2.唯民主义;3.职业主义;4.兽性主义。陈独秀对兽性主义解释为:“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21)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这些思想与蔡元培由教育入手革新思想文化,整肃有着严重官场和科举习气的旧北大,开创新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思想可谓不谋而合。因为在蔡元培看来,“理想的教育应当是一种人格教育,一种健全、优美精神的培植。所以,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从文科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而且还必须具有明确的新教育主张。”(22)庄森:《一份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1期。所以陈独秀是符合蔡元培认定的文科学长标准的不二人选。由此,自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发布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令起,蔡元培即天天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在征得陈独秀同意后,蔡元培于1917年1月11日正式致函教育部呈请派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13日教育总长范源廉正式签发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布告》正式宣布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对此蔡元培回忆说:“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23)③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新青年》自2卷5号由上海迁至北京。至此,蔡元培与陈独秀联手,“一校一刊”珠联璧合的局面正式形成。《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的联姻不但使其获得了雄厚的人力与思想文化资源,而且也使其站到了引领全国思想与文化的制高点上,具有了合法性的权威话语权。而蔡元培则借助《新青年》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人脉关系和舆论效应,大刀阔斧地对北大进行改革。包括整肃旧北大的官场和科举遗习,裁汰旧的官场式、不学无术的教员,延揽认同或支持“新文化”的专业技术人才,建立“教授评议会”的教授治校制度等。所以,“一校一刊”的正式联姻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开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随即把在《新青年》上积极参与倡导新文化的胡适和刘半农引荐到北大任教。他在1917年1月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此处“北京总长”是“北大校长”之误),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可以此数。”(24)陈独秀:《致胡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1页。可见陈独秀对胡适的器重与期待之情。而胡适也确实没有辜负陈独秀对他的期待。胡适来北大后,不但以其贯通中西的学识和锐意改革的精神成为引领《新青年》和新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而且为北大引荐了一批与其同时期留学海外的青年才俊。如蔡元培所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③可见,“一校一刊”的结合,很快促成了一个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支持和认同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群体。除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之外,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的语言学家钱玄同,也开始公开高调支持新文化运动。由此《新青年》最著名的四大记者聚首北大。再加上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等,新文化阵营已经初步形成。到1918年1月,《新青年》的4卷1号,不再由陈独秀自己编办,改为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陶孟和、李大钊八个主要编委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标志着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正式形成,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正式进入高潮期。
再看文学革命运动。到此时期,启蒙思想先驱播撒的新文化的种子首先在文学领域开花结果了。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意识的重要载体。在思想文化启蒙的深入开展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旧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表现的多为纲常礼教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所以必须“革”旧文学的“命”。由此,1917年1、2月间,《新青年》的2卷第5、6号分别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前者从语言形式上集中批判文言文的僵化的形式主义弊病,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后者则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对封建旧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并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设想与目标。这些革新文学的主张随即得到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陈望道等人的积极响应。很快形成了一场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随后,钱玄同在《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发表的致陈独秀公开信中,提出了汉字“竖改横”的见解。之后,钱玄同又陆续提出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等文字改革的主张。1919年11月,胡适、钱玄同和周作人等联名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1920年1月,教育部颁令“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25)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同年4月,教育部再次通告,要求到1922年,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各级学校均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在文学创作方面,胡适率先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2卷6号发表了他的白话诗八首。此后,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新诗,而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展示了新文学的实绩,标志着白话文地位的确立,新文学取代了旧文学。从此中国文学开始以全新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样式融入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中。
最后看政治领域爆发的五四运动。经过几年的思想文化的启蒙,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从数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被唤醒的个体独立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使他们不再甘于做奴仆和顺民,而是要以主人翁的精神与姿态担当起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使命。由此,当北京青年学生得知,“巴黎和会”上各协约国不但拒绝了同样是战胜国的中国所提出的正义要求,竟然还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居然准备签字的消息后,群情激愤,随后于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群众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显示了思想文化启蒙的成果,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峰。
四、落潮期的时间节点与标志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期的时间节点大致在1920年9月至1926年底或1927年初。此间《新青年》自8卷1期迁回上海,自1922年7月9卷6期后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其办刊宗旨由“人”的启蒙转为了阶级的革命。此后除陈独秀外,原《新青年》同人不再在该刊发表文章。此时期的特点是新文化阵营逐渐分化并最终解体,以有着不同政治诉求的党派纷争取代了之前的文化思想的启蒙。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与高一涵在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民众要求,则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由此被军警逮捕。在多方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陈独秀获释,但需定期向警厅汇报行踪且不准出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协助下,陈独秀离京赴沪,在上海设立了新的《新青年》编辑部。此后,原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逐渐分化为“法日派”和“英美派”。“法日派”知识分子或自身就参加了国民党,或曾与同盟会成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与交集,所以在政治上倾向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该派的核心人物是国民党人李石曾和顾孟余,骨干人物有被称为“三沈二马”的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马裕藻和马叙伦等。而“英美派”知识分子群体,则是以胡适为核心的一批信奉欧美民主价值观的学者或技术性官员,主要成员有陶孟和、王世杰、蒋梦麟、陈源、朱经农、任鸿隽、陈衡哲、王星拱、皮宗石等。他们以《努力周报》和《现代评论》为阵地,以自由独立相标榜,提倡西方的价值理念并积极推动建立所谓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好人政府”。在蔡元培离开北大之前,两派的矛盾还未公开化,双方在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与对抗北洋军阀政府方面还是采取一致步调的。1923年初,蔡元培为抗议“罗文干案”而愤然辞职离京后,两派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到1925年,围绕“女师大风潮”,双方的矛盾大爆发。“法日派”出于配合国共领导的国民革命、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的目的,发动师生抵制北洋政府派到女师大接替因“驱彭挽蔡”而辞职的许寿裳来做校长的杨荫榆。而“英美派”则认为要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不能为了党派的利益而以学校和学生做筹码。指责“法日派”发动的斗争是“暗中鼓动”风潮。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而另办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的关键时刻,“法日派”为声援女师大学生,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召开北京大学教授评议会,提议北京大学脱离教育部而独立。这个议案遭到“英美派”的王世杰、王星拱等人激烈反对。最后以七票赞成、六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议案。于是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而胡适则联合陶孟和、陈西滢、颜任光、王世杰等20名“英美派”教授抗议评议会所做出的议案。并公开发表《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明确反对北大介入政潮与学潮。可见在五四落潮期,五四新文化阵营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热衷于政治而疏离了思想文化的启蒙。就像鲁迅所描述的“后来《新青年》的团体解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26)②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的境况。尽管少数人如鲁迅还在以创作和翻译坚守启蒙的新文化阵地,积极支持创办《语丝》周刊并成为主要撰稿人,热情扶持和帮助青年人组织的浅草社和沉钟社,与高长虹、黄鹏基、韦素园、韦丛芜等狂飙社和未名社成员组织莽原社并亲自主编《莽原》,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试图组成一个新的阵线,坚持继续五四启蒙的未竟之业,但终归也只感到“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②。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控制了北京政权,对倾向革命与民主的文化和教育界的人士采取高压政策。1926年3月18日,执政府卫队开枪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和市民,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随即,执政府又以“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对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教育界名流发出通缉令。此后,《京报》于3月26日和4月9日,载出了执政府通缉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名单。4月16日,《京报》被查封,总编邵飘萍被逮捕并于当月26日以赤化罪名被枪决。8月5日《社会日报》经理林白水被捕并于次日被处决。北京各高校都成了搜查“赤化”者的重灾区。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北京文化界人士纷纷离京南下。仅北京大学离京南下者就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法日派”与“英美派”的核心人物如李石曾、顾孟余、胡适、王世杰、陶孟和、蒋梦麟、高一涵等均相继离开,而包括鲁迅在内的国学系教师沈兼士、顾颉刚、魏建功、潘家洵、黄坚等几乎是集体到了厦门大学。至此,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阵营彻底解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五、小结
在上文中,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的概念及运动的发展阶段、起止时间、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与界定。认为“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文化启蒙在文学领域和政治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新文化运动发起阶段的标志是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其特点是专注于批判封建专制文化和迷信思想,宣传民主精神与科学理性;1917年1月,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一校一刊”正式联姻,这是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开端。此后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正式形成。此间发生的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峰;1920年9月,陈独秀离京赴沪并把《新青年》迁回上海。此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以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的党派纷争取代了之前的文化思想的启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落潮。而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后实施的文化上的高压恐怖政策,造成北京文化界人士纷纷离京南下。大致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随着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阵营在文人南下潮中的解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基本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