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浪中的幽灵
2019-12-02傅适野
傅适野

2012年3月11日,一个11岁的女孩回到大川小学拜祭遇难的同学和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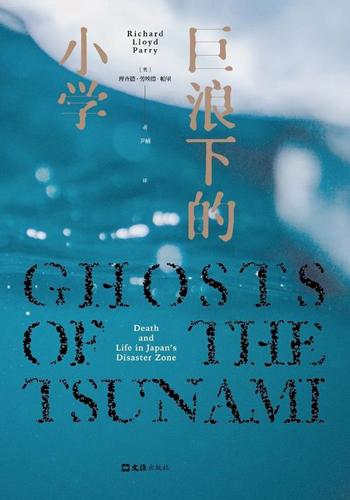
《巨浪下的小学》
作者: [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译者: 尹楠
出版时间:2019-10
从东京出发,搭乘新干线一路向北,不到两小时,便可到达仙台市。仙台市是日本宫城县首府,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与繁华的、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大都会东京不同,仙台市及其所在的东北地区,似乎代表着现代的反面。那里地域广阔,但人口稀少,有着令人费解的地方方言和古老而怪异的民间传说。即便新干线、无线网络及其他21世纪的便利设施也覆盖了东北地区,移动网络信号在偏远山区和沿海地区仍十分微弱。这让东北地区显得像高度发达的现代日本的一块飞地。
也正是这一片怪异孤绝的区域,在2011年3月11日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日本各大媒体、吸引着日本民众甚至世界各地人民的目光。这天,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近海发生地震,震级达到9.0,震源深度约为24.4千米,是有记录以来日本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地震。此次地震也引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海啸,在东北地区许多海岸测得海啸高度在10米以上,海啸溯海岸而上达到最高40.1米的位置。距离震中最近的福岛、岩手、宫城三县的沿海地区遭到巨大海啸的袭击,仅宫城一县的死亡及失踪人数便接近11000人。
大槌、大船渡、陆前高田和气仙沼,伴随着这些地名的频繁出现,这片在地图上基本未被标记任何地名的区域逐渐被人熟知。这片区域名叫三陆海岸,有着三个与众不同的地理特征。一个是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河流,它从山林中一路向南流向两处不同的河口,一处在石卷市,另一处位于人口稀少的追波湾。第二是有尖突的溺湾,形态上类似峡湾。上千年来,不断上涨的海水淹没河谷,将之分割,从而形成这种地形。第三个则是深藏于大洋下的地壳,那是两个巨大板块太平洋与北美板块的交界面,正是这两大板块的剧烈摩擦催生了地震和海啸。
这些与众不同的地理特征让这里成为海啸中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其中,石卷市受灾最为严重,这座城市的市中心大部分都被洪水淹没,此次海啸中1/5的罹难人员来自这个人口只有16万的小城。石卷市内部被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其中1/4是渔港,在海啸中被彻底摧毁,另外3/4则满是陡峭山林、广阔的农业平原以及點缀在河口的一个个小渔村。大川小学就坐落在其中一个渔村对面,靠近追波湾那参差不齐的海岸附近。
在“3·11”大地震中,大川小学的87位学生和11位教职工仅五人幸存。
在此次地震中,没有一所学校因地质倒塌或者遭受到严重的实质性破坏。在九所完全被海啸淹没的学校中,只有一所位于三陆海岸。一名13岁的学生在跟随班级撤往高地时不幸淹死,此外其他八所学校的学生都平安撤离到安全地区。全日本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照顾的情况下不幸遇难,其中74个来自大川小学。
为什么偏偏是大川小学?
这个问题萦绕在大川小学遇难孩子的家长心头,也萦绕在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心头。帕里是《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3·11”大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东京,已经在日本生活了16年。帕里长期关注日本社会议题,也撰写过大量相关文章和著作。大地震及海啸发生后,他走访了很多幸存者,也听说了很多关于海啸的故事,其中大川小学的悲剧,让他难以忘怀,也让他迷惑不解。为何在日本最安全的、拥有最坚固的教学楼的校园,却发生了如此悲剧?帕里用了六年时间对大川小学事件追踪调查,其间他多次前往石卷市,也和不幸遇难的孩子的家庭保持密切联系,最终写成《巨浪下的小学》一书。
随着走访的深入,帕里逐渐意识到,日本秩序井然的表现背后,隐藏着由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带来的深刻危机。海啸并非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而发生在大川小学的悲剧,则是这些问题和矛盾的集中爆发与展示。
孤魂野鬼
平塚直美的女儿小晴是74个遇难儿童中的一位。地震发生时,直美正在位于横川家中的卧室哄两岁半的小女儿小瑛睡觉。横川并没有受灾,高高的堤防和河湾挡住了巨浪,以至于待在家中的直美并不知道发生了海啸。由于网络瘫痪,直美发给丈夫的信息没有送达;由于断电,直美无法收看电视,就连村里用来广播紧急消息的扬声器也悄然无声。在地震发生后,直美仿佛与世隔绝。虽然相信小晴所在的大川小学能应付这样的地震,直美还是想去学校接女儿回来。直美的公公阻止了她——地震发生后公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查看了河堤和河坝的情况。当他走在一条被海水冲洗过的公路上时,新的巨浪迅速涌来,把他往河里拽。
两天后的周日早上,直美从公公口中得知小晴的死讯。她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或者说,她被要求不要表现出悲伤。“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你要放弃希望。现在的重点是照顾活着的孩子。”直美的公公这样对她说。直美的婆婆在一旁默默流泪,也被自己的丈夫喝止。
和直美一样,丈夫真一郎也在石卷市一所高中教书。他所在的学校已成避难所,收留了上千因海啸而无家可归的人。真一郎回家后,直美得以出门看看,她和丈夫一起开车寻找女儿小晴的尸体。但第二天丈夫就和家人告别,回到市里的学校帮忙照顾避难者。直美没有质疑这一决定。她希望丈夫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公务员,不因自己的私事而耽误公职。类似地,她也希望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即便经历丧女之痛,也应该照常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家人,听从公公的嘱咐,“照顾活着的孩子”。
但与此同时,直美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小晴的尸体。一有机会,直美就会回学校,或者在学校周围徘徊。每天都有遗体从瓦砾堆中被挖掘出来给了直美信心,总有一天会找到女儿的,直美心想。到了6月,从日本各地增援而来的自卫队士兵陆续撤离,推土机从10台变成一台,参与搜索的人数从几百人变成几个人。6月底,直美在仙台附近的一家培训中心参与了为期一周的培训课,成了日本少数几位拥有操作挖掘设备许可的女性之一。拿到许可证后,她立即借了一台挖掘机,开始淤泥中的筛寻工作。

2011年3月11日,日本宫城县,海啸席卷居民区
无果的搜寻让直美和警察部陷入无望,也让他们转而求助于“迷信”。有一天警察部的指挥官提议,让直美求助于灵媒或者巫师,询问可能的搜寻方向。经朋友介绍,直美找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他是一个灵媒,据说能看到死去的人,也能听到死者发出的声音。在和灵媒接触的过程中,直美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大川的很多妈妈都求助于灵媒,她们借助灵媒寻找自己孩子留下的种种踪迹,也借助灵媒和故去的孩子对话。
这种情况在“3·11”后并不罕见。大规模的突然死亡产生了很多“孤魂野鬼”,也让生者遭遇了很多“超自然现象”。在家、在办公室、在公共场所又或是海滩和被摧毁的村镇遇到幽灵,是“3·11”后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有的人会做噩梦,也有的人会被亡灵附身和控制。各种和亡灵有关的故事在受灾地区广为流传。基督教的牧师、神道教或者佛教的僧侣都忙于安慰愁苦的亡灵。一位寺庙的住持认为灾后发生这种情况再自然不过。“海啸突如其来,他们就这么消失了。死者毫无准备,活着的人也没机会说再见。失去亲人的人和死去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依恋。死者眷恋生者,生者怀恋死者,自然会出现鬼魂。”
在日本传统中,当人们怀着愤怒或痛苦死于非命时,极有可能变成饿鬼,游荡人间,散布诅咒和怨念。此时人们便要举行仪式来安抚鬼魂。但这场海啸却冲走了家庭祭坛、牌位和全家福。举行祭拜仪式也变得十分困难。祖先崇拜的传统被突如其来的灾难中断,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契约无人兑现,孤魂野鬼成群结队地游荡。
鬼魂的大量“出现”似乎符合人们对东北地区的想象。在《巨浪下的小学》中,帕里写道:“在古代,东北地区是臭名昭著的苦寒之地,充满蛮族和妖怪。即便在今天,它也是一片遥远的边缘地带。对城市人而言,它就是传统乡村的象征,只是一种民间记忆。”早在20世纪初,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便将出生于岩手县远野市的佐佐木喜善口述的民间传说整理成《远野物语》一书,其中涉及天狗、河童、座敷童子、山男、神隐以及死者相关的传说。对于认为妖怪故事的传承与民众心理和信仰有密切关联的柳田国男来说,他编撰和整理《远野物语》的目的在于,重新激发生活在东京和大阪这种大城市的居民心中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柳田国男担心,在都市生活的噪音、雾霾以及宽慰人心的消遣中,未知世界的神秘和大自然的神奇将逐渐被人们遗忘。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民间传说和鬼怪故事处理的是快速的现代化带来的眩晕感和迷失,是日益发达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生活和栖居自然的幽灵鬼怪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和前现代的关系,那么一百年后,当“3·11”地震和海啸席卷东北部后,漂浮和游荡在海岸线上的亡灵和孤魂野鬼要处理和解决的则是高度现代化的日本面临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在爱丁堡大学历史系的学者克里斯托弗·哈丁看来,一百年间,日本超自然力量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生者安抚死者的亡灵,到死者重新被召唤来抚慰生者的灵魂,将他们从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中拯救出来,召唤他们回到一种更加老旧、更加自然和更加充实的在此世存活方式。”
那么,这种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究竟是什么呢?
脆弱之城
在伊塔洛·卡尔维诺著名的《看不见的城市》里,有一个名叫奥塔维亚的蛛网之城。
“在两座陡峭的高山之间有一座悬崖,城市就悬在半空中,用绳索、铁链和吊桥与两边的山体相连。你在狭小的木板上走动,战战兢兢惟恐脚步踩空,要么你也可以抓紧大麻绳编织的网桥……虽然悬在深渊之上,奥塔维亚居民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城市的更令人不安,他们知道自己的网只能支撑这么多。”
内生于城市的脆弱性成了一种新的常态,这用来形容日本再合适不过。从地质构造角度看,日本位于两个“三联点”上。所谓“三联点”即地球上三个构造板块相互碰撞和摩擦的交接点。这种构造决定了日本应接不暇的自然灾害——火山、台风、洪水、山体滑坡、地震和海啸。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让日本人将生命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视作理所当然。
当帕里第一次踏上日本这片土地时,他惊讶于人们以一种兴高采烈的语气谈论东京这座“不会在原地存在太久”的城市,人们谈论地震就像谈论“一场急剧的阵雨或不合时宜的降雪”。这座光鲜亮丽、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同时脆弱得如同一张薄纸,这让帕里兴奋得难以自持,“感觉这座城市真的在颤动,而且随时可能倒塌。”
同为记者的彼得·波帕姆在1985年出版的《东京:世界尽头的城市》一书中写道:“东京人的生活基调和活力,源于对危险的敏锐意识,绝不是对危险的迟钝反应。他们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而且那是这个世界上正常运转的机器中最为精密的一台,而认识到这台机器正悬在深渊之上,又让这一满足感呈现出一种近乎色情的扭曲。”
正是彼得·波帕姆观察到的日本人“对于危险的敏锐意识”,让日本建立和发展出一套应对自然灾害的完善机制——从预测到预防到救灾,环环相扣。事实上,在坚固建筑的保护下,直接由地震引发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十分轻微。在“3·11”那场大地震后,人们对地震的焦虑不增反减。即便是在距离震中最大的大城市仙台,由地震導致的破坏都十分轻微。也就是说,在一场由地震引发的灾难中,只有很小部分受害者是直接死于地震的。其中超过99%的受害者,都是在伴随地震而来的海啸中被淹死的。在地震发生时,开阔的地方——比如一片整洁的海滩——是安全的。但当海啸来袭时,出现在这种地方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在灾难发生后,日本民众对于安全感的整体感知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从地震直接带来的威胁转化成溺水身亡带来的伤害。

2011年3月23日,海啸过后的大川小学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众对于脆弱性的感知,鲜少来源于日本这个国家建立于其上的脆弱地基,也不是自然灾害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死亡。脆弱更多的是一种关乎本体存在的生存状况,一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脆弱性(precarity)。
脆弱性(precarity)一词最早在1970年代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被使用,代表一种“在雇佣者眼中充满不确定性的、难以预测的以及充满风险的雇佣关系”。按照这一定义,世界范围内的工人们其实一直被这种脆弱性包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脆弱性对工人而言并非例外,而是常态。如今它时常指代一种更加灵活、随机和不规律的工作状况,并且逐渐从雇佣关系蔓延到日常生活,蔓延到个体的生活方式以及身份认同。
尽管脆弱性已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状况,一种资本主义晚期的普遍寓言。但对刚刚经历过地震和海啸的日本,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以一种更加暴力、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在《脆弱的日本》一书中,人类学家安妮·艾莉森认为战后日本经历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剧烈变化都加剧了日本的脆弱性。
1970年代到1980年代间,日本曾经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对于男性雇员的高水平工作保障之间达到过短暂的平衡。在终身雇佣制的庇佑下,男性员工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日本一度被认为是一个“超稳定社会”:低犯罪率,没有战争或者军事干预,能够提供持久稳定的工作、婚姻以及社会关系。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经济出现大倒退,进入平成大萧条时期。孤独死、零工经济、无缘社会逐渐成为日本的代名词。越来越多人丧失了稳定的工作,丧失了公司的庇佑,也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
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可被视为一个转折点,它将脆弱性叙事推至高潮。这种叙事混合了天灾和人祸、自然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制度造就的不安全感,重新塑造着人们对于脆弱和风险的感知。后“3·11”时代的日本,雇佣关系的风险、脆弱性和不安全感夹带着对于不知何时就席卷而来的自然灾害的恐惧,迅速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一种更加普遍的脆弱状态。
政治冷感
也恰恰是这种脆弱的双重性,给了政府和官员一个推卸责任的正当理由。

2019年11月5日,日本和歌山县,世界海啸日,当地居民和儿童参加海啸预警疏散演习
在事故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大川小学就复课了。那一年冬天,大川小学校长柏叶幸向家长提交了一封署名道歉声明,表示是自己的粗心大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状况。两个月后,柏叶幸提前退休。海啸发生23个月后,石卷市政府宣布成立大川小学事件核查委员会。这个由10位知名人士——包括律师、大学社会学、心理学与行为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用一年时间审查各种文件,进行采访调查,于2014年2月发表了一份长达200页的调查报告。最后的结论是:老师和学生的死亡,既是由于操场疏散工作的延误,也是因为他们最终没有逃离海啸,而是朝着海啸的方向走去。
报告还表示,学校、教育委员会和市政府对这样的自然灾害准备还不够充分。然而,报告也写道:“大川小学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这些情况的学校。这样的事故在任何学校都可能发生。”如此一来,报告将注意力从人和制度的疏忽转向自然的不可抗力和不确定性。正是自然的脆弱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个体得以免责。正如帕里在书中所言,“这似乎是一个强有力而又令人不安的结论,是对整个国家的警告。但它的实际作用是淡化任何针对个人的指责或应承担的责任。”
这种叙事也确实奏效。帕里观察到,在灾难发生后,幸存者迅速组织起来,开始自救。这一方面是出于求生本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对官方救援不抱任何希望。灾难发生后,政府在哪里?在2011年的日本,这是一个鲜少被提及的问题。脆弱性的天平已经失衡,从制度性的和人为因素的一端徹底倾向自然的和天灾的一端。
正是这种倾斜让日本人面对灾难时隐忍克制,不问责政府,不批评当局,甚至没有愤怒。这种个体层面的坚忍克制虽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灾民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自力更生——却也造成了日本人的政治冷感。在帕里看来,它“阉割了政治,让日本人觉得个人权力无用,对国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担个人责任”。
在日本学者堀田江理看来,大川小学的悲剧背后除了萦绕着那些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夺去生命的幽灵外,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性的幽灵——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幽灵。而这一意识形态在19世纪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被证明是强有力的。在这一意识形态的统摄下,民众是国家的仆人,那些对官方说法挑三拣四的人,稍微好一点会被认为是好事者,坏则被认为是应该驱逐的自私自利的麻烦制造者。
这一天平极度失衡的后果,就是民众似乎也将制度性的脆弱性自然化了。政治制度的缺陷和由体制造成的恶果变得和突如其来的地震海啸一样,不可预知,也无法挽回。日本人对待国家和政治的态度与他们对待地震、海啸这种自然灾害的态度并无二致,充满着一种无能为力的顺从感。正如帕里在书中所言:“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自然灾害,而日本人就是无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响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无助地接受和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