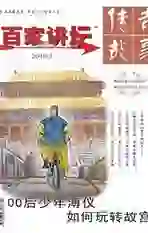钱穆与胡美琦:枯桐欣有凤来仪
2019-11-28潘彩霞
潘彩霞
乱世初见
1949年4月,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钱穆告别妻儿只身南下,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之邀前往教学,尽管国民政府对钱穆青睐有加,但他不愿从政。自15岁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钱穆就立志深入中国历史,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经过多年奋斗,他终于从一个中学未毕业的乡村教师成为与胡适齐名的著名教授。抗战时,他的《国史大纲》更是横空出世,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界的重要著作。
可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钱穆只想靠“安安静静教书做学问谋得稻粱”这样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情势所迫,与家人短暂团聚后,钱穆不得不再次离别。那时,他最小的女儿还不到9岁。不久,钱穆随华侨大学迁到中国香港,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生再也没能踏上故土。
战乱中,流落香港的青年很多,他们流离失所、无处问学,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钱穆决心办学。他联合几个内地学者创办了“新亚书院”,自任校长。
那是他最窘迫潦倒的时候,书院资金困难,流亡青年缴不出学费,教授领不到薪水,在香港湿热的天气里,钱穆常常忍受着顽固的胃疾,蜷缩在教室地板上呻吟。他牵挂在大陆的家,写信让妻儿赴港,收到的却是严词拒绝——他已和胡适、傅斯年一起被“归于另册”,对于一个“不爱国”的父亲,孩子们不愿亲近。远离家人,没有理解和支持,钱穆没有退缩,他只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那一年流落香港的,还有钱穆后来的妻子胡美琦。其父亲曾任江西省主席,她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随着国内形势巨变,在厦门大学就读的她无奈放弃学业,随家人避难于香港。他们一家人在战乱中长途跋涉,早已身无长物,为了生存,父母靠糊火柴盒补贴家用,她也到纺织厂当了女工。一次聚会上,她的父亲结识了钱穆,两人相谈甚欢,得知钱穆办学后,遂让胡美琦到新亚书院继续读书。
在中国文化史课上,胡美琦见到了钱穆,他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看似瘦弱,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却非常有震撼力,从他的身上,她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
“望之虽严,亲之即温”,课余,钱穆经常和学生一起散步、爬山,在途中也不忘教诲学生:“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思想峻厉、处世温煦”,他的积极乐观和蓬勃的生命力深深感染了胡美琦,她对他由敬畏到仰慕,一颗种子就此埋进青春的心里。
然而,他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有妻有子,她只把他当作敬仰的导师,从不作过分之想。一年后,胡美琦随父亲去了中国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读。
困境陪伴
一次意外令她与钱穆重逢。1951年,新亚书院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来源断绝,钱穆只好“行乞办学”,他到台湾筹募捐助、受邀在一所学院演讲时,不承想,新建的礼堂顶部突然坍塌,正好砸中他的头部,他当场昏迷。
得知钱穆在台中养伤,胡美琦赶来看望,并对他悉心照顾。她上班时怕他无聊,特意带一些文学小品供他消遣;下班后,她陪他一起吃晚餐;遇假日,两人则同去公园散步,畅谈国学。朝夕相处,她对他由崇拜转为爱慕,他则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她朝气蓬勃,有学识,有教养,对历史、文化心怀执着,也讓他无比欣慰,那正是他渴望的青年人的模样。
短短四个月,情愫像花木一样在彼此心中生长,生命变得坚韧、充盈。
钱穆返港后,受他影响,胡美琦决心走教育之路,于是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就读。1954年毕业后,她飞赴香港,不顾世俗羁绊,选择照顾他、陪伴他。
像一束光照亮了万千个黯淡时刻,她的到来为他带来好运,焦头烂额的事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先是新亚书院得到香港政府承认,再是钱穆的教育理想获得社会的同情与赞助,后来又在一家基金会的捐建下,有了新的校舍。钱穆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与此同时,内地沧桑巨变,钱穆知道,自己原先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1956年,他决定与胡美琦结婚。那时他61岁,她27岁,他心怀感激,亲自撰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在给学生的信中,他这样说:“穆之婚事,实非得已。以垂老之年,而饮食居处,迄少安顿,精力有限,甚何能久。唯美琦以盛年作此牺牲,私心甚望其能继续治学,勿专为家庭琐务毁耳。”
事实上,她不只是贤内助,照料他的生活、应酬人际,同时也是他的同道和知己,她非但没有让家庭琐事绊住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在他的引导下,她的学问日趋精进。
有了她的照顾,钱穆几十年严重的胃病终于好转,精神愈加充沛。他喜欢大自然,与她一起望月、观海,到山顶看落日,去乡村漫游,阴晴冷暖意味无穷;蜗居里,他们一起培育花草,品茶下棋;她最喜欢做的是听他吹箫,每逢有月亮的晚上,她就关掉家中所有的灯,月光下,他吹箫,她盘膝聆听,寂静的夜里,箫声回荡,满心舒畅。
生活步入正轨,他精神振作,办学成就随之而来,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其他两家书院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名字是钱穆定的,他立志要传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弹丸之地变得动荡不安,一心只想著书立说的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在台北选址后,胡美琦亲自绘图设计,请人施工,为了纪念母亲,钱穆把新的居所命名为“素书楼”。岂料,他们返港后才得知,有人为表诚意,已安排政府兴建,钱穆无从推辞,只好答应,这为他晚年的一场风波埋下了伏笔。
学术传承
定居台湾后,钱穆受邀担任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在家授课,胡美琦也在中国文化大学兼任中国教育史课程,他对她有期待,她懂。
此后,“素书楼”成为青年学生的问学圣地,楼前楼后,胡美琦精心栽种了红枫树、黄金竹,庭园里是钱穆最喜欢的茶花。清幽的花香中,他全力讲学、著述。在他背后,她默默操持,他爱穿中式衣服,她亲自为他做唐装;他不爱去医院看病,她就找医生配制药丸;为了接送他出行,她特意学开车。学生们都说:“师母照顾他以后没有自己了,我们都很羡慕先生有这么一位贤内助。”
1977年,82岁的钱穆大病一场,青光眼也日益严重,几近失明。医生禁止他长时间看书,亲戚朋友也劝胡美琦限制他写作,但胡美琦深知,离开学问和教育,他才是最痛苦的。为了支持他,她辞掉教职,帮他读稿、改稿,《八十忆双亲》《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重要著作就这样一部部面世。
著书之外,钱穆一直牵挂着多年杳无音信的儿女,1980年,终于和他们取得联系后,在给幼女的信中,他这样介绍了胡美琦:“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52岁,我们结婚已25年,但未有子女。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眷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也不能再写许多稿。”
虽双目不能见字,但他还有很多心愿未了,“素书楼”里,当年听课的青年已成长为教授,他依然教学不辍。1986年,91岁高龄的钱穆在胡美琦的搀扶下,结束了最后一课,他给学生的临别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告别杏坛,没有告别教育,他忧心于青年对中国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渐低落,她为他创办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楼廊上,他们谈学问,聊人生,所有的谈话,她都精心做了整理,他的智慧与学识,她要留给青年一代,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楼廊闲话》。
1989年,她陪他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一同散步时,他突然握紧她的手,兴奋地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回台后,他口述,她执笔,完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初稿,谁也没有料到,这成为他晚年最后的成就。
那时,钱穆已陷入“素书楼风波”一台湾某机构指责他“侵占公共财产”,要求收回“素书楼”,逼他们迁出。95岁高龄的他不愿争论辩解,那天夜里,他们坐在廊上深谈,他长叹一声,说:“我有一句话要交代你,将来千万不要把我留在这里。”
“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為着他的尊严,她毅然提出,“宁愿迁出素书楼,而不愿住下去徒遭羞辱”,他称赞她所说是“得道之言”。
然而,一介书生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内心终是抑郁的,搬家后,他怀念“素书楼”庭院的花木,常常望着窗外茫然地问她:“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仅仅三个月,一个台风肆虐的早晨,他就带着失望离开了世界,临终前叮嘱她:“得空时向社会作一个交代。”
他走了,留给她无尽的悲痛和未了的责任,30多年的共同生活,她深知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他属于时代,属于将来,她必须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国传统文化而活。
依他遗愿,几经周折,她将他安葬于大陆故土,太湖西山湖滨山坡的景色,正和他们在香港家中时远眺的一样。紧接着,她撰文向社会说明了“素书楼”的前因后果,2002年,“素书楼”恢复旧貌,定名为“钱穆故居”,台北市市长主持典礼时亲自向她道歉,还钱穆以清白。此后,她终于可以全身心投入整理他的全集了,连续几年,她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2010年,他去世20年后,2000万字的《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字宾四)在大陆出版,依照他的心愿,“一字不改,繁体直排”。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他的学术思想被称“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而到过“素书楼”的人都知道,没有她,便没有他辉煌的晚年。
他生前所托已悉数完成,2012年3月,完成使命的胡美琦病逝,香港新亚书院的讣闻是:“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
因为钟情与执着,他成为她一生的意义与价值。他们的爱还在延续,那些不朽著作就是证明。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