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生上城》,农民的帽子呢
2019-11-27陈思
陈思

一个民族绵延的秘密,就在于其具有坚实的精神内核,能够穿透岁月与历史的叠嶂。一个国家的诞生与繁荣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民族的支撑,当然更需要有以人民为主体为依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基底不在于形式的存在,更在于其携带有内在的文化、观念、伦理、历史、记忆等构成的内涵。
中华伟大民族是由一代代的中国人民,以顽强不息的生命意志,坚实的精神品格,铸就了光荣与梦想。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在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场上敌我冲突的氛围里,中华儿女在战斗中获得身心成长,在革命信念、精神磨炼上“追赶”革命理想,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也可捕捉到,从高涨激进的新中国城乡建设与改革场景中,从生活丰富多样性的诸多侧面烘托出,一个具体的新历史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以及人民对走向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之情。
而在新中国“转变”和“成长”的这两个主题当中,中国人民积天地精神之精华,在历史与现实的衔接处,秉持家国情怀,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奇迹,也将精神向度的追寻构成一条隐线,贯穿在城市与乡村中,由此形成自己的精神生活乃至塑造自己精神结构的冲动,这是现代中国城乡建设共同的精神诉求。
本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奉上的文章,“民族精神”与“精神生活”成为核心关键词,我们倡导与时代同行,发掘中国精神底蕴及内核所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赓续与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转换与创新;创造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逻辑及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
新时代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也是产生新型文明的时代。我们反观历史、观察现实,探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运,打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库藏,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人伦精神、思维方式,以及伦理文化的特征,获得文化自信与精神资源,体现人类意义上的代际性、持久性与公共性价值的追求。我们要以中华民族精神与文明为支撑,也要以激越的主体姿态为中华文明注入新时代的内涵,赋予中华魂的再塑造,并承担建构人类意义和价值的功能,进行本土格调的主体性精神建构及实践,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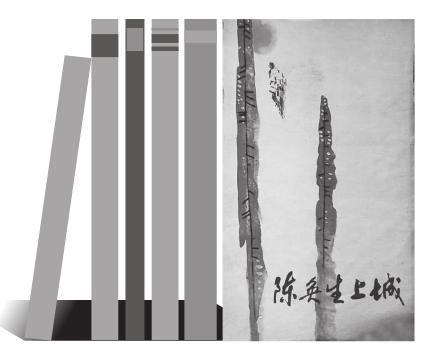
高晓声在70年代末复出后可谓一鸣惊人,《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分别荣获《人民文学》主办的1979年和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于塑造李顺大、陈奂生等一系列成功的农民形象,关注农民“吃”与“住”的切身问题,描绘苏南地区特有的乡村生活与文化风貌,加上作家本人出身农村、先后四十多年生活于苏南乡下,高晓声又被称为“农民作家”。
《陈奂生上城》是新时期文学中脍炙人口的小说名篇,小说于1980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2期后,迅速引起巨大的反响。从最初的“漏斗户”主,到上城、转业、包产、出国,系列小说的主人公陈奂生成为理解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农村改革的切入点,这一系列小说也自然构成了高晓声的经典代表作。
1979年一年高晓声发表了11篇小说。陈奂生作为文学形象首次出场是在短篇小说《“漏斗户”主》里(《钟山》,1979?年第2期)。主人公陈奂生的原型就是高晓声本家亲戚高焕生,一个住在他隔壁、朝夕相处的劳动力很强的农民:
《“漏斗户”主》里的材料,几乎是从一个人身上得来的,他的出身,他的家庭、性格、遭遇,以及他对劳动的态度,对群众、对干部的态度和群众、干部对他的态度,几乎全同小说里的陈奂生一样,可以说,这是一篇文学报告。
其时,《“漏斗户”主》在坊间的关注度还不够高。在接到《人民文学》约稿之后,高晓声很快寄去了《陈奂生上城》。高晓声认为自己已经写过陈奂生,比重新塑造一个人物形象方便,同时想通过《陈奂生上城》重新引起读者对《“漏斗户”主》的关注。
小说中的情节是这样的:陈奂生是一位中年农民,因常年贫穷而负债累累,素享“漏斗户主”雅号。1979年农村政策落实,副业复苏,他的日子好起来,开始做起小买卖──去城里卖油绳,赚零用钱买顶保暖的新帽子。陈奂生决定在油绳卖完后再去买帽子。结果,油绳卖完了,满怀喜悦的他却因为没戴帽子着了凉,竟一头病倒在车站候车室。曾在他们村蹲点的县委吴书记及时发现了他,并好意安排他住进县招待所。第二天,受宠若惊的陈奂生在房间里小心翼翼,生怕弄坏了东西。但是,当结账时听说只睡一晚就要五元钱后,他大吃一惊,进而忿忿然,在房间大搞“破坏”。回村路上,陈奂生凭着自己的“精神胜利法”想通了,不怒反喜。回村后,他果然因为坐过县委书记的车、住过一晚五元的招待所,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
《“漏斗户”主》和《陈奂生上城》,都分享一个共同的背景:1978年粮食政策宽松,1979年农村落实“三定”(定产、定购、定销),超产有奖,多种多收,多劳多得,苏南农民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农民手中有了富余的粮食,副业生产开始恢复。解决吃粮问题的陈奂生,随即出现了新的问题。从作家自我表述的“创作谈”上看,“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差距问题,是“上城”故事为农民进一步叹的“苦经”。
从作家有意识在创作谈里表达的内容看,“城乡差距”是小说的重心。例如,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中用“算账”的方式体现农民的生活水平:“卖完一算账,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当陈奂生阴差阳错住进招待所,他又以复杂的换算方式开始了新一轮算賬:
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
在帽子、油绳、工分、住宿费、住宿时间等元素的复杂换算关系中,高晓声把“城乡差距”用数字呈现出来。
在与时代风潮、评论界的频繁互动中,作家本人越来越倾向于认同“国民性批判”的有关话语。高晓声后来更多去强调农民的弱点和缺陷,“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因此“当代中国要有大量作家花大力气去为九亿农民做文学的启蒙工作,我们的文学才能前进。讲到反封建,这就要对农民做大量启蒙工作。我敬佩农民的长处,也痛感他们的弱点,我们不能让农民的弱点长期存在下去,不能让他们这样贫困愚昧下去”。对鲁迅笔法的肯定,与当时的现代化、新启蒙主义话语紧密相关。这种对当时新启蒙主义话语的自觉认同与靠拢,一定程度也影响了陈奂生系列后续小说的创作。现在看来,这样的解释,过高估计了小说叙事者与人物的批判性的距离,刻意降低了叙事者对人物的认同感。
当我们拨开作家当事人创作谈与80年代新启蒙主义话语这两重迷雾,回到文本细节和作家其他作品的光谱当中进行比对,第三种解释路径浮现了出来。
小说从一开始就强调陈奂生上城的原因:买帽子。陈奂生打算在进城卖完油绳之后用这些闲钱给自己买一顶御寒的冬帽。然而,阴差阳错,卖完了油绳正在兴头上的他却因为没有先买帽子,而着凉病倒,才有了后面的情节。从情节看,帽子是一个推动情节的道具。
同时,帽子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一开始,帽子带有“身份认同”的含义。“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在陈奂生摘了漏斗户主的“帽子”后,需要一顶新的帽子。那么,这“帽子”象征着什么呢?
高晓声显然想在帽子里附加精神层面的内容。此时的陈奂生,不缺吃,不缺住,却还少了点什么:“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围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可是讲话偏偏是陈奂生的短处,“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陈奂生最佩服的人,居然是本大队的说书人。“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陈奂生的这个念头,在结尾处得到了应验,招待所一日游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在这个故事里,陈奂生所欠缺,而又意外获得的,是“精神生活”:
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
我们必须先从“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样的后设观念当中解放出来。依据克里奇利对幽默理论的阐述,这一故事的幽默底层逻辑,主要采取的是康德式的情节“期待落空”(虽然不排除对喜剧人物的“优越感”)。观众发笑的原因,很大部分在于“失而复得”式的情感补偿,而不在于嘲笑陈奂生“自作聪明”。
当我们把视线延伸到高晓声其他小说,就会发现对“精神生活”的追寻构成一条隐线。《水东流》(1981年)中刘兴大与女儿的分歧在于,他只知道“做蒲包”,而女儿则渴望收音机、看电影所代表的精神舒展的生活方式。《蜂花》(1983年)聚焦父亲、老教师苗顺新与新一代“能人”苗果成的观念差别:一边是压抑的顶职进城,另一边则是在农村身心舒展地养蜂。小说特别强调“养蜂”生活的精神属性:“白天任凭太阳晒,夜来同星星比赛眨眼睛,风霜雨露,日以为常;饥饱无时,天天如此,任你大声笑,任你高声唱。”《崔全成》(1981年)则强调了农村新人崔全成在城中茶馆获取信息,形成与农村共同体新的连带感。《极其麻烦的故事》(1984年)中,农民主人公为了筹建“农民旅游公司”从乡村一路拜访到省一级的领导,奔走在乡间与城市之间。农民能不能有“旅行”这样的精神需求?“旅行”的行为实践(游学、宦游、贬谪、逃难、下放或观光),是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加深对世界及自我的认识的途径。农民是否有权“无利害地欣赏”风景并由此形成自己的精神生活,乃至塑造自己的精神结构?
这样看来,农民的精神生活诉求,最早就是从《陈奂生上城》中萌发出来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