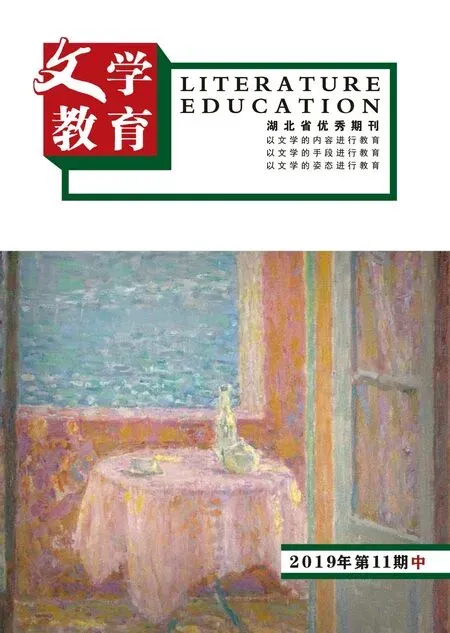从肖成碧形象看《红蔷薇》中西文化的碰撞
2019-11-27施发笔
施发笔
电视连续剧《红蔷薇》表现了“七·一五”政变前后,武汉几家人颠沛流离,时聚时散、分道扬镳的故事。剧中的肖成碧是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她与革命者夏恒煊恋爱,忠贞不二;他一度思想进步,坚决抗日。夏恒煊为救地下共产党员任致远牺牲后,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后与宋光恋爱,逃到上海,由武汉卫戍区妇女政训部主任变成了上海市党部的宣传委员,成为汪伪政权的骨干。抗战胜利后,被捕入狱,自杀身亡。
剧作通过夏成碧这一形象,表现了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或者说,表现了编剧者对观众进行的中西文化的深层次暗示或解释。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但人必须为他所有选择负上全部责任。肖成碧由进步青年沦为汉奸,没有任何人强迫她,是由于她自己的自由选择。在抗战有可能会死亡和投靠汪伪政权可以青云直上的选择上,她和宋光都选择了后者。被捕后,昔日的好姐妹夏雨竹对肖成碧发问:“如果那时你们占上风,还会选择与敌人合作吗?”她未回答,但观众可以通过她的沉默和表情看得出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她之所以与敌人合作,是因为个人升迁、利益的驱使和活命需要,是她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膨胀导致而作出这样的选择的。夏雨竹所问的“如果”毕竟是“如果”,历史没有“如果”,不可能倒回,所以肖成碧只能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肖成碧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判的不是死刑,结果让自己生不如死、求死不得。原来是宋光替了所有罪责,成了主谋,肖成碧才得以被判无期。早在第2集中,肖成碧“投案自首”,把营救共产党人的策划人、主谋,全都揽到自己身上。这些都是当着宋光面说的。这次宋光回报了她。但她说:“死不可怕,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肖成碧不同于萨特面对荒谬的焦虑不安,也不同于加缪面对荒谬进行的反抗,她自杀了。也许正是为了说明荒谬不导致自杀,体验荒谬的意义也不导致自杀,而良心的绝望则会导致自杀。
肖成碧“死”了两次,一次是为爱情而自愿走出牢房被执行枪决(实际上是狱警放空枪吓唬她),但未死成。这一次是儒家思想的胜利,为了感情,宁愿被枪杀。第二次是自杀,死成了。这一次,片中不断地让她头脑里浮现(或假想)宋光被枪毙的场景,实际上意在说明的是她自杀的原因。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1]肖成碧一定是判断生活不值得经历了才自杀的,因为她对不起宋光,悲剧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为官理论,宋光为实现她的理想而活,不惜去当汉奸,迫使宋光先是挨了锄奸队的枪子,后来苦恼无限而抽起大烟,最后被判处死刑。正如肖成碧所说的那样:“让你做了那么多你不愿做的事。”的确,宋光是“被绑架”的。之所以她觉得对不起宋光,是因为她有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她出身豪门,受过教育,换了陈得道,根本不会出现自杀的情况,他对不起很多人,包括他的妻子顾霜菊,但他不会自杀,他把顾霜菊救出献给孙天普,只不过是作为给戴笠和孙天普的见面礼,并非出自感情。他是典型的自私自利者,是与传统道德水火不相容的。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即找回自己的良心)(《孟子·告子上》)肖成碧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想起宋光陪伴自己的“开灯”和“吹灯”的日日夜夜,她要找回自己的良心,否则心不能安,而找不回良心而心也不能安则只有死亡才能了结,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活着,生不如死。”她引用肖伯纳的话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种是万念俱灰,一种是踌躇满志。万念俱灰正是她自杀的原因之一,没有了思想动力和追求目标,也看不到任何前途。显然这不是存在主义所能解决的。存在主义认为,有无意义均应活着,活着就是经历,即使经历这种无意义也是可以的。但肖成碧为什么自杀了?存在主义没有答案。也许肖成碧的自杀正是一种回答,即一旦人的良心无法找回,出现严重自责时,会导致自杀。
肖成碧的自杀可见存在主义在她身上的破产。她在被捕入狱后,在人的情感面前,再也不信只要活着就能做事,而是儒家思想占了上风,她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她觉得对不起宋光,所以她自杀了。在这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发生了碰撞,其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中国女人身上起了终结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