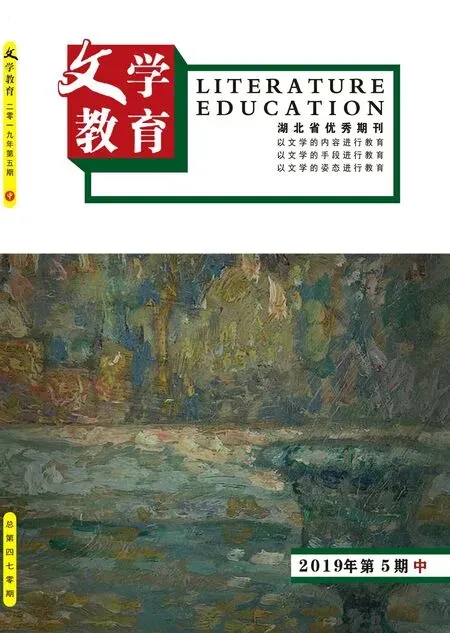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发展研究
2019-11-27徐行
徐 行
1.引言
语言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升我国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实力可以有效地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对于提升“文化自信”具有不可言喻的作用[2]。甚至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立足,这个国家的语言就一定要走向世界,一个成为强者的国家,其语言必须是“强势语言”。汉语国际教育作为汉语对外传播的主要渠道,研究其语言政策的发展路径对于我国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借助语言政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使用文献综述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汉语国际教育的语言政策做一个历时性综述。笔者认为,研究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可以清晰地认识过往政策所产生的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原因。
以往的关于汉语国际教育政策的历时性研究不多,大多研究集中在对于汉语推广政策研究与外国语言政策推广研究的对比上,用别国的语言推广政策对比汉语的推广政策,通过汲取其他国家的语言推广政策的有益之处,来提升汉语的推广实力。例如:
(樊荣,彭爽2009)通过新加坡本土的华文教育政策中的“文化融合”的角度,提出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是如何体现“文化融合”的,以及提出汉语国际教育在“文化融合”上的几点策略[3]。
(刘洪东,2014)通过对法国语言推广政策的研究,从语言政策制定的背景及语言推广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揭示法语推广的特点,以及对于汉语推广的启示[4]。
(马思梦,宋紫薇,张豫2016)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在语言推广政策方面的共同之处及差异,提倡学习借鉴日本的语言推广政策,有效推进汉语国际化进程,以便能使汉语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发展[5]。
诸如此类,介绍其他国家的语言推广政策的内容与特点,望借此来启发汉语推广政策的创新与发展。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政策本体研究有所缺失,对其发展路径,演变过程没有详细的研究。
2.语言政策与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
2.1 语言政策
关于语言政策的界定有很多,最基本的就是指对该国语言问题所持有的根本态度。曾担任国家语委的副主任陈章太先生认为,“语言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关于语言地位、语言作用、语言权利、语际关系、语言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等的重要规定和措施,是政府对语言问题的态度的具体体现[6]。”Bugarski则认为语言政策是一个社会在语言交际领域中的所制定的政策,语言沟通的地位还有原则及决策反映了社区与语言沟通潜力之间的关系[7]。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语言政策的概念为:“语言政策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对所使用的语言所抱有的态度从而制定的相关的法规、法律等。”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现状不尽相同,语言政策的定义也必将会受其影响。
2.2 汉语国教育语言政策
2.2.1 开创期: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教学机构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50年的清华大学的“东欧班”,“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开学,标志着中国第一所对外汉语教学机构的成立[8]。1962年7月,国务院外事办,拟定了外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工作的两个试行条例草案。1963年8月,高教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的制定和第一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召开,使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以及有关院校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更加明确,开始步入有章可循的规范化轨道[9]。1965 年1月,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在办学规模、模式,以及办学层次上都把对外汉语教学提到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1956年,成立了以外国驻华机构为服务对象的专门机构-外交人员服务处,使针对外国驻华使团人员的汉语教学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
2.2.2 发展期:党和国家也十分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多次召开各种会议指导各类工作,为对外汉语教学铺平了道路:(1)成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专门负责和协调汉语的国际推广工作。(2)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1984年开始研制“汉语水平考试”(HSK),1991年中国向海内外推广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该考试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员)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3)建立了对外汉语学科。中国教育部把对外汉语教学提升为二级学科,即在汉语言文学项下设一个“国际汉语教学”二级学科。保证了对外汉语在理论研究上和教师供给上的科学发展[10]。1999年12月,第二届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组长,陈至立作了《提高认识,抓住机遇,增强紧迫感,大力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主题报告。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任务与目标最明确的一次关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会议,为新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是这项事业深入发展的全新的、强大的动力[11]。会后,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加强对外汉语工作和实施五年工作计划的请示》,这为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会议精神的全面落实。由国家语委参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其中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使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有法可依。
2.2.3 深化期:(1)确立了“汉语国际推广”未来发展方向。2006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指导思想、总体规划和政策措施。同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改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教育领导小组”,其下设的国家汉办将一系列政策统筹与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大目标下。制定《对外汉语教学事业2003年至2007年发展计划,及“汉语桥工程”》。(2)孔子学院的建立。中国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现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于2002年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2004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将中国设在海外的非营利性汉语推广机构正式定名为“孔子学院”。她指出:孔子学院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12]。2004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院举行协议签字仪式。这是第一所签订合作协议的孔子学院。2004年11月,韩国首尔孔子学院挂牌成立,它是全世界首家正式挂牌成立的孔子学院。2005年7月,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在北京召开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国家政策开始全面实施。(3)汉语国际教育成为展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具2011年以来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提速的时期,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需进一步增强[13]。2012年,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作出了具体要求,文化中心自此加速了建设步伐[14]。
3.用语言政策分析影响汉语国际教育政策的因素
Spolsky在语言政策一文中提出,影响语言政策的因素可以从社会语言状况、国家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信仰、语言权利几个方面来分析(Bernard Spolsky 2005)[15]。而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的转变也可以由此为基础来分析,并且可以对未来的政策趋势作出合理的预测。
3.1 社会语言状况。社会语言状况是最客观最基础影响语言政策的因素。语言政策的制定必须根植于社会最基本的语言状况,一个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考虑最现实的语言状况。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政策转变也受社会语言状况的改变而改变。首先,随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以及我国普通话政策的推广和普及,这就为汉语国际教育中的语音,词汇,语法制定了规范教学的依据。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英语作为普遍学校初级教育的第二语言,越来越多的教育人才和双语人才被发掘,这都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人才储备提供了资源。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的制定正是基于国内一系列语言政策的改变而变化。
而最基本影响社会语言状况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汉语国际教育起步阶段,正是因为政治上需要,才促成了这一学科的建立,新中国成立的初期,需要通过交换留学生来宣传新中国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新中国要谋求生存空间的同时还要缩短与世界的距离,而交换留学生很好的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这正是这个时期语言政策的最基本社会环境。而到了“发展期”,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不论是从经济基础还是国际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就直接影响了语言政策需要更大发展空间和发展平台,而此时政治因素不在是决定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制定的唯一的基本因素,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作用乃至全球化的进程都是影响政策制定的最基本因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攀升,政治基础的不断稳固,国际化的大国形象深入人心,汉语国际教育的语言政策会紧随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变化。
3.2 国家语言意识和语言信仰。Spolsky就指出“语言是一种选择”(Bernard Spolsky),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直接决定了对本国语言和使用该语言的信念。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的制定其中重要的一点,我们并不是“文化输出”,也不是“文化渗透”。这就涉及到语言信仰,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信仰,进行汉语推广和建议孔子学院的国家大多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意识形态与我国截然不同,所采用的国内语言政策也很不相同,采取分国别的汉语推广政策也是汉语国际教育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应强调受众者对于汉语的态度,这包含了对汉语本身声誉和形象的评价,也包含了对于推广者的方式方法的评价,建立或改善汉语在受众者心中的形象,这就是一种对于汉语的“声誉规划”(Haarmann 1990)[16]。这样的政策多集中于民间,例如,江苏大学与奥地利合作的孔子学院,推出一种“汉语老爷车”的汉语推广方式,即在城中开通一条“汉语专线”,每个上车的市民可以学习几句的简单汉语,并在行程途中介绍中国的文化、经济、历史等方面内容。在下车时候颁发“掌握基础汉语使用”证书,市民凭此证书可到孔子学院免费试听不同种类的课程。这就使得汉语在基层得到很好的推广,这就有助于达到“汉语成为外国人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的目的。
3.3 语言权利。语言作为公民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权利,在许多国家已经被写入宪法当中。还有少数国家特别设立了专项语言法。可以说我国语言法的成熟和完善,也为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奠定了基础,只有当母语为汉语的公民学习汉语,使用汉语的权利得到保障,才有可能将汉语发展为一门“世界性”的语言。我国关于语言权利的法案集中呈现于《宪法》:1,1954年《宪法》为标志的语言权利初步确立。2,1982《宪法》和2004《宪法修正案》为标志的语言权利的增强和全面保障期。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国家语言政策的一部分,已被纳入我国法律体系当中。其标志性的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是我国原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重要依据,该法从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成文法律。而此时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进入发展期,教授规范化的汉语是我们事业的一贯宗旨,而《语言文字法》的确立,让我们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当然,我国关于语言权利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例如:关于海外华侨语言权利的法律法规就很欠缺,关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海外华人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得到海外华人的帮助,使得本土教师迅速融入当地生活,这仅凭借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怀”是不够的,我们首先要保障他们使用汉语的权利,在交流时使用汉语不会被本土民众藐视,在使用汉语时有获得翻译的权利,当然这不仅仅涉及语言权利,也同样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但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海外华人的使用汉语的语言权利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后盾作为支持。
4.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1 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语言政策的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学界大多关注语言本体的研究和语言自身的结构,而我们认为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语言,而应该兼顾言语,提倡把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来研究语言,研究语言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能是如何使用的。而在语言推广过程中,各个国家语言和各个国家的关系同样十分重要。想要处理好汉语和国家本土语言的关系,仅凭借语言学知识是不够的。汉语国家教育语言政策与我国的国家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的研究内容应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国家等多方面内容。我们认为在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中有几点问题需要解决:
4.1.1 有关法律法规缺失,相关政策制定和更新不及时。现阶段我国明文规定的有关语言的法律,除宪法外。只有一部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学法》,其中关于关于汉语推广只有一点:“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先关法律的缺失不仅会影响政策制定的权威性,其约束性也会大大减弱。我国关于汉语海外推广的立法工作,设立汉语海外推广机构的门槛设定,监管福利优惠政策的制定、机制的监督,相关的法律是严重缺失的。且相关机构的规范化运行、人员活动的权限、汉语教师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等尚没有规范化的政策。同样,面对风雨突变的国际形势,我国和各个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微妙的改变,无论是政治上的关联,还是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些都会影响汉语在该国的“热度”,而相关语言政策没有及时跟进,就会导致在该国的语言推广的失败。
4.1.2 国内的汉语教育收到“冷遇”,国民汉语能力下降。语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推广政策的重要基础。而在我国语言和教育政策过分强调外语教育,忽略的汉语母语教育。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在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学习上,忽视了对外汉语的学习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国汉语语言教育政策也很不具体,语文的教学方法也缺少突破和创新。这样的现状会直接导致优秀汉语教师资源的稀缺。这也会直接影响对外汉语“教书匠”的人才匮乏,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不利的影响。
4.1.3 孔子学院“一枝独秀”,缺少多样性机构以及机构角色单一。在如今迅猛发展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汉语教师不仅仅是一名“教书匠”,其更承担了传播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而汉语推广实施的机构(孔子学院)却显得功能单一,使得汉语推广渠道少,效果不尽如人意。现存的实施机构,如“孔子学院”,缺少模式的创新和范围的扩展,缺少相应的细化机构。教学系统和管理系统仍然不够完善。缺乏不同职能的组织机构协调分担各项工作,只是统筹发展,细化分工的语言推广系统缺失,使得汉语推广的效率低下,落实程度较低。
4.1.4 缺少国别和不同地区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之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不应该只停留在一个平面,应该多层次、全方位、既要符合国家利益、又要满足多方需求,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地开展。“在这个更高的境界里,我们不仅要有汉语的眼光,还要有印欧语的眼光,非洲土著语言的眼光,美洲印第安语的眼光”(沈家煊 2009)。在全球范围内的汉语国际教育推广也需要不同的“眼光”。目前我国对于重点国家重点地区的汉语推广政策研究并不深刻。由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国家和我国的历史渊源和国家关系不尽相同,对于不同国家缺乏汉语历史和现实政策的考察,这对汉语国际的推广产生巨大阻碍。
4.2 汉语对外传播政策构想与建议
4.2.1 政府应对汉语对外传播高度重视。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周边国家的接触和往来的机会增多,语言是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我国实现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机会,这就要求汉语成为其中关键要素。国家的战略政策应该包含汉语推广。我国主张四个自信,其中做主要的就是“文化自信”、“走出去”战略,这都为汉语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对外汉语的传播要成为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应该与国家外交政策紧密相连。我国也提出了“汉语加快走向世界,增强我国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提高汉语国际地位”的战略,为此我国需要全面调整汉语传播策略,学习其他国家对外语言传播模式。目前汉语的国际传播需要完善政策主要有:成立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职能机构;确定汉语国际传播的总方针;汉语国家考试系统的完善等。
4.2.2 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汉语教师水平。汉语推广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与之相反的却是汉语教师的稀缺。海外汉语学习者与汉语教师数量完全不成比例,从事汉语教学者的所学专业不同,导致汉语教学质量下降。我国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但据调查分析,毕业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毕业生少之又少,大都从事了与汉语国际教育不相关的职业,在培养模式上也过于单一,重视汉语基础,即语言本体的研究,对于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的训练缺失,注重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但缺少学生走上课堂的机会,缺少课堂实践注定无法一毕业就能担任传播汉语的任务。因此改变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的培养机制势在必行,首先应改变学科设置,多利用学校本身的留学生资源作为训练的对象,在教授汉语基础、中国文化的时候更应该注重其在汉语教学中是如何应用的。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学生不仅要有深厚的汉语言功底,并且要有熟练地跨文化交际能力。各高校可以考虑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方式经性改革,丰富课程设置、优化课程结构。此外,应该借鉴别国关于外语教师的评价政策,不断修订《汉语国际教师标准》。
4.2.3 面对有着不同语言意识形态的国家采用不同的语言传播形式。汉语推广要想取得成功,应该因地制宜,不同的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传播政策,其中国家语言意识形态应该重点考虑。由于地缘特点和文化具有传承和一致性,亚洲地区的汉语传播明显要优于其他地区和国家,同时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是促进汉语传播的重要因素。美国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同时美国华裔人数众多,使得汉语的传播工作在美国能够顺利进行。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本国语言政策的保护意识以及国家语言意识形态迥异,使得汉语推广陷入困境。对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要经行详细的调查,了解该国民对汉语和汉文化所持有的态度,研究和分析民众对汉语的需求程度和和对汉文化的包容程度,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汉语推广政策。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根据当地民俗做好汉语融合工作。目前,这方面的汉语政策研究和实施已经展开,但仍需要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的探索。
4.2.4 最大限度的满足和保障海外华人使用汉语的权利语言权利,包括个人和群体两种语言权利,涉及公民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保护人民语言权利的目的是保障权利主体可以自由选择语言,立法可以起到保护语言权利的作用,而政府的发展举措,宣传、培训、教育教学、相关机构的设立都对语言权利的保障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境外同胞的母语掌握程度是影响一个国家语言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国家(例如俄罗斯)语言境外传播政策很大一部分作用是为了满足境外同胞对语言的需求,成为联系境外同胞和国家文化之间的纽带。在我国,海外华侨和华人承担起连接国内和国外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制定对外汉语传播政策和实施时要将海外同胞作为传播的重要对象,我国汉语传播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华侨华人的语言权利,致力维护境外同胞的利益,要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国家的语言文字信息应保持畅通,保障海外同胞通过汉语获取信息和表达思想的权利,帮助海外同胞方便的学习和使用汉语等等,最大程度满足他们的语言需求,以全面促进汉语国际传播。
注 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 原网址: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 iness/htmlfiles/moe/s6811/201209/141518.html
[2]任君,赵雪爱.外来语在汉语中的使用及对汉语的影响 [M].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
[3]樊荣;彭爽.汉语国际推广中的“文化融合问题”—以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为例[M].东北师大学报,2009
[4]刘洪东.当代法国语言政策推广及启示[M].东岳论丛,2014
[5]马思梦;宋紫薇;张豫.日本对外语言推广政策及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启示[M].科教导刊,2016
[6]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5:2
[7]Ranko Bugarski;Celia Hawkesworth.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M].Slavica Publishers,Inc,1992:15
[8]程裕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程裕祯.国际汉语教学动态研究[J].2006
[10]曾海云.中国的汉语推广政策[M].金田,2013:13-15
[11]杨秀华.深化时期的对外汉语教育政策与课程设置研究 [J].长江大学学报,2012:6-15
[12]陈觉万;吴端阳,海外孔子学院发展历程、动因及特点评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4-15
[1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
[14]王祖嫘;吴应辉汉语国际传播发展报告(2011-2014)[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30
[15]Spolsky.Language Policy (Key Topics in Sociolinguistic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87
[16]赵守辉.语言规划研究新进展—以非主流语言教学为例[M].当代语言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