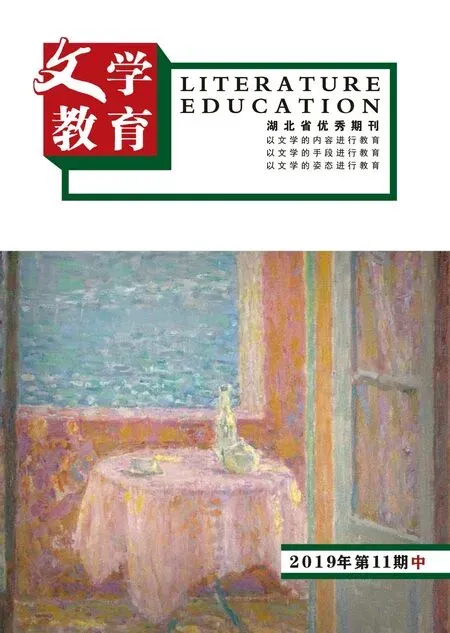从福柯看《延禧攻略》中后女性主义话语构建
2019-11-27徐丹
徐 丹
女性主义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从“女权主义”到现代女性主义,再到后女性主义阶段。后女性主义试图指出传统定位中的性别偏见和父权制根源,以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方法解构传统的学科领域,积极构建女性主义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有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综观福柯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块,“一是对权力话语的分析,二是伦理主体的构建”[1]。
一.福柯理论概述
通过“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福柯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作为理性本源的“先验主体”,话语只是在进行“无主体”运作,话语的驱动力实际上是权力意志。话语的形成是要使知识服务于获取权力、排除他者。因此,要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她们就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去回避对“女性”和女性特征的任何界定,而且对所谓的女性的主体性不再进行无谓的追求,因此,女性需要建构女性自身的话语。而对权力的抵抗如何可能呢?福柯认为权力是非中心化的,个人在权力网上流动着,他们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是权力实施的对象。抵抗权力通常采取两种形式:“反话语”和“倒置话语”。反话语即“产生新的知识,说出新的真理,并由此建构新的权力”;不同于反话语直接的对抗姿态,倒置话语并不直接对抗主导话语,而是利用主导话语中的概念和范畴为自己正名,积极争取合法化的地位,从而以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方式起到颠覆主导话语的作用。[2]P61后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福柯推崇的是微观权力论,他所言的权力已经走向日常生活,无处不在,其理论“提供了一个视角,丰富了权力理论,但不能替代宏观权力论,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系统的、全面的权力理论”[3]P21。
福柯后来集中探讨“生存美学”,也就是一种伦理主体建构理论。在他看来,人不应该把自身界定或确定在一个固定身分的框框之内,而是要透过逾越游戏式的生存美学,发现人生的“诗性美”。即人可以通过摆脱“主体性”,利用“自我的技术”,经过“关怀自身”,到达创造自我。
二.《延禧攻略》中女性形象分析
《延禧攻略》的播放引发了有关服饰道具、历史、和女性意识等方面的讨论。宫廷作为一个极端父权社会的缩影,宫中女性被严重的“物化”为男性的“私有物”,她们如何用各种方式对男权统治进行规避、反抗,建构女性自身的意义,这引起观众浓厚的兴趣。
(一)富察皇后——女性主体性的解构
历史上孝贤皇后富察氏出身满洲镶黄旗,她15岁时便嫁给16岁皇四子弘历为嫡福晋。史料记载,在她最后失去了两个儿子后病逝于德州的船上,皇帝便下令把这艘大船运进紫禁城,并从此后性情大变,从早期的“宽仁”转变成高压统治。剧中,富察可以说是一个符合“三从四德”标准的“完美的妻子”:她可以不顾个人得失,照顾愉贵妃肚子里的皇子;她体谅其他妃嫔是远离父母的“可怜人”。然而,剧中最终以她的“自尽”解构了这种“完美女性的形象”并且指名了原因:她是“贤良淑德的妻子,礼仪天下的皇后,却已经不是最好的自己”。她死前那段表白,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天下本就无情,礼教森严不可逾越,却妄想着君王有情,全不知人心险恶,天道残忍,一而再再而三得遭到背叛,一步错步步错。”
现代女性在现代的家庭关系中也同样容易成为一个满腹牢骚的“绝望的主妇”,贝蒂·弗里丹在她的《女性奥秘》一书中对女性满足于做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的神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父权文化所塑造的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妇女形象,对女性来说实际上只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
如同富察皇后一样很多女性由于对父权制心理上的认同,主动放弃了话语权,这是由于福柯的所说的从社会宏观层面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全景敞视”下的“规训技术”。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4]。从女孩到妻子再到母亲,在成长过程中就被观察,被“监视”,被要求符合各个阶段的特征。福柯对主体性的解构恰好能将女性从对女性“主体”的设定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让她们真正去发现自我。
(二)继皇后——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失败
继皇后本名辉发那拉·淑慎,在乾隆为宝亲王时,为侧福晋,虽为满军旗出身,但家室不如富察皇后。她前期与世无争,后因家族生变而黑化:她不能干涉朝政,因此也无法保护她被冤屈的父亲,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她默默的买通了官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在父权制权力控制下的知识体系中,女性在知识生产中往往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女性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沉默或者以男性的声音说话(生产知识),这两者都是女性主义者所极力摆脱的旧的知识生产模式。’”[2]P58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可以抵抗权力的新的话语生产模式。
(三)魏璎珞——独立女性形象的构建
关于魏璎珞的“晋级”很多观众认为是一种“玛丽苏文本”。实际上,玛丽苏一词并非完全贬义,而且历史上魏佳氏确实深得乾隆宠爱,她原属汉军正黄旗,后经“抬旗”转为满人籍,在继皇后之后统摄六宫,其子被封为嘉庆帝,她死后被追封为皇后。实际上玛丽苏文本的创作动机可以理解为“当代女性要求主动介入社会、重整性别意识形态的乾坤、与男性共同分享顶层世界的幻想。”[5]而且“玛丽苏”不再是男性意识中的“灰姑娘”类型,她们拥有强大的能力,甚至是全面智能型,在各种斗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6]
首先,魏璎珞的“全能”表现在其绣活出众;另外,知识广博,她知道步步生莲的典故,还有枇杷叶的知识等等;最后,她多才多艺,会说书,会魔术逗太后高兴。福柯认为关心自己最重要的方法还是自我修行,“成功的修行能够让人直面所有偶然的事件,让人具备充足的应对措施。”[3]P180
传统美德方面,她把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发挥到极致。入宫是为了找出杀害姐姐的真凶,她忠于富察皇后,关心底层人民,坚持心中“公义”,帮助宫女吉祥,明玉等,拥有“有仇必报”的侠义精神。她敢于说真话,在高贵妃迫害怀孕的愉贵人时,敢于揭穿枇杷新叶有毒,甚至她对皇帝坦言最初接近他是为了给皇后报仇。福柯认为“修行让说真话成为一种主体的生存方式……是关心自己应该追求的境界。”[3]P181福柯相信说真话对于改变社会状况有重要的作用。
剧中并没有去突出魏璎珞的美,反而故意把眉毛化细,突出她的“圆滑刁钻”(于正语)。实际上,她人格独立,有勇有谋,面对对手的正面挑衅先摆出自己的立场“我魏璎珞最不怕斗,越斗越精神”。在遭受危机时,她不会第一时间追究对错,而是冷静分析,耐心等待,合理布局。
作为一个女性,在任何判断选择面前,她都首先考虑自我而不依附于男性。在皇后要搏命生下皇嗣时,魏璎珞道:“若没了性命,纵有泼天的权势富贵,这有什么用啊”。不同于那些仅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女性,她始终理性的节制着情感。在一个宫女故意跌倒引富恒注意,她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后来这一词语成为网络流行词,它既可以用来吐槽自私自利、不懂照顾的钢铁直男,也可以用来说男人的善变。
总而言之,如同明玉说她是“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幸福”的女子,即福柯所言之“关怀自我”,让个体成为主体,让自己有获取幸福的能力。
三.两性的和谐统一——“双性文化特征”的家庭的建构
宫廷剧从皇帝戏,到公主格格戏,再到妃嫔戏,女性话语的建构日益明显。2011年《甄嬛传》被称为少有的女性书写的一次胜利,不同于其颠覆男权的模式,《延禧攻略》试图描述的是具有“双性文化特征”的美好的家庭模式:这种家庭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关心、彼此理解的基础上,夫妻双方保持独立人格,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
《甄嬛传》中的皇帝仅仅把甄嬛当做“菀菀类卿”(同纯元皇后长相相似),这无疑属于女性只是“被驯服”“被物化”的对象的极端的男权观念。相比之下,《延禧攻略》中皇帝最初也有“大男子主义”但逐渐走出中心位置与女性平等进行双向交流。其中,魏璎珞发挥了她的优点,灵活运用“反话语”和“倒置话语”的方式赢得了话语权。比如皇帝南巡时观赏官员送的歌姬舞蹈表演,继皇后指“对声誉有损”,但皇帝不理睬,魏璎珞表示也要找长相俊俏的太监来服侍自己,令皇帝主动撤了表演。这是利用“倒置话语”,用主流话语中的概念为自己辩护,既避免了发生正面冲突又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另外,在他们婚后,魏璎珞还保留着“自我”的特点,不会为宫规的条条框框改变自己,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四.总结
福柯的理论主张解构主体性,放弃对人的一致性、普遍性的诉求,因此人不应去“发现”自我而是应该去“发明”自我,这帮助女性主义者把关注的焦点重新放在了“关怀自身”上。《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就是一个通过“自我的技术”将个体构建为主体,并且在一个男性话语权力机制中坚持了“自我”并最终成功建构出具有“双性文化特征”的家庭模式的成功的女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