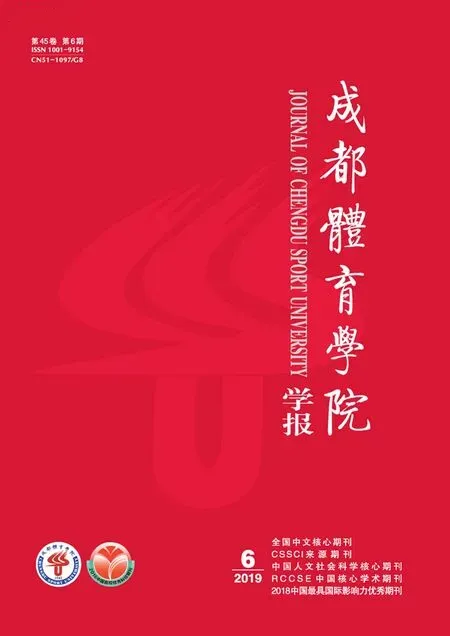一体、分化、结合:武医关系演进与重构的反思
2019-11-26卿光明冯媛媛
卿光明,冯媛媛,何 颖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体育运动与医疗卫生的有机结合。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传统武术与传统医学关系的重新审视。根据中国知网检索近10年以“武医”“武术与中医”为主题词的学术指数统计,2008年以后,武医的学术关注度稳步提升,尤其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更是明显增长。在这持续的关注中,对武医关系问题的再认识,不乏客观、理性的见解。如有学者提出武医“同根同理,互参共荣”同构了“武医一体”的文化典范[1];近代以来“武术文化碎片化、异化及体育化变迁”导致“武医分化”[2];“借鉴传统武术与中医融合的历史经验,促进现实体育与医疗融合发展”[3]等,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武医关系的研究深入和武医传统的复兴与发展。本文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武医一体”的生发逻辑,分析“武医分化”的文化嬗变,探索“武医结合”的重构思路。
1 传统文化:“武医一体”的生发逻辑
“武医一体”,就其产生而言,是指早期的武术与中医在“起源上的同根性、技法上的互利性、目的上的同一性、传承上的融通性”[3],体现出二者在历史上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源自于农耕文明下的乡土社会场域,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武者善接骨斗榫、跌打治疗,医者运用武术进行布气、点穴、舒经活络、打通经脉来医治内科疾病”[4]的武中有医、医中有武、武医一体的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为一种常见的形态。就这种形态产生的原因来看,与农耕文明下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息息相关。
1.1 农耕文化的“封闭性”,蕴育了“武医一体”的技艺传统
技法是传统武术和中医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技法上看,“传统武术以中医藏象学说、精气血津液神学说及经络学说为准则,提高对人体结构的认识,进而提升传统武术的科学训练水平和技击的有效性;而中医把传统武术的发力和功法练习方式运用在推拿、正骨等医疗手段中,获得诊疗的精准性”[3],体现出“武医一体”的技法互利性。这种技法上的互利性传统,不仅是传统社会乡野环境中有效应对医疗条件落后、卫生知识缺乏、缺医少药生存苦痛的技术层面创设,更是“忙时种田、闲来造拳”的武者对强健体魄、健康生命的宏观把握。就这种技艺传统的形成而言,传统农耕文化的“封闭性”是其形成的主要因素。
传统中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居住分散性、交通闭塞性、生活自足性的农耕社会,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体现了农耕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使得中国古代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自秦商鞍变法后,封建统治者多实行重农拟商政策,以至于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山无径迹,泽无桥梁,不相往来,舟车不通……”(《鶡冠子·备知》),从而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封闭性”农耕生业样态[5]。在这种生业形态上,造就了“和于自然、安土重迁”农业民族性格,此为代代相继的知识与技艺的文化根源。传统武术和传统医学,也正是在农耕生业形态上所形成的知识与技艺,这种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里所形成的知识和技艺的相类性为“武医一体”奠定了基础。
1.2 乡土社会的“差序性”,承载了“武医一体”的传承空间
共同的传承空间为“武医一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从传承空间属性看,以家族、师徒相承的武术,在乡土社会的封闭性空间中,具有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序性传承特点。这种差序性传承不仅体现在“横向的亲疏远近、纵向的等级次第”,更体现在嫡传、正宗的传承序列结构[6]。为维持这种差序,代际之间往往将代表“祖传秘方”的医方,视为核心技术和象征符号进行传承,如形意拳秘传丹方“五行丹”,不但是练功药方,更是嫡传弟子的身份象征,从而体现为“武医一体”在传承空间上的一致性。这种传承空间的一致性,自然深受古代乡土社会的影响。
在长达数千年的乡土社会中所形成的对“土”的根性依赖,产生了与土地相匹配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也形成了“血缘与地缘合一”的家庭本位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为武术以家族或模拟血缘关系的师徒传承,提供了传承空间的制度性基础。这种制度主要是“宗法血亲传统”长期延续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文化形态及其传承模式所具有的特征。在宗法传统倡导“礼和仁”的规训下,武者不仅要恪守封建礼法和授徒择仁,而且要有效对武、医进行掌握与合理运用。从而形成了“习武、先习医”的“武训”,以及“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点穴)出焉,圣人之用心苦矣”(《罗汉行功短打》序言)的点到为止的“武德”,体现了儒家伦理对“武医一体”的传承规训[7]。
另外,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呈现出一种“差序”性格局,体现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5]的差序性特点。这种差序性特点所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乡土社会,男性在膂力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形成了家长制形式和父为至尊的代际阶序。在父为至尊的伦理下,男性子嗣自然成为父权的继替者,徒弟也视师父为尊长,形成了“师徒如父子”古训,这也成为武术与中医以家族和师徒代际传承中所秉持的原则体系。而这种体系,也成为承载武术和中医共同传承空间的主要载体,在这种共同的传承空间中核心技术的传承往往“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学武习医成为嫡传弟子身份象征,有力地保障了武术核心技术的有效传承。
1.3 实用理性的“整体观”,框定了“武医一体”的思维理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体现了传统哲学“整体观”的认识基础。传统武术和传统医学在技理上的互鉴,在思维方式上的统合,是以满足人们生存需求为价值取向,具有“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实行”[8]的实用理性思维特征,这种“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武医一体”提供了“整体观”基础。也即是说,传统“武医一体”的知识与技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体现。
从武医发展的理论导向上来看,传统武术以中医药剂为练功保障,以经络学、脏象学为理论指导,传统医学以传统武术为实践对象和治疗手段,形成了互利互鉴、二元通和的一体化发展。武者通过传统医学理论明确身体机理与规律,从而“有理有据”地进行健身、防身和养生实践,故有“理成于医”之说;通过中医外敷内服的药剂解决练武易伤和提高习武者功力等现实问题,从而为习武过程保驾护航。医者通过习练传统武术强健体魄、明确受伤机理,运用武术招术进行推拿按摩治病、康复训练。如华佗编创的具有祛病治疾、健身养生的“五禽戏”;兼具练功与治病的武术内功“易经经”等,都体现了武术治已病和治未病的实用性目的。武医“同根同理,互参共荣”的一体化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整体观”思维模式。
从武医的发展历程来看,武医的产生源于解决传统社会中民众疾苦、治疗战争创伤的实用需求。原始时期“人民少而禽兽众”“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蠪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严酷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对“武”和“医”的现实需求;夏商周时代,在天命神权、宗教迷信、阴阳五行等思想下,武与巫医、原始宗教、教育、娱乐交织在一起,是素朴的、杂揉未分的武医雏形;隋唐太医署设有按摩科,有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掌管导引之法以除疾病,损伤折跌者正之;元代战争频仍,出现了靠师授家传的技术“理折伤”的“下甲人”,武医骨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武医的独立形态形成[9]。可以看出,实用理性是“武医一体”的思维理路,贯穿着武医发展的整个历程。然而,近代社会,伴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武医一体”逐渐走上了“分化”的发展历程。
2 西学东渐:“武医分化”的嬗变动因
近代以降,随着列强的强势入侵,西方文化裹挟着“现代科学”“个体主义”和“物质还原论”掀起的东渐浪潮,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导致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武医”在技艺结构、传承制度和思维理路出现了分化。
2.1 现代科学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促使“武医一体”传统技艺的结构性分解
现代科学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推动下,以强硬姿态冲击了中国传统知识结构。近代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并全方位扩展,中国人的态度,一开始是拒斥,然后“完全信服”,再到“全面拥抱”,这个态度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科学”被挤兑到“边缘地位”的过程[10]。“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当“以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以及科学哲学为代表”[11]的西医以高昂的姿态进入我国,不仅推动了中国人的现代医学观的转变,动摇了武医的传统文化根基,促使其理论基础的现代科学转向,而且导致“武医一体”传统技艺的结构性分解。
从思想史看,“五四集聚的思想势能、思变洪流最早冲击的是传统中医,使中国人医学观发生嬗变,医学生态巨变,发生坐标式漂移,医学彻底投入赛先生怀中,成为科学的医学,技术的医学,物象(客观)化、对象化;中医逐渐被知识界质疑、批判,甚至抛弃,中西医格局大改观”[12]。具体而言,中医理论不断被质疑最初来自经学领域,笃信西医的吴汝纶提出“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民间则有俞樾用考据学方法对《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从而提出“废医存药”论[13]。这种否定传统中医的热浪持续接力,在“科玄之争”中以“玄学鬼”被人唾骂,进而上升1929年南京政府卫生部“废止中医案”的政治意识层面的争斗[14]。几番争斗,中西医“由中强西弱,演变为中西并茂,继而形成西强中弱的格局”,中医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容与徘徊,医者不仅亦趋新求变地转向西医,而且抛却传统诊疗方法,从而导致武医技法的分离。
传统中医理论被否定,动摇了武术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武术在“中西体育”之争的文化自觉中,逐渐采取了“中体西用”的变通,参照西方体育运动的基础学科,阐述拳术技法的科学性。如“徐致一著《太极拳浅说》以心理学原理解释太极拳‘以心行气、以气运身’,意识、呼吸、动作三者配合的技法;以生理学原理解释太极拳中人体各部位姿势要求的道理;以力学原理解释太极拳的发劲”[15];中央国术馆开设“生理学”课程,推动学校武术理论的改革。这些著述与课程开设,不仅促进了武术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借鉴,而且导致武术对传统中医理论的进一步抛弃。质言之,西方现代科学的冲击,迫使传统武术作出革传统中医理论之故、鼎西学理论之新的转向,加深了武与医分离的裂痕;迫使传统中医作出弃武技疗法之旧、容西医疗法之新的转向,从而导致武者不学中医理论、医者远离武术练功的结构性分离。
2.2 个体本位对家庭本位的冲击,促使“武医一体”传承空间的制度性分割
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家庭本位和个体本位是中西价值观的根本区别[7]。以家庭为本位价值观念建立在自然经济下乡土社会的基础之上,这种社会结构为武医以家族或模拟血缘关系的师徒传承,提供了传承空间的制度性基础;而个体本位“以个人价值为中心,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一切道德思想与社会活动都以是否符合个体目的、要求和利益为准则”[16]的价值观念,建立在西方传统社会的基础之上,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原本“武医一体”的传承空间产生了制度性分割。
首先,人口的流动,撕裂了“武医一体”师徒制的传承纽带。个体本位观的引入与传播,引起了乡土社会的巨大震荡,也对传统师徒制所依托的家庭本位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具体而言,一是个人本位与人地矛盾的合力,产生的大量“流民”,成为乡土社会脱出家庭本位常轨的重要离心力。据记载:“清末道光年间,全国人口由清初六千万激增的四亿多,翻了七倍。但该时期,耕地的开发增长率却只有百分之十左右”[17],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加之外来势力争夺业已有限的生存空间,不仅导致了农耕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和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而且促使了南北人口的流动。二是西方外来势力(如传教士)在进入乡土社会中,播布具有个体本位价值观的西学,引发的中西文化冲突和内乱,也加速了城乡人口的流动。持续的冲突引起和义和团运动等内乱频发,导致“到处兵灾匪患,乡间人无法安居,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都市都邑”[18],乡间人口的流失中断了“武医一体”师徒制的传承纽带。
其次,城乡的疏离,挤压了“武医一体”师徒制的传承空间。人口流动、自然经济的解体不仅导致传承纽带的撕裂,也导致传承空间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为:一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传统师徒制模式,在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人口流动,已经失去了师徒制传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空间;二是现代学校在城市的兴起,学校传承制度逐渐替代了师徒传承制。在个体本位和寻求生存的推动下,武术家纷纷流向城市,并依托于现代学校进行武术的传播。如,武术家霍元甲创立的精武体育会,王子平、孙绿堂等大批武术家进入中央国术馆任教,著名武医名家郑怀贤在由河北—上海—四川的迁徙中,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成都体育专科学校传播武术。这种现代学校的传承空间,不仅导致了师徒制传承空间的巨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师徒传承制。概言之,个体本位与内部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疏离,加速了“南来北往”的人口流动,破坏了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家庭本位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最终导致个体本位逐渐取代家庭本位观,促使“武医一体”传承空间的制度性分割。
2.3 物质还原论对整体观的冲击,促使“武医一体”思维理路的行业性分离
“还原论”是西方哲学的一种观念,它“认为某一给定实体是由更为简单或更为基础的实体所构成的集合或组合;或认为这些实体的表述可依据更为基础的实体的表述来定义。[18]”这种观念在近代西医中,则体现为“总是潜在地把人作为‘物质集合’的化学运动的承载者来看待”的物质还原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联系的观念不同,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分析性思维方式;后者是“自上而下”的整体主义的综合性思维方式[19]。近代以来,西方“物质还原论”伴随着西学,突然出现在中华文化的对面,造成了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学的式微,也致使“武医一体”的行业性分离。
从中西医的思维模式来看,西医从“物质还原论”这一根本思维方式出发,“将因果链上的规律关系,拆成一个一个环节、‘零件’来处理,结果和原因都是具体的、可以独立存在的”,从而形成了以实验科学为标志的医学体系;中医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从生命的整体理念出发,以经络学和藏象学说为基础,形成了以“问闻望切”进行感知的经验主义学说体系[20]。随着近代中国士绅和民众对西医的接受与认同,武医的整体思维方式遭受质疑。为获取生存空间,中医在“中体西用”的折中变通中,采取了抛弃传统整体观,借鉴“西医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力求成为一门物质基础明确、实验指标客观、数据精确、标准具体的科学”的适应性措施,由此导致了武术与中医思维理路的“物质还原论”转变和行业性分离[21]。
西方体育的传入,武术的体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武术与中医的行业性分离。从西方体育传入历程来看,肇始于洋务派对有强兵目的西方近代体育的接纳和效仿,采用的内容主要是为军队服务的兵式体操,这不仅形成了我国近代最初的体育观念,而且裹挟的“物质还原论”思维方面,对武术造成了巨大冲击[22]。随着以体操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由军队向学校的传播,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体育的主导地位,挤压了武术的生存空间。为应对这种挤压,武术主动向西方体育学习、借鉴,实现中西融合和体育化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一是参照西方兵操和徒手体操教练法,将传统武术套路改编成按口令进行教学的教本,如马良编《中华新武术》、吴志青编《查拳图说》等;二是以现代竞赛规则引领武术的竞技化发展,如国术国考和民国第5、6届全运会对武术竞赛规则的尝试,等等。概言之,传统武术的学校体育化、竞技体育化发展,不仅使武术走向了近代化道路,而且也造成武术与中医的行业性分离。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被纳入体育行业,中医归属医疗卫生部门管辖,进一步固化武医的分离态势。
3 健康中国:“武医结合”的重构思路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促进了体育运动与医疗卫生的深度结合,引发了对“武医”问题的重构反思,使得“武医结合”作为一种学科交融的趋势和体医融合应对人类健康问题的一种创新形式,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大卫生、大体育、大健康”的健康实践理念,为武医结合的思维模式、传承方式和技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3.1 在“大健康”理念下,重构“武医结合”的思维模式
当下倡导的大健康观,是强调“人与社会、生态和谐,强调神形和通、天人合一;追求健康生活和行为方式,实现躯体、心理、社会责任和道德的整体健康,最终提高生活质量”[3]的“全面健康、全周期健康”新理念。它既是对以往狭窄健康观和行为的反思,又是对健康干预的系统性、复杂性特征的反映。这种理念下“武医结合”的思维模式重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破除武术情结,树立立体型思维。一般而言,武术情结是在“武医分化”的行业性分离的思维禁锢下,武者往往从行业领域出发,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强调武术的“治未病”的价值功效,缺乏整体、全局性的单向性思维方式。这不仅容易导致武术在健康中国实践中决策的滞后和发展机遇的流失,而且也不利于健康促进的有效实施。因此,面对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理念,应竭力破除就武术论武术的单向思维,树立立体型思维方式,从纵向上,承继“武医一体”的“整体观”思维和历史经验;从横向上,充分协同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技术与理论,致力于构建健康促进新谱系。
(2)破除守旧情感,树立创新性思维。守旧情感,表现为注重于“旧”,总是试图恢复传统社会的“武医一体”形态、观念或习惯等。大健康观下“武医结合”的重构,客观要求摒弃照抄明搬历史的经验,跳出“武医一体”的守旧情感,运用新的视角和手段,探索解决全面健康、全过程健康的新途径和方法。如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将武术动作与中医经络分布、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与脏腑、肢节相互关系建立三维虚拟仿真,以解决武术与中医结合的不可视、盲目性等问题,提升健康促进的效果。也就是说,要“从新的思维角度分析、处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产生新成果的思维过程”[23]的创新性思维出发,重构“武医结合”新体系。
(3)破除封闭思维,树立开放性思维。封闭思维,体现在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中,对待武术、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往往凸显出一种强烈的固守武术和中医传统、排斥现代科学渗透的封闭思想。尤其是对待武医分化的问题,有较为浓烈的回归传统,排斥外来的“仇外情绪”,导致了武医的复兴脱离社会土壤,陷入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困境。当下“全面健康、全过程健康”的大健康理念,客观要求以开放性思维,突破思维定式、拓展视野,走出封闭的、狭义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开放的文化胸襟对待西方医学、科技等人类文明成果,这不仅是武术与中医传承需要,也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总之,在大健康理念下,重新审视武医传统复兴中的武术情结、怀旧情感、民族情绪,以“全面健康、全周期健康”理念为导向,重构“武医结合”的立体型、创新性和开放性思维,把武术的非医疗手段融入医疗过程,致力从躯体健康到全面健康、从治疗医学到健康医学的转换,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3.2 在“大体育”理念下,重构“武医结合”的传承方式
传统武术与中医生发于差序性的乡土社会,家族和师徒代际传承确保了“武医一体”的文化赓续;近代社会武术与中医分化,嬗变为以学校教育为主的传承方式,导致了武术、中医的学科与行业隔离。当下倡导以开放的心态,突破行业体制壁垒,“跳出体育看体育,立足全局抓体育”[24],构建跨界协同的健康促进体系的“大体育”理念,为重构“武医结合”的传承方式与人才培养提供方向指引。
重构“武医结合”所需的“师徒制”。重构武医结合需要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新型师徒制构建观。武医结合是一种时代的症候反映之一,其所对应的是经历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如何应对人类健康的问题。作为大健康理念下的武医结合的师徒制重构,其实质是以一种开放心态、跨界融合、行业协同的理念构建新型师徒制的问题。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传统师徒制在传授实践体悟、临床经验、操作技术,潜移默化影响传承人技术体系构成和人格养成的优势,竭力厘革其具有的传承不稳定性、封闭单一性等不足。基于这种新型的师徒制构建观就能够用分析的眼光去看待当前如火如荼的程式化拜师仪式,去发现复兴和重构师徒制的逻辑规律,使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构建观成为引导和批判师徒制复兴的力量。
促进师徒制与课程制的耦合。师徒制的传帮带、口传身授,有益于弥补现代学校“一对一、精英化和实践性”的缺失;学校课程制的高效率、规范性,亦可弥补师徒制的自发性、缓慢性等短板。因此,应探索发挥师徒制与课程制优点和先进性的有效途径,促进二者的联姻、取长补短。从实施路径来看,武术院系和中医院系毋容置疑地处在“武医结合”的前端要地。具体而言,武术院系和中医院系应以“全民健康”为目标,加强二者的协同与合作,通过破除学科和行业壁垒,采取联合办学、联合培养、师徒传承措施助力“武医结合”人才培养。中医院系增强“武术非医疗手段干预”理念,通过开设武医专业,构建武术练功法、推拿练功等课程体系,促进武术与中医的结合;武术院系增强“理成于医”观念,通过开设中医理论基础、伤科诊疗法、武术损伤诊断与救治、临床实习、物理疗法等中医理论与临床课程体系,促进中医对武术的渗透。概言之,加强武术、中医院系的深度合作,实现师资的互鉴互学,课程体系的融通,武医技理的融汇,从而达到优化武医结合的传承模式,致力于培养“武术健身指导+医疗服务”二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
3.3 在“大卫生”理念下,重构“武医结合”的技理体系
传统社会武术与医学技法互利、技理互参共同致力于防病与治病的健康保障;近代社会武术与中医行业隔离、技理分化,逐渐形成以“医学治疗为中心”的单一健康维护模式。随着这种单一模式的种种弊端的凸显,“防治并重”日益成为健康促进的策略选择。当前倡导“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5]的大卫生理念,正是对“防治并重”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适时回应。“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大卫生理念,理应对“武医结合”进行承继传统和采借西医的技理重构。
以传统武术与传统医学的菁华,重构“武医结合”的技理体系。武、医技理互鉴、融为一体是武术文化惯性与传统,但“传统集优劣一身、合强弱一体”,故应对其进行甄别后方能体现实践价值。如武谚:“酸多练,痛少练,麻不练”和著名武医名家郑怀贤根据正骨理筋手法与武功技法的密切关系,融擒拿、点穴与正骨理筋于一体所形成的“十三手法”“经穴按摩”“正骨推拿”和“推拿练功法”等郑氏伤科按摩技法,是武医家躬身践履的实践总结,也是被广泛证实的武医技理精华。而武医中依据情感体验的意象训练和以类度类的类比推理所形成的如《少林拳法秘诀》中“龙拳练神,虎拳练骨,豹拳练力,蛇拳练气,鹤拳练精”[26],以及武医中内涵一些诸如巫术、迷信色彩的技理内容,应加以甄别和祛除。故而,应对武医传统技理加以多面剖析和了解,以取得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后,以传统菁华重构“武医结合”的技理体系。
采借现代西医的科学技术,重构“武医结合”的技理体系。虽然,西医以还原性科学方法,以拆开生命的形式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其功能的片面性和过度科学理性饱受诟病,但西医的一些诊疗方法可成为弥补中医短板的有效方式。如以“制器以正之”为指导,西医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等方法,为骨折后解剖对位提供客观的依据。据此,应对现代西医科技加以多维解析和把握,以取得一种明确的他者认识后,重构“武医结合”技理体系,实现武医传统的创新发展。概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分化与融合并存,整个现代科学体系呈现出结构的整体化趋势,学科跨界融合、兼收并蓄已然成为常态,使得每一学科只能在整个科学体系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得以发展。武医技理体系的重构,在“防治并重”和“全民健康”目标下,应合理承继武术中治病与养生的技术手段与方法,采借现代医学之新技法,“设计能够组合、共用或互补衔接的技术模式,选择不同生命时期、不同身体状况下武术技术、医疗技术共同干预健康的最佳组合,合理运用武术非医疗干预及医务监督技术作用于生命全周期”[3],促进健康中国的建设。
4 结语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不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自然界是动态的,人类社会的文化也是动态存在的。作为人类文化表现形式的武医关系,在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体现,既表现为传统场域中的一体化,也表现为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分化。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为“武医关系”从“分化”到“结合”的现代流变提供了时代机遇。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文化实体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承担着对应的历史发展任务与文化使命”[27],明确武、医的文化使命,是着眼于“武医结合”理论建构的应有命题,也是助力“健康中国”应有的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