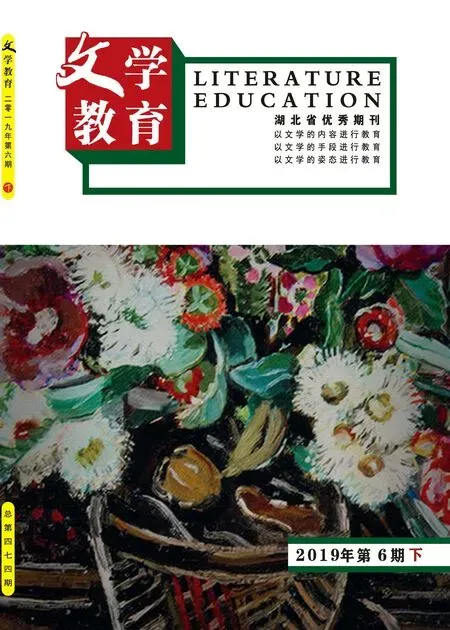论席勒《美育书简》中的“理性的人”
2019-11-26李同花
李同花
一.“美育”概念的提出
18世纪的德国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和社会都是可耻的,但所有伟大的德国思想家都怀有反抗社会的叛逆精神,这其中包括诗人席勒,他满怀对于法国大革命进程的疑虑和愤懑,从审美批判的视角分析当时的社会危机,以人本主义的哲学为基础批判人性的堕落。他认为正是文化或现代文明这种历史的必然产物导致了人性的分裂与生存碎片化。基于康德先验哲学中人性以及美的相关理论席勒提出了“美育”这一划时代的理念,他企图通过审美或艺术改变人性、塑造完美的人格,建立理想的政治社会。美育在席勒是一种手段,他把美看作是人的“第二造物主”,审美状态是一个过渡,最终目的是使人恢复到自由可规定状态的人(道德的人),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是单方面受感性冲动或理性冲动的制约,这两种状态需要一个中间状态进行平衡,在这个中间状态中人处于一种“无限的可规定性”,因此可以重新生产与创造人的心理机制。这个中间状态的实质是“从感觉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向的能动状态的转变,只有通过审美的中间状态才能完成。虽然这种状态本身不决定我们的任何见解和信念,也不会由此否定智力和道德的价值。然而,这种状态仍然是我们活得见解和信念的必要条件。总之,要是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们成为审美的人之外,没有其他途径。”(《美育书简》第二十三封信)席勒假设通过“美育”可以达成一个自由王国“在力量的可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在的显现的愉悦的王国。在这里它卸下了人身上一切关系的枷锁,并且使他摆脱了一切不论是物质的强制还是道德的强制。”(《美育书简》第二十七封信)于是通过这种近乎“零”的自由的可规定状态,人就可以凭道德的人建立伦理王国(席勒理想的政治)在这种王国中“指导行动的不是对外来习俗的呆板模仿,而是人们自己的美的本性,在那里,人以勇敢的质朴和宁静的纯洁来应对及其复杂的各种关系,既无须以损害别人的自由来保持自己的自由,也无须牺牲自己的尊严来表现优雅。”(《美育书简》第二十七封信)如孔子的随心所欲,不逾矩。
二.人性本质:理性的自由选择
席勒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决定性因素是:理性的自由选择,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席勒在费希特将人性分为经验自我和抽象自我的基础上将人性抽象出人格与状态两种因素,“在人身上可以区别出一种持久的东西和一种经常变动的东西,持久的东西称为人格,变动的东西称为状态。”(《美育书简》第十一封信)理想人格只存在与人格与状态的绝对统一中,有限存在的人人格与状态始终是两个东西。席勒把理想的人格等同于神性:“在绝对的主体中,是以人格保持全部的规定不变,因为这些规定就是来自人格,神性所具有的一切,人格也都具有,因为他就是人格”。(《美育书简》第十一封信)而且席勒还 指出:“人格只显示在永恒不变的自我中,它是不能形成的,不能在时间中开始的”(《美育书简》第十一封信),但是经验中的人并不是一般的人格因为它只是一种形式,人不能只作为一种形式“人不单纯是一般的人格,而是处于一定状态下的人格,所以人才是形成的”。(《美育书简》第十一封信)这种神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能作为一种倾向,而人的人格有这种趋向于神性的天赋,那是如何趋近的呢?席勒说是靠感性,作为自然产物,人最初是感性的存在是靠着感觉、欲望、按照欲求行动,人格如果离开了感性物质材料就只是空洞的形式,但是人不能只是作为世界而存在,但又不能作为形式而存在。“为了不仅作为世界而存在,人必须赋予物质材料以形式;而为了不仅仅是形式,人必须赋予自己身上的素质以现实性。”于是人身上就分立出两种要求,即感性本性与理性(通常与形式等同)本性,感性本性要求绝对的实在,理性要求赋予内容以绝对形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席勒说人之为人最本质的是按照理性的自由选择不作为物质而作为道德的存在。这种理性的自由选择是人性尊严的保有:“自然界对待人并不比对待其他作品更恩惠些:自然界为人做的,还不能使人作为自由理智而行动。”“使人之为人的正是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界所创造的样子,而有能力通过理性完成他预期的步骤,把强制的作品转变为他自由的选择的作品,从物质的必然性提高到道德的必然性”(《美育书简》第三封信)。所以,人是不按自然强制生存的,而是按照道德自律生存,是超越自然界的道德存在物。
三.美育的人格构建目标:“自由”与“完整”
“自由”与“完整”是席勒对于完美人格的追求,席勒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性都被文化以及启蒙现代性异化,人性堕落分裂为“粗野”与“文弱”两种极端的状态,在他看来古希腊人才是完美的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现代人在古希腊人面前是羞愧的,因为在席勒看来人的本性在希腊人可以内在的展现艺术的魅力和智慧尊严性的结合,而不同于现代人已然将其变成了文化的牺牲品。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希腊人在其灿烂的文艺活动中展现出形式的丰满,以及内容的丰富,他们既可以从事哲学思考,又可以进行艺术创造。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温柔与力量。青年性的想象与和成年性的理性相结合结合。所以,席勒认为古希腊人呈现了神性的人格,那时候的人在其文艺活动中可以看到饱满的精神力量,感性和精神并非处于敌对领域。实际上追溯西方美学史可以发现,在其源头上最早的戏剧虽然在其作用上是为了教育,但是仍然展现出美的形式。在淳朴的思维中诗并非为了投机取巧,而是真实情感有节制的流露,最诡辩的思辨学页没堕落为吹毛求疵。那种席勒所认为的神性确实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即理性与感性平衡状态下的完整的人性。当然席勒再怎样赞誉希腊人完美的人性,他也明确指出历史不会倒退,而且古希腊人也只有在它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上才保有这种人性,不能后退也不能提高,这是历史局限。席勒旨在借古希腊人与现代人作一个比较,以此来披露现代人的人性弱点,指出以个体的发展谬误换取整个人类的真理这样一个文化悖论,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对立席勒提出审美的教育“用更高艺术的艺术来恢复被艺术破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这种完整性。”
(《美育书简》第六封信)他认为这种完美的人性存在于审美活动中,因此构建了美育可以拯救人性的尊严的理论。
四.美育的内在逻辑:美是人的第二造物主
席勒将现实中的人性的分裂归因于审美的丧失,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同时席勒也对美进行了分析,由此得出人的三种冲动:感性冲动、理性冲动、游戏冲动,它们分别决定了三种人:感性的人、理性的人、审美的人。经由游戏冲动将人格中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相结合,使人进入审美的自由状态,最终成为理性道德的人。可是美如何实现?首先,席勒在《美育书简》第十五封信中给美下了一个定义:美,是活的形象。他的论证思路是:感性冲动的对象从普通概念上可以视为最广义的生活。而“形式冲动的对象的普通概念“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与各种思考力的关系。”而游戏冲动的对象的概念就可以叫作活的形象。“活的形象”指现象的一切审美性质,总之是指最广义的美。”所以把美的定义推及到整个生物界就可以延伸到人身上,一个人有生命内容也有外在形象,但并不会因此就等于活的形象。只有当一个人的形象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形象时才称的上是活的形象。“只要当他的形式活在我们的感觉里,他的生活在我们的知性中取得形式时,他才是活得形象。(《美育书简》第十五封信)”但是他们如何结合呢?席勒假设在形式冲动与感觉冲动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状态(游戏冲动),结合人性是实在与形式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受动与自由的统一的概念。在这种连结美与人性的先验假定基础上席勒建立了美育思想。因此,完美人格的实现应该是在游戏冲动的客体中也就是活的形象中。“在美的直观中心灵处于规律与需要之间恰到好处的中点”(《美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在审美中人既可以维持生命的需要又可以保持生命的尊严,所以席勒将充分意义上的人、美以及游戏等概念密切连结在一起“人应该同美一起只是游戏,人应该只同美一起游戏。”(《美育书简》第十五封信)
与完美的人性一样美的最高理想也只是存在于观念中,“美的最高理想要在实在与形式的尽可能完美的结合与平衡里去寻找。这种平衡永远是一种观念,他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完全达到。”(《美育书简》第十六封信)所以经验中的美永远在掣肘,他们表现为松弛与紧张两种作用,表现在经验中就是融合性与振奋性。凡是把观念实现与人性中的时候,都会有各自的任务比如道德、真理、幸福。而美育的任务就是由美的对象产生美。振奋性的美的作用是通过紧张力使精神既适应于物质又适应于道德,而融合性的美是使精神在物质与道德领域得到放松,呈现在审美活动中就是崇高感优美感。对于不是在物质就是在形式受到强制的人需要融合性的美,对于沉醉在审美趣味中的人需要振奋的美。自由本身是自然的一种作用,在人最开始的状态,感性冲动最先起作用,人还没有成为人,人要力图从受动状态转变为主动就必须以理性代替感性,但是人又不能完全抛开感性直接过渡到理性,于是就需要一个介于感性与理性的中间状态,暂时摆脱单纯的可规定性的状态,借助这个中间状态到达自由的可规定性状态,以实现理性的人,因此席勒将美视为人的第二造物主。虽然席勒的思想带有乌托邦的意味,但由他的思虑所得出的人应该是理性的自由选择者的这一理念确实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最内在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