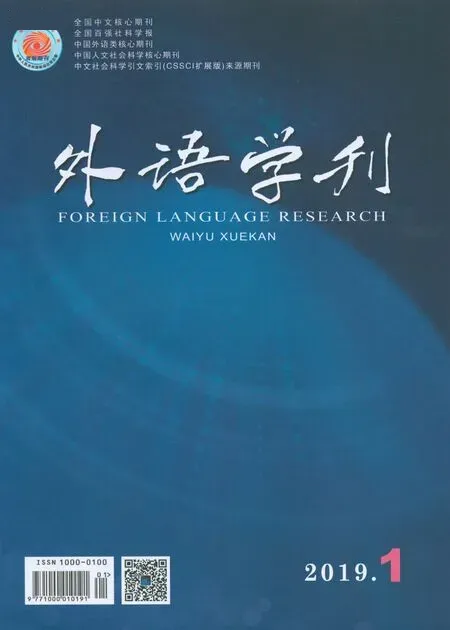“马”给出的是什么意义∗
——语词的最小语义内容问题管窥
2019-11-26刘利民
刘利民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4)
提 要:本文考察钱冠连的“‘马’给不出马的概念”与公孙龙的“‘马’者所以命形也”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容的命题,由此讨论概念与语词意义的关系。本文认为,语词不能给出一个概念的完整内容,但必定具有最小的语义内容,这个内容是概念的碎片化、静态化抽象。与能指相组合而构成一个语词符号的不是概念整体,而是概念内容之一的抽象。
1 引言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被后世诟病为“诡辩”的命题——“白马非马”。2015年钱冠连发表论文《“马”给不出的马概念——谓项与述谓的哲学含义》(钱冠连2015)。这篇文章与《白马论》都是在概念层面思辨语词“马”的意义问题,而不是在经验层面讨论实在的马,但两者关于“马”的意义却表达了截然对立的观点。钱冠连认为一个名称或名词不能指称出任何概念(同上2015:1);公孙龙却宣称“‘马’者,所以命形也”,即“马”作为名称指称且只能指称马之形;即是说,语词“马”除指称马的概念外,不指称别的东西。不过,两人的命题虽直接对抗,但如果联系起来思考却可能很有价值,因为这可能有助于揭示更深刻的哲学、语义学道理。本文就两者论点的分歧与通约、以及这一通约对于语词意义问题的启发展开思考。
2 两“马”论之分歧
公孙龙与钱冠连的“马”论各自都站得住脚、具有合理性,但在命题意义上确实又是对立的。
钱冠连意在讨论对于弗雷格“一个概念不能由主项表达式指称出来”命题的理解及误读。该文指出,一个名称或名词不能指称出任何概念;概念不在作为主词的名称身上,而是由其后的谓词给出;是谓词使得主词的概念由空到实。按此,“马”只是语言符号,本身不是马概念的指称。“马”独立使用并不给出马的意义,其意义有待“马”作为一个命题的主词时,由其后的述谓予以给出。如果一个谓词不够,那么数量不确定但足够多的谓词(单蹄的、食草的、家养哺乳动物;可供人骑;能赛跑;可驼重;等等)将能做到,使得关于马的概念意义充实、丰满起来。
这个观点站得住脚,因为“马”如果单独使用,那么不知道马是什么的听话人不可能从“马”这一单个符号中形成关于马的概念。这等于说,“马”只是一个符号,无法表达出说话人脑中关于马的整体概念,因而无法回答“马是什么、马怎么啦”的问题。这源于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确定性难题。从心理学角度看,概念是“心理胶水”,联系人与世界交流及过去的经验;概念本身就与人的更大的知识结构相连接(艾森克 2009:344)。如是,那么概念不是单一的、边界清楚的心理表征,它由心理胶水粘连的一定是多方面的内容,并形成结构化的意义。但是这一意义的心理表征是整体的还是生成的仍存在争议(Jackendoff 2010:277-280)。从哲学看,这更是一个难题:概念到底是什么迄今为止并不清楚。从柏拉图到罗素,传统西方哲学家们倾向于将概念视为某种自主的实体,但关于概念的属性、条件和标准等问题的认识莫衷一是(Weitz 1988:260-264)。而按蒯因的语义整体论,既然任何单个句子的理解有赖于人关于世界的整个信念网络,那么任何一个概念意义的把握也必定取决于这个信念网络中的种种意义联系(Quine 1953:41)。
关于概念意义,心理学和哲学的观点意味着:第一,要求单一的语词符号表达出概念的结构化意义是行不通的;第二,要求语词清楚地给出尚不清楚的意义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面对概念与语词意义之间关系的经验及逻辑难题,钱冠连采用塞尔的SVBAUN 方式或许还真是一个出路:把“马”置入命题中去担任主词,而由谓词给出马概念的意义(联系)之一(Lycan 2000:42)。至少,求诸于句子乃至语篇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是可行的,因为一个句子不够的话,由多个句子组成的语篇总能逼近“马”概念的整体意义。
公孙龙的“马者,所以命形也”表达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命题。他在先秦时代提出这个命题,旨在为其“白马非马”命题辩护;其论证目标是:语词的意义不在于实指客体,而在于指称概念。公孙龙承认“马固有色,故有白马”,因此“马”当然可以用来言说具体的马;但他认为语词“马”的意义不在于它与客观世界中的马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而在于“马”作为名称,命名的是马概念。既如此,他指出,马概念本身是无色的:马概念不含有任何颜色性质;即颜色不是马概念的定义性内容,不属于“马”表达的概念意义(刘利民 2015:34-36)。语词“马”不与客体马相联系,又不包含颜色等属性,那么其意义内容只能是抽象的马形。这一马形是纯粹的马意义,不含有马形之外的其他任何属性和功能等内容。可以确定的是,他说的这种纯粹的马形不是关于具体马的感知信息,而只能是单一的马概念本身。如是,公孙龙的命题事实上提出:“马”给出的只是马概念。
公孙龙的观点也有道理,完全吻合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本质的理论,即符号就是音响形象与概念的不可分的结合(Saussure 1983:66-67)。“马”这个记号(能指)与马形(所指)的结合(命名)使得“马”具有意义,即“马”指称马的概念。诚然,在公孙龙所处的时代,汉语中并没有“概念”这个概念,但这并不能否定公孙龙的思想已经涉及到与感知经验不同的抽象概念性知识的问题。事实上,他对这个问题已做出深刻的论述,即他关于“力与知果,不若因是”的洞见以及由此而提出的“离”的分析方法(刘利民2015:15,39)。不仅如此,本文认为公孙龙在关于所指到底是什么这一个点上的陈述可能比索绪尔更加到位。索绪尔将概念作为所指,强调其心理属性,但困难在于,概念是什么并不清楚。如前所述,即便从科学的角度看,概念问题也涉及面太广、太复杂。公孙龙提出的“形”作为舍去概念的众多可能内容之后的意义抽象,则可能更符合语词意义的实际。这一点本文稍后再讨论。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说公孙龙对“概念”的认识比索绪尔更全面、准确、深刻,而是说他的“形”更有助于我们探讨和认识语言符号的意义问题。
3 两“马”论之通约
钱冠连是对的,但公孙龙也没错。这不符合逻辑道理。于是,极有可能的是,他们的观点并不对立。本文认为,他们关于“马”意义的这两个观点能够契合,两者的所论是相容的而不是相斥的。
一方面,如前所述,钱冠连列出一系列谓词,表明作为主词的“马”的概念意义由谓词给出(马是单蹄的;马可以驼重;等等)。须注意,钱冠连讨论的不是具体实在的马,而是马之为马的概念。马概念的内容肯定包含有诸如马的属性、功能和类属等十分丰富、复杂的意义,但“马”却无法给出这些意义,只能依靠一个个谓词分别描述其中之一。对此,公孙龙不会否认,因为他自己也使用马作主词,并以谓词给出马概念的描述。例如,在他的关键命题之一“马无色”中,“马”是主词,命名的是马形,其后谓词“无色”正是他要描述的马形作为概念对象的属性特征。
既如此,有一点显而易见。钱冠连指出语词“马”如果不是在句子中使用而是单独使用,那么它并不能表达出马是什么、马怎么啦之类的意义。换言之,它无法提供关于马的任何知识或信息(无论是内在于心的知识信念、还是当下现场的感知信息)。对此,公孙龙应当无异议,因为他自己的核心命题“‘马’者所以命形也”本身也只能是以句子的方式予以表达。单独使用“马”语词,他不可能表达出“是用来命名马形的”这一意义,也就不能指望人们理解他关于“马”的这一思想。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关于“马”意义的讨论都涉及句子表达,两人所论之“马”事实上是通约的。这恰恰是由于句子(这里指陈述句)的主—谓结构及这一结构组合成的命题意义的合法性和真值问题;即,一个句子表达的命题是否合法、是真或是假,取决于句子的主词与谓词的搭配。主—谓搭配如果不合法,那么句子将是无意义的;只有合法的搭配才能提供真值条件,即根据事实判定句子表达的命题为真或为假的可能性。在一个句子中,如果“马”做主词,那么“马”所命名(指称)的必须是马,而不能是狗或笔,否则主词之后由谓词搭配而组成的命题就会因不合法而无意义,或者因不符合事实而为假。例如:在“笔是单蹄的”一句中,主—谓搭配不合法,因为笔是书写工具,根本不具有任何生物才可能具有的用来走或跑的器官,所以该句不可能具有真值判断的价值,因而事实上没意义;而在句子“狗是单蹄的”中,狗虽然是生物、且跟马一样具有用来走或跑的器官,但其有爪,却没有蹄,于是这个句子的主—谓搭配虽然可以合法地提供真值条件,却与事实不符合,因而其真值只能判定为假。同理,“马是前轮驱动的”不合法,因而无意义,而“马是守夜的家养动物”不符合事实,因而为假。命题意义层面上讲是如此,感知经验层面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想说的是狗,却使用“马”一词,结果只能是语词使用错误。
由此观察钱冠连和公孙龙论“马”,我们发现两者的命题其实是相容的:一个谓词能够或者不能够与“马”搭配,取决于“马”是否命名了马,即“马”必须且只能给出马的最纯粹而基本的意义。某一谓词能够成功地将意义送给主词,前提是主词允许、接受该谓词送来的意义;一个句子要能表达为真的思想,其谓词意义必须是主词标示的概念的一个合理内容。
进言之,如前所述,马概念的内容可以是多维而庞杂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语言社区的成员都必须把握马概念的全部内容才能使用语词“马”进行交流。语言哲学家普特南早就提出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假说,认为一个语言社区就像一座工厂,其中成员的语言使用具有语言劳动分工特点。他说,关于语词“金”的意义,语言社区的成员并不一定把握其本质意义,即“原子序数为75”,但这并不妨碍所有成员使用“金”一词来言说金,因为在这个工厂中,有的成员的分工是穿戴金饰品,有的卖金饰品,还有的则确定金的定义标准。确定金标准的成员通过不断研究而深化关于金的本质的理解,因而有资格在其他成员关于“金”的意义发生争议的时候进行裁决。因此,一个社会的语言交流成功取决于社会成员之间有条理的合作(Putnam 1999:236-238)。
普特南的假设有助于我们观察两个“马”论。钱冠连在文中给出的言说“马”的谓词涉及的正是不同层面的马的属性。动物学家的知识信念系统中具有的马概念的生物学定义内容、骑兵心中关于自己与马“生死与共”的意义等显然是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许多人不具备的。但是,动物学家、骑兵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用“马”来说马,而不是说汽车(虽然汽车也跑得很快)、不是说骆驼(虽然骆驼也能驼重)、也不是说狗(虽然狗也是家畜)。而这又刚好符合公孙龙“马” 论的要求——“唯乎其彼此”;即,使用“马”名称时,其所言对象必定是、且只能是马。钱冠连与公孙龙的两“马”论在此获得通约性。
4 两“马”论的启发
观察研究钱冠连和公孙龙的“马”论,当然不仅为理解他们表达的思想,而且因为两者观点都指向一个重要问题:语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很大,但总得有个起点。《文心雕龙》提出“因字而生句、集句而成篇、集篇而成章”(刘勰2008:336),而现代语义学的组合性原则也提出,句子的意义由其组成词项按句法规则组合而成。可见,语词的意义可作为这个起点。
关于语词符号的意义,索绪尔很确定,即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的不可分组合(Saussure 1983:67)。但如前所论,根本困难恰恰在于概念本身。一个极简单的日常语词,如“晚餐”,涉及的概念内容都竟然可以因地域、文化、个体,乃至食材、餐具、进餐方式、地点和时间等因素而千差万别。这也就是为什么如雷卡纳蒂等语境论者能够宣称“任何词、句的意义只有相对于具体语境才可确定”(雷卡纳蒂 2013:153)。再如,“所有人都准备好了”之类的句子意义不确定,因为“所有”指什么范围不清楚、“人”是什么人不清楚、准备好做什么不清楚、甚至准备什么及如何准备等等都不清楚。既如此,词句的意义须要由语境来充实并加以确定。本文这里无意批评语境论的观点,只想指出一点:正如卡培伦等人所说,语境论无法解释通过文本获取知识以及在不具有语用背景知识的情况下人们之间能够交流等事实(Cappelen,Lepore 2006:425)。比如说,看到教室的黑板上写着“10 毫克尼古丁足以杀死一头牛”“大家不要在教室里抽烟”时,汉语使用者恐怕不会说不知道或者不确定这些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是谁、在什么语境下写下这些句子。很显然,只要一个人知道这些句子中每个语词的意义及其语法关系,这个人就至少能理解这些句子的字面意义。
但问题是:既然每个语词符号的意义就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而概念内容又非常复杂,那么一个能指无法与概念的复杂内容相组合。换言之,索绪尔符号理论中的所指是什么需要澄清。本文对钱冠连和公孙龙的“马”论的围观似乎能够提供一个思考。
本文的观点是,这两个“马”论的和谐说明:一个语词符号的意义不是概念,而只是概念的一个碎片化、静态化的抽象。“碎片化”是在找不到一个现成的、更恰当的术语的情况下,本文生造的语词,其意为概念的一个意义成分或部分的抽象表征;“静态化”是语词把所截取的概念之一个成分或部分由社会约定而固化了。“静态化”比较好理解,本质上就是“语言共同体”的“公共约定”(陈波2014),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传递内容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Borg 2017)。这不是新见解,索绪尔早已指出,能指与所指之结合虽有任意性,但一旦两者的结合成为社会约定,则一般不能由任何个体随意改变(Saussure 1983:68)。因此,本文主要说说“碎片化”。
碎片化是必须的,因为单个语词不可能完整地将一个概念整体和盘托出。否则就不会产生语境论的质疑。一个直观的简单例子就是,即便是指称个体的单称词项(名称、描述语等)也无法给出该个体的完备信息内容。“张三、当今美国总统”等充其量能够指称出(挑出)特定个体,但该个体的种种属性,包括音容笑貌、习惯和经历等方面却不可能由单称词项给出,这也不应该是单称词项的任务。至于通名、动词和形容词等词类就更是如此。例如通名“枪”,即便按经典范畴论,枪范畴的成员具有用火药能量发射子弹打击目标的武器的属性,但这并未同时给出手枪、冲锋枪、狙击步枪、高射机枪等(功能)有区别的意义;更何况经典范畴显然将排除射钉枪和水枪等对象。典型性范畴论虽可以按家族相似性原理收入这些意义,却显然又增加概念定义的难度(玩具枪是枪吗?)。本文提及范畴论问题想说明:说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还不到位,因为一个概念的整体内容无法由一个能指予以给出。概念整体只能被“拆”成一个个不可再分的最小意义内容,才能由语词分别给出。
碎片化的结果即是这些最小意义内容的抽象表征。一个语词给不出概念的全部意义,但它必须给出一个最小的意义内容,即对概念内容之一碎片的抽象。所指之所以是所指,因为它具有意义内容。既然所指不是概念整体,而是概念整体碎片化之后的一个最小意义内容,那么符号就是“音响形象”是与一个“最小意义内容”的不可分组合。须说明的是,所有语词的结构都符合这一要求,无论是指称概念的语词或是描述属性、功能和关系等的语词都只能给出一个最小意义。鉴于本文的主题,这里只讨论代表概念的语词。其余语词的语义讨论可以类推。
那么,代表概念的“最小意义内容”是什么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可以给出一个参考。对于说话人,语词“马”的使用并没有、也不能给出马概念的完整内容,但“马”的使用必须也只能是其脑中马概念表征激活的结果;而在舍去被激活的概念的众多方面内容后,说话人使用“马”语词表达的只是抽象的马形意义,是其所在的语言社区约定来用“马”命名的最纯粹而基本(即最小)的马意义。马概念包含的其他意义均可舍去,因为他们不能必然地在听话人脑中激活同样的概念意义。例如,“驼重的动物、战友、家畜”等马概念可能有的意义内容都不能必然地在听话人脑中激活其关于马的概念,能够做到激活马概念的只能是马形这一最小意义内容(马形不可能是其他事物之形)。马形不是随机选择的概念碎片,而是一切关于马的陈述、判断和推论等思想及其表达所必然涉及,却不包含任何此意义之外的属性描述(颜色、大小、功能、类属、甚至本质属性等)的意义。这一最小的马意义成为语词“马”的语义内容,除将马概念区别于其它概念外,并不负责给出任何其他的关于马的知识信念。这正是让公孙龙与钱冠连的命题看似对立、实则通约的原因:公孙龙的马形,即马的最小意义的抽象表征作为所指,与能指“马”结合成为命名马的语言符号。至于马是什么、有什么、做什么,则应如钱冠连所论,由谓词来给出吧。
与之相应,听话人的理解是一个去碎片化过程;即,听话人接收到“马”的音(符)之后,其头脑中关于马的概念意义得到激活;这一激活并不只是马形,而是听话人具有的关于马的知识信念。按语义整体论,说话人具有的概念与听话人的概念不一定甚至不可能等同,但是“马”激活的是马概念意义,而不是其他概念的意义。虽然说话人与听话人关于马的知识信念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很大,例如说话人头脑中表征的可能是他自己饲养的马,或者军马或者其它什么马,而听话人可能只见过徐悲鸿画的马,但是说话人用“马”这个语词表达的意义却是社会约定的马概念的最纯粹而基本的马形,而不是其它任何概念之形,同时在听话人脑中激活的也是马概念的意义,而不是关于狗或笔等的概念及相关信念。语词、由语词组成的句子的语言交际功能在于激活听话人关于对象、属性、功能、关系等相关信念,而不是直接负责把说话人掌握的信息内容一揽子传递给听话人。
本文这个认识不仅可以说明人际语言沟通是可能的,还能说明为什么误解同样也是可能的。语言表达式肯定具有最小的语义内容,这是语言之为语言的本质属性,也正是这个属性使得一个语言社区关于语词意义把握、理解具有通约性,从而保证人们能够成功使用语言交流。即便有误解,人际沟通仍然是可能的,其方式仍然是通过语言而建立意义把握、理解的通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