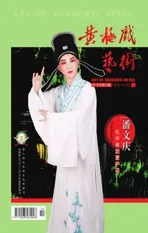严凤英、王少舫的过人之处
2019-11-22王秋贵
□ 王秋贵
从清代至民国,黄梅戏在皖江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在凄风苦雨中顽强地成长壮大,在艰难的生存竞争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中,锤炼并涌现出风格多样的民间艺术明星。
到了新中国,社会安定,政策扶持,体制保障,机制激励,如春风化雨般催发百花争艳,终于众星捧月般簇拥出两位艺术大师——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与王少舫。
两位大师的生平经历、艺术成就、演唱风格与特色等等,业内业外的评议,亲人同事的回忆,专家学者的研究,音频视频资料,论文专著作品,都相当丰富而翔实,毋须重复。这里,只想探讨一下,他们之所以成为公认的艺术大师,有什么过人之处。
先天条件与禀赋自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又是不可言状也无法探讨的。所谓“过人之处”,也并非他二人独有,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见有别的人能像他俩那样做到极致,能像他俩那样为业内业外普遍公认而毫无异议。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什么独门秘籍,只是比常人更勤奋,更用心,做得更加优秀,更加令人赞赏和信服。
一 、博采好学,善于融通。
慕新奇,好声色,是人类的本能。但许多人之慕新奇却停留于欣赏;不少人好声色而沉湎于享受。能从临渊羡鱼转为退而结网,把欣赏与享受化作学习动力,把美声美色变成自己的艺术才干,进而收获创造能力,就可望成为优秀的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属于后者。
王少舫出身梨园世家,9岁拜师学京剧。11岁在师母家当保姆,住上海。他把好奇心转为好学行动:听到街头巷尾各种叫卖声,里弄流行的民歌小调,就跟着学会了。后来,随师兄们到浙江杭、嘉、湖搭水路班子,看过扬剧、苏滩、沪剧、文明戏、滑稽戏、京韵大鼓等等,他还是边听边看边学。13岁(1933年)随班到安庆演出,住在南阳旅馆,听到一位洗衣大姐一边干活一边哼唱,他觉得好听,就上前搭话,知道唱的是黄梅调《苦媳妇自叹》,也就一字一句地跟唱学会,还用到京剧《戏迷传》、《拾黄金》等小戏里,居然还很受欢迎,就平添了融汇的信心。街头叫卖、里弄小调、多种地方戏和曲艺,都收入了他的艺术素材库,而《苦媳妇自叹》则成为他投入黄梅戏队伍的导引曲。
严凤英五六岁就跟着京剧票友父亲的京胡咿咿呀呀地学唱。七八岁时全家回到老家罗岭,她和小伙伴们一起挖野菜,打猪草,扒茅柴,放牛,学会了许多山歌、茶歌、田歌,很快就成为娃娃们对歌、赛歌的领头羊。12岁那年,偶然听到镇上白铁铺里传出歌唱声,原来是严云高在教几个男孩唱黄梅戏,她就偷偷地跟着学唱,后来干脆死缠烂打,硬是逼着严云高收她为徒了。而这一切都是瞒着家长的。儿时小姐妹们练弹舌发声不过是闹着玩的游戏,她后来演《蓝桥汲水》,就把[汲水调]“哆儿唻,唆儿唻”的“儿”用弹舌音唱出来,别出心裁,别具一格,别有风味。
1946年遭土豪囚禁,逃出虎口后流落江南,经池州到大通、芜湖、南京,她搭过黄梅戏班,也搭过京剧班,也曾街头卖唱,也曾舞厅唱流行歌,往日随处留意所得,都成了困窘中糊口的本钱。1950年在南京甘家大院几个月,她又刻意学京剧,学昆曲。后来又学庐剧、越剧、评剧、吕剧、川剧等等,有很多被她化入黄梅戏的声腔和身段。
二、勇于创新,持守本色。
继承与创新是个老话题,也是个永久性课题。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事物发展和生命力旺盛的关键所在。然而,创新不是重起炉灶、另搞一套,继承也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如同人体之吃喝拉撒、吐故纳新可形成造血功能,而输血则必须认准血型。艺术生命的存续与发展也是这样。严凤英、王少舫则是黄梅戏界正确对待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典范。
王少舫由京剧转型,他演唱的吐字行韵都是京剧功底,而京剧的韵白又是继承徽调,正是以安庆官话为基础的。但这还不够,他13岁就接触黄梅戏,18岁又与黄梅戏艺人同台,还参与黄梅戏演出。这仍然不够,30岁正式加盟后又努力向黄梅戏艺人学习,演《夫妻观灯》、《补背褡》,讲“小白”就是地道的安庆方言,唱花腔就是黄梅戏本色了。
王少舫由外入内,带着京剧扬剧等戏曲、苏沪民歌与曲艺等宝贝,纳投名状似的进入黄梅戏。但一旦进入,就得放下装满宝贝的包袱,先把自己化为黄梅戏人,把安庆话黄梅调化为自己的本色,然后再打开包袱,根据角色特征选取需要而适用的宝贝,如用京剧花脸或老生的演唱方法和共鸣位置,来唱黄梅戏。这才唱出了特色鲜明的黄梅调,既别具风采,又契合黄梅戏本色。
1938年,王少舫被同仁和观众戏称为“京托子”,那是他初唱黄梅戏不适应“三打七唱”的无奈之举。到1950年,他已经有多年演唱黄梅戏的经验,具备黄梅戏本色了,这才动了改造“三打七唱”的念头,于是鼓动琴师王文治和鼓师饶广胜,三人联手,王文治编曲,王少舫试唱,饶广胜以鼓板应节,加上其他演员配合实验,经过两年多数百次实践,终于创造出一套黄梅戏弦乐[过门]。对于王少舫来说,这是由外入内,先入后出,在把握本色基础上的创新。从此,黄梅戏在声腔特色音(女腔与男腔之外,又有了自己的弦乐[过门]特色音:
严凤英是道道地地的安庆人,她的路子与王少舫正相反,是从内向外,如佛道化缘,走出去广采博收,吃进来咀嚼消化,使之成为自己体内的营养。“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是因为佛性在济公心里扎了根。对于严凤英来说,安庆话、黄梅调就是她的本色,就是她的基因,所以,京、评、豫、越、川,无论什么外来音乐,被她学进去就成了严凤英的素材,经她唱出口就是安庆黄梅调。
1952年秋,王兆乾为《柳树井》作曲,其中一段“一人只有一条命”,用传统男[平词]宫调式写女腔,旋律还带北方歌剧味,他怕被误认为西洋大调,有点洋气,就试唱一遍,让严凤英评判,再定取舍。严凤英听了却自信地说:“我一唱,准有黄梅调的味儿,你不用担心。”当然,她学唱时,偶尔会“冒出来很有特色的小花音、装饰音或者下滑音”,有的还会不自觉地顺着情感而发挥,改变了原谱旋律。王兆乾也就按照她唱的修改了曲谱。(见《安庆文史资料·安庆徽剧黄梅戏史料专辑》下册<总第二十二辑>第136-137页)所以王兆乾自己也说,这出戏的作曲实际上是两人共同完成的。
黄梅戏原来没有[导板],在重要的核心唱段需要加强情感表达时,往往用[叫头]加[哭板]以吸引听众,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如前举曲50《白扇记·当坊会》黄氏唱“左牵男右牵女”,就是这样。1951年,严凤英在移植京剧《玉堂春》中饰苏三(即玉堂春),《三堂会审》唱“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京剧这一句原是[西皮导板],可是黄梅戏声腔没有[导板],只能唱[平词起板],但这就显得平淡而没有爆发力。严凤英别出心裁,把这一句用男[平词迈腔]的上半句与女[平词迈腔]的下半句糅合在一起,构成了新的腔句,同时,又把[平词]的“一板三眼”改作自由节奏的散板演唱——
男[平词迈腔]: 4/4
由此,黄梅戏的“导板”诞生了。而这个“导板”,只是借鉴了京剧[导板]的节拍板式和情感激发功能,旋律则完全是黄梅戏[迈腔]的重组式革新,既新鲜别致,又是地道的黄梅戏本色。(参阅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编《严凤英、王少舫的艺术历程》第32-36页。)
这个新板式腔句很快就推广开来,男腔、女腔普遍应用,如《天仙配·路遇》董永唱的“含悲忍泪往前走”,《女驸马·洞房》冯素珍唱的“我本闺中一钗裙”等等。
这种创新,不敢说没有“天分”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它乃是在地方声腔本色已成为演唱者本能的前提下,为追求情感激发效应而大胆创新的结果。
三 、 深入角色,走心用情。
戏曲表演的根本任务是刻画人物,展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所谓“装龙象龙,装虎象虎”,要装得像,仅靠衣着、身段、嗓音等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些都是表象。关键还在于体现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面对不同对象、不同情境时的心理活动,在交流与冲突中的必然反应和反应的方式方法。严凤英、王少舫就是努力走进角色内心的优秀演员。
1980年6月,王少舫对安徽省艺术学校应届毕业生谈自己扮演《罗帕记》中王科举的体会。首先是给角色身份定位:“维护封建礼教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然后还要对人物在具体时间、场合、情况、环境之下的心理活动作具体分析。如,在赴京赶考途中宿店时,听说妻子陈赛金与仆人姜雄有奸情,第一反应是“奇耻大辱”,表现为气急败坏,立刻连夜返回。返回途中一段唱念,环境是黑夜、寒风、道路崎岖。心理活动是由羞、急、气转为疑、信相杂,爱、恨交加。“舞蹈身段不太多,但是要表达内在的东西却很多。要脸上有、身上有、嘴里还要唱着”,“人物内在的情感线不要断”。
后来,王科举明白了妻子是被诬陷的,可自己已经把事情做绝了,妻子被他休弃,又被娘家赶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后悔、自责,想到妻子的种种好处,思念不已,就画了肖像,以寄情思。这时有一段唱:“一腔忧恨难排解,挂起画轴对我贤妻诉忧愁。”若仅从字面上理解,很可能把“诉忧愁”作为主题,唱得很悲催,但王少舫不是这样,他对角色此刻心理的判断是:
王科举这个人呢,还是在维护封建礼教。他宁可陈赛金死了,纪念她,想她,是我的爱妻,但不要流落在人世上。倘若再嫁了人怎么办?倘若做了奴婢侍候人又怎么办?你可是一个大家闺秀呀!……他还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维护封建礼教的卫道士。
——骨子里还是爱自己,好面子,慕虚荣,是力图维护妻子“尚书之女、举人之妻”的封建节女形象,其实还是维护自己的举人形象。这个判断与最后两句唱词完全契合:“愿亡妻保佑我功名就,拿姜雄报家仇,请皇封造牌楼,节女英名万古留。” (参阅王少舫《谈<罗帕记>中的人物塑造》,见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编《严凤英、王少舫的艺术历程》第162-169页。)王少舫对这个角色的分析,真可谓入木三分。
1956年第3期《中国电影》载严凤英《我演七仙女》一文,她总结自己塑造人物的经验:
我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拿到一个戏,要搞清楚它说的是个什么故事,我扮的这个角色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台去干什么。
她给七仙女的角色定位是:
七仙女是个神仙。按理也要从神仙的角度给她来分析一番、设计一番。神仙我没见过,也没法见到,但是我可以把她按照“人”的思想情况来处理的。
我想,她敢从天上跑到地上,又敢当面向一个陌生的男子主动提出婚姻大事,并且能想到一些巧妙的办法打动董永的心,难住刁恶的傅员外……那么,她一定是既大胆又聪明、既热情又能干的姑娘。
演《路遇》中的七仙女,严凤英这样分析:“我要大胆地向董永吐露真情,要抓住机会,不然他要走了”。“在这种心情下,我发急地干脆瞪着眼对他唱:‘我愿与你——’可是哪能真像老年人骂的‘不知羞耻’那样?(所以)到了唱‘配成婚’时,我还是羞得低下头来。”她对这场戏的整体把握也相当精准:“这一段戏还是以神仙假装村姑的身份演的,是‘戏中戏’。我是神仙,又是村姑,我要把这两种身份都演出来,把这场戏演像。何况我是真心爱着董永呢。”
《分别》的前半场喜,后半场悲,形成强烈对比。刚刚脱离苦海又身怀有喜,满心憧憬未来幸福,突然面临生离死别,此时,严凤英进入角色已到了身不由己,无力自拔的地步了:
这颗心,实在已紧紧地系在他身上了,离开他,真得用刀把这颗心割下来。没有了董永我怎么活得了!每逢演到这里,我总止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卸完妆,还止不住热泪如泉。明知是演戏,就是从戏里出不来。我自己劝自己:‘这是演戏啊!’但总是不行,老怕他会遇到什么不幸,老怕他离开我。
严凤英、王少舫就是这样深入角色,走心用情。分析角色深入骨髓,进入角色忘我动真情。
有的戏曲家把戏曲的“虚拟”原则强调得过分,认为戏曲表演悲剧不能真哭,要哭出美来。过分强调“虚拟美”的负面效果是,有的演员哭成了有节奏有韵律的干哭,笑也变成了中规中矩的假笑。他们忽略了美与真的紧密联系。
梅兰芳对严凤英的赞赏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严凤英的表演和唱腔,贵在有真实的感情。她的唱腔、眼神、身段、脸上的表情,举手抬步,一举一动,一声一腔,充满人物的真实感情。正是因为有情,才能感人,才能抓住观众。她表演悲痛时,自己流泪,观众也流泪;表演快乐时,自己喜气洋洋,观众也跟着欢乐。一个演员,如果只知在舞台上做戏,干巴巴地表演和唱,是抓不住观众的;反之,像严凤英这样的演员,既有基本功,又有充满的激情,演任何一个角色,既能出戏,又能出情,才能算上一个受观众欢迎的演员。(见《严凤英的艺术人生》第43页。)
四 体验生活,提炼艺术。
艺术来自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话人人都懂。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人人都生活在人群之中,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别人怎样生活。但真正留心体察,记住体验,并积累成艺术素材,提炼成艺术表现,就未必人人能做得好。严凤英和王少舫正是那种常留心,能记住,重积累又善于提炼生活的表演艺术家。
王少舫阅历丰富,从小随父母、师傅、师兄们跑码头,南京、上海等大都市,芜湖、安庆等小城市,他都跑过,也唱过堂会,登过乡村草台,1938年还被日本鬼子抓去做过苦力。见过士、农、工、商、官各种各样的人物,他都留心观察,记在心里,存为自己的艺术素材。他说:“塑造这样一个人物,那就必须在生活当中去找许多许多的依据。没有依据,这个人物在舞台上就站不起来。”(《严凤英王少舫的艺术历程》第163页。)他自述扮演《罗帕记》的王科举、《女驸马》的刘文举等角色分析,就是长期观察、认知和积累生活的成果。
在从京剧走向黄梅戏的过程中,他又得到一个新的体会:“觉得学习黄梅戏,就是学习生活。黄梅戏的味道,要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找,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中去捕捉各种人的变化。” (《严凤英王少舫的艺术历程》第370页。)惟其如此,他演《夫妻观灯》的王小六、《补背褡》的干哥哥、《天仙配》的董永,这三个角色,一个乐观俏皮,一个清纯机敏,一个老实憨厚,既个性分明,又都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声口、农民形象,让你不能不佩服。
严凤英比王少舫小十岁,又只活了38岁,但她的阅历甚至比王少舫还丰富。在旧社会,除了王少舫见过的以外,她跟流氓、恶霸、土豪都打过交道,有着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而这种痛苦的记忆,并非只成为她的精神负担,同时也成为她磨练意志的砺石,成了她艺术创造的生活素材:她身为坤旦,却演过《戏牡丹》里狂傲自负又带流气的吕洞宾(老生),还演过《瞧相》里调戏妇女的花花公子(小丑),而且都演得活灵活现,让人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参阅《严凤英的艺术人生》第207-209页。)这样的能耐,不仅来自“百家闹”的多行当基本功训练,更来自观察、分析、认知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积累。
至于她的本行,花旦、青衣角色的创造,她就有了更多的体验和积累。在《我演七仙女》一文中,她自述:
我要演得像村姑,并且要演出这个村姑是热情、真诚地爱着董永的。
小时候,我是在家里放牛的,我有很多“村姑”的姊妹,也可以说我自己就是个“村姑”。提起农村生活,我马上想起小时候我调皮地跟放牛娃在山坡上打架的情景。对她们的生活还是比较熟悉的。
演《打猪草》的陶金花,我主要是抓住一个天真活泼的农村小姑娘。演《砂子岗》的杨四伢,主要是抓住一个挨打受气的苦媳妇。
1952年,她22岁,在《打猪草》中饰陶金花,令人忘记了台上的演员是个成年妇女。《柳树井》中饰招娣,在与王兆乾一起练唱时,她“唱着唱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噙着泪说:“我就是个‘苦媳妇’啊……”(《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第137页)她自然而然地调动起儿时的记忆,把自己化为角色了。
这样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提炼,仅用“好记性”和“聪明灵气”是解释不了的,随时留意,用心体察,充分积累,把这些“笨功夫”化作习惯甚至本能,才是积累生活、提炼艺术的真谛。
很多人说严凤英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那眼睛之所以会说话,那是因为她心里有话,才能用眼睛传递出来。很多人说王少舫“眼睛传神”,那是因为他心中有神,才能从眼里传出神情。这种心里的话和心中之神,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以学习的态度观察体验生活,以广博的胸襟吸纳多种艺术元素,并经充分积累才可以获取到的。
学习的态度、执著的精神、不懈地追求,才是他们成功的“秘诀”。掌握了这个“秘诀”,有几年、十几年的艺术生命,也足以让他们成为响当当的艺术大家。缺失这个“秘诀”,就只有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撞大运——指望名人提携?人家一松手,你就会像“猪大肠”似的稀里哗啦瘫下地。指望大腕捧场?人家一翻脸,你就两手空空一文不名。
世上事,求人不如求自己,投机取巧不如熟能生巧。熟之所以能生巧,是靠下笨功夫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