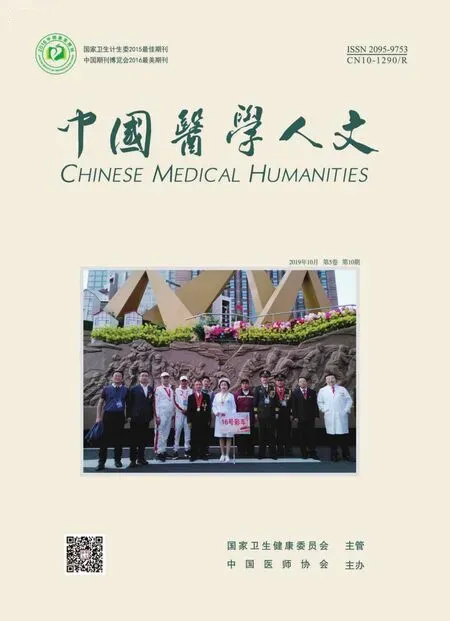我国医事法的人文回归与展望
2019-11-21张玉鹏
文/张玉鹏
70 年来,我国医事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半人文状态不断回归人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路走来,我国医事法不畏艰难,在反思中砥砺前行。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医事法不忘初心;从今天到明天,医事法必将在人文的陪伴下迈向新的征程!
不忘初心,医事法逐渐回归人文
医学病了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医院环境、医疗器械和药品供应等物质条件明显进步,缺医少药的现象逐渐改善,与此同时,医学人文精神却在退步。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医疗服务逐渐倾向市场化,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日渐凸显,医患关系紧张程度不断加剧。医生只见疾病不见患者,诊疗过程中的浮躁情绪越来越明显,与患者的沟通解释工作不到位、无视患者的知情与同意,甚至出现疑难杂症往外推、发烧感冒滥用药,有病慢慢医、无病也吃药的现象。患者动辄认为医生多开药、乱开药、过度医疗以骗取钱财,更有甚者,因不满于医生的诊疗,发动医闹、动手伤医,给医疗行业造成恶劣影响。医患之间宛如天敌,彼此的信任度严重降低。残酷的医疗现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医生和患者究竟怎么了?我们的医学本身难道也“病”了吗?
病在何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更多的是非常和谐的医患关系。战国的扁鹊,汉朝的张仲景,隋唐的孙思邈,明朝的李时珍……他们都是全科医生,内外妇儿样样精通;诊断治疗、处方煎药,悉数躬身为之;做临床、传弟子、著医书,可谓是医教研结合。此外,古代医药先贤时刻坚守“医乃仁术”的价值准则,始终秉持“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的大医精诚之精神。无论是全能型大医还是崇高的医德医风,无不散发出浓厚的人文气息。
反观我国现代医学,却是如下一番景象:
一是学科分工日益细化,导致医生更加追求治“人的病”而不是治“病的人”。建国后,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发展日渐加速,分科越来越细甚至逐渐剥离开来。完整的医学学科被专业化的同时也被碎片化,每个医师只关注自己负责的那一个或几个病种,医学分工的对象脱离开了人本身。这使得医师很难再对病人产生深厚的关爱之情。
二是现代医疗服务与世俗紧密联系。当医疗服务与商业、经济挂钩,医疗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一种价格体现,处方开药更多的是为医院收入考虑……医学变得不再纯粹和神圣,医患之间更缺少了人文交流。“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世俗因素对医学人文精神造成严重冲击。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曾说:对“物”理解越深入,距离“心”就越远!现代医学的种种“症状”都指向一个“病症”:医学人文精神的丧失。
开具处方
从199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到2002 年底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而这场改革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就是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重构。面对学科分工、科技、经济等因素对医患关系、医学人文精神造成的冲击,如何让医学重新回归人文的定力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医患双方交流不畅、信任缺失,我们就搭建沟通医患的桥梁,打造绑定医患关系的“法锁”。于是,社会契约逐渐浮出水面,为帮助医生抵制世俗因素的诱惑,医学需要有形的规范——法律。就这样,医事法便肩负起拯救医学之“病”的艰巨使命。
第一疗程效果:医学与法学平行发展——半人文状态
医事法学术研究蓬勃发展
医事法研究队伍逐渐发展壮大。1989 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法学专业学组,编写出版了一批医事法教材和专著,如冯建妹编著的《现代医学与法律研究》(1994)、吴崇其、达庆东主编的《卫生法学》(1999)、龚赛红编著的《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2001)、郭自力编著的《生物医学的法律与伦理问题》(2002) 等。许多医学院校相继开设了医药卫生法学课程,研究医事法的学者增多。1993 年9 月4 日,中国卫生法学会成立,中国卫生法学会现有近千名会员,我国逐渐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卫生法学研究队伍。
医事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中国法学会先后召开了多次医事法理论研讨会和有关专题研讨会,对现代医学技术突破引起的关涉医学人文关怀和人类尊严的法律问题,诸如安乐死、生殖技术、生育限制和控制等问题进行研讨。此外,我国医事法团体还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原卫生部与WHO 合作,定期举办卫生法学研讨会,借鉴国外有价值的卫生立法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医事法的发展。
医事法立法进程加快
医学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党的十五大明确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为医事法立法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等与医事法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修订和完善,我国的医药卫生工作逐渐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
医学法律的人文色彩逐渐凸显。是否蕴含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文思想是衡量医学法律质量的重要尺度。在以李丽云悲剧为代表的事件的推动下,我国的医事法在注重数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法律的质量。从国务院1994 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到199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执业医师法》,我国患者自主决定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从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到2010 年的《侵权责任法》,我国患者自主决定权的代理制度从“患者家属”时代演进到了“患者近亲属”时代。医事法的发展使得患者逐渐从“家父主义”中解放出来,“患者中心主义”逐渐确立,医学人文精神逐渐回归。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更加公正
随着医学法律的完善,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变化也反映出医事法向人文的回归。从《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到2017 年12 月14 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从举证责任倒置到“谁主张,谁举证”。对于医疗机构的过失和因果关系要件,从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到由患者承担举证责任,并且不强制患者承担举证责任。患者可以依法提出医疗损害的鉴定申请,通过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确定医疗机构一方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举证责任的缓和,能更好地保护好患者的权利,有利于实现诉讼结果的公平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医事法向人文的回归。

没有硝烟的战场 摄影/杨 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医患法律意识逐渐增强
随着法学这“一剂猛药”注入医学,医疗机构、医生、患者法律意识显著增强。医生因忌惮于法律这一约束机制,而重新关注患者。患者也因有了法律的保护,在就医过程中变得更加安心。尽管在法学的引导下,医学逐步回归人文,但是“第一疗程的施治”,也给医学带来了一些“不良反应”。现有的医学法律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了医患双方保护自己的“武器”。医生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忙于填写病历资料等基本文书之外的各种材料,以随时保留证据,以备应对患者的“责难”甚至是起诉,本来就已经忙碌的工作之外又增负担。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不专注于依从医生诊疗疾病,而是随时准备录音录像、投诉医生。
反思处方
这一阶段,我国医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人文,但仅是治标,未能治本。究其原因在于,作为一门复合型学科,医事法虽然交叉了医学、法学这两门学科,但是交叉融合程度依旧不够,仅仅把法学作为医学回归人文的最后保障手段,未能抓住医学、法学在本质上的共通性——人的病,需要医学来治;社会的病,需要法学来治,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医学、法学最终都是治人,医事法作为交叉学科,其初心更是治人。医事法应该不忘初心,继续在“莫贵于人”的人本思想的指引下,深度融合发展,致力于健康中国建设。
再开处方
从2016 年8 月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到2017 年8 月全国卫生计生系统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保护医务人员安全,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广大医务人员要为人民服务,钻研医术,弘扬医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提供最好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两次会议精神无不体现出人民尊医生、医生爱人民的人文情怀。2018 年,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培养跨学科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促进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由此可见,推进医学、法学深度融合发展,重塑医事法人文精神成为第二次治疗的处方。
第二疗程效果:医事法融合发展——渐趋人文状态
立法更有人文高度
以法律助推人文医学的复兴。2017 年7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这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综合性法律,标志着祖国传统医学——中医药事业进入了依法治理和发展的新时期,这在我国医事法人文回归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其他医学法律的约束与规制,这部法律更多的鼓励与支持。如前所述,祖国传统医学的医道、医理都蕴含着深厚的人本思想,对中医药发展的大力支持无疑体现了我国医学向人文的有力回归。
以立法巩固医学人文成果,继往开来。2018 年10 月1 日,《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条例》及时将近年来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不仅平衡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人民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主渠道作用,更强调诊疗活动应以患者为中心,畅通医患沟通渠道,严把医疗质量安全关,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纠纷。《条例》中关口前移、“治未病”的思想无疑对医事法的人文回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医药领域其他法律的修订和完善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医事法的人文回归。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作为药品管理工作的使命,对“药神”事件给予符合人情的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加紧制定,目前三审稿已提交审议。作为医药卫生领域的一部专门法律,该部法律牢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不断“扩容”,致力于实现“大健康”。综上可见,我国的医事法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初心,不断回归到对人本身的深切关怀。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更加人文
从最初的对簿公堂到和平调解,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向人文转归。相较于诉讼激烈的对抗性,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更加人性化。一方面,作为一种相对柔性的方式,调解有利于减少医患之间的对抗,促进医患和谐。另一方面,调解的成本更低、专业性较强、效率更高,有利于及时还医院以宁静、还医患以公正、还社会以和谐。截止到2013 年,全国各省市就已纷纷出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规范性文件;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418个、人民调解工作室1029 个,共有人民调解员22802 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基本覆盖了地市以上行政区域,化解医疗纠纷成功率在86%以上。诸多进步让医事法的实践走上人文的快车道。
院内制度彰显人文
近年来,医疗机构对医学人文建设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医院和科室自觉践行医学人文精神,将医事法的外在约束转化为具体的医院人文建设管理措施,从事后处理纠纷转移到事前防范风险,增强医疗机构的人文关怀制度化建设。一是彰显医德仁心,通过院内制度约束医生的行为。在医患关系中,提倡关爱生命,拥有同理心;通过较好的沟通,保障患者利益和多方面的人性需求,重塑医德医风。二是保障患者安全。18 项医疗核心制度不断修改优化,医院伦理委员会建立并完善,“平安医院”各项工作保障医疗秩序平稳有序。三是保护患者权利。医院信息化时代尤其注重采取技术手段和制度手段,保护患者的基本医疗权、知情同意权、医疗选择权、隐私权等权利。
成效显著
经过一番苦口良药,之前丧失的医学人文精神逐渐复归原位,医学逐渐恢复往日的“精气神”。从2013 年到2017 年,我国医疗纠纷数量实现了五年小幅递减。不仅纠纷逐渐减少,医患关系还变得更加亲密和谐。近年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通过创建“心音坊”“心语墙”和“心空间”,用“三心联动”为患者打开希望之门,赢得患者及其家属的支持和好评。2016 年,为感谢华山医生的及时救治和十几年如一日的细致看病,上海高龄老夫妻卖掉一套房,向罗心平教授的团队捐赠100 万元研究经费。华山医院不忘医者初心,用爱赢得了医患同心。2019 年医师节前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收到了近3000条患者朋友的留言,他们在讲述自己就医经历的同时,表达着对北医三院医务人员的信任、感激和祝福。
医事法前景展望:道阻且长,人文陪伴
学科建设应继续向纵深迈进
进入21 世纪以来,作为医学人文学科中的一个专业,我国的医事法学科取得了很大发展,许多高等院校特别是医学院校都设立了医事法专业。但是,不可否认,目前医事法的学术资源可及性不强,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学科评价不高,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较低,依旧处于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要想长远发展依旧面临很多困难。因此,医事法的研究队伍要持长远的眼光、以强烈的使命感,怀大医精诚之心,秉公平正义之志,医法兼修,在理论与实践上做更深入的研究,让医法不断融合,回归人文,造福天下。
引领医事法在更宽广的道路上拥抱人文
尽管我国的医学法律在数量、质量以及人文的回归上都有较大进步,但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依旧不免捉襟见肘。器官假捐案带来的困惑、互联网+医疗领域法律的空白、人工智能医疗等对人性尊严和自主权的挑战、基因编辑对医学伦理法的追问……诸多问题不仅对医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迫使我们对医学本身、人本身、人类的未来做出更深刻的思考。而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始终坚守人文初心,如此,医事法才能开辟新的道路,向着更广阔的天地不断迈进!
结 语
赞往昔,我们精于专业,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开拓医法奋勇创新。看今朝,医法助力,医学人文偕行,彰显人性之光辉,映照生命之神圣。望明日,我们挥洒热血,饮医法之朝露,汲人文之营养,继往开来,让仁(人)心仁(人)术共铸医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