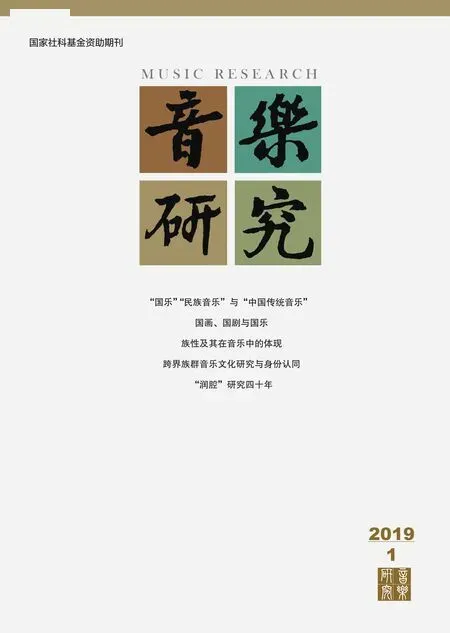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
——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
2019-11-21杨民康
文◎杨民康
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和音乐与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已经在学界酝酿了很长时间,但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的学术话题。如今,两个学术话题在自身范围内都已经有了不少初步的课题和成果积累,并且进入到必须深化学术议题和展开进一步的学科“跨界”研究新阶段。而将两个学术话题结合起来讨论,如今也水到渠成,成为借他山之石,以微视和浓描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必然之举。本文将结合笔者近年来在云南西双版纳与境外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和课题研究的实例,对之进行延伸和展衍性质的讨论。
一、从社会分层角度看音乐文化层、文化流与认同网络的关系
(一)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是一张文化身份认同之网
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隶属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体系。有学者提出:“众所周知,社会文化体系好比一盘棋,或一张巨网,在每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个人必然要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遵循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①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37—44页。作为国家、民族社会文化体系的子项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亦呈现为一张文化身份认同之网,并且携带着自己的编码程序和表述方式。一方面,该认同之网上存在着按文化圈、文化层的历史性规律而发展、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同阶段和层次序列,其中的不同认同类型,是自族群和地域内部传承向跨地域、族群、文化传播的方向,前后依序,顺着时针,由小渐大,由点到面,滚雪球般地自然增长,最后形成一张认同阶序之网。比如,由族群认同、区域认同、信仰认同到国族认同,就是一个规模大小不一,文化同质程度有异,带有历史形成和层次区分特征的认同阶序。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文化个体携带着自身的(音乐)文化标识,如同网眼、网点、网点群落(后文简称“网群”)和网线,分布于整个认同之网上面。并且,这些网线、网眼、网点是随着人群的流动,在自然形成的地理环境中线性地漫游和流动,呈不规则状排列和组合的。相应的是,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每一层面、种类的音乐文化及其内文化持有者,都身处于文化层或社会分层阶序之网上的某一个位置,并且按照文化身份认同的规律和目的,由“自我”向“他者”,依上下左右各方关系来认识、调整自己的角色关系。而相应课题的研究者,则有必要通过对自身目的意义的认识和表述过程,将我们的微观、定点个案研究和线索、多点比较研究同该音乐类型及其文化持有者在身份认同之网上的定位和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握好主位认同与客位辨析两方面互补、互渗的关系,以真正达致音乐与身份认同研究的深层意义和学术目的。
(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圈、文化层与身份认同阶序之间的关系
广义的音乐文化圈,兼有理论和实践层面,其对象包括文化圈、文化层、文化丛;从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角度看狭义的音乐文化圈,多与宗教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圈相关。一般情况下,在前者意义上较少涉及文化认同问题,但在关乎后者的研究中,文化身份认同的讨论则必不可少。在以往的多篇论文中,笔者基于长期、持续的观察和研究,曾经提出了在云南与周边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内包含了下述三个基本的文化演生层次的观点。
1.地域性——原生性民间音乐文化层:有关“前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同一条边境两侧呈定居状态的跨界族群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
2.区域性——次生性佛教音乐文化层:因传统的国家政治、人为宗教、经济等横向传播交流影响而形成的跨界族群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
3.整体性——再生性杂糅音乐文化层:指现代——后现代背景下,通过原生、次生文化层与分布、环绕其上、其侧的主(流)文化层——具现代民族国家及其现代政权特征的各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上层因素的并存合力,且受到外来的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互融现象的影响而形成的杂糅音乐文化的研究。②参见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探析: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民族艺术》2014年第1期,第45—51、111页。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以往在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文化圈内外关系脉络中,族群认同居于地域性——原生层次,亦是圈内外诸族群(尤其是部分不信仰三大宗教的族群)内部最早生发的、最根本的文化认同因素。而在相对显性的文化层面上,跨界族群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文化圈相互交织,所生发的信仰认同便居于区域性——次生层次。其中,以南传佛教为代表的信仰认同一直是东南亚不同跨界信仰文化圈内外较具整合性和稳定性的要素之一,起到维系不同地区、族群之间文化交往及情感和谐关系的重要的纽带作用。如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里,居于底层的族群认同和中层的信仰认同、区域认同已经逐渐让位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其他文化认同因素,诸多同音乐与文化认同相关的实际问题也伴随而生,从而为我们的专题性考察和研究创下了较大的空间。从前期的相关研究看,我们较多关注到上述三个基本层的第一、二个层面,尤其是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对于南方和北方地区跨界族群文化中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含音乐文化)所起到的传播、交融作用给予了较大的重视和考察研究。但对第三个层面的研究相对较薄弱。因此,在下文的讨论里,将对涉及该层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
二、从身份认同角度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分层和属性
在当今中国学界,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理论框架里,国家认同可视为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整体文化认同,然后才是各单一民族的民族认同。这个问题或许涉及我们必须进一步从概念到实体去认识和讨论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性质和特征。对此,一种可藉以参考的说法是:“‘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在具体层面是指国家获得其特征(国家是一个活动主体;国家是制度建构和公共权力代表的主体)的过程;在抽象层面,‘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指的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存在、使用和更替的合理化过程。”关于民族,“许多学者认为‘民族’(nation)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构建的,是在政治权力的推动和保障下构建的。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国家就没有民族。③参见严庆《民族、民族国家及其建构》,《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9—14页。可见,在跨界族群音乐的文化认同研究里,“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族群”(ethnic group)“宗教”“区域”等,是涉及基本分析思维和身份认同阶序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民族”与“族群”是两个有必要加以明确区分和加强认识的重要概念。一般认为,“民族”指的是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成员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和领土。它可以是由单一“族群”(ethnic group)构成的,也可以是由多“族群”结合而成的。也有学者指出,在1908年之前,民族的意义跟所谓族群单位几乎是重合的,不过之后则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及独立主权的涵义”——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族群通常是指移民群体和在政治上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少数群体。族群产生于个人和家庭移民,他们往往都希望并入更大的社会,并希望被接受为该社会的完全成员。④同注③。由此而论,目前国境线两侧拥有共同族源的居民人口,其共有的身份认同基础和相应的概念表述,应该是先在于(建构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的“族群”,而非后来才建构产生的“民族”或“国族”。同理,“跨界族群”相比“跨界民族”而言,也是一个更为合适的概念表述。
此外,鉴于研究对象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背景,在跨界族群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上,仅只提及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还远远不够,还有必要提及宗教认同、区域认同与地域认同等不同的认同因素。倘若结合音乐认同网络与不同认同类型之间的关系看,将上述诸项文化认同因素按其社会文化内部关系予以排列和定位,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大小不一(由小到大),文化同质程度有异,带有历史形成过程(由下而上,区分先后)和归属层次区分(由上而下,逐层统属)的认同阶序网络。现以云南西双版纳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的音乐与认同阶序及其层次划分关系为例列表于下:

表1 音乐与认同阶序与层次划分关系图表
根据表1,每一文化层及音乐认同层级均同时向上具有隶属性或依附性,向下具有统领性或管摄性。并且,对外、向上时,通常凸显自身的个性和标识性特征;对内、向下时则强调共性和认同性特征。进一步讲,对外、向上时,重在通过客位的辨析、归并和描写,突出和区分文化(音乐)形态、地(区)域风格的差异性;对内、向下时,重在通过主位意识的观察和归纳,突出和强调文化的同一性及其社会调适作用。举例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民族识别期间,语言学、人类学及音乐学不同学科学者,便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及斯大林的相关论述,为民族识别定下了“四个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的理论基调,都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一齐为辨析、区分、归并和描述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其结果便是通过大家的努力,一方面就此凸显了不同民族文化外部身份标识的差异性特征,另一方面规范了各民族内部文化认同的尺度和标准,并且最终达成了民族内部多数成员之间的一致性认可。可以说,在这项工作中,外部身份标识与内部文化认同乃是一种内外交合,一体两面的关系。这种关系还同样反映在我国各民族的节庆仪式(音乐)之中。比如,在傣族和孟高棉语诸民族的泼水节、彝语支各民族的火把节、瑶族的盘王节等许多民族节日里,如今往往形成了两种(或多种)节期,两套(或多套)程序,同一种音乐舞蹈也往往准备了多套表演曲目,以应付对内(祭祀、自娱)、对外(旅游、展演、公务),向下(族群、村社)、向上(民族、国家)的不同层面需求。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语境下,传统节庆仪式和民间表演艺术都普遍具备了面临不同活动对象和环境要求而必需的潜在适应能力。在不同民族自治区域,上述内外、上下功能作用及适应能力的发挥,皆依其所处级别而有相应的表现。以下简略论述音乐民族志方法适应于文化认同阶序研究的几种基本类型。
三、定点、多点音乐民族志研究与族群、地域文化认同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究其实质,乃是一种聚焦于族群文化层面的研究性课题。对此,可用广义和狭义加以区分。
广义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即指跨地域性(区域性)历史族群的研究,属次生文化层。比如,当我们对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内圈(含云南与周边泰、缅、老、柬、越等陆路国家和地区)和外圈(含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海岛国家)的区分时,便可以看到自古以来孟高棉、壮侗、汉藏和苗瑶等四大历史语言族群便一直居住在整个内圈,其分布状况是:
a.孟高棉语族诸族群,主要居住在国境线两侧,境外如柬埔寨高棉族和缅、泰等国的孟族,境内主要是布朗、德昂和佤等民族,为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最早的世居族群,其分布状况除了在柬埔寨为聚居状态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均为自然铺开,非均匀散布。
b.壮侗语族诸族群,主要居住在国境线两侧,以掸傣族群为主,由内向外,自然铺开,均匀分布。
c.苗瑶语族诸族群,跨国境线分布,由内向外,国内主要分布在中南地区的广西、湖南及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等省,国外则由内向外,呈哑铃状,两头相对密集聚居,中间较为稀疏狭窄。
d.藏缅语族诸族群,西南地区的白、纳西、藏、彝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部分民族(如藏、彝、拉祜、傈僳、景颇等)在境外也有分布。
从此意义上看,笔者曾经做过的一项有关西双版纳景洪傣族(属傣仂支系)与缅甸景栋掸族(属傣艮支系)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因为涉及了同一历史语言族群中两个不同支系(族群)之间的音乐文化关系,便属于相对广义性层面的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课题。⑤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探析:叩问最难询访的近邻——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
而狭义的跨界族群比较研究,则主要涉及现今于同一广义族群内部,按山区、平坝、河流等地理条件自然分布的,较小规模和体量的跨国境地域性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相比而言,笔者在上述课题中,同时也涉及了中国傣族的傣仂支系与缅甸掸族的傣艮支系在周边国家地区跨境分布以及布朗族与居于景栋地区的同源族群傣娄人⑥泰娄人,又称洛人,属孟高棉语族。今天,景栋的这些人被称为“泰娄”,被划归掸族;在清迈称之为“洛”或“拉佤”,在中国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则被认定为布朗族。的关系,便是狭义的地域性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的例子。并且,与文化认同阶序中“民族认同不跨国境”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所提到的广义或狭义的“族群认同”或“族群音乐文化认同”,其历史上与当代时期的分布和传播,都是不受国境所区隔和阻拦的,同时也是诸音乐认同层面中形成时间最早的一种认同层面。
20世纪末叶,通过对中缅边境中方一侧的布朗、傣、佤、德昂、瑶、傈僳等民族不同地区分支的传统仪式音乐所做的较细致的考察和研究,笔者在定点个案的课题研究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同时也认识到,若从跨地域性(区域性)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仅针对跨界族群的国内部分展开考察研究是存在明显问题的。比如,国内的布朗族的三个分支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巴达、西定和布朗山以及临沧市的双江等地;傣族的三个最大分支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和临沧三地;瑶族的两个主要支系盘瑶和蓝靛瑶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两个地区。这些通过民族识别而产生的少数民族,其国内各分支(族群)彼此过去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而各分支自身却由于是跨界族群的原因,其历史上联系最密切的往往是分布在国境线外方一侧的同族群村寨居民。因此,要想真正对之展开跨地域性(区域性)比较研究或多点音乐民族志研究,必须把学术触角展延到境外同族群及有共同信仰生活的其他地区。比如,传统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仂人,目前也有部分居住在泰国、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地区,在与其周边族群(壮侗语族其他族群及布朗族)共享南传佛教信仰(为前述“广义族群”的共同信仰)的同时,还以“祭勐”“祭寨”仪式及相应的自然宗教崇拜作为自己的“亚信仰”,并以其中民间歌手赞哈的演唱活动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和传载方式,共同构成区别于广义族群信仰及大传统(或主文化)层面的,专属于狭义族群和小传统(或亚文化)的另一种音乐与文化认同层面。与赞哈歌手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缅甸掸邦的傣艮人与中国云南省孟连县孟阿乡的傣艮移民中,也同样流传着共有的“森”“拽”等叙事性民歌,如今乃是作为两地傣艮人及孟高棉语族群(如景栋的傣娄人)之间形成族群认同或虽未形成族群认同,但形成文化交融纽带(如缅甸傣艮人、傣娄人与中国布朗族之间)的一张张重要“名片”存世。
四、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与国族音乐文化认同
从跨界族群音乐的角度看,历史形成的跨国界族群(音乐)文化分布以及族群认同,产生并形成了边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境外同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诸多交融性和同质性因素,这类因素同已经包容、滋生了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跨境宗教文化圈因素一样,与主要通过文化建构途径形成的当代国家、民族及其国族文化认同关系之间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些矛盾问题,若像以往那样仅只通过对历史形成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态及其族群属性和族群认同层面加以区分和分析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有必要结合21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发展变迁与文化认同状况,着眼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语境下,因种种社会音乐文化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复杂矛盾状况而导致的各种文化认同问题展开相关研究,才能据此提出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
以云南景洪的傣族与缅甸景栋掸族的比较为例,两地的民族认同,都聚焦于泼水节于一身。不同的是,在景洪一侧,以傣族为主体的泼水节庆祝活动有了国家在场(国家认同)作为支撑,布朗族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希望设立本民族“桑刊节”(为泼水节的别称)的呼吁,由此便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文化建构的意向。而在景栋一侧,这种国家在场(国家认同)的力度大为减弱,乃至其中包含了甚多的族群认同因素。而这个族群认同的因素又与掸族(傣艮人)与傣娄人的长期交往历史纠结在一起,⑦在掸族人乃至东南亚的其他掸傣族群中,一直有认为孟高棉人是这里最早的主人,应该给予特殊尊重的看法。从而出现了每年以傣艮人为主举行泼水节庆祝活动时,必须出现以40位傣娄人通宵击大鼓“守岁”的特殊场景。而在民族设立的问题上,由于缅甸政府一直没有将娄人视为单一民族,而是按“傣”的分类,将之归入后一民族,称为“傣娄”,以致在泼水节活动中,娄人的击鼓守岁,也就习惯性被看做是掸族庆典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西双版纳地区,除了上述为彰显民族文化身份而提出的“桑刊节”呼吁外,由传统民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布朗弹唱”也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作为布朗族的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出现在几乎所有布朗族人出没的社会公众场合,以此彰显出布朗人着力建构自己族群文化标识,以凝聚自身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意愿。⑧参见杨民康《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与此类似的立足于民族区域文化标识及身份建构的思路和做法,还可以举出今天中国南方彝语支民族的火把节、苗族的三月三,北方蒙古族的那达慕、藏族的藏历年等,都有从以往的宗教或民俗节庆泛化为民族节日的倾向。还有,各少数民族的许多传统音乐品种,如今已借助国家或省市级“非遗”评审而成为著名的民族或地方文化品牌。而一些国产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五朵金花》《阿诗玛》《芦笙恋歌》《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则借助于大众媒体传播手段声名远扬,被冠上了“族歌”“省(市)歌”的名衔,既导致种种新的“族性音乐”由此而生,也形塑出一批与“民族”“国家”政治实体相匹相依的族性文化标识。因此,从本文的视角,并结合相关民族学理论来看,上述在民族、国家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产生、形成的诸多音乐文化类型,无论其与传统的联系密切、深厚程度与否,都已经成为带有新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包含国族认同的隐喻、标识和文化认同印记,拥有了与“国家在场”相互匹配、彼此支撑的艺术功能和社会作用,并以此区别于族群层面的象征、隐喻和认同意义的其他艺术产品。
此外,凡是带有国族文化标识与认同特征的节庆仪式音乐艺术产品,其相关展演或展示活动主要是以国境线中方区域为基本界限和范围,并且在具有国家公民及民族成员身份者中间产生、发挥其文化认同效应,并以此拥有了可区别于族群性音乐产品的跨界族群文化标识与认同范围,及其境内外贯通的社会性传承与传播功能。反之亦然,境外于“民族”“国家”层面产生的音乐文化产品,其社会流通及文化认同也一样受制于这个同“国家”“国境”相关的文化规律。所以,在音乐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中,有效地区分出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阶序性关系,明确建立起“民族不跨界、跨界乃族群”的文化意识,不仅可以让我们去正确地认识跨界族群文化的基本性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较准确地去辨识国境两侧不同衍生性乐种、舞种的社会性质、流通范围及其文化变异过程。
五、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圈研究与信仰认同
文化圈研究是来自于人类学的一种比较重要的研究方法,而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文化圈方法的应用往往是与宗教研究及信仰认同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此类研究中,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传统宗教文化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如何处理好信仰认同与国族文化认同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节庆,有许多原本就与传统宗教仪式活动相关。在云南与周边地区,当20世纪中叶以来“宫廷与寺院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结构纷纷遭致解体时,南传佛教节庆仪式及其吟唱活动在境外地区被奇迹般地保留下来,而在境内地区则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在许多年销声匿迹之后,也得以迅速的复活和还原。可以说,南传佛教节庆及其吟诵艺术所包含的文化大传统基因及其所拥有的“跨族群——地域——文化”传播能力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维护和纽带作用。今天,中缅、中老等国境线两侧的节庆仪式活动都可为三类:1.各族群民间节日;2.以泼水节、安居节为代表的佛教节庆;3.以国庆节为主的各种现代国家节庆。它们分别对应于前述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原生、次生、再生三个文化演生层面。其中,南传佛教节庆仪式居于中层,是维系国境两侧南传佛教文化圈各族群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最稳定的纽带之一。
从文化与族群的关系看,三类节庆或三个层次中,原生层次里,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对族群本身有着明显的依附性;次生层次里,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相对具有较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导向性;再生层次里,显性的旅游文化、官方节庆(如定为民族节日的官方泼水节)等因素则对隐性的佛教大传统及政治文化具有依附性。
因此,从文化认同的情况看,在跨界族群文化三层次中,在各人为宗教文化圈里,位于中层的、传统意义上的泼水节、安居节以及北方民族的同类节日,如藏族的祈祷节和雪顿节、维吾尔族的肉孜节(即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以及存在于南方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督教圣诞节等,在文化的自身独立性、自主性及国境两侧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等要素上居于比较显著的地位,在诸对象层次中据有相对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学术性意义。比之而言,处于原生、再生层次的诸文化形态则不同程度体现出孤立性或局部性的认同状况。例如,原生形态中,传统民间音乐较多为纵向传承为主的地域性乐种、乐器;再生形态中,各国的国庆节均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属性和相异的政治文化色彩。此外,像泼水节这样的传统节日被定为民族节日后,也被赋予了国家庆典及国族认同的新的象征意义,并有相异于民间传统节日的较固定的举办时间。像新生的布朗族桑刊节,也是在此意义上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信仰认同的情感因素,往往通过传统节庆及节庆仪式音乐来予以体现。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里比喻的是一种乡土文化情缘或(广义的)族群、地域文化认同情感。在信仰南传佛教的不同国家和广大区域内,来自四面八方信众的类似的情感交流和信仰认同,可以通过《南无经》里的一句十八字巴利语偈言来予以实现。当然,偈言必须配上与不同语言的音调、语调相适应的曲调旋律。在同一族群或相同教派内部,仅凭曲调旋律的一致性,便可以获得很好的沟通效果。而在不同地域来源的信众之间,由于存在着异文化语言引起的沟通障碍和陌生的音调、语调带来的种种心理、审美隔阂,当双方同时使用巴利语(而非梵文)的偈言作为相互沟通的信号符码时,便立即达到了彼此接受和认同的效果。同样,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有多么复杂的民族杂居区域背景,来自任何族群的外来客人,一进教堂,听到赞美诗的吟唱,马上就能够进入彼此认同和乐于交往的情景。应该说,这众多的日常生活事例就充分体现了音乐认同在各种传统人为宗教文化圈内所具有的传播能量和社会效应。此中,除了南传佛教经腔外,诸多的道教、伊斯兰教经腔及少数民族基督教赞美诗,都是一张张亮眼的文化名片,在各族群、民族群众的跨地域性交往中,起到显示自己的外部身份标识和促进彼此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
六、区域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与区域文化认同
21世纪以来,区域音乐研究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其研究过程从当初的音乐色彩区研究、音乐地理学起步,如今已在理论视野和学术空间上有了较大的拓展,成为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和学术层面加以比较、综合、互渗的、包容性较强的学术话题。从此意义上看,笔者多年来在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所提倡和奉行的多种研究方法中,文化圈——文化层分析观念及方法,既与区域音乐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意义范畴有所关联,又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本文在此主要涉及与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相关的两个对象层面:一是传统的跨界族群宗教文化圈(南传佛教、基督教)内部,曾经分布在国境两侧,历史上形成并依托当地族群部落及地方政权存在的、具有可比较研究意义的不同族群音乐文化区域。比如20世纪50年代以前分别存在于西双版纳以傣仂为主体族群的传统音乐文化区和缅甸景栋以傣艮为主体族群的传统音乐文化区,⑨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杨民康《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第46—55页。还有德宏地区以景颇族为主建立的基督教音乐文化区和境外以缅甸克钦邦克钦人为主建立的基督教音乐文化区,⑩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徐天祥《缅甸克钦族基督教音乐的本土化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都是该领域有一定典型区域划分意义的研究对象。二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于当代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区域性音乐文化区和以次级“主文化——亚文化”结构呈现的文化层。其中,尤其让人注目的是一些当代国族文化语境下民族自治区域(音乐)文化体系建构的例子。⑪参见张林《建构的传统——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中央音乐学院2017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苗金海《鄂温克族音乐文化建构与认同——以巴彦呼硕敖包祭祀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9—29页。比起前一类文化区来说,该类文化区因同时显现了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国族认同(在国境两侧,各自的族群认同已经多半分别演化并体现为国族认同关系)与信仰认同等各类认同因素,以致更显现出多层性、立体性、复杂性和对比鲜明性等特点。
七、离散族群音乐与族裔散居身份认同
族裔散居及其身份认同是跨界族群及族群认同的一种变体形式,也是跨界族群区域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由此看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地区,中国少数民族的同族群人员中,有不少是以族裔散居的方式在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分布。从外迁的环境及方式看,鉴于整个西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通是以陆路为主,海路为辅。其中,云南与周边紧邻国家,亦即东南亚内圈诸国的关系,则更多是陆路的特点。云南少数民族的离散族群也是沿着陆路的山地、平坝向境外迁徙和散居。若将此推及整个中国与周边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可以说也是一个共性特点,并且,与西方学者以海路为主要对象及相关方法相比较,这也是显得非常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外,这些离散族群在迁徙和居住方式上存在着点性散居和线性散居的区别。其中的单点性散居族群,可举云南西南部少数民族与现居缅甸景栋的各民族之间关系为例。20世纪50——80年代,景栋以其具有的境外城市地位和条件,曾经作为解放战争之后流缅国民党军队暂住基地而存在,此间还接受了大量外流的各族移民。至数年前笔者访问该地时,在景栋这方圆几十里土地和几十万人口中,就包含了本土各族原住民,来自前述云南沿边各地各族的自然、政治移民以及半个世纪以前迁来的战争移民、军人眷属等不同成分来源。县城内外傣族、汉族及其他族群移民社区鳞次栉比,互邻互市,交错而居;城边街道上,佛寺、教堂、清真寺、道观密密麻麻,传道诵经,声闻数里。从身份认同角度看,每个移民社区、寺观教堂,都是一个带有清晰的社会、政治身份的族群单位,都有自己包括音乐文化(经腔、佛韵、赞美诗等)在内的、鲜明的文化标识和不同的认同诉求。这样强烈、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我们数十年来因偏居中方西南一隅而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的民族(音乐)居处文化观念和认识。⑫参见杨民康《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第46—55页。多点散居的例子,如原居于中国西双版纳的傣族傣仂支系,如今同时以半圆圈状散居在泰国、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他们藉以维护族群认同的一个共同的音乐文化标识,就是都非常重视祭寨、祭勐等传统自然宗教仪式活动及其中赞哈歌手演唱对于凝聚族性情感的重要作用。比之而言,南传佛教仪式及其仪式音乐这样已经泛化至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信仰认同因素,对于境外傣仂人这样的地域性——离散性族群来说,显然由于已经超出了该族群共同体文化归属及认同情感的具体范围的原因,而被归之于认同阶序中较次一级的位置。线性散居的情况,可举瑶族、苗族等,以贵州、广西和湖南等相对靠近内地的区域为主要据点,一方面与境内汉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成密切的交融关系,另一方面则从很久以前便向东南亚地区长途迁徙,最后倚助现代化战争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外力,远徙至欧美和澳洲地区,从而进入迁徙路线最长、历史和文化跨度最大的跨界(境)族群之列。在这类散居族群中,赖以支撑其族群归属情感的一个重要的音乐认同因素,就是通常采用汉字经籍及歌书记载,并在度戒、还盘王愿及各种人生仪礼中演唱的传统瑶(苗)歌。
结 论
从本文关于民族学的讨论里,我们产生的一个结论是,古代四大族群与当代自然族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当代国家、民族与自然族群的身份认同,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而信仰认同、区域认同等则是其中起衔接、沟通作用的,大大小小的桥梁和润滑剂。据此,我们将面临着去着手解决如下几个与之相关的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以藏彝走廊为历史语境,考察和研究在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多民族(或单一族群)原生节庆仪式(如彝族火把节、白族绕三灵)音乐型态向次生型态转型,以及由族群、信仰、区域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过渡的方式及过程。
2.以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为历史语境,考察和研究在当代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节庆仪式及仪式音乐类型怎样由多族群、跨区域宗教音乐与认同(如泼水节仪式音乐和云南洞经音乐)向单一民族、共同区域民族文化标识与认同分化、转型(如泼水节分化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桑刊节、阿昌族浇花水节;洞经音乐分化为多民族分别拥有的音乐文化标识)的方式及过程。
3.以梅山文化、苗疆走廊等为历史语境,考察和研究在当代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节庆仪式及仪式音乐类型怎样由单一族群、区域、信仰认同(瑶族盘王节,苗族苗年节、三月节,景颇族目脑纵歌等)向民族、国家认同转型的方式及过程。
4.考察和研究在当代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传统音乐类型怎样由单一地域、族群乐(歌)种衍变为多地域、族群(支系)民族文化标识(侗族大歌、布朗弹唱),由族群、地域认同上升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式和过程。
5.考察和研究在当代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少数民族题材歌曲怎样由电影、创编作品衍变为民族文化标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五朵金花”“芦笙恋歌”“阿诗玛”“刘三姐”)并产生民族及内外文化认同的方式及过程。
在分别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考察和局部比较研究之后,便能够结合西南各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民族、国家音乐文化认同的凝聚、形成过程问题去进一步展开“跨地域、族群、文化”的整体性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