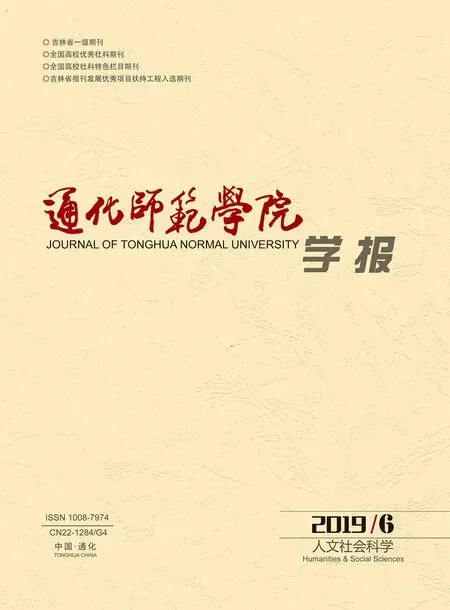汉译佛经个体量词“众”的来源及其历史发展
2019-11-20鞠彩萍
鞠彩萍
一、引言
调查佛经语料,个体量词“众”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于称量大数、约数,数值多为百、千、百万、千万、亿万等,称量对象较丰富,如天人、鬼、神、夜叉、比丘等,本文称之为“众1”;一是用于称量佛、道教徒之类,称量数目多为具体精确的数值,本文称之为“众2”。例如:
(1)《大宝积经》卷六二:“实时毘沙门天王,以无量那由他百千亿众夜叉围遶,譬如壮士屈申臂顷,一念之中从天宫没佛前而现。”(T11,NO.310,P356)
(2)《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二〇:“(邬波难陀)即往诣彼寂静林中,见四十众苾刍缝补破衣极生劳苦。”(T23,NO.1442,P730)
例(1)量词“众1”称量对象为“夜叉”,前面数值为“无量那由他百千亿”。那由他,梵语Nayuta,数目名,相当于亿。例(2)称量对象为“苾刍”,即比丘。量词“众2”前为具体数值“四十”。
研究发现,佛经文献两种量词的来源不同,“众1”沿袭了中土文献量词“众”的用法,“众2”与佛经文献“众”本身语义的发展演变有关。以下分别探讨。
二、个体量词“众1”的来源及其历时发展
(一)个体量词“众1”的来源
调查语料发现,作为个体量词的“众1”早在两汉时期就出现了,叶松华认为,量词“众”在俗家文献中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1],似不确切。“众1”是汉语中产生较早的几个个体量词之一。
众,本义为多。《说文解字·㐺部》:“众,多也。从㐺目众意。”《史记·周本纪》:“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
众,还用作集体名词指人;士兵或军队。《诗·小雅·无羊》:“众维鱼矣。”朱熹集传引或曰:“众,谓人也。”《左传·昭公元年》:“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杜预注:“以兵入逆妇。”又《风俗通义·祀典》:“众者,师也。”
语法化为量词的“众1”跟它的上述语义有关。
先秦两汉时期,“众1”用作集体名词的例句较多:
(1)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商君书》)
(2)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论衡》卷二八《正说篇》八一)
上述例句的“众”皆为名词,指军队或士兵。这个时期的“众”也用在数词之后,构成“数+众”结构:
(3)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论衡》)
(4)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一七)
例句“众”名词语义明显,可以理解为士兵、士卒。例(3)“四十万众”作主语,例(4)“十万众”作兼语,晋鄙为人名。这些“众”虽然是名词,但已经处于“数+量”结构量词的句法位置上,且句子的焦点集中在“众”前面的数目上,为其语法化为量词提供了基本条件。
重要的是先秦两汉文献出现了下列例句:
(5)将军市被死已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战国策》卷二九)
(6)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四〇)
(7)甚者,兴师十余万众。(《汉书》卷七三《列传》第四三)
(8)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后汉书》卷二一《列传》一一)
(9)是时项羽率诸侯兵四十万众,号百万众。(《前汉高祖皇帝纪》卷二)
(10)青、徐之贼,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万众。(《东观汉记》卷十《传》五 按,古代六十骑为一辈。见《六韬·均兵》)
例句(5)~(10)跟例(3)(4)不同之处在于,“数+众”结构前已经有了用作主语的名词“死者、兵、师、辈”等,形成“名+数+众”结构。这与两汉时期较常见的“名+数+量”格式相同。
关于量词的来源,李宇明[2],戴庆厦、蒋颖[3]等学者认为最初来源于反响型量词(Echo Classifiers)。反响型量词,也称拷贝型量词或反身量词,是指数词之后通过重复前面名词全部或部分音节而构成的结构,如:“马三马”“俘人五人”。反响型量词不仅在古汉语中有(如羊五羊;人五人),在汉藏语系的许多语言中有不少用例。
安丰存指出“汉语量词的语法化整体经历了同形回指——回指替代——个体化标记——冠词化的发展历程”[4]。反响型量词所起的作用是同形回指,但反响型量词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持续时间不长,是量词语法化的初始阶段。之后多选择同范畴内部的词语来回指数词之前的名词。分析(5)~(10)例句,“众”与“死者、师、兵”都属于“人”的范畴,在上述句子中有回指替代前面“死者、师、兵”等的作用。从句法结构看,两汉时期常见的是“名+数+量”格式,上述例句的“众”占据了量词的位置,和前面的数词联系紧密;从认知角度看,当人们的焦点集中在“众”前“千、万、百万、千万”等大数目时,“众”原来表“多数”以及表示集体名词“人”的语义相对弱化,“众”发展出概括性更强的语法意义,获得了量词的用法,称量“人”类范畴,这是“众”语法化为量词的最终结果。
朱德熙指出:“名词和跟它相配的个体量词之间有的时候在意义上有某种联系。”[5]48量词“众”的形成与最初表示“多数”以及表示集体名词“人(士兵,师,死者等)”的语义有关,这是“众”语法化为量词的语义来源。也就是说“众”的语义来源影响了量词“众”的称量对象及称量范围:称量对象为人,称量范围为多数。上述“名+数+众”结构中,充当名词的“死者、兵、师”等与“众”范畴相同,语义相类或相近。
我们可以将量词“众1”产生的途径归纳如下:

人;士兵;军队→
试比较下列例句:
(11)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史记》卷九九《列传》三九)
(12)是时汉兵以逾句注,三十余万众,兵已业行。(《汉书》卷四三《列传》一三)
按,《汉书》体例大多模仿《史记》,主要记述西汉230多年的史事人物。两者有一定的时间距离。上述两例句记载的是同一史实,数词“三十余万”和名词“兵”之间,《史记》没有用“众”,《汉书》用了“众”。如果“众”后不加句读,“三十余万众兵已业行”则是成熟的“数+量+名”结构了。由于是孤例,此时量词“众”的成熟结构尚未形成。但结合例(12)语境看,第一小句主语是“汉兵”,第三小句主语是“兵”,第二小句“三十余万众”之“众”视作量词较为妥当。
至此我们认为两汉时期量词“众1”已经形成,与当时另一个体量词“人”有些类似。
学者们已经论证早在先秦时期“人”就具有量词的属性了(王绍新[6]、范崇高[7]等)。“人”与“众1”的区别在于:“众1”多量大数、约数,这与“众1”本身表示多数的语义特征有关,“人”则不受限制。下列相似例句,“众1”都可以用“人”来代替,此类例句较多:
(13)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史记》卷七六《列传》第一六)
(14)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史记》卷九一《列传》第三一)
两汉时期“众”是量词,还体现在,“数+众”结构前可以带有统计功能的副词“凡”:
(15)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汉书》卷九四上《列传》第六四上)
按:数词前用“凡”,带有列举的特点,有较强的统计性,也证实了“众”的量词属性。数词又同表示估量的副词“余”组合,形成“数+余+万+众”的组合格式。
早期汉译佛经量词“众1”沿袭了中土文献的用法,多为“名+数+量”格式,例:
(16)《佛说兴起行经》卷二:“时(佛)在波罗㮈国,与大比丘六万八千众,皆是罗汉。”(T04,NO.197,P170)
以下一句用于“者”字结构:
(17)《佛说兴起行经》卷一:“尔时,第二贾客,五百众者,则今五百罗汉是。”(T04,NO.197,P170)
此时译经多为“比丘众、和合众、优婆塞众”之类的组合,量词“众1”用例较少。
(二)个体量词“众1”的历时发展
以上研究表明,个体量词“众1”在两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从句法结构看,多为“名+数+量”格式,尚未进入成熟阶段。以下探讨个体量词“众1”在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的发展情况。
1.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名+数+量”的格式仍然占优势,中土文献用例如下:
(1)渊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魏书》卷四七《列传》三五)
(2)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裴注《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
也有少量“数+量+名”格式:
(3)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裴注《三国志》卷一八《魏书》一八)
句中“数万众卒”为兼语。“众1”也可以用在双重否定句中,表示强调:
(4)斛律明月不易可当,兵非十万众不可。(《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上一一)
常见“人”“众”前后同义互用的例子,“众”相当于量词“人”:
(5)若停十万众追一人,非上策也。(《北史》卷二八《列传》一六)
这个时期的佛经文献,“名+数+量”的格式也占优势,但“众1”的称量范围比中土文献广泛,可以量“兵、鬼神、民、人民、群臣、国人”等。如:
(6)《普曜经》卷六:“我众兵仗十八亿众,皆共并势。”(T03,NO.186,P520)
(7)《长阿含经》卷一二:“何由乃能见,鬼神七万众?”(T01,NO.1,P79)
(8)《撰集百缘经》卷二:“时彼国王将诸群臣数千万众出城游戏。”(T04,NO.200,P211)
“众”还可以用在特殊判断句中:
(9)《增壹阿含经》卷二二:“尔时王女者,今须摩提女是也;尔时国土人民之类,今八万四千众是。”(T02,NO.125,P665)
佛经文献“数+量+名”格式的例句明显多于中土文献,所量名词也比较丰富。如:
(10)《佛般泥洹经》卷二:“第二帝释将十万众天人来下。”(T01,NO.5,P173)
(11)《弘明集》卷二:“情构于己而则百众神受身。”(T52,NO.2102,P10)
(12)《经律异相》卷二九:“王见八十一万众神人皆列坐师子之座。”(T53,NO.2121,P157)
(13)《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卷二:“濡首与二万三千众菩萨俱,及诸声闻眷属围遶。”(T15,NO.627,P420)
以上各例中的“鬼神、天人、神、鬼、菩萨”等皆是异化了的“人”,都能用“众”称量。王绍新指出,各种语法成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语法化的过程。多数名量词来自名词,进入量词队伍后,或多或少会失去或改变原义而发展出概括性更强的语法意义。[6]“众”原来表示集体名词的词汇意义有所虚化,只保留了称量人的语法意义。
还出现了“一量对多名”的例句:
(14)《经律异相》卷二九:“王虽有数百万众车兵马兵,适可以拒小敌耳。”(T53,NO.2121,P157)
(15)《经律异相》卷三六:“二十万众人马车乘一时还国,王即会群臣怪其所以。”(T53,NO.2121,P193)
例(14)“众”称量“车兵马兵”,例(15)称量“人马车乘”。
2.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量词“众1”发展渐趋成熟,从中土文献语料看,可以进入以下结构:
Ⅰ.“名+数+量”格式
(1)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旧唐书》卷一九八《列传》一四八)
从称量对象看,中土文献“众1”称量的名词仍与士卒类有关;从句法功能看,与“众1”结合的数量短语可以作主语、兼语、宾语等,还可以用在有字句中,数词依然为大数、约数。佛经文献情况如下:
(2)《佛本行集经》卷一九:“其虚空中,常有无量诸天玉女百千万众,悉大欢喜。”(T03,NO.190,P742)
(3)《佛本行集经》卷六:“又诸菩萨百千万亿那由他众,护持彼宫。”(T03,NO.190,P680)
(4)(五祖弘忍)今现在彼山说法,门人一千余众。(《祖堂集》卷二)
佛经文献“众1”称量的对象有“天龙、玉女、菩萨、门人”等。范围比中土文献广泛。
Ⅱ.“数+量+名”格式
先看中土文献情况:
(5)单于亲领万众兵马,到大夫人城,趁上李陵。(《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
(6)禄山即刻遂发所部十五万众兵卒;反自范阳,号称二十万。(《隋唐演义》八八回)
佛经文献用例如下:
(7)《佛本行集经》卷二:“阿难!彼一切事见如来有三亿众声闻弟子,皆阿罗汉。”(T03,NO.190,P659)
(8)《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二:“遏拏挽多城,亿众神围绕。”(T19,NO.982,P426)
(9)《大宝积经》卷七〇:“千亿众魔军,不能迷惑彼。”(T11,NO.310,P400)
总体来说,隋唐时期中土文献“数+量+名”例句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稍多,但称量对象比较单一,称量数目多为大数。佛经文献称量数目亦为大数,称量对象相对丰富。
此外中土文献还见“数+量+名”格式加上“之”形成加强式:
(10)思明集军将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万众之兵降国家,赤心不负陛下,何至杀臣!”(《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列传》一五〇上)
此句在数量词之后名词之前加了属格标记“之”,成“数+量(众)+之+名”格式。吴福祥等认为,这种格式中的“数词+单位词”是描写性的,主要用来刻画名词的某种属性或泛指名词的量度特征,所在的语句大多出现在论证类语域里;与之相反,不带“之”的“数词+单位词”是计量性的,主要用来指称名词的实际量度。[8]姚振武则认为带“之”的一般是描写性的,而不带“之”的既可用于描写,也可用于实际的计量记数。带“之”的结构可以看作相应的不带“之”的结构用于描写时的加强式。[9]上例用在名词之前的“之”具有描写加强的作用,强调数量之多。
3.宋元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中土文献量词“众1”搭配对象更加广泛,所量名词不局限于士卒之类。“众1”的量词地位更加巩固。可以进入下列格式:
Ⅰ.“名+数+量”格式
(1)师雄领叛卒,益聚村民十余万众,攻城益急。(《宋史》卷二七五《列传》三四)
(2)日里有华工万余众,噶罗巴华民七万余众,……华人二十余万众,宜设总副领事以资保护。(《清史稿》卷一五九《志》一三四)
Ⅱ.“数+量+名”格式
(3)贪狼之讳,阳明之星,玉皇尊福,亿万众兵,来扶我身。(《云笈七签》卷二十五)
(4)派迷魂太岁田章,同单刀太岁周龙、笑面貔貅周虎、黑毛虿高顺一千众人,由南面进城。(《济公全传》第二百零一回)
(5)当中二干步队是粉面金刚徐胜督队,骑着一匹坐骑,在马两旁是众战将……公馆一千众办差官俱在两旁。(《彭公案》一五二回)
(6)此人非他,便是正月间大破数十万众回子的那个荷生。(《花月痕》七回)
(7)去年民叛其上,童妇操戈,官军攻城,互相屠戮,五万众苍生之命将欲何处索偿耶?(《庸闲斋笔记》卷八)
上述例句可知,这个时期的“众”称量范围已经扩大了,“众1”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量词。
三、个体量词“众2”的来源及其历时发展
佛经文献量词“众2”多量佛、道教徒,量词前多为具体精确的数值,不局限于大数、约数。其来源与名词“众”在佛经文献中的语义有关,同时也受中土文献量词“众1”的影响。
佛经文献“众”和“僧”意思相当。“僧”为梵语,“众”为汉译。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众,梵语僧伽,此译众,旧译家谓四人已上之和合,新译家谓三人已上之和合。”又:“僧,僧伽之略。译曰和合众。四人已上之比丘和而为众。新译家以为三人已上。《智度论》三:‘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僧非可名一人之上。”《佛光大辞典》:“僧众,即指僧,乃梵语、汉语并举之语。又称众僧。僧,为僧伽之略称,意译为众。即多数之比丘和合为一团体。”
常见“比丘僧”“比丘众”“比丘众僧”“比丘僧众”互用的例子,如:
(1)《长阿含经》卷八:“尔时,世尊以十五日月满时,于露地坐,诸比丘僧前后围绕。”(T01,NO.1,P49)
(2)《正法华经》卷九:“有一比丘,为菩萨行,因时号名,常被轻慢。实时往至,于比丘众,及比丘尼,所覩颠倒,但劝化之。”(T09,NO.263,P123)
(3)《十诵律》卷五三:“问:‘颇比丘众僧不差教诫比丘尼,不得波逸提耶?’”(T23,NO.1435,P393)
(4)《佛本行集经》卷五七:“尔时,佛告诸比丘等:‘汝诸比丘!若有心疑,于彼盘头摩城之内,婆罗门子,供养彼佛及比丘僧。’温室洗浴,心发是愿:‘愿我来世,当得似此比丘僧众清净无垢香洁之身。’”(T03,NO.190,P917)
上述例(2)“比丘众”与“比丘尼”并举。例(3)“比丘众僧”与“比丘尼”并举,“众”即“僧”。
也多见“和合僧”“和合众”“和合众僧”“和合僧众”混用,例不赘举。
同样程式化的句子中,“众”和“僧”常可互换使用:
(5)《佛说兴起行经》卷一:“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精舍,与大比丘僧五百人俱。”(T04,NO.197,P168)
(6)《修行本起经》卷一:“一时佛在迦维罗卫国,释氏精舍尼拘陀树下,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T03,NO.184,P461)
例(5)用“大比丘僧”,例(6)用“大比丘众”,“众”即“僧”。
“众”单用也可以指僧人:
(7)《中阿含经》卷九:“(郁伽长者)常请二十众食,五日都请比丘众食,施设如是大施。”(T01,NO.26,P481)
(8)《四分律比丘戒本》卷一:“应二十人僧中出是比丘罪,若少一人,不满二十众,出是比丘罪。”(T22,NO.1429,P1016)
按:例(7)“二十众”即“二十僧”。例(8)“不满二十众”即“不满二十僧”。
“僧(僧伽)”是出家佛教徒的团体,至少要三人或四人以上。据《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记载,僧有三种,即理和僧、事和僧、辨事僧三种。就理和而言,一人就可称之为僧;就事和而言,三人及以上始称为僧;就辨事而言,四人以上才称为僧。这就是说在佛经文献中,一个人也是可以称之为僧的,义同沙门。“众僧”亦可以指单个人,也可以视作并列关系的复合词。例如:
(9)《大智度论疏》卷一五:“本国有一人,极大学问,不信一切经书,唯信观世音,何以然?此人同村,有一人破落,江南去,极远有数千里地,其母昼夜诵念观音,愿得早见其子,正为他犁地,忽有一众僧来语言:‘汝母为煎,我欲见汝,我当将汝还去,当送作具还他。’此人言:‘道里极远,复无船乘,何由可到?’众僧言:‘汝但送作具,我将汝去。’”(X46,NO.791,P841)
(10)《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一〇:“若熟食鸣钟分食,即无盗罪,若一众僧不鸣钟食,名同共盗损。既许分食,不望一人,皆有食分。约盗无满五义,望僧结轻,以僧分业无满五故。”(X43,NO.737,P260)
按:例句(9)“众僧”指单个人,“众”显然不是表多数。例(10)“若一众僧不鸣钟食”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僧人不鸣钟就吃饭的话。
朱冠明指出,佛经翻译中“移植”是影响汉语词汇的一种方式。[10]所谓“移植”,是指译师在把佛经原典语梵文(源头语)翻译成汉语(目标语)的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假定某个梵文词S有两个义项Sa、Sb,汉语词C有义项Ca,且Sa=Ca,那么译师在翻译中由于类推心理机制的作用,可能会把Sb强加给汉语词C,导致C产生一个新的义项Cb(=Sb);Cb与Ca之间不一定有引申关系,且Cb在译经中有较多的用例,这个过程我们便认为发生了语义(包括用法)移植。
“僧”是梵文词,“众”是汉译词。“僧”可以用来指称多个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单个人。“众”汉语指称多个人,由于受语义移植的影响,“僧”指称单个人的用法也类推到“众”,“众”也获得了指称单个人的用法。
佛经文献常见“众”“僧”连用的例子,当“众僧”前带有数量短语时,可以两解。看下列例句:
(11)《摩诃僧祇律》卷一六:“祇洹精舍有五百众僧,今有何因缘,正有六十比丘来?”(T22,NO.1425,P352)
(12)《经律异相》卷三五:“佛与千二百五十众僧往舍而坐。”(T53,NO.2121,P191)
以上例句如果看作“数+名”结构,“众僧”即“僧”,是一个复合词。如例(11)前文用“五百众僧”,后文用“六十比丘”,可以理解为“数+[众僧]”结构。由于“众”在佛经文献和中土文献已经有量词的用法,受“众1”量词的影响,很容易重新分析为“[数+众]+僧”结构,“众”为量词,修饰“僧”。
以上似乎两种理解都可以。而当“众”之后接续其他佛徒类名词尤其是双音节或多音节名词时,“众”就只能理解为量词了。例如:
(13)朝门外有五众僧人,言是东土唐国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西游记》三〇回)
(14)又有十三众尼僧,搭绣衣,趿红鞋,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红楼梦》一四回)
(15)孟升们算算看,共是八百九十一众和尚。(《红楼复梦》二四回)
因为量词“众2”的语义来源是僧人,所以多用来修饰僧徒之类。偶见“众2”修饰一般人的例子:
(16)(张孝基)又雇了个生口与过迁乘坐。一行四众,循着大路而来。(《醒世恒言》一七卷)
“众2”的用法在明清小说中常见,也可以用统计性副词修饰:
(17)忠贤问道:“合庙多少道士?”住持跪下禀道:“共有四十二众。”(《明珠缘》二九回)
(18)成珪依言,次日即请南北两山僧众共二十四众,单单只念《怕婆尊经》。(《醋葫芦》一七回)
四、小结
通过对“众”由表人名词进一步虚化为量词这一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总结以下几点:
1.量词“众1”的来源与“众”表示多数和表示人的语义有关
“名+数+众”结构中,充当名词的“死者、兵、师”等与“众”范畴相同,语义相类或相近。“众”具有回指替代前面名词的作用。无论从句法结构还是从认知角度看,“众”在两汉时期已经获得了量词的用法。到魏晋南北时期已基本形成“数+量(众1)+名”的格式,这是量词成熟化的明显标志。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2.量词“众1”主要用于称量大的数值
从称量对象看,中土文献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为士卒之类,宋元明清时期范围有所扩大,可以量“流民、土人、回子”等,甚至出现了一量对多名的现象,但总的来说称量范围比较狭窄。佛经文献中的“众1”的语义与本身宣扬的教义内容有关,称量范围比中土文献略广。
3.“众1”和“人”一样,量词性始终不强,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一直不高,呈现昙花一现的趋势
我们推测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众”受它的强势语义“多数、多人”影响,“众人、民众”等基本词汇使用频率一直较高,所以要对其彻底语法化是比较困难的;二是“众”的本义势力强大,所以它不可能抛开本义成为像“个”那样的专用量词,只能在保存本义及其他不可缺少的引申义的同时,兼负量词职能。所以晚近时期作为个体量词的“众1”就逐渐衰落,被其他量词代替了。
石毓智指出,“汉语的量词的类别和数目的设立,远非随意的,而是深刻反映了汉民族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特征。”[11]从整体使用情况来看,量词“众”是严格按照“人”这一范畴来称量的,佛经文献中佛陀、菩萨、天人、鬼神等其实也是异化了的“人”。
4.量词“众2”的来源跟“众”在佛经文献中表示“僧”的语义有关
“众”和“僧”都可以用作个体名词,佛经文献“众僧”原是复合词,可以指单个僧人。当“众僧”前带上数词时,“众”很容易重新分析为量词;当“众”后接双音节僧尼类名词时,“众2”就是完全成熟的量词了。由于受到“众”表示僧的原有语义的影响,作为“众2”的量词多用来称量僧尼。而佛教、道教文化的互相影响,“众2”也扩大到用来称量道教徒了。
正如“众1”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一样,“众2”也是用频低,范围窄,所以跟“众1”一样,到晚近时期就消失了。但此时出现了“众”用作集体量词的用法,多为“一众”的固定用法,相当于“一群”。如:
(1)一众人俱出了衙门,上了酒肆谢了主人。(《欢喜冤家》三回)
(2)(红衣娘)便招呼林兰英等一众美娘齐到殿上。(《七剑十三侠》二九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