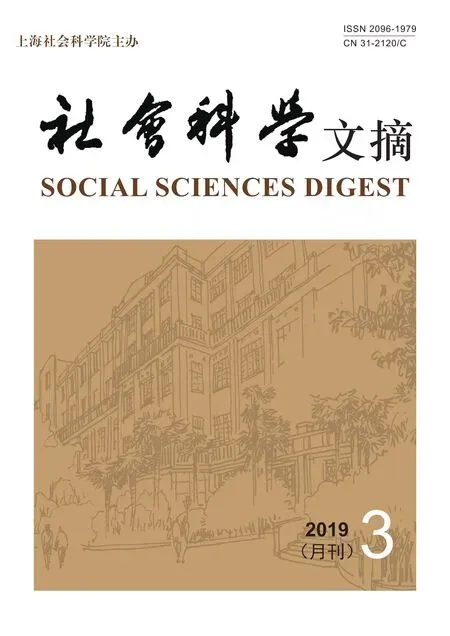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中国思想溯源
2019-11-17
很长时间以来,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市场经济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事实上,中国有超过2000年的市场经济探索史,战国到西汉以及唐宋时期产生了两次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普遍认为的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对两宋时期萌芽的深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早在1910年就指出,中国宋代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了几百年,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产生或光大于宋代,包括钢铁冶炼在内的很多工业生产大大超过六七百年之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成就。实践上,中国有比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工业革命早得多的市场经济探索史,理论上又如何呢?亚当·斯密一直被公认为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但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理论“自由放任”这一核心思想不仅可以追溯到《货殖列传》《道德经》,而且这两部典籍中所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场交易途径,术有专攻、因时而变的市场主体技能,以及多层次的市场治理手段等思想,其中一些方面比《国富论》的论述更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入探寻市场经济的思想渊源,让中华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气。
《国富论》中的市场经济理论、影响及其问题
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总结并系统描述了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国富论》主要在两个地方明确阐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一是在“论分工的起因”中,斯密认为,为了生存与发展,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但是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为此只能通过交换,这就是交易的通义;二是在“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中,斯密强调,一个企业主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他自己资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围绕这一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分工、货币、价值与价格、分配、资本积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学说。
毋庸置疑,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影响广泛,但其原创性却一直饱受争议。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马克·布劳格强调:“人们不能说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坎替隆、魁奈和杜尔阁更有资格享有那个荣誉。”熊彼特、罗斯巴德等也都对《国富论》的创新性提出质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放任和分工一直以来都为世人所称道,对后世影响巨大且毫无争议,但都非斯密原创,那么它们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罗斯巴德为它们寻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则强调这些西方根源的东方渊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货殖列传》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经》。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农学派渊源
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是“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的精髓是个人权益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永远不会被割裂开来,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这无疑是很明显的“自由放任”。罗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与当时“改革开放”启蒙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样,都崇尚自然,一直视中国为标杆,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则。但在启蒙方向上有所差别:后者侧重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与教育,而魁奈在启蒙时代就寻求将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学”还原为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学科。
重农学派对斯密及其市场经济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为斯密准备了很多他“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和“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而且在经济自由的论述方面也比斯密更为透彻、全面。斯密重农业、轻工业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国好友杜尔阁,以及与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事实上,杜尔阁和魁奈对《国富论》所强调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尔阁为指导两个中国学生做好中国问题调查时完成了一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册子,对分工的重要性、货币(包括资本与利息)理论等方面研究颇深。而魁奈已经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且在关于自发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的持续作用、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自由等方面也有着深刻分析。
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国重农学派,那么重农学派的思想又源于何处呢?马弗里克对魁奈的重农学派与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关系有深刻研究,他认为,魁奈及其追随者们是那个世纪深深崇拜中国的欧洲运动的顶峰。魁奈的一位学生指出:“我们知道,只有中国人,他们的哲学家,从远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贯彻,他们称之为法则或‘天道’,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根据于这一个原则:顺乎天意。”除了天道,重农学派还受到中国哲学哪些影响呢?一位追随者在魁奈葬礼上的悼词说,孔子的整个教义,目的是“……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非理勿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密理”。由此我们知道,重农学派的理论来源包括孔子的儒学和宋明理学,也清楚地看到魁奈这位“欧洲的孔子”作为孔子事功在欧洲的直接继承人,在中国学说基础上做出的“新贡献”。
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国专著《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认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农业思想、合法专制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等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和魁奈经济学非常相似。魁奈的一位同时代人曾说他缺乏新创见解,为什么呢?因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来自中国。谈敏认为,“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如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和“垂拱而天下治”等。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认祖归宗
随着18、19世纪西方对中国了解越来越深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共识,那就是寻找“自由放任”的道家渊源,包括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一)西方逐渐认识道家
道家哲学对西方影响的研究至少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稍晚的时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讲到中国哲学时写道:“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作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20世纪以来,这一认识更加深入。利奇温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详细分析了20世纪以来老子对西方深刻而全面的影响:由于当时世界所谓的机械化、工业化、人的异化而引起巨大的“人类堕落”的悲观,很多人对19世纪攻城略地、征服自然的狂躁的人类文化已经失去信心,无论是老子,还是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都对习惯法、道德和一般文明等制度的虚伪性持有怀疑态度,而“顺乎自然”成为了当时不断发生的“青年运动”的口号之一。利奇温概括了老子学说连接西方青年一代的三大环节:向内心发展、虚静为道、回归自然,并认为在当时的欧美,“老子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先觉人物,《道德经》变为当代一代人沟通东西的桥梁”。当代哲学家克拉克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陆续完成了“东方三部曲”:《荣格与东方思想:与东方的对话》《东方式启蒙:亚洲与西方思想的相遇》《西方之“道”:道家思想下的西方转型》,最后一本著作对道家思想的源流、内涵以及西方世界对道家的解读做了完整的梳理,系统、全面地研究了道家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
(二)“自由放任”的认祖归宗
早在1964年斯宾格勒就已研究过道家和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但遗憾的是,作者认为,司马迁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自由放任提倡者,并未对西方的经济理念产生什么影响。不过30多年后,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甚至认为两个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典籍的中国学生与杜尔阁的交流传达了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并对斯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杨格不仅认为司马迁首创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若水之趋下”,而且很深刻地指出,司马迁的“看不见的手”比斯密阐述得更加明确、清晰,因为司马迁将之与价格机制做了直接的关联——“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遍观《国富论》,无此清晰、明白的表达。因此,司马迁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家”。
对于道家和老子,罗斯巴德认为,老子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哲学家”,“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第一个认识到政府干预的系统后果的政治经济学家,老子在援引人类的共同经验之后,得出了他的富有洞察力的结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使政府保持简单和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对于司马迁,罗斯巴德认为“是一位自由放任的捍卫者”,并认识到了“人是财富的本能的追求者”,“专业化和分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市场……产生影响”,“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所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而具体的“自我矫正”方法则是“通过企业家对时机保持敏锐目光”:“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三)《货殖列传》与《道德经》的市场经济思想
自18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终究难以系统地呈现《货殖列传》《道德经》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思想。
首先,《货殖列传》深刻阐述了斯密“经济人”的思想,以及利他才能自利的途径,且这种“利他以自利”的思想比斯密纯粹“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更加合理、科学。一方面,人类在基本需求上,“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但另一方面,要想满足这些欲求,就需要利他以利己,需要分工合作,因此,《货殖列传》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如果没有分工合作,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正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通过分工合作,市场交易,在利他基础上实现人的自利,在满足别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对分工合作、利他才能利己的多层次作用的强调,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斯密对分工重要性的分析,原因在于:斯密对分工的分析仅限于微观层次的效率与效果。基于这一人性假设,在宏观管理上,老子深刻地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其次,在市场运行与价格机制上,正如杨格所指出的:《货殖列传》也比《国富论》阐述得更清楚,比如“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在价格的高点卖出要毫不吝啬,正所谓“贵出如粪土”;在价格的低点买进要毫不迟疑,正所谓“贱取如珠玉”。因此,市场主体应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再次,正如罗斯巴德所分析的,“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老子反复告诫,“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强调遵循天下大道,切忌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万能,以为计划万能,但遗憾的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结果只能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为此,老子推崇“无为而治”的思想,认为应当“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然而,为何看上去放任自流、“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无为之治,反而能够导致“我无事而民自富”“民莫之令而自均”?原因在于:任何市场主体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希望获得财富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而市场主体需要术业有专攻,并通过不断尝试、不断实践来积累知识和经验以达成这一求富欲望,正如商圣白圭那样,“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只有通过反复的试验,发现各自的专长,才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市场主体经过市场的摸爬滚打,积累经验教训,皆可以“取与以时而息财富”,达到“其智足与权变,勇足以决断,仁能以取予,强能有所守”的程度,才能“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在市场竞争中做到游刃有余。
最后,《货殖列传》还提出了有效的治理之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治理策略首先是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通过利他以实现自利;其次,通过推行有效的政策,来引导百姓去追求各自的财富与幸福;其次,如果百姓知识与能力不足,就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他们掌握相应的技能,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帮助他们去追求富足与安康;再次,需要运用适当、适量的刑罚来规范市场的运行;最糟糕的治理方式则是“与民争利”。显然,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上述多层次的治理手段缺乏清晰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