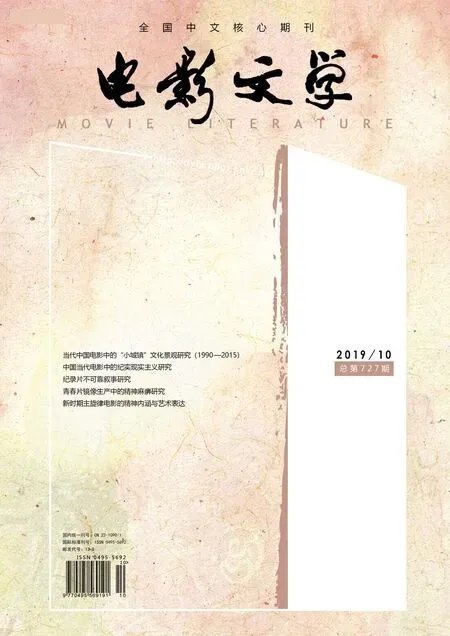大众、娱乐、奇观
——新媒体时代动画艺术的审美趣味
2019-11-15胡媛媛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上海201620
胡媛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1620)
自动画诞生以来,其大众化、娱乐化、商业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动画审美趣味的主要标签。经济利益与艺术水准之间的拉锯战似乎总是以经济利益的胜出为结果。为了全方位地吸引大众眼球以取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动画审美趣味的倾向大体是朝着大众化、娱乐化、商业化、奇观化发展的。特别是新媒体时代无论是制作技术还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都使得这一倾向不断加剧。
一、新媒体时代动画审美趣味大众化
动画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早在动画发明之初,动画就有着大众化倾向。作为和电影几乎同时出现的大众文化的一种,动画的目的就是让人在观看过程中获得一种“感性愉悦”。动画艺术可以通过特定的角色形象、场景设置、叙事解构来给人们塑造一个充满天马行空般想象的影像空间。在动画的影像时空中,人们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猫和老鼠》的幽默夸张,还是《大闹天宫》的紧张刺激;无论是《魔女宅急便》的温馨感人,还是《攻壳机动队》的沉重压抑,动画艺术给人们带来了多重的审美感性愉悦,为人们的精神文化世界增添了色彩。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文化自身的组成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动画艺术也是一样,无论是创作方式还是传播媒介、传播效果都出现了一种泛大众化的趋势,动画成为全民参与、全民娱乐的重要大众文化形式之一。
在新媒体时代,大众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受众,也是文化审美创造的主体之一。普通大众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软件制作出属于自己的动画作品,同时由于制作程序的设定,使得动画创作过程成为一个动态的、交互的、可以逆向修改的过程。如网络flash动画系列剧《泡芙小姐》将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故事情节以动画形象进行演绎,创作者根据网友的反馈对剧情走向进行适时的调整,由于该动画反映了大众较为感兴趣的当代青年白领女性丰富的情感状态,贴近生活时尚,情节短小紧凑,因而受到了大众的好评。
在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的发展使得经典成为人们消解重构的对象。高雅文化所代表的特定阶层的审美趣味被大众文化不断地消解与重构。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就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进行西式消解与重构的作品。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花木兰作为中国传统诗歌文化中重要的女性形象之一,代表了中国女性勤劳、勇敢、智慧的性格特点,但是动画电影《花木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消解重构之后,把木兰变成了一个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西方女孩,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表。
二、新媒体时代动画审美趣味娱乐化
在以现代数字传播技术为传播平台的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下,手机、互联网、移动电视成为动画传播的重要载体,由于以上传播媒介具有即时、迅速、短暂等传播特点,碎片式播放与观赏造成了碎片式的审美特性。因此为了能让动画在最短的时间吸引眼球,达到创作者的既定目标(1)这些目标大致可以分为商业目标,如广告动画;教育目标,如公益动画。,动画的娱乐精神在可能的范围里得到了极致的扩大,审美趣味娱乐化比例逐渐超重以至于失衡。
(一)动画的娱乐性
自诞生之初,动画就以一种娱乐的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带给人快乐、带给人欢笑成为绝大多数动画的特点。例如中国传统动画就一直具有一种“寓教于乐”的精神,在中国的动画艺术家们看来,动画就是在让人们产生感性愉悦的同时还能受到一定的教育。而欧美国家的动画则没有过多强调动画的教育功能,美国式的诙谐幽默与欧洲的幽默智慧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愉悦。如美国经典动画《猫和老鼠》,将猫和鼠之间的斗争演绎得诙谐幽默,让人在完全放松的情境下得到了娱乐。
(二)碎片式娱乐
大众文化的传播具有碎片式的特征,碎片式的信息产生了碎片式的审美特点,动画传统的娱乐精神成为碎片式的娱乐精神。在电视、网络、手机以及其他各种移动终端显示设备的全面覆盖下,人们每天都要接收着大量的碎片式信息,这些信息没有前因后果,只是呈现出你想要知道的,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情除了可以被人们充当谈资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大量的碎片式信息使人们来不及对信息进行理性的思考,同时也割断了大众的情感链接。
作为新媒体时代动画艺术的新类型,手机动画由于其特性充满着碎片式娱乐。一般来说,人们在上下班途中、等地铁、工作间歇等零碎时间内进行动画产品的消费,从而进行精神的放松。闲暇时间的零碎使得动画必须短而有趣,以娱乐观众为目的,不宜承载严肃而冗长的主题。因此充满了碎片式娱乐的动画作品就特别适合在手机平台上进行传播,这正好解决了现代都市人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需要丰富文化娱乐进行放松却缺乏大块的时间进行休闲的困境。
(三)娱乐至死
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手机等新型传播媒介娱乐化有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娱乐化的节目、娱乐化的新闻、娱乐化的动画,大众生活在了一个超真实的娱乐化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放弃和疏离,对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等情感的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个世俗梦想、儿童乐园和文化游戏,它不需要我们殚精竭虑,不会让我们痛不欲生,它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智力消耗降低到几近于零[1]。在这个集体的娱乐化梦幻之中,人们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放置到一个理想化的幻景之中[1],娱乐化使得大众能够共享一种被图像制造出来的欢乐。
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描述了草原上一群可爱的小羊对抗狼堡的灰太狼和红太狼的故事,这是一个没有复杂逻辑关系的动画,狼和羊的斗争处于一种单纯的“狼要吃羊,羊儿逃脱”的“天敌模式”。其中羊族中喜羊羊的智慧勇敢、美羊羊的美丽可爱、懒羊羊的贪吃贪睡、暖羊羊的充满爱心、沸羊羊的活力充沛,得到了小观众的喜爱;而作为狼的灰太狼则在羊前阴险狡诈,但在妻子红太狼的强势面前却奴颜婢膝、俯首帖耳。作为一部定位于儿童的动画片,《喜羊羊》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这部动画的不断播出,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严重的娱乐化倾向。
首先,模糊了儿童娱乐和成人娱乐之间的界限。本来动画应该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文化产品,在动画中加入适当的成人化内容,可以增加动画对于成年人的吸引力,使得动画的传播受众更为广泛。可是《喜羊羊》中却大量充斥成人化内容,如红太狼对灰太狼的家庭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老婆,我错了”是灰太狼常有的台词,而红太狼在面对灰太狼的无能(抓不到羊)时常常感叹:当初瞎了眼才找了你这么个笨蛋。这些成人化的内容具有的娱乐性在吸引大批成人受众的同时,对儿童却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让儿童过早接触成人世界而导致早熟。正如波兹曼在其另一本著作《童年的消逝》中所认为的: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分界线在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童年被娱乐化的各种文化所抹杀。
其次,降低了动画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日本,每年动画电影排行前三的都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绝佳的动画。然而对娱乐性的过度追求必将导致动画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缺失,娱乐符号的不断自我重复与放大必将导致观众思维的惰性与麻木。在日复一日的娱乐符号的重复中,成人变得幼稚化,而儿童变得成人化。仍然以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为了增加娱乐性,这部动画中还充斥着大量的网络流行语,如灰太狼在面对狼族拆迁队时发出“狼籍被吊销,没有医保、社保,没钱买奶粉啊”的哀号;在喜羊羊和羊群走散时,懒羊羊安慰美羊羊说:“喜羊羊是男一号,他不会有事的。”其他诸如“给力”“浮云”等使得这部动画的语言充满了网络社会的娱乐特性。为了追求最大的娱乐效果,《喜羊羊》将现实生活所有的娱乐符号都在动画中加以利用,特别为年轻女性所津津乐道的就是灰太狼对妻子的绝对服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永远以老婆为第一位,因此在网络调查中,最受欢迎的形象就是灰太狼,甚至年轻女性们还发出了“嫁人就嫁灰太狼”的宣言。
三、新媒体时代动画审美趣味商业化
当我们把动画艺术放置于当代消费社会之中来看的话,动画艺术就成为一种可供生产与消费的商品,因而就无可避免地具备了商品的一切属性。作为一种不断被更新生产的商品,动画成为最为流行与时尚的文化商品之一 。从动画艺术诞生之初我们可以看到其发展一直与商业行为密不可分,除了少数的艺术动画之外,绝大多数动画都是朝着商业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和电影艺术一样,动画艺术的商业性十分明显。因而其审美趣味上就不得不具有商业化的特点。
(一)动画艺术的商业美学
一般来说,人们对消费的商品都会有一定的审美需求,这就要求商品在视觉、听觉、触觉上能带给人美的感受,如匀称的外形、舒适的手感、漂亮的颜色等。而电影、电视、动画等视听艺术则具备有感人的故事、精美的画面、动听的音乐等要素。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在给大众带来美的享受的背后,是制造商对商业化利益的最大追求。对于制造商而言,制造的商品要给消费者留下美好的形象,使得消费者产生购买的欲望,从而将商品推销出去。在遵循了这个设计原则之后,动画艺术也成为一件不折不扣的商品。美国学者理查德·莫拜在他的HollywoodCinema中提到,好莱坞是电影商业美学运作的典范,其核心是在电影的制作中尊重市场和观众的要求,来有机配置电影的创意资源和营销资源,寻找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点,确立自己的美学表达模式,并根据市场和观众的变化不断推出新的惯例,“商业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动机上的机会主义”[2]。对于电影、动画等文化消费品来说,其所遵循的商业美学就是要求其制作发行必须满足市场的需求和规律,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好莱坞动画和日本吉卜力动画就是在充分考虑地市场的需求和规律之下,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市场化商业化之后,成功地引来了大量的拥趸。
(二)审美趣味商业化对动画创作的影响
在商业化的内在趋势之下,在商业化的内在驱使之下,动画的创作需要贴近当下的流行文化,无论是动画形象、动画场景、叙事内容还是声音配乐需要满足大众对流行文化的需求。为了迎合绝大多数观众的欣赏水平,制作方会将其中原本晦涩难懂的故事内容进行剔除,加入适当的改编,以获得观众的喜爱。如梦工厂的《埃及王子》是一个从宗教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出自《圣经》的《出埃及记》,描写了希伯来人摩西放弃原本作为埃及王室养子的身份,带领在埃及受尽苦难的族人在上帝的指引下,在经历了埃及人的围追堵截之后,终于回到了上帝对希伯来人的应许之地——迦南。这原本是一个讲述虔诚、信仰的宗教故事,但是作为一部商业动画电影,许多严格的宗教意义被加以简化甚至剔除,摩西和埃及王室之家的父母之情、兄弟之爱都被加以强调和渲染,这些充满人性化的情节使得观众产生共鸣,更加增添了影片的吸引力。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商业化进程,计算机网络、手机通信、移动电视除了为动画的商业化传播增加了新的传播平台,使得动画消费市场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新型传播媒介的支持下,为了追求最大的商业利润,动画的受众群被不断地细化,出现了针对特定受众群体的各类动画,使得动画的传播深入到大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除了传统的以叙事为主的影视动画之外,各类广告、MV都可以以动画的形式在各类传播平台上进行播放,各类热播的电视剧、相声小品、曲艺节目也被进行了动画的二次创造,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如央视节目《快乐驿站》,以flash动画的形式将有着广大受众基础的各类小品、相声进行了改编,使得原本充满中国式幽默的相声小品在时尚先锋的动漫手法的包装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听效果。除了以上的娱乐节目,就连新闻事件为了增加关注度,也以动画的形式使得大众了解到新闻的细节,获得更加翔实的感性体验。如对7·23甬温线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新闻播报使用了电脑三维动画模拟事故发生过程,使得大众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四、新媒体时代动画审美趣味奇观化
法国学者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TheSocietyoftheSpectacle)给人们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和后来的鲍德里亚的所论述的消费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消费社会的生活情境是建立在大量消费符号的堆积之上的,那么景观社会则将生活本身建立在景观的庞大堆聚上,现实存在的一切转化成为一个表象。也就是说在景观社会中,一切与人相关的存在都被异化成一种图景般的展现。作为行为主题的个人与真实世界的联系被这种异化的视觉图景展现所割断,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视觉奇观的社会里,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逐渐被各种奇观化的景象所湮没。在以消费为主导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对消费品的认识和选择都来源于奇观化的“广而告之”。多媒体、全方位、系列化的视觉图像刺激使得人们将注意力和金钱投入到了与之生活相关的一切消费产品中,这些视觉图像刺激成功地激起了人们内心的消费欲望,形成了景观社会构成基础。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之外,人类的文化与观念也被奇观化的外衣所包裹,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电影、电视节目、体育、书籍、宗教、名人都以“创意”和“灵感”为名与产品、销售、市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融为一体,种种被“标新立异化”了的“文化”和“理念”,也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商品的属性[3]。作为文化消费品的动画艺术在审美趣味上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奇观化的审美趣味。
在这个充满奇观化视觉图像构成的消费社会里,动画以其特有的创作特性与制作理念为大众建构了一个奇观化的动画世界。在技术的支撑下动画所创造的奇观场景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能力。真人电影与动画的结合所产生的奇观化场景极大地刺激了观众的视觉神经。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侏罗纪公园》中,巨型的史前生物出现在了现代社会之中,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恐龙的造型在专业的生物学家看来只是一种“生物的大杂烩”,但是在观众的眼中,这种巨型生物所带来的破坏力与灾难才是电影观赏乐趣的重点。到了2010年,乔治·卢卡斯的《阿凡达》将这种视觉奇观发挥到了极致,这部电影中的动画部分为观众建造了一个瑰丽多彩、充满了奇幻生物与植物的潘多拉星球。严格来说,《侏罗纪》与《阿凡达》不能算是动画电影,动画场景的加入只是为了弥补真人电影根本不可能表现出来的奇幻场景。
五、结 语
动画艺术的审美趣味建立在大众文化的基础上,诞生之初,动画发展的基础是为了娱乐大众,让人们在生活中多一份轻松与休闲。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技术的急剧变革使得动画艺术娱乐大众的阈值变得岌岌可危,对动画艺术的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商业化、娱乐化、奇观化过度追求很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这需要社会大众、动画制作机构一起努力将动画审美趣味的追求维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