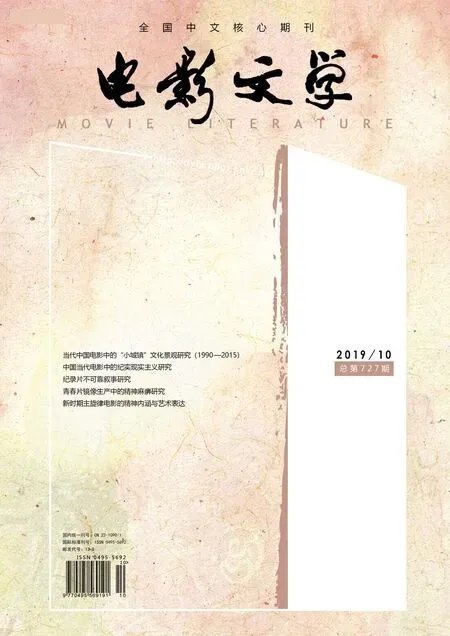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绿皮书》的现实主义表征
2019-11-15郑州西亚斯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郑 强 (郑州西亚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在艺术多元化的当下,人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主义艺术遭到其他话语的冲击,尤其是电影艺术被认为进入了“后假定性”时代,观众更热衷于为一个虚幻的,充斥奇观的世界消费,现实主义似乎面临着式微的尴尬。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彼得·法拉利执导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绿皮书》(2019)却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表征,一举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等奖项以及长时间在美国国内外市场上的热映,宣示着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
一、生活的“镜像”
以写实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客观可信的再现,这是现实主义最首要的基本原则。现实主义作品的性质与形态,都是基于这一原则上体现出来的,如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新客观现实主义抑或是神秘现实主义,作品都应该被视为生活的“镜像”。
《绿皮书》中展开的,正是一幅现实生活的画卷。电影中的主人公托尼·瓦莱隆加和唐·谢里在1962年相识,并一起经历了一段前往美国南方的,充满了酸甜苦辣的旅程。钢琴演奏家谢里从纽约一路南下巡演,一直到全美种族隔离问题最为严重的伯明翰,两人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他们在2013年相继去世。电影所聚焦的,正是两人这一段旅程,而片名“绿皮书”,则来自当时唱片公司给身兼司机、保镖、助理等职于一身的托尼的一本 “黑人出行”指南(由黑人邮政员维克多·雨果·格林编写),这一绿色封皮的指南介绍了在种族隔离,尤其是“白人至上运动”正掀起高潮的时候,黑人可以进入哪些旅馆、餐厅等公共场合。谢里在明知南方对黑人的态度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用自己的演出来提升黑人地位。而受雇于他,与他形影不离的托尼却是一名意大利裔白人,且托尼自身就有着不自知的歧视思想,一路上,托尼就看到了谢里的种种遭遇,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对黑人的看法。
例如,在谢里晚上一个人去酒吧时,喝醉后被一群白人围殴,白人壮汉们仅仅是因为谢里的肤色就认为可以对其随意欺辱,托尼不得不以暴制暴,面对一堆拳头和一把对准自己的刀,做出了即将拔出腰上手枪的动作震慑了对方,救回了谢里。又如谢里和托尼来到一所豪华的庄园后,庄园主十分有礼貌地接待了前来表演的谢里一行,然而在演出中的间歇,与谢里同行的三重奏另外两位音乐家因为是白人,就可以使用洗手间。而谢里却只能使用院子里一个简易棚子里的茅坑,即使谢里是地位崇高的钢琴家,甚至曾经在白宫演出过,他也不能动摇这种种族隔离制度,为表示反抗,谢里马上让托尼开车带他回宾馆上洗手间。谢里的黑人面孔还让他遭遇了交警的寻衅,在托尼殴打了警察后,两人被关进监狱里,如果不是谢里打电话给了总统肯尼迪的弟弟,得到了“特赦”,两人还将毫无尊严地被关押下去,错过之后的演出。初次出现在托尼面前的谢里,因为财富、考究的举止和某种优越感,是托尼眼中的“黑人酋长”,然而他们越是向南方走去,社会对于黑人的压迫感也就越强,谢里的狼狈无助之态也就越多。托尼感受到,歧视是无处不在的,他渐渐开始反思社会,也反思自己。
一言以蔽之,《绿皮书》记叙的是托尼和谢里两人的个人体验,八个星期的生活在吃饭、赶路、演出以及一次次与他人的冲突中度过,但是给予观众的却是对一个时代的整体性感知,观众的观影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生存世界的过程。
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曾经在给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信中针对《城市姑娘》提出典型人物的命题:“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后来这也被视为是现实主义的原则之一。所谓的“典型人物”,指的是不可替代的艺术典型,他必须是主创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体、生动,有代表性的人物,主创在表现人物的特征时,还有必要真实地、历史地对人物何以具有这样的特征进行揭示,人物与环境要具有统一性,同时人物的命运,还要符合或暗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绿皮书》中,前述人物活动的被镜像化了的,南方与北方,种族矛盾缓和和尖锐交错的环境,正是一种20世纪60年代初,平权运动还没有充分展开,但已在酝酿之中的美国社会典型环境。而谢里和托尼两个人,则是本身就具备了诸多代表性,同时又被电影强化了这种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托尼由于姓氏瓦莱隆加发音复杂,因此有“托尼·利嘴”的别称,出身市井的他正如他自己坦承的:“我生长在一个小社会,周围全是我的亲戚和熟人,我没读过什么书,没见过什么世面,不像你受过这么多教育。”也正因如此,托尼拥有着谢里不具备的街头智慧。如在夜总会做保安时,托尼知道夜总会即将要停业装修,于是贿赂衣帽间女郎藏起了黑社会大佬罗斯古德的帽子,夜总会被不痛不痒地“停业”,衣帽间女郎因为拿了钱而不敢揭发托尼,托尼趁此帮罗斯古德“找回”了帽子,得到了成为黑社会大佬“兄弟”的机会。除此之外,托尼还有勇敢的一面,如在失业后敢去和大胃王挑战吃热狗等,正是这样的街头智慧和勇气,让托尼一次次地保护了谢里。但这种生存环境也造成了托尼的种族歧视意识,在电影一开始,因为家里请了黑人工人,一帮亲戚全来到家中“保护”托尼的妻子德洛瑞斯,在工人走后,托尼还嫌弃地将工人用过的水杯扔到了垃圾桶中。在知道托尼要做谢里的司机后,所有亲戚都觉得托尼没多久就会将谢里痛打一顿。原本就是边缘族裔的意大利裔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对黑人的歧视。
而谢里则曾经留学苏联,拥有博士学位,怀着改变黑人地位的一腔孤勇离开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低调而坚定地用演出支持黑人民权运动,相比起托尼的“小勇”,谢里具有一种“大勇”。而对比托尼的粗鄙庸俗,谢里则处处表现出优雅自尊的一面,在谢里看来:“暴力永远无法取胜,坚守尊严才会赢,因为自尊总能让你占理。”这是动辄对他人拳脚相见的托尼不能理解的。在路上,讲究言行的谢里不愿意在车中吃炸鸡,托尼却大快朵颐,还将炸鸡扔到谢里的手中,并示范如何将吃完的鸡骨头扔到窗外。谢里也学着吃炸鸡,扔骨头,但却在托尼将有可能对环境有危害的杯子也扔到窗外时勒令托尼倒车捡回杯子。谢里甚至对托尼承认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袒露了自己“不够黑,不够白,也不够男人”的痛苦。在托尼慢慢改变自己对黑人的狭隘认知的同时,谢里也主动接近这位处于社会下层的朋友,情谊最终超越了两人在种族、阶级上的隔阂。在电影的最后,谢里终于回绝了让他感到不被尊重的演出,在酒吧的破钢琴中放下身段弹奏了爵士乐,并和托尼驱车回家,参加了托尼家的圣诞晚宴。
可以确定地说,托尼和谢里是电影塑造的成功的艺术形象,两人在种族、财富、性取向、文化程度等方面截然不同,分别是社会不同场景中的强势者或弱势者,但二人又有着善良、公义上的相同之处,两个角色体现出了法拉利等人丰富的艺术经验。
三、人文情怀与娱乐元素
现实主义与纪实主义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二者虽然都对现实生活进行较为完整忠实的记录,并不刻意去改变其面貌,或干预人物行为的自然进程。但是纪实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疑而模糊的,因此纪实主义电影中的情感、道德判断或意识形态分析是缺席的,观众必须自己去为电影中各种“原汁原味”的场景寻找意义。而现实主义则不然,现实主义所呈现的“大写的真实”,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的人文情怀以及理性力量,早已内化在其本体价值之中,电影人正是在某种先行的价值理念的驱使下进行创作的。
《绿皮书》批判了种族隔离这一与人类发展相悖的制度,提倡多种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并且对居于歧视链中的弱势者给予了同情。谢里在努力为黑人群体正名的同时,遭遇的却是来自黑、白双方群体的共同敌对,黑人们认为谢里为白人演出,满足白人的附庸风雅,不弹爵士而弹古典,以及他高高在上、西装革履的生活方式是对种族的背叛,因此并不以谢里为骄傲,反而讥讽他。但是黑人在自我保护时做出的这种与白人划清界限的行为,其实又是对种族隔离的一种变相支持。在电影中,谢里在托尼停下来修车时注视着一群正在田野里劳作的南方黑人,对方也用一种疑忌的眼神看着谢里,认为这个能让白人给他工作的黑人是天外来客。谢里陷入沉默之中,他感到了自己的格格不入。尤其是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更是在社会群体中无所适从,如果不是托尼的介入,他将成为一个孤独对抗整个世界的人。但电影又给予了观众不少温暖而美好的片段,预示着诸多歧视终将消弭,如托尼带谢里离开谢里被欺负的餐厅时,黑人侍者脸上露出微笑;原本都当黑人是潜在犯罪分子的托尼的亲戚们,在谢里登门后毫不犹豫地欢迎了他;平安夜路遇警察,托尼和谢里原以为又将面临冲突,不料警察只是友好地提醒他们车胎瘪了等,人并不应该被贴上“黑”“白”“同性恋”的标签而被羞辱压迫,这正是电影传达出来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话语类型,在不同的时代,现实主义都在进行自我更新。就电影而言,当代的现实主义电影更是积极地与商业美学进行对接,或是提升形式上的精致感,制造视觉冲击力,如《拆弹部队》(2008),或是在叙事上与类型片结合,如《国王的演讲》(2010)等,都是得到奥斯卡首肯的,进行了商业和娱乐包装的现实主义电影。而在《绿皮书》中,法拉利选择了为电影加入大量幽默的情节,提高电影的娱乐性。托尼和谢里在一起时因为文化背景,文化程度不同而常常鸡同鸭讲,如托尼说妻子买了谢里的“孤儿”(Orphan)专辑,封面上的火炉旁边围了一群小孩,然后谢里告诉托尼那张传记的名字叫“俄尔普斯”(Orphus),那些也不是小孩而是地狱里的魔鬼;在开车的时候托尼总是喋喋不休,于是谢里叫他安静一会儿,而托尼就继续唠叨自己的妻子是如何也叫自己“安静一会儿”,谢里在车上十分无奈;又如托尼在用“听写”的方式写情书时,将“亲爱的”(dear)写成“鹿”(deer)等。种族和解的问题是复杂而沉重的,但是电影在进行“以小见大”的处理时却能将“小”安排得笑点不断,妙趣横生,使电影受到观众的欢迎,这其实也是《绿皮书》给予我们的启发之一。
可以说,《绿皮书》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电影在还原历史人物生活表象的同时,也还原了他们生活的本真状态,托尼·瓦莱隆加和唐·谢里作为典型人物被观众认识,他们的生存体验能被观众较好地感知,而电影追求平权,主张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乃至提升人的生存意义的价值立场,也由此传达了出来。奥斯卡以及观众对于《绿皮书》的嘉许,无疑证明了现实主义在电影市场多元化格局中依然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电影对严峻残酷生活的洞察,对不乏温情和希望的人性的透视,正是其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