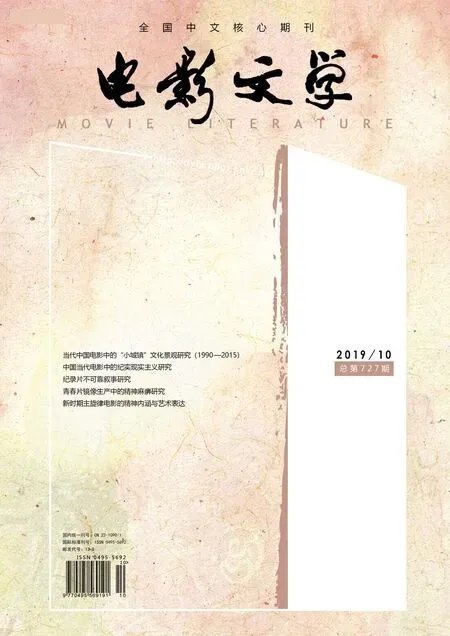疾病的隐喻与生存焦虑
——论电影《无名之辈》的疾病书写
2019-11-15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龙 艳 (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写道:“疾病是生活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5疾病,指的是生物体在一定条件下,由体内或体外的致病因素引起的一系列复杂且具有特征性的病理状态。疾病,“作为生理学层面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1]56
作为隐喻的疾病不仅是身体缺陷的外在表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人生存困境的内在隐喻。社会的进步带来竞争的加剧,有关生存的焦虑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自从婴儿时代开始便“位于难以置信的焦虑边缘”。电影《无名之辈》讲述了围绕着一把老枪而发生在一座山间小城中一对劫匪、一名保安与一名身体残疾的女性之间的温情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个人的疾病与生存的焦虑,个人的生命与社会的认同,使其成为喜剧电影中的佼佼者。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分析其电影中的疾病的书写方式来呈现出当下大众来自生存上的焦虑,而《无名之辈》中的这种叙事亦成为当下电影在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结合之范式。
一、早期电影中的“疾病叙事”
清末民初的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寻求变革以图自强成为知识分子之责任。而对于变革之法的传播,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了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小说与戏曲,“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 。小说、戏曲等大众艺术形式因其“感人也为易,而其入人也必深”被广泛关注。电影自然也带有“教化民众”之功能。查看早期的电影之后发现,疾病成为其叙事的一个重要元素。以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为例:一位富家少爷因吸食鸦片而性命难保,遂由其表弟来掌管家产。然其表弟心术不正,不久便将家产挥霍殆尽。少奶奶规劝丈夫不听也无能为力。不久儿子因误食鸦片而送命,少奶奶悲痛之下自杀身亡。少爷也被其表弟赶出家门,流落街头,正巧遇到被卖为娼的女儿。父女相见,抱头痛哭,但女儿被鸨母强行拖走。父亲望着女儿,泪如雨下,无力相救,最后含恨而死。整个故事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国人的经济侵害与精神毒害。在这个故事中,以少爷身染鸦片之毒而代表了一种身体的疾病与精神疾病,故事情节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再以《桃花泣血记》中德恩与琳姑的爱情遭遇德恩母亲的阻挠,后琳姑患病,身体虚弱,最终在临终之时德恩探视,母亲也终于在琳姑墓前忏悔。在这里,疾病化解了爱情的困局,成全了痴儿怨女。若仔细分析,中国电影史上以“疾病”为叙事情节之一的电影数不胜数,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随着技术的进步,竞争的加剧,社会的不安全因素增加,最为直观的体现便是各种疾病的增加,从SARS到口蹄疫,从癌症人数的增加到艾滋病等,疾病的风险成为现代社会里的主要风险了。吉登斯曾说:“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2]作为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影视文化,疾病已经成为其重要的叙事内容。近年来,医疗剧的蓬勃发展,《产科男医生》《外科风云》《儿科医生》等受到追捧;电影方面则以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我不是药神》为代表,围绕着白血病与药品格列宁讲述了草根众生相。疾病,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二、作为身体“缺陷”的疾病
身体是世界的图景,尼采认为身体是道德谱系中的唯一准绳,可见身体是精神世界的依托。而疾病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在佛教看来,严重的疾病甚至可以看成是对今生或前世所犯罪行的报应,如麻风病人在身体上表现为长恶疮、皮肤溃烂,被认为此人是道德卑下甚或被认为是被诅咒之人。身体的缺陷,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文学作品的描述中,甚至在一般路人的眼中,它是令人嫌弃的、是可悲的,这些人面临着漂泊不定的生存状态。与有“缺陷”的身体相比,正常的身体与自我安全感的获得相关,“正常的外表意味着个体可以继续现行的活动而无须对环境的稳定性投以太多关注”。[3]《无名之辈》中马嘉琪因车祸而导致了身体瘫痪:全身上下仅仅只有头能活动,不能直立、不能挪动且大小便失禁。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给马嘉琪造成了恐惧,产生了生存焦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热情的消耗,而伴随着情绪消沉而来的是对希望的放弃。因此电影中的马嘉琪瘫痪之后放弃了对生活的希望,“在个人不能实现或被制止实现某一行为的时候”[4]产生了来自生存上的焦虑——一种对于死亡的渴望。正因为如此,在两个劫匪即眼镜与卷毛到来之时让她看到了“死”的可能性,也才会有后面的故事的展开。
影片中身体有缺陷不仅体现在马嘉琪的身上,马嘉琪的哥哥马先勇也是如此。同样是中年人,同样是讲述小人物的命运,与《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相比,马先勇在身体上的形象呈现上带有的“缺陷性”:脸上带着伤,衣服邋遢,胡子拉碴,外在的形象无不传达着此人“危险”或者此人“不正常”之信息。马先勇的身体表征着其所处的生存焦虑:因酒后驾车妻子去世后,女儿与其处于冷漠状态;因为工作的不稳定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这种种情形隐喻了马先勇在生存上的焦虑。
除了以上这两种身体上的缺陷之疾病外,《无名之辈》中还有书写了第三种有着身体“缺陷”的疾病,其代表人物便是眼镜与卷毛。眼镜与卷毛来自乡下,进城之后展开了其人生第一次抢劫活动——打劫手机店。在正常人的思维中,手机店的旁边是银行,因此要抢劫应首选银行。而抢劫手机店,眼镜和卷毛却又抢的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手机模型。这一系列的行为表明这两人在智力上是有些不足的。表现为智力上缺陷的疾病有很多如痴呆症、弱智症等,伴有智力缺陷疾病的人物成为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书写对象,如韩少功在其小说《爸爸爸》中的主人公丙崽“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会说的话只有两句,一是“爸爸”,一句是“×妈妈”;影视剧中则对智力障碍的人物的表现更多,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用医学标准来看便是一个智力障碍之人,一个在智商上只有75分的人。《无名之辈》中的眼镜与卷毛也是类似于阿甘这样的带有智力障碍的人物形象,属于疾病的一种。
三、作为精神“缺陷”的疾病
随着心理学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可信度开始,人们普遍认为众多的疾病,或者说大多数疾病,并非是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1]126。作为与身体疾病相对应的疾病类型之一,也许我们用精神疾病来指称更符合当下社会对其的认识。从医学角度而言,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强迫症、抑郁症等。2016年由经济学人智库发起的《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报告中显示,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影响亚太地区第二大健康问题,中国的精神健康综合指数竟然未能及格[5]。可见,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日常生活与生存的重要问题。《无名之辈》在讲述小人物命运之时不仅涉及到其来自身体上的“缺陷”疾病,还叙述了人物的精神“缺陷”疾病。
在电影中,马嘉琪因身体的缺陷进而产生了其精神上的疾病——暴躁、易怒。她骂走了照顾她的保姆,对于追求她的人是谩骂,对来看望自己的哥哥也是谩骂且不让其进屋。从个人角度而言,无论谩骂所追求自己的人还是执着于“死亡”,马嘉琪所进行的对其身体资源的自我剥夺都是心理失衡的表现,是一种精神疾病,预示着其在精神上的焦虑:缺乏安全感,缺乏对未来的可控性,即使是面对大小便这样的生理反应,马嘉琪也失去了对其的控制。作为马嘉琪的哥哥,马先勇的精神上是偏执的——偏执型疾病。做过一段时间协警的马先勇,最大的梦想是加入警察队伍,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因此其参加警队招考四五年后终于考上了。然而悲剧的是其因酒后驾车不仅导致妻子当场死亡,妹妹瘫痪,也让自己失去了进入警队的机会。然而,马先勇并没有放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名保安但进入警队参与破案工作成为其精神上的执念,所以影片中导演向我们展示了马先勇发现枪——枪丢了——找枪的过程,推动这个叙事进程的便是马先勇精神上的执念以至于影片结束之时队长向马先勇承诺会为他争取这个身份也是对其执念的回应。电影中的眼镜将自己喻为“悍匪”却从未杀过人,内心自卑却又善良,害怕自己的兄弟卷毛吃亏上当,对马嘉琪虽有着不少恐吓却又胆小,事事依着马嘉琪,而卷毛最大的愿望则是娶上自己所爱之女孩,对自己兄弟眼镜是无条件支持。眼镜与卷毛也有着精神上的“缺陷”,但这种疾病却像阿甘一样,正常人眼中的白痴却天真质朴。
作为闭合叙事的电影,既然疾病在这其中扮演着推进叙事的作用,那么电影在讲故事之时必然需要“治愈”疾病,从而让整个作品在叙事上完整。治愈疾病,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解决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焦虑,让人物去坦然面对焦虑。纵观《无名之辈》整个叙事,“治愈”疾病的方式采用的是“死亡”。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亡”与“新生”相关联而形成一种“向死而生”的人生观。影片中两个劫匪应马嘉琪的要求打开煤气让其死去,本以为应该死去的马嘉琪在烟花绽放的晚上醒来,看到了墙上的那句话“我只想陪你走过剩下的桥”,马嘉琪获得生活的热情与希望,其疾病终获治愈。对于马先勇而言,当女儿马依依有危险时奋不顾身救下女儿时,“死亡”不仅让他与女儿之间的父女亲情得到修复,也让他的“职业目标”得到助力;在救护车上他与两个劫匪之间进行对抗时劫匪开枪打伤他时,他面临着可能死亡的情形,这种“死亡”最终也让其获得警察身份,甚至将其人格崇高化。 两个劫匪——眼镜与卷毛“不小心”向马先勇开枪,面对“死亡”的手足无措最终埋葬了其“悍匪”言论,也预示着随之而来的监狱生活,对于两个人而言,这也预示着一种“重生”。
四、结 语
作为修辞方式之一种的隐喻通常意义上是用某种事物、特性或行为的词来指代另一种事物或特性或行为。电影中疾病叙事不仅与身体的脆弱、命运的不确信、生存的艰难相关,不仅向我们展示来自现实的焦虑,也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善良、人性的质朴等。随着疾病的“治愈”,我们也在寻找自身的定位与存在之意义,找寻生活的希望所在,这也是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进行沟通的认可方式,疾病的“治愈”也是来自生存或精神焦虑困境的解决——我们终会获得自我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