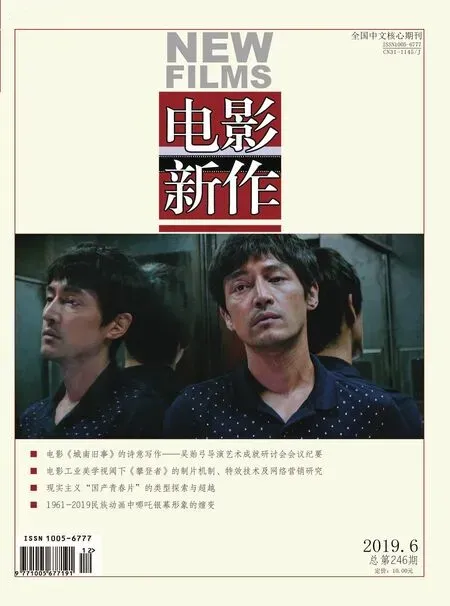新丝路题材电影叙事话语建构与嬗变
2019-11-15张阿利
王 璐 张阿利
丝绸之路的故事已多次被记载在史书中、撰写在小说情节里,因其发生历史久远、文明冲突激烈、族群杂糅繁复,加之流传而来的各类传奇故事、各种英雄人物,使得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叙事题材,有着被叙述的无限可能,并在不同的叙述范式下又生出多样的故事类型。纵观丝路题材电影,主要以汉族与异族、异族内各争权势力之间、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发生的各类冲突为主要矛盾,涉及国与家、个人与族群、正义与邪恶、对立与统一、权谋与人性等叙事母题,而新丝路电影与早期丝路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故事叙述者、主题阐释以及矛盾解决方式的差异上,有着明显不同的叙事话语体系。
一、丝绸之路与电影
有关丝绸之路题材电影的研究,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下而逐步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以丝路故事为背景的电影作品不时出现在银幕上,只不过并未成体系地作为研究对象被关注过。与此同时,丝绸之路题材电影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创作观念下,在影像表达中不断更新着叙事话语体系,呈现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影像文本。在这里,我们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把丝绸之路题材电影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文本解读,一是在倡议提出之前的早期丝路题材电影,另一个是倡议提出后的新丝路题材电影。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批以构筑“丝路精神”、传播“丝路文化”为目的的新丝路题材电影开始出现,这些作品有着自觉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审美主张,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与产业化意识,期望借助电影媒介实现同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因此,这类影片在叙事话语体系建设上带有更为明确的指向性和实践性,比如《天将雄师》(2015)、《大唐玄奘》(2016)、《丝路英雄·云镝》(2016)、《功夫瑜伽》(2017)等,建立在文化认同机制上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使得新丝路题材电影呈现出全新的艺术风貌。
二、新丝路题材电影叙事话语建构与嬗变
新丝路题材电影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主动重构新的丝路叙事话语体系,在挖掘古丝绸之路故事元素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当下的时代需求相呼应。一方面在镜语风格、叙事特征上兼具观赏性与文化价值,以电影工业运作的方式寻求画面叙事的新突破;另一方面在叙事中进一步深化丝路主题,将本国历史中各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延伸至中国同丝路沿线各国间的交往关系,以古鉴今,对丝路精神做了更具现实意义的全新阐释。相比早期丝路题材电影,分析两者在叙事视点、戏剧冲突、叙事主题与叙事空间方面的差异,可以梳理出新丝路题材电影的叙事话语体系与嬗变脉络。
(一)叙事者的转换:由零聚焦到内外聚焦
阿尔贝·拉费认为“叙事由一个‘画面操纵者’、一个‘大影像师’安排”,这里的“画面操纵者”“大影像师”也被后来的学者表述为“看不见的叙述者”“陈述者”“暗隐的叙述者”等,探讨的就是在摄影机的操纵和引导下,观众观看视线的变化。零聚焦指的是“画面并非被任何虚构世界的机制、被任何人物所看见,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无主镜头’”。在早期丝绸之路题材影片重现历史事件和塑造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影片画面机制,主要建立于本国文化视角,特别是以中原文化为表述中心,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大漠紫禁令》中,影片的叙述者是以全知视角出现的,在影片开始以旁白的方式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人物关系等要素,接着进入到演员演示故事的叙事层面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叙述者。在该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及其行动,都是受“看不见的叙述者”所操纵的,叙述的重点在于完整呈现一个故事,即唐朝如何与吐蕃实现和谈,和睦相处。文慧法师作为和谈使者贯穿情节发展始终,在摄影机“操纵”下完成叙事任务(和谈),却始终没有以叙述者的立场对情节走向产生丝毫影响。这种画面机制使得影片叙事的视点始终围绕着事件本身进行讲述,形成了情节闭环结构,矛盾的解决以文慧法师用佛教教义去揭露阴谋、化解怨恨,并最终达成结盟的方式来实现,通过宗教连接了本族和异族之间的分歧,最终归属于唐王朝的统一大业之下。
与早期丝路电影中的全知视点不同,新丝路电影中的叙事层次更为丰富,叙事视点兼顾内聚焦与外聚焦,叙事结构更为复杂。热奈特把内聚焦分为固定式(始终在片中人物的“有限视野”下讲述故事)、不定式(由片中不同人物的视点不断变动中讲述故事)、多重式(不同片中人物视点多次追忆同一事件)这三种,而外聚焦主要指的是从外部注视人物,且并无法得知人物的思想和情感。由此可见,从早期丝路电影中“代上帝言”的全知视点,到新丝路电影中的内外聚焦视点,叙述者从“看不见的叙述者”到“可见的叙述者”,叙事层次更为丰富,片中人物也被赋予更多叙述主动权,而不再只是故事的演示者。
在《天将雄师》中,叙事结构被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叙述者是摄影机,即“大影像师”,通过运用“画面、音响、话语、文字和音乐”进行讲述;次叙述者是克里斯蒂等人组成的考古队,依据一部流传而来的史册考察“骊轩古城”遗址,并由此进入古城叙事时空;第三层叙述者是历史中的霍安、卢魁斯、抵比斯等人的讲述;第四层是被讲述中的事件演示。可以看到,由于叙事层次之间的转换,叙事视点也在不断转换中。观众通过“大影像师”(外焦点)进入故事讲述情境,再借由克里斯蒂等考古学家(外焦点)的现代科技进入彼时远古的故事时空,认知故事中的各位人物,再通过他们的讲述(内焦点)进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带领观众窥探“历史真实”。这种讲述更有利于观众进入戏剧情境,对片中人物的行为动机更具认同感。同时,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被充分展现,较之传统叙事中事件大于人物的叙事模式,这种表述方式更具现代人本意识。
影片中的叙事主体不再局限于民族性和地方性,而是拥有更开阔的视角,在正视因文化差异和族群利益而起的矛盾冲突后,以世界眼光去寻求解决方式。作为外方的罗马帝国被全程纳入到矛盾冲突的构筑和解决中,且赋予他们讲述的权力,在展现罗马帝国政权斗争时,该叙事段落是以卢魁斯的内焦点来完成的,这种内焦视点在早期丝绸之路电影中的匈奴、吐蕃等少数民族的表现中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把握这种内外聚焦的叙事视点,一方面是叙事学层面上的叙述视点问题,另一方面是创作者在架构故事情节时主动由国内转向国外的叙事视野。
(二)叙事结构的转变:由“二元对立”到文化融通
早期丝绸之路题材电影在构筑和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缺乏他者和外族的参与,甚至将其作为对立面,成为矛盾冲突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到,在《大漠紫禁令》《大唐公主西域记》以及《西域大都护》这些影片中,往往都有着情节片的叙事结构:设置悬念,制造尖锐的矛盾冲突,运用命运的突变、机遇与巧合来完成情节的戏剧性发展,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结局圆满。故事背景截取历史上中原与西域各国交锋的集中时间点(汉朝、唐朝),塑造一批代表中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正义使者(官吏、僧人、商人等),以及代表着破坏力量的西域各族内的部落首领(包括部落内主张结盟和反对结盟的两派人),双方就“反抗还是结盟”这一问题,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无论是文慧法师、文成公主,还是郑吉大都护,都是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去担任矛盾的“解决者”,而尚恐热、千户等人成为阻碍结盟和统一的破坏分子、邪恶力量,成为矛盾的“制造者”,矛盾最终的解决往往是通过武斗、宗教认同或和亲等方式来实现。在《大唐公主西域记》中的松赞干布被塑造为有着浑身武功的斗士,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下,铲除异己,两人终成眷属。矛盾的“制造”和“解决”均没有第三者的参与。在这种矛盾构筑模式下的“二元对立”戏剧冲突设置中,以时间或事件为主导的线性叙事倾向,有利于主要情境的建构和情节的演绎推进,同时能满足在塑造英雄人物的过程中,呈现其完整的成长历程。
在《西域大都护》中,影片的人物关系和矛盾设置始终围绕着“营救罗马商队”这一任务而展开。郑吉作为西域大都护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受到了匈奴右贤王、楼兰王、车师王等人的重重阻挠,而矛盾的焦点在于郑吉和右贤王之间因为“对抗还是结盟”这一丝路主题而产生的,依然是二元对立的矛盾构成方式。在矛盾、对抗、解决的线性叙事中,完成了“营救罗马商队”这一任务,也同时塑造了郑吉作为西域大都护的英雄形象,最终实现了异族同盟的统一大业。
新丝路电影中对多元文化的呈现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给予同等地位的客观呈现,一方面展现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思考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影片中有意设置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碰撞,并注重表达不同文化间的融通与共生。与早期丝路电影在展现文化差异、处理文化冲突的方式不同,新丝路电影以更为平和与客观的方式进行讲述。在解决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点,让融通与共生成为可能。
《天将雄师》中霍安和卢魁斯共建“骊轩城”的段落,有很多细节的设定都在讲述文化融通与共生的实践可能。在都护府与罗马军队之间的比武过程中,虽然双方武者的肢体在较量(画面),但周围“观战”的人群却不时发出对对方的赞叹声(声音),用声音讲述的方式消融了异族间的对抗性。在比武的结果上,也与传统表现文化冲突的手法不同,不再是我方取得胜利向对方示好,而是反向操作,罗马士兵在击败都护府大将之后,主动表示感谢,这其实实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平衡感。不仅在中国与罗马之间,在大汉境内的各少数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也被写在这个叙事段落里。一个龟兹人昏倒后,周围的龟兹人、突厥人、南狄人纷纷前来搀扶施救,被搀扶起的龟兹人受到鼓舞,继续起身干活,这一幕以霍安的内焦视点表现出来,引出当年霍去病的宏愿“我要看到西域三十六国旗帜共存在这雁门关之中”。在霍安这里,文化融通的宏愿被进一步延展至大汉境外,三十六国旗帜外又加入了罗马帝国的旗帜,影片主题得到深化,与当下“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间相生共融的时代主题紧密呼应。共建“骊轩城”便是实现中国与罗马之间文化融通、民心相通的融合点。
这种有意识寻求各国文化融合点的叙述在新丝路电影中较为多见,有别于争战与和谈,而是一种更为朴实、更不具备攻击的方式。比如在《大唐玄奘》中,玄奘作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已成为“文化符号”的存在,通过他西行取经的经历和两国间宗教往来的文化交流为基础而达成融通;在《功夫瑜伽》中,用功夫和瑜伽两种“身体符号”作为连接两国文化的中介,将中国武术哲学与印度瑜伽“樊我合一”的哲学境界相融合,最终在影片结尾“功夫+瑜伽”的宝莱坞歌舞大狂欢中达成了文化融通。
(三)叙事主题的深化:由丝路故事到丝路文化与丝路精神
早期丝路电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以“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的使用,对丝路故事的讲述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叙事风格。一种是以“真实性”为前提进行的故事讲述,另一种是以“戏说”为审美旨趣的夸张演绎,由此形成了早期丝路电影多样化的类型样式。
首先是“真实的”故事。这类作品以历史视角为切入点,忠实记录了丝绸之路这段历史中的人文历史事件,塑造了许多让人铭记的历史人物,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当然,区别于纪录片,这类影片中的“真实”是在建立“公设”的前提下来展开的,是创作者对历史的一种先验认知和解释。在《大漠紫禁令》中文慧法师的人物设定,就符合唐朝与吐蕃之间宗教文化往来的历史背景。唐朝时期佛教盛行,吐蕃从唐朝引入佛教成为今天藏传佛教的前身,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文化融通的政治手段。影片中的文慧法师是当时众人敬仰的高僧,派他去和谈既能表现结盟诚意,也更能以隐形的宗教力量实现对异族的教化和改造。虽然文慧法师是虚构的,但这一人物设定的时代背景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与“真实的”故事截然相反的是“戏说化”的丝绸之路故事。有些历史人物经影视剧的改写与杜撰后,遭到了戏说甚至被扭曲的命运,甚至成为供影视文化娱乐消费下的虚拟存在。这类作品的出现,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繁荣于90年代的中国娱乐片紧密联系。这也是中国电影作者开始注意并在创作中践行电影商业美学的集中时期。丝绸之路,在这类影片中更多被作为一种叙事元素来出现,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功能性的使用。商业电影中的传奇故事、英雄人物、离奇情节,与古代丝绸之路这一遥远的故事想象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蕴于影片中的环境空间、武打场面、服装配饰等,具有奇观化的视觉效果,故事内容大多涉及寻宝、探险、魔幻等,这些都是商业娱乐片故事构成的核心要素。与此而来的弊端是,一些经典人物形象惨遭扭曲和变形,影片品质迅速下滑,成为哗众取宠的笑话。比如历史中的玄奘形象,从1983年版的《西游记》中的唐僧开始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直到美国版的《美猴王》,为着商业利益的无底线篡改的电影作品层出不穷,使得玄奘这一形象愈加无法辨识,最终被抽离于历史和文本的叙述语境,成为一个虚空的存在,且这一存在即使是在影片自身建构的规则之下,也使人无法信任。玄奘的公设在这类影片中荡然无存,阻止了我们接受叙事整体的一致性,因此当美版《美猴王》中的唐僧武功超群,且和观音菩萨谈起恋爱之时,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如果说早期丝路电影的叙事更多是一种情节片的模式,重在表现戏剧冲突和戏剧性场面,实现观众对商业类型片的观赏消费。那么新丝路电影的叙事目的则更为明确:传递一种“和平、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也是一种向世界传递出的普世价值。“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种丝路精神和普世价值在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坐标中被记录、书写和传承,并被放置在当下进行全新的演绎,扩大其阐释空间,以更具现代意义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解读,用这种精神传承和文化交流重构丝路电影新的叙事体系,使丝路故事带有更为明确的叙事指向性。
这种明确的叙事指向性首先表现在努力唤起世界各国人民共通的人类本性和情感基因。电影《天将雄师》的叙事主题具有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中国还是罗马,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人人都渴望生活在一个安居乐业、平等互助的世界里。“谢谢你们为我修建这个破城,证明了不分种族,互相扶持是可成的。”霍安这段说给雁门关内各族群的话,不仅打动了差点被瓦解的集体,也感动了场外的观众,正是因为触动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基因,才实现了各族、各国人民的团结,最终靠着众志成城对抗抵比斯庞大的罗马军队而争取到了和平。
其次表现在积极找寻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历史交往中共有的文化基因或历史记忆作为故事素材。比如《天将雄师》中的“骊轩城”,可以使人联想到今位于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的“骊靬古城”,又名“犁靬古城”,相传在汉朝时期安置过流散的罗马帝国士兵,该城也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市和军事要塞。电影《大唐玄奘》根据《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西行取经,途径138各国家的经历改编而成,他的思想和精神不仅对包括印度在内的丝路沿线各国,甚至对日本、韩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功夫瑜伽》也是从历史故事入手,以一张千年前的地图勾连起两国的历史记忆,借助中印两国共同寻找“神秘宝石”的冒险故事,延续两国从历史到当下的文化交往历程。
(四)叙事空间的延展:由单向到双向、单一到多层次的空间维度
早期丝绸之路的叙事空间是较为封闭的,无论是在族群、国家间的地理区位空间,还是在电影叙事中呈现的文化空间,以及在人物的心理空间,都是单向且单一的。为了解决“二元对立”的戏剧冲突,完成“统一大业”的叙事主题,在故事的空间表述上非常有限。表现在:从地理区位空间上主要集中于族内或国内,此外的他者空间几乎没有涉及;在文化空间的表达上以中原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为本,以此观照和审视除此之外的异文化空间,带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性;在人物心理空间的呈现是缺失的,人物服务于事件,人物行为动机符合故事逻辑,而内心世界并不涉及。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理区位的空间延展,也契合了当下“全球化”背景中全世界在空间维度的变化。频繁的贸易往来与密集的人口流动,不断逾越和消融着所谓“国界”的概念。新丝路电影主动突破国界的限制,主动寻求和丝路沿线各国在电影叙事对话中的可能性,形成了早期丝路电影中所没有的多空间层次,构筑了全新的戏剧性叙事空间。
《天将雄师》按照时间划分的空间层次大致有三个,分别是克里斯蒂等考古学家所处的现实空间,霍安所处的故事空间,以及霍安童年这一更早时期的回忆空间(霍安的心理空间)。三个层次的空间彼此交融,用立体架构的方式承载了整部电影的叙事结构。克里斯蒂等考古学家所处的是当下已经岁月风沙侵袭的古城遗迹,这里是用现在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的开始。在用现代高科技现场复原古城原貌之后,我们跟随空间转换进入到历史情境中去,和克里斯蒂等人一起以看幻灯片的方式回顾了“骊轩城”建造的始末,用幻影重现历史故事。霍安作为带领各族群共建古城的发起者,其行为动机来自于他童年的回忆,霍去病搭救了他,并灌输给他“世界和平”的理念。“骊轩城”作为一种叙事空间,带有一种包含着所指和能指的符号意义。它的能指是西汉雁门关的一座古城,连接着中国和罗马两国的交往,它的所指是一个没有战争、平等美好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的存在,代表着中国和罗马在曾经交好的历史印证,也是当下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理想空间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共同主导和建构的交往实践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丝路电影扩展的不仅是电影叙事的戏剧性空间,更是扩展了为文化融通这一叙事目的而建的电影文化空间。
结语
早期丝路电影的叙事范式更贴近情节片的叙事模式,在80年代中国娱乐片刚刚兴起的年代,丝绸之路更多被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的功能性使用,以跌宕起伏的情节、激烈的戏剧冲突、善恶分明的人物关系以及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视听语言风格,成为一种题材丰富、类型多样的电影样式。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新丝路电影,将叙事重点更多放在实现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媒介功能上。在沿袭早期丝路电影中的情节片模式外,又建立了新的叙事话语体系,以此传播丝路文化和精神,不仅创新了丝路题材电影的叙事范式、进一步挖掘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资源,还为实现丝路沿线各国文化共生共进的交流融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