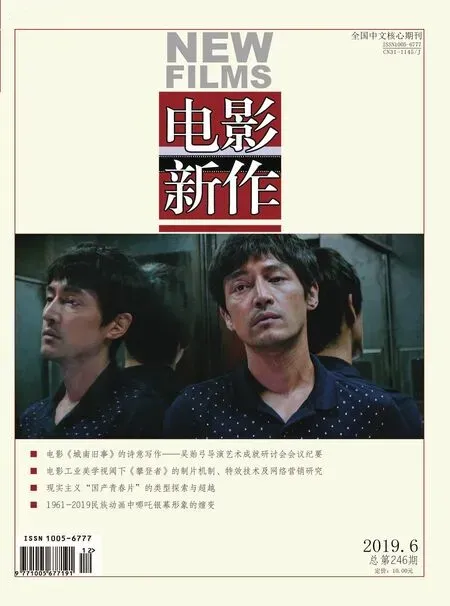跨文化传播视野下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的关键策略
——基于外国专家访谈的启示
2020-01-14高凯
高 凯
一、研究缘起
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电影贸易壁垒逐渐降低,电影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全球电影权力竞合加速,电影作为全球文化竞争中的重要构成部门,不仅可以带来外汇,而且可以传播本国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
近年,中国电影产业呈现井喷式增长,无论是从电影产量、电影票房、放映场次,还是从观影规模、影院建设或电影投融资等方面来看,均取得长足发展。可喜的是,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国产电影在全球电影产业竞争中实力逐渐凸显,另一方面可以发现,诸如《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叫好又叫座”的优秀电影出现,国产电影质量有可见提升。然而仔细观察其票房构成不难发现,这两部电影的国内票房贡献比重都超过99.5%,由此可见,其海外票房收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墙内开花墙外不香”的瓶颈依旧难以突破,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任重道远。
孙绍谊对世界电影版图的“权利”不平衡问题予以关注,提出“世纪之交中国电影在商业和艺术两翼出现的跨国、全球性制作模式以及叙事、影像风格等方面的‘世界性’,为我们超越‘支配/抵抗’的两元模式提供了可能。”贾冀川依据2003年到2013年间电影总票房、年度票房增长率、进口电影票房等数据,分析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现状,指出中国电影海外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武侠片热的落潮”“单向的文化隔膜”“竞争惨烈的北美电影市场”及“技不如人”四方面。对于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问题还应该平和对待,使其真正回归文化交流本体意义层面,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既要竞争,也要合作。
明确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必要性,以及探索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问题,学者们积极提出对策建议。丁亚平指出,当前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发展较为滞后,拓展中国电影的发展空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借助走向世界的市场机制与新型战略,寻求中国电影的海外发展空间与潜力,密切关系中国电影“国际化转型”的实现。赵卫防认为,中国电影的海外推广的实现主要依靠海外传播产业策略的实施,该策略既有“依托于中国电影优质资源的推广、依托海外影人和海外流行文化的区域影响力的借力推广、利用海外销售代理商进行的国际营销等等。此外,还有电影节和电视平台的文化推广等”主体路径,亦有重点辐射亚洲主体区域。
总体看来,中国电影要实现“走出去”,需多方努力。同时,好莱坞成功的海外传播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借鉴。当下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从传播学、文化学、营销学、电影学等学科视角展开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规律探讨,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国内目前该领域研究虽已起步,然而数量仍旧有限,尤其是研究质量仍有待继续提高。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电影制作”概念,基于访谈的语境,主要指“filmmaking”,即电影制作的全过程,而非仅仅指代“film production”(电影生产)。本研究主要提出以下方面问题:吸引外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的因素;与好莱坞大片相比,中国的大片最大的问题;阻碍中国电影被外国观众接受的因素;中国电影与韩国、日本电影比较;中国电影实现海外传播的有效路径等。
外国实践经验丰富的电影从业人员与相关领域学者,他们凭借自身深厚的专业背景及从业经验,不仅可以发现、分析专业领域中的问题,更能为本研究提出宝贵的有代表性、建设性的策略与意见。采用专家访谈,虽然采访数量有限,然而从获得的信息质量看来,可能要比大范围的简单访谈普通调查对象的结果还要精确可靠。与受访对象的采访方式有面对面、电子邮件、音频录制等方式。受访者职业涵盖媒体研究及东亚文化研究学者、电影发行公司负责人、电影导演及剪辑师、期刊杂志主编等。代表接受访谈对象,如下表:

表1:代表受访者简介
本研究的采访是完全开放式的,并不提供任何答案选项,得到的回答是多样的,这自然与受访对象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职业背景等都有密切关系。他们有从政策角度,有从电影类型角度,有从市场营销角度,亦有从观众接受习惯和心理角度对该问题予以回答,然而对所有的回答进行总结,不难发现,所有的回答又基本有较为集中的指向性。
三、研究发现
基于访谈结果,可以发现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核心是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实现“高水平制作”(High Production Value),而实现这一核心的主要路径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
(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国电影自产业化改革以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式大片涌现,而这一批电影也一直被诟病‘眼热心冷’,如何从‘高概念’(high concept)转向‘高品质’(high quality)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问题。”而提高电影品质的首要条件也是核心问题便是需要有一个“好故事”(good story),提升电影的叙事能力。“好故事”是在与多位外国专家学者访谈中,他们提到频率最多的词汇。他们大都认为当下中国电影在故事性及情节设置方面存在欠缺,甚至已经丢掉了曾经(诸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优秀的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其实就是电影创作者与观众之间进行的一种斗智斗勇的博弈游戏。对此,导演张建亚的态度值得参考,“喜剧片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与观众的关系上,既不能太耍弄编导的聪明,那样他会排斥你;但也不能比他笨,那样他会嘲笑你,要始终领先他一点儿跟他一起往前走,恰到好处地卖个破绽给他,趁他要笑你的时候,又赶到他前头给他个意外,让他佩服你的聪明,喜剧就是与观众斗智的游戏。”其实,不仅仅是喜剧片如此,其他类型的电影也是这样。“电影剧本的前10分钟必须提出戏剧性前提、戏剧性情境和主人公的戏剧性需求。‘戏剧性前提’指的是这个电影剧本讲的是什么,即这个电影剧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提供了一种戏剧性冲动,而且促使故事指向最后的解决。”“实践证明,走进电影院里看电影的观众对电影的要求是很苛刻的,耐心也是很有限的,如果一部电影放映了十几分钟还没交代清楚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还没有营造出充满戏剧张力的悬念,观众很可能选择离开。”由此,即便后面的故事多么精彩有趣,甚至蕴含丰富人文思想内涵,观众一旦选择离开,那么这一切的后置的蕴含也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如访问奥斯卡评委、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资深教授Norman Hollyn时讲到的,“中国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故事库,这是美国所不具备的”,然而现实是尽管我们拥有丰富故事源,在很大程度上却并未善加开发利用,更没有把如此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中国电影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而想要有效地实现此转化过程,则需要提高叙事智慧、灵活运用叙事技巧。”让中国故事走向国际市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中国软实力。
(二)加强国际电影人才培养
“电影业的‘国际化’,不仅包括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等环节,也应当包括电影教育的国际化。因为,教育是电影行业最为基础的部分。”一个完善的电影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不仅包括中国人才到海外学习,也包含吸引海外人才到中国学习。
“没有专门的人才,没有翔实的数据资料,没有细致的实证研究,没有国际市场运作方面的经验,使得国内文化企业对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认知不足,竞争力也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文化产品的出口方面有所突破,是十分困难的。”电影从创意到拍摄完成,再到后期的衍生品开发等一系列的链条上,都需要专业人才的投入,而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能力的提升对国际影视人才更是有着针对性的、特殊性的需求。电影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门类的一种,其核心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国际影视人才是中国参与国际电影市场竞争最有力的智力支撑与创意保障。加强高素质、国际型的电影人才培养有利于提升电影艺术水平,更好实现跨文化语境传播,激发电影企业管理运作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等。
在电影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目前,全国上千所大学都在开电影专业,而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是相当部分的电影专业毕业生找不到从事本领域的工作,电影学及广播电视艺术学等影视类相关专业已有多年被列为“红牌”或者“黄牌”专业,如此一幅“电影人才过剩”的形势;而另一方面,又常有电影导演或企业哭诉“缺人才”。如此对比,值得玩味。谈及当下中国电影教育的问题,多有研究者或行业人员对学生的在校学习与实际操作有脱节,如2016年冯小刚导演就曾在中国电影投资高峰论坛提到开办“影视蓝翔技校”的必要性,“一个剧组90%的工作人员是没有经过(专业)培养的,我们电影产业特别需要‘蓝翔技校’,培养录音助理、化服道(化妆、服装、道具)这些人才,现在我们没有一所学校教授这方面技能。”如他讲到,让一个道具师布置一个晚宴的场景,这个道具师可能都没见过那种正式的晚宴什么样,根本无法去布景。由此看来,中国国内并不缺乏学习电影专业的人,而是欠缺真正能够投入电影创作、产业的人才。而另一方面,能够适应国际化、全球化的电影人才更加缺乏,比如,一方面,在当下电影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年代,3D、4D、4K和IMAX技术逐渐已经普及到电影制作中,一直以来,我国的高技术电影制作技术人员多依靠从外国引进,或者与外国合作,借用外国团队,虽然近年来这个问题有所好转,然而中国本土电影科技人才的缺失依旧是中国电影整体制作水平提升的一块短板。同时,优秀影视翻译导致中国电影译制障碍,从而更难以降低文化折扣,不便于外国观众更好接受。另一方面,既懂外语,有了解甚至精通国际文化(尤其是电影)贸易流程的复合型国际人才更是稀少,更妄谈具有丰富操作经验的该类型人才。
电影作为文化产业中极具高风险且投入大的门类,不仅制作过程复杂,而且对于创意等方面要求更高,由此对于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便有更高要求。在电影全球竞争背景之下,一个优秀的电影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及文化底蕴,还要对先进的科技理念熟知并能运用,同时,还需要能够很好地运作电影复杂的营销发行体系。由此,为更有效实现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提升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能力,需要重视国际电影人才的培养。
目前在国内无论是综合性大学影视类专业抑或是专业影视艺术类大学的课程教学中,应该合理开设国际影视类相关专业理论课程及实践课程,目前由于师资及硬件条件的不足,国内的影视系科课程设置多偏向人文社科,除了传统影视学专业课程《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剧本写作》《电影评论》《导演》等,多设置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课程,而这一方面无法满足业内实践需要,更无需言满足国际影视人才的培养需求。考虑当下国际电影产业竞争环境,除了重视影视专业学生实践操作技能提升以外,可以尝试推行“影视专业英语”“国际文化贸易”“市场营销”类课程;其次,加强中外联合办学、交流,可以通过聘请专职、短期交流培训等形式,吸引外国优秀电影制片、导演、编剧、教授等加入到我国的国际影视教育建设中,这方面目前已有可喜尝试,仅以上海为例,上海纽约大学、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上海交大-南加大文创学院等学校、机构相继成立,在跨文化理念下对学生进行专业培养。前者与纽约大学合作,而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专业素来闻名,后者更是以“建设一流的电影人才教育机构”为任,并有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贾樟柯亲自挂帅担任院长,重在培养影视制作人才。另外,上海科技大学与世界顶级电影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合作,开办影视制片人、编剧、导演培训班,课程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教师教授,并邀请诸多中美影视业内人士进行交流,这都为当下国内国际影视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途径。此外,加强国内师生的派出和学习也是加强人才国际化培养的重要途径,例如,目前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将人文社科及艺术类专业列为重点扶持出国交流学习专业之一;最后,需要建立人才长效机制,引进人才、培养人才,能留住人才也是被足够地重视。
国际影视人才的缺失是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一大制约。要真正走入国际市场,还必须培养出一批“学贯中西”的既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又熟悉西方经营体制的“杂糅型复合人才”。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有效解决文化隔阂问题,推动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之路走得更长远、更有效。
(三) “互联网+”下跨域资源整合
当下,互联网基因逐步深入注入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除了以往视频网站为电影提供新的播放平台以外,网络IP成为电影创意的新来源,网络售票成为票务主流,社交媒体成为电影营销新途径,网络众筹成为电影投资新宠,网络大数据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参照支持,互联网电影公司纷纷进军电影行业,网络大电影概念也日渐火热等,一幅电影产业的新图景呼之欲出。“互联网+”不仅为中国电影内容生产带来变化,同时为中国电影丰富了收入渠道、营销机会、展映平台、投资来源及衍生品开发。
互联网越来越影响电影的创意来源及内容供给,在“互联网+”热潮之下,并依托“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IP在近年逐渐成为行业热门词汇,各大影视公司亦不惜成本对此展开争夺。2015年被誉为“IP电影”元年,出现了一批现象级IP电影,诸如由《鬼吹灯》改编的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和乌尔善导演的《寻龙诀》,尤其是后者实现口碑与票房的双赢,被认作IP电影崛起的标志。“所谓IP电影,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概念边缘模糊,但它的两个构成要件是明晰的:一是改编,或原创;二是IP具有版权,改编需购买版权。”网络小说、网络剧、网络综艺节目、网络游戏及网络动漫等是IP电影的主要来源,而这一批来源正是互联网的产物,就目前国内电影市场上热卖的一批电影,不乏IP电影,除了已经提到的《九层妖塔》及《寻龙诀》以外,诸如《何以笙箫默》《煎饼侠》和《万万没想到》等都在此范畴以内。而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逐渐走俏,影响力日增,未来未尝不可借此“东风”。
乐视影业洛杉矶子公司副总在南加州大学演讲时,曾提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拍出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由此可见其发展之雄心。而这也不禁联想到亚马逊公司。2015年,在亚马逊工作室刚成立之时,公司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就提出一个目标:每年制作或购买12部电影,还要赢下一座奥斯卡。在当年看来,这个目标的提出显得有些“遥不可及”,然而就在亚马逊工作室成立一年刚满,不仅把电影买齐,而且在刚落下帷幕的第89届奥斯卡,凭借发行的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本片主演卡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斩获“最佳男主角”;而亚马逊买下美国地区发行权的伊朗电影《推销员》则拿下最佳外语片。由此,亚马逊一口气拿下三座奥斯卡,并成为第一家获得奥斯卡奖的互联网公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国内诸多试图国际化发展,尤其如乐视影业洛杉矶子公司同样有争夺奥斯卡奖目标的公司来说,亚马逊工作室是很好的参考案例。
谷歌曾向南加州大学、美国电影学院、加州艺术学院、罗德岛设计学院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影视专业大学生发出邀约,让他们帮助探索“谷歌眼镜”这一可穿戴计算设备在电影拍摄方面的潜力。而上述学校将会用谷歌眼镜在纪录片拍摄、人物形象塑造、基于地理位置讲故事等方面尝试探索。而其中负责此项目的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教授Norman Hollyn就表示,他会鼓励学生借助谷歌眼镜,拍摄第一人称电影(first person perspective film)。并且Norman介绍,学生们会可能尝试一种类似于导演麦克·费格斯(Mike Figgis)在电影《时间密码》中所采用的拍摄手法。Norman希望,可以探索到谷歌眼镜的叙事潜力,而不只是带着谷歌眼镜去游乐场游玩。
可以说,除了得益于广大观众的支持,“互联网+”亦成为中国电影起飞的重要助力。在与外国专家访谈时,他们都指出,在互联网发展方面,中国具备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基础,所不具备的发展速度,以及所不具备的优势现状,中国电影无论在制作理念、方式还是发行推广等方面都应该对此优势善加利用。互联网拉进全球的距离,“互联网+电影”为中国电影国际化提供有利平台,有益于以更强姿态投入全球电影市场竞争。“中国和世界正经历着一场以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导的多重工业和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在社会文化生产层面上的特征之一,是铅字印刷为载体的文本文化的相对移位,影、视、数码(包括网络)为载体的媒体文化的兴起,及其两者之间充满张力的动态关系。媒体文化的构成及其意象性不仅具有国家特征和民族属性,而且具有跨越民族书写语言的高科技工业驱动力和跨越民族语言共同体的全球覆盖度,成为21世纪社会心态和文化认同再生产的强势机制,各国文化社会重组的边界条件,和国际相互认知的关键媒介。”对媒体革命、技术革新以及国际格局中的文化创意与跨国合作机制构建等问题需要深入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产业需要加强与相关产业间的协作与互动,从而形成更强大的纽带,得以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结语
在电影产业中,电影的质量往往会被看做衡量其制作水平的重要指标。诚然,高水平制作需要雄厚的资源和财力,但是高水平制作并非只是对应A级大片,因为在电影市场中从来不乏低制作水平的高成本大片,反之也常可以看到高制作水平的低成本小片。由此,无论高概念大片抑或中小成本电影,高水平制作都是其实现商业成功的主要前提条件。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所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除了本文所探讨的因电影制作水平等所造成的电影海外接受困难方面,其他诸如,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可见度”很低(渠道问题);中国电影每年定额引进好莱坞大片,可是美国究竟引进多少中国电影,并能在美国的主流院线有上映机会?另外,中国文化历史深远,有相当内容有“不可译性”或“不可通约性”问题,加上英语如今作为一门世界语言,在全球被使用,中文虽然使用人口数量大,可主要限于国人和华裔,远远不构成世界范围,这也是中国电影被国际观众理解的障碍。限于文章主题,在此不展开探讨。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伴随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变化,面对新语境、新形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仅需要做到自身利益维护,还需把握大势、胸怀大局,打开全球视野,创新国际传播理念、内容、形式与途径,积极建立有效的、外向型的国际传播机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及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同国家的观众因从小生活背景、文化理念及受教育情况等差异,对电影的期待视野及审美需求各不相同,这就导致在国内颇受欢迎的热门电影在海外很容易“遇冷”。如果想让本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同样受到观众接受与认可,就需要对出口国家的观众、市场做充分了解及调研,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制作去满足、丰富观影体验,从而招揽更多海外观众。由此,提升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能力的关键除了要具备“国际吸引力”有一幅“全球卖相”以外,更需提升电影制作水平,拍摄出高质量的电影作品。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