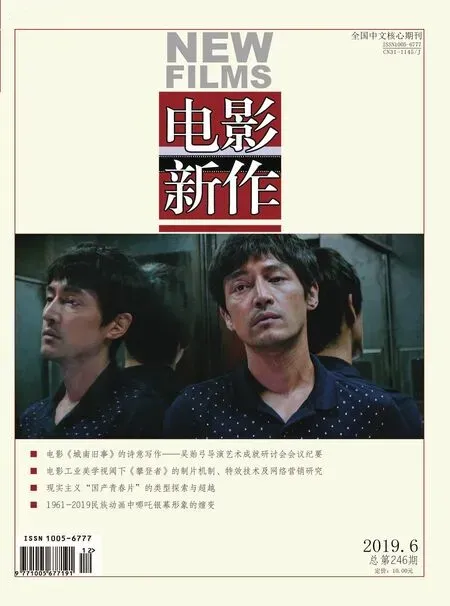牧野流光:蒙古族电影70载嬗变考索
2019-11-15苏米尔
丁 彦 苏米尔
蒙古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文化艺术历史源远流长。在影像时代,蒙古族电影成为追溯历史、反映现实、照亮未来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更名的《内蒙人民的胜利》(1950,原名《草原春光》)至今,蒙古族电影已走过近70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历史进行回溯,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北线国家增强电影历史交流,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俯瞰蒙古族电影历史,既是蒙古族电影的审美史,也是内蒙古人民的心灵史。
一、初创期的“他者”观照(1950-1978)
在1950-1978年的初创时期,蒙古族电影在“族群性”与“融合性”中倾向后者,是一种“他者”观照下的民族影像抒写。这一阶段涵盖了“十七年”电影阶段。“十七年”电影时期红色电影大量涌现,这是政治环境与观众需求的双重因素使然。这些红色电影通过对历史创伤记忆的追溯,衬托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缔造的丰功伟绩,是一种政宣需求。与此同时,社会大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亲身体验也激发了其强烈的表达欲望,这些红色电影正是抒发“新旧社会两重天”之感慨与社会主义新生活之感恩的情感“场域”。
作为“十七年”电影时期的蒙古族电影,自然从自身角度诠释了这一阶段的作品形态。1949年8月14日,中宣部指出:“电影事业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内蒙人民的胜利》作为毛泽东同志亲自更名的作品,最初在展现蒙古族上层矛盾时与党的民族政策有所违和而被停映,后来经过周恩来同志组织电影界专家探讨修改之后,才重新上映。
这一时期蒙古族电影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具有一定的模式,是个体不幸命运与民族启蒙觉醒的重合,影片中往往有一个有待觉醒的民族代表形象,还有一个政治引领的启蒙者形象。《内蒙人民的胜利》中的顿得布和《鄂尔多斯风暴》(1962)中的乌力吉开篇都是王爷的马倌,遭受压迫,命运坎坷。顿得布起初由于国民党特务挑唆与爱情上的误会,对汉族与共产党持有偏见,后来随着情节发展出现反转,遇到领路人苏和,顿得布觉醒,最终加入中共的革命队伍。乌力吉亲人遭受迫害,他前往北平告状结识共产党人刘洪太,受到启迪而觉醒,最后加入中共的革命队伍。在一种“他者观照”的创作中,由于对民族文化与相关问题欠缺深入考察,人物塑造容易陷入标签化、脸谱化泥淖,人物关系容易陷入简单化、表面化窠臼。恰如《内蒙人民的胜利》编剧王震所言:“我们只看到了王公对人民的压迫和少数民族中的败类通敌叛卖的事实,却忽略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者面前,这样的王公虽然与其本民族的人民大众之间有着矛盾,但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就有把这些上层分子争取过来或使之中立的可能。”
一些蒙古族电影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指导下创作,竟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实属难能可贵。比如,《沙漠的春天》(1975)虽然也大量表现了“阶级斗争”,但影片中牧民娜仁花带领群众植树造林、缓解沙化的生态意识和家园意识,在当时是一种难得的生态文明先进意识。《战地黄花》(1977)展现了内蒙古草原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的风采,闪耀着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蒙古族能歌善舞,将歌舞元素融入银幕叙事,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艺术形式,凸显了蒙古族的歌舞优势,也以轻歌曼舞柔化了“政治图解”的刚硬刻板。
二、复苏期的题材突破(1979-1985)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中国社会局面的同时,历经寒冬的文艺创作也迎来了复苏的春天。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贯彻和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中国电影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相应的,蒙古族电影也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下开启了新的征程。这一时期的蒙古族电影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直白表述,而是通过对人性深处的探访委婉地揭示主旨,更接近艺术情感特质。这一时期有三部重要的作品,对题材的突破具有探路者意义。
第一部是《玉碎宫倾》(1981),这是一部蒙古族爱情片,仿照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模式,讲述了主人公塔娜公主与善于骑射、英俊潇洒的洪古尔相爱,但是遭到塔娜父亲甘珠尔王的百般阻挠,塔娜万般抗争,最终与洪古尔双双殉情。深长思之,这段爱情悲剧源自不可调和的封建礼教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将国家意识形态隐匿于草原儿女的悲情恋歌之中。当然,该片也存在不足之处。由于主创人员悉数非蒙古族,在“他者观照”视阈下,人物塑造、演员气质与舞美布景等方面比较欠缺民族性与地域性,使故事不免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二部是《重归锡尼河》(1982),影片讲述了蒙古族青年哈日夫随父亲到城市生活,经历了种种不幸,落魄地回到草原后,又遭逢不顺。经过一番生活的磨炼,哈日夫终于回归往日温馨的牧民生活。在这部作品中,首先,“城市”作为一个被扭曲的意象,成为与游牧文明对峙的工业文明化身。在这场文明较量中,来自草原的牧民之子伤痕累累。其次,继母实际上是“城市”生活的“代言人”,其无理苛责与蓄意陷害带给蒙古族青年难以弥补的心灵伤痛。这似乎隐喻了牧民对城市的一种扭曲的想象。最后,作品直面道德善恶与世态炎凉,透过文明冲突深入到人性与心灵深处,也赞颂了人间至情至善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洗礼与升华。
第三部是《猎场札记》(1985),作为田壮壮导演的一部代表作,不仅于蒙古族电影谱系而且于80年代的中国影坛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也是一部“他者观照”的作品,但影片以类似纪录片的纪实美学手法较为真实地再现了牧民与草原的血脉相连。同时,电影在视听语言上的创新、叙事情节的简略、纪实美学的承袭都对电影本体的探索是一种贡献。应该说,这部介于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的作品由于弱化情节而没有充分满足当时观众的定向期待,然而在弱化情节的同时强化了生活的记录,从而较为充分地诠释了蒙古族的粗狂与豪情,将游牧民族的阳刚之美与洒脱飘逸展现得较为淋漓尽致。
总体而言,蒙古族电影复苏期的三部代表作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意义。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回溯蒙古族人民革命斗争而又融政宣于审美的《阿丽玛》(1981)、《母亲湖》(1982)、《骑士的荣誉》(1984),以及规避宏大叙事而聚焦日常生活的《绿野星辰》(1983)等。这些作品在“乍暖还寒”的复苏期既有“政宣品”创作模式的自然沿袭,也有对“艺术品”本体价值的主动探索,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蒙古族电影全方位的大发展提供了范本。
三、发展期的“自我”诠释(1986-2000)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文化思潮八面来风,中国电影整体上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产业思维推动了商业片的兴起。相较于初创期的“政宣品”,经过复苏期的探索,发展期的蒙古族电影彰显了电影的本体属性“艺术品”特质,并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电影“版图”。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具有至少两个方面突破。
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突破表现为题材突破,较为典型的是对历史时空再现的突破。1985年抒写蒙古族历史伟人成吉思汗丰功伟绩的同名电影《成吉思汗》问世,电影将历史推至相较革命历史更为前端的历史时空。无独有偶,在屏坛上,我国首部帝王题材电视剧《努尔哈赤》次年问世。该剧中的努尔哈赤形象从“神人模式”“伟人模式”中解放出来,并未隐去其政治生涯中的失误,也未借用“脚踏七星,帝王之相”等传说,而是遵循唯物史观,审美地再现了一个从普通女真贵族到反抗明末暴政的革命者,再到开国帝王的成长史与心灵史。这说明创作者已经获得了相对的创作自由,可以开掘之前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封建帝王题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推动中国“银屏”历史之双轮,《成吉思汗》在蒙古族电影版图和中国影坛中功不可没。由蒙古族导演塞夫与麦丽丝夫妇执导的蒙古族历史题材影片《东归英雄传》是继《成吉思汗》之后的又一力作。影片审美地再现了公元1771年由中国迁徙至伏尔加河下游近200年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遭到沙皇种族灭绝政策的戕害,在部落首领渥巴锡汗率领下开启了东归大迁徙,历尽艰辛回到中国。应该说,不论是表达国家一统思想的《成吉思汗》,还是歌颂回归故国事迹的《东归英雄传》,都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宣传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突破表现为对单一“他者观照”的突破,强调“他者”与“自我”的协同合作。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在谈及“他者观照”与“自我诠释”孰优孰劣时回答:“有些蒙古族题材的电影我看了就觉得不太切实际,很多内容在我们蒙古族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有的人想当然地以为只要穿上蒙古袍、住上蒙古包,就是蒙古族的电影了,这是不对的……是否只有本民族的电影人才能拍好本民族题材的电影?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但是编剧和导演非常重要。”哈斯朝鲁导演的经验之谈启示我们,少数民族电影的“族群性”是其存在的价值所在。对这种“族群性”的彰显需要主创者把蒙古族文化放在56个民族的文化碰撞交融中去体悟,方能发现蒙古族的个性与民族间的共性,这一点应处在创作的第一位。
四、成熟期的多元呈现(2001至今)
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和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文化贸易日益频繁。在文艺领域,随着2002年国家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划分,以及2009年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颁布,电影迎来了全面商业化时代。随着跨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和网络时代受众力量的逐渐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更加开放和包容。在新时期,蒙古族电影的外部要素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环境相对薄弱,整体而言文化环境的影响显著。文化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态家园焦虑、精神家园隐忧与普世价值共鸣三个方面。
一是生态家园焦虑。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国家在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之后,也反思了过去粗放型生产,开始转向集约型生产。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美丽中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蒙古族电影自新世纪以来就十分注重对草原生态文明的忧虑。在《天上草原》(2002)中,宝日玛带着虎子归还鸿雁蛋,对着天空向鸿雁喊话道歉;在《索密娅的抉择》(2003)中,荒芜的草原成为老牧人心中的遗憾;在《圣地额济纳》(2010)中,当红柳林被砍伐时,不仅牧人潸然泪下,连骆驼也发出哀嚎。这些电影都闪耀着蒙古族与生俱来崇尚自然、爱护家园、尊重生命的生态观。
二是精神家园隐忧。随着国际文化交流在网络时代不断加速,不同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也日益严重。不必讳言,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市场上“哈韩风”“哈日风”“欧美风”轮番登场,所谓“中国风”大都只是拼贴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较为表层化而且边缘化。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文化和对应的草原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各类中外文化驳杂碰撞的今天,蒙古族通过银幕也抒发了文化隐忧。《长调》中的琪琪格为了发扬蒙古长调来到城市,但是最终失声,失落而归,最后在草原重新找回久违的天籁之声。长调作为蒙古族声乐艺术,2005年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长调》作为一种银幕象征,代表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面对工业文明时的焦虑,这宛若是对于蒙古族精神家园日渐式微的一曲挽歌。
三是普世价值共鸣。从国内来讲,社会学家费孝通对于我国多民族格局提出“多元一体论”,并以十六字诠释之,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对于民族文化危机和精神家园焦虑具有启迪价值。从国际来讲,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与网络文化的高度普及已经使过去山海永隔、不相往来的国度变成无远弗届、鸡犬相闻的村落,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延伸”与“地球村”的命题已经兑现。因此,在国内外大势之下,蒙古族文化在注重保护其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当以更大的格局、更广的视野在人类普世价值坐标系中定位自身的民族文化坐标。比如,《狼图腾》在对蒙古族人图腾崇拜与精神世界的刻画上,由于对“他者”文化的误读,造成了蒙古族观众对“狼图腾”说法的质疑。然而,该片正是试图探寻文化“误读”中人类共有的生命意识与生命母题。影片通过陈阵的同源叙事,变换了姜戎同名小说中“狼”的叙事视角,正是冲破“自我”和“他者”壁垒的一次尝试。陈阵与牧民之间于人类生命母题面前所形成的的精神共鸣正是其他民族走来与我们走入异质文化的关键一步,也是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重要维度。
结语
立足今天,回望昨天,是为了照亮明天。巡礼了蒙古族电影近70载的征程,也就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文艺政策和审美变迁的历程。对于内蒙古文艺创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期间接见乌兰牧骑队员时指出:“乌兰牧骑是内蒙古这个地方总结出来的经验,很接地气,老百姓喜闻乐见,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蒙古族电影就要在“乌兰牧骑精神”指引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继往开来,不断创新,在与我国其他民族和“一带一路”成员国的电影文化互鉴中形成“美美与共”“大同和音”,创作出更多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深情献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