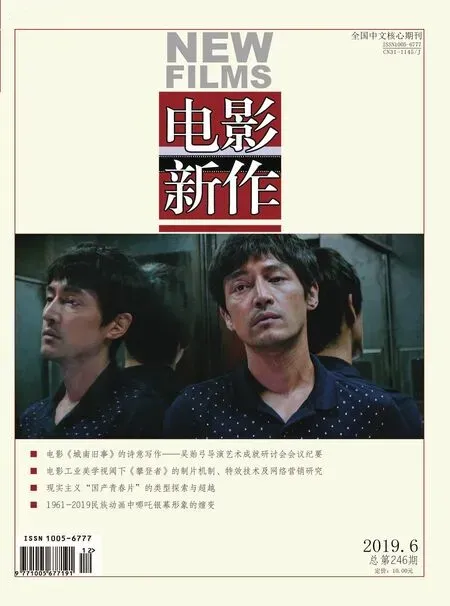张建亚:在上影学到手艺
2019-11-15本刊编辑部
本刊编辑部
张建亚和上影厂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小学三四年级,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参演科教片时,他最喜欢去模型车间看各种飞船和飞机的微缩模型。“在镜头里跟真的一模一样,我那时就知道了电影是一个大游戏。”在他几十年的“游戏生涯”中,上影厂作为他坚实的后盾,为他提供了许多电影技术创新的条件,各种题材也都在他手中玩出了新天地。
一、上影厂的导演实践课
喜欢把电影当成大玩具的张建亚,就像他曾经拍过的孙悟空,再厉害的齐天大圣也有几位地位非凡的师父。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再次回到上影厂,张建亚在白沉、谢晋和桑弧三位上影厂恩师的身上学到了今后“大闹天宫”的本领。
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张建亚是上影演员剧团的一分子。“上影厂几年待下来,耳濡目染,我觉得导演是最有创造力的,只有做了导演才可以实现自己的创意想法。”当然,拥有导演身份只是“创造”的第一步,当张建亚从北电毕业回到上影厂跟组工作实践,上影厂老导演白沉用《大桥下面》给他上了第一堂电影导演实践课。
“白沉导演是个老党员,他吃过很多苦。”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白沉导演回到上海,并没有刻意以宏大视角为主题,反而倾向于女性婚姻与事业的个人情感主题,拍出了《大桥下面》《秋天里的春天》《落山凤》等家庭伦理电影。“白沉导演的电影非常细腻,在当时的我看来甚至有点细腻到琐碎。”但也就是自己做不到的这种“琐碎”让张建亚顿悟:“没有个性就没有作品,没有作品也就没有导演,当一个导演要追求的就是鲜明的不可替代的个人风格。”无法理解的“琐碎”背后,就是作为导演的独一无二。“从那时开始,我比较自觉地就想要做和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做人家做不了的东西。”
果然,当张建亚在上影厂第一次独立执导电影《冰河死亡线》,他就做了一件人家做不了的事—炸黄河。
《冰河死亡线》是一部灾难电影,乘客在渡船上遇到了黄河流凌,被冰冻的黄河危机重重。最后,在解放军战士的直升机营救下,乘客才化险为夷。影片的剧本根据当时的真实事件改编,当时,上影厂的导演们看完剧本虽然都说好,却没人敢拍。“寒冬腊月在黄河中拍戏,又是流凌,又是直升机悬停营救,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当时的上影‘僧多粥少’,所有人都在抢机会,这片但凡可实施性高一些,根本就轮不上我们。”于是,觉得一定得干出不一样的张建亚带领着年轻团队,向厂里请命领衔,接下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影片的外景地在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交界的河曲县,弯曲的黄河道虽然壮丽恢弘,却也给张建亚“添”了许多麻烦。为了方便拍摄,团队先是让真正的造船工匠按照1:1的比例做了一条几十米长的大船作为全景模型,然后又按比例放大25%,在岸边陆地上建造了上下两层的船舱作为局部模型。船造好后被安排在一个常年不结冰的拐弯道,“这地方年年不结冰,可是今年轮到我们,就冻上了!”结冰的黄河就像一面镜子,完全无法制造影片中的冰凌效果。一开始大家本来想着在冰上做轨道推动大船,但轨道根本上不了船。此时,留给张建亚的只有一条选择—炸开黄河。
炸开黄河的冲击波把沿岸居民的住宅玻璃全部震碎,但张建亚没想到的是炸完之后的情况。“如果不把冰块清掉,第二天早上又是冰,坑坑洼洼的冰。果然第二天早上又结成冰了,变成高高低低的冰层,蛮崩溃的。”崩溃归崩溃,张建亚和团队想了许多办法,最后他们又做了个三米长的小船。“我们开车几十公里,到下游一段不封冻的黄河上拍摄行船的大全景。船模做得很像,上面的小人裹着棉衣围巾,完全能以假乱真,所以我从第一部戏就开始做模型用特技了。”从第一部戏开始,从第一个模型特技开始,爱捣鼓的张建亚就决意要做人家做不到的东西。
二、“三创”的“创作集体”
20世纪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改革势头正劲,去陕西剧团组织剧本《人鬼情》的张建亚也被西影厂厂长吴天明相中:“你赶紧到我这儿来,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都来了,还有好些同学在这儿,你也赶紧过来吧。”张建亚拒绝了吴天明的邀请,因为他答应了上影厂厂长吴贻弓的委任,要助上影厂“重振雄风,再塑辉煌”。
“吴贻弓厂长的电影理念非常超前,他提出要拍电影化的电影,要训练出一批有电影思维的导演。我们不能永远是改编小说、话剧和歌剧。不做《新民晚报》的胶片版,要让电影成为第七艺术,电影就是电影。”被吴贻弓厂长提拔为第三创作室主任的张建亚非常怀念当年吴贻弓厂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改革“创作集体”体制。“创作集体”是导演中心制的保障,在那个以文学性见长的电影创作时期,吴贻弓厂长推行的电影化思维是至今为止规模化和制度化最大的导演中心制实践。在“创作集体”体制里,以导演和趣味相近的主创构成组合。导演从一开始就介入其中,当导演有一个电影念头产生后,可以立刻和文学编辑、美术、摄影和制片主任等沟通,及时将一个概念化的雏形具象化成可操作的标准。
当时的上影厂有三个创作室,张建亚所在的“三创”创作最为活跃。“我们‘三创’由三块构成,一块是‘五花社’,桑弧、白沉、徐昌龄、谢晋。中生代一拨的是我、黄蜀芹、江海洋等。”比起另外两个创作室的创作者多为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张建亚所在的“三创”依据着导演中心制的思路,生机勃勃地开创着一个又一个的新视角和新道路。“最高产的一年,上影厂一年出品16部影片,就有11部出自‘三创’。”
张建亚至今依旧赞叹当年吴贻弓厂长关于电影本体论的远见卓识。1987年由吴贻弓掌舵,张建亚操刀的西德和中国合拍片《少爷的磨难》就是一次遵循电影创作规律,以电影本体思维去尝试的类型实践。影片公映后,观众立刻被电影里这种用极其认真做荒诞事的喜剧风格感染,该片成功成为当年上影厂的票房吸睛之作。
“《罗马》这种电影肯定也有文学性,但它的文学性不是用词组来构成的。那时我们需要真正按照电影规律特性创作的导演。”虽然后来的“创作集体”突围随着商业大潮而逐渐偃旗息鼓,但在张建亚心中,作者属性的个人创作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你有自己想要说的话,但你说别人不一定听。所以我学会了一种说话(创作)方式,外层是人家喜欢听的,比如用漫画的形式,但里面依旧是我的东西。”从《三毛从军记》《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开始,张建亚正式开始自觉地以一种文化自嘲的喜剧形式来树立个人的创作美学和风格。当同时代的第五代导演在用沉重的历史负担刻意向海外观众展现猎奇的中国民俗影像时,已经超前跑去后现代的张建亚早就站在市民文化的角度去解构现代性—“这个意思你晓不晓得我无所谓,但是我就要让你看个滑稽故事。”
三、考据式电影论证
“从谢晋那里,我学会了考据式的电影论证。”跟着谢晋导演筹备的《赤壁大战》虽然最后项目流产,但张建亚扎扎实实地学到了导演是把电影引向具象而非概念的工种。“《赤壁大战》做了很多的设计,那时候不能在电脑上进行美术和特效渲染,先是要地点考据、道具考据,然后再画战争场景。我们晚上都在谢晋导演家听他讲戏,师娘就熬一锅粥配酱菜给我们吃。”
那时上影厂一年的拍片预算总计就两千多万,每部电影的预算差不多为一两百万,而《赤壁大战》事无巨细的考古式筹备几乎就占尽了上影厂一年所有影片的预算。项目在最后虽然终止,张建亚却传承了谢晋导演的考据式电影论证。后来张建亚执导历史剧《贞观之治》时,他立刻用考古式的严苛,考证最日常的唐代衣食住行等问题。“不要戏曲化代替民族化,服装要汉唐不要明清。”“穿”的问题解决后,张建亚又向编剧阿城讨教“吃”的问题。“那个时候北方牧民刚刚统治中原,更多是刀叉而不是筷子。筷子只是在汤里捞食物,也应该是长筷子。水煮牛肉是最古老的食物,简单架起来就可以做,然后再放辣椒去腥防腐。”
进上影演员剧团之前,张建亚干的是木匠手艺活,第二次以导演身份进入上影厂后,张建亚意识到电影依旧是个手艺活。跟着桑弧导演拍摄《邮缘》时,张建亚记住了桑弧导演“开机在完成之时”的这句话。“上影厂有一套成体系生产电影的模式,而桑弧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一直讲导演就是个工程师,画了一张图纸,叫人家去加工,你若给人家一张废图纸,加工出来就是废品。所以他会在开机前想清楚所有的镜头调度和分镜头脚本,所以就叫开机在完成之时。”
在桑弧导演那学会了电影的“计划”,张建亚又举一反三出了电影的“变化”。在后来执导的灾难剧情电影《紧急迫降》里,张建亚已经把“变化”玩得炉火纯青。
电影中一个镜头需要摄影“大炮”绕着邵兵饰演的驾驶员一周后再推近特写他的双眼,狭窄的摄影棚无法提供“大炮”绕圈360°的空间。“我们不转摄影机,转人。这样大炮就只剩下一个从高处降到邵兵眼睛的动作。”自谦歪点子一大摞的张建亚就这样解决了一个好莱坞需要一个半月才能完成的特效镜头,大假小真、考据论证、随机应变,爱把电影具象到细枝末节甚至汗腺毛孔的张建亚真正传承了上影厂电影工业体系最珍贵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