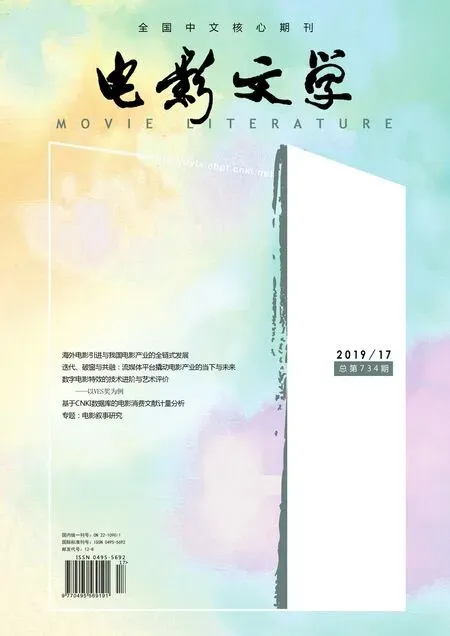由是枝裕和电影空间透视日本电影的底层意识
2019-11-15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厦门363105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0
林 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 厦门 363105;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
从标志着导演转行标签的处女作《幻之光》到近期上映的《小偷家族》,是枝裕和的作品始终聚焦日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生活,这些家庭多是不完整、经过重组后的,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从一个个微小的视角呈现了日本社会环境中的人情冷暖和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枝裕和的电影富含了深厚丰富的社会信息,故事、人和物是呈像的基础,而空间元素则直接关乎主题指向。空间的意义和电影的意义同步创建起来,梳理是枝裕和电影所设计之大量空间,我们才能发现导演于电影里所构建和电影外所指向之“异托邦”,正如他自己所说“电影中的风景并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这个世界”。
一、开放与封闭——“一天一地一人间”
天空、大海和山林等自然空间描写在是枝裕和电影中最常出现,但并不是简单呈现而是被赋予情感和意义,《海街日记》中姐妹们在视野开阔的高山和海边互诉心声;《如父如子》在交换孩子之前两家人一起去山涧溪流游玩……这些自然环境一方面让剧中人物有了宽松的交流空间,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作品影像的诗意情感特点。正如是枝裕和所说:“如果我没有和侯导相遇相知,就不会用显著这样的手法拍电影了……我非常认可侯导‘天地有情’这样看待世界的态度。这是一种如何来凝视这个世界的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包容世界的胸襟。电影中的风景并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这个世界。”[1]是枝裕和的电影作品空间设计中所强调以自然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为中心,所谓“天地有情”,这“情”阐释为人间生活。《小偷家族》里有两处对天空的描写,一处是柴田一家人在狭窄的院门外共同仰望星空观看烟花表演,然而画面中却没有出现天空的仰角,而是由高处俯拍了坐在台阶前的一家人,他们只能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烟花的绚烂。还有一处是夜里治去找祥太,在那个废弃车场,同样也是一个高角度的俯拍镜头。这样的镜头设计都让观众感受到了天空,却不再是仰望湛蓝天空般的美好希冀,而是俯视底层渺小卑微的暗夜生活。
是枝裕和关注家庭关系的重构和维系,榻榻米、厨房、浴室、卧榻、门外院落等日本电影必不可少的常规空间,也是枝裕和的影片中的要素,即便是发生在当下日本皆是现代都市住宅的时代中。封闭有限的空间有利于细致的人物刻画,如《步履不停》的主要场景就是父母的日式传统住宅,母亲一直在屋里洗菜做饭整理家务;《海街日记》的三个姐妹各有不同的空间,大姐的有条不紊,二妹的懒散自由,三妹喜欢在屋里练习钓鱼,四妹在屋里的灵活跑动,都是性格的写照,是枝裕和的兴趣似乎永远是传统的日式房屋,不过以往的空间总是有一种日式的井井有条和简洁,《小偷家族》却不是。这一次是在宽敞街道一旁低矮破烂的小平屋,封闭空间混乱拥挤,如同这一家人在这个世界中艰难生存一样,但本该给人一种压抑杂乱之感,却在电影的前段通过打光、布景等各种手段强调了浓郁的生活感和丰富的光线层次,晕染了乐融融的温馨调值,是导演有意不想让观众感受到它的实际空间感猥琐拥挤,而是去体味作为“家”的处处包容心,隐喻了“小偷家族”的这个空间是社会中被欺凌者、被遗弃者流浪中途的温暖寄居之所,延伸了家的含义。因为这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血缘关系,所有积累的物件都在透露着长年累月的偷窃密语。空间设计有赖于镜头的实现,如果说电影前半段是浪漫现实主义基调的话,镜头更倾向于聚焦人物内部关系,摄像机仿佛也是家庭成员之一,设置在封闭的房屋内调度。后半段则转为冷峻理性,把视线聚焦由家庭内部扩展到社会外部,形成了一个由外向内看的转变,逼近人物的镜头是完全封闭对称的构图,逼近房屋的镜头则是警戒线围栏之外、大众视野中的危险区域。
二、虚幻与现实——“死亡与生活”
死亡是日本电影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同样成为是枝裕和作品中所热衷的,《幻之光》里本来幸福生活的三口之家却因丈夫的无故自杀让妻子不知所措;《足不出户》里妹妹小雪的死亡而被哥哥装在行李箱里葬在了飞机场附近;《空气人偶》里的人偶娃娃最终失去身体里的空气而消逝死去;《步履不停》里的良多带着丧前偶的妻子回家度过因救人去世的哥哥的忌日;《海街日记》里三个姐妹因回乡参加父亲的葬礼才开始接纳同父异母的妹妹一起在城市生活。“在其历史过程中,一个社会可以造就出存在并继续存在的异位,并以不同的方式来运作”,这些是枝裕和电影中累积而成的死亡,呈现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赋予死亡的不同社会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追寻生存的意义。死亡与生活形成了明与暗两个调值,《小偷家族》中所涉及的死亡有四个:一是在影片中离世的初枝奶奶,二是以祭祀照片出现的初枝奶奶老伴,三是以德报怨规劝祥太不要教妹妹偷盗的小卖店老爷爷,四是以台词背景交代被信代杀死的丈夫。福柯在《词与物》中说“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小偷家族》中,初枝奶奶的最后一场戏正是坐在海滩沙地上,感谢远处那拼凑在一起的“柴田一家”。此时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死亡的即将到来,更感受到了老人至深的孤独感,这样的临终关怀是建立在现代而非传统家庭观念和人际关系理解上的。然而,无情的现实总是给予情感冷冷的回应,在初枝奶奶离世之后,信代“夫妻”却为了能继续取得养老金而把奶奶的尸体掩埋在自家的屋里,原来那个充满了温暖模样的家突然变得阴森可怕。
电影还通过食物来拉近观众对影片中生活感知的距离,展现生活空间的烟火味,《步履不停》里妈妈的家常菜、《海街日记》里姐姐的拿手菜、《空气人偶》里的苹果等不胜枚举。《小偷家族》里也不免出现,火锅时间就是全家人最热闹的时刻,专门喂给小玲玲吃的面筋和面条正是维系一屋子人感情的纽带,祥太给妹妹偷来的小零食和火锅料,信代给祥太买的弹珠汽水,还有压抑不住性爱激情的冷面,这些都是电影中生活感的承载,同时也伴随着空间的感知。超市和小卖店是《小偷家族》中许多重要情节的发生场景,电影一开场就是超市里祥太和治的一场父子偷盗,配合默契,思路缜密,而后是祥太在街角小卖店里教妹妹偷东西。基于日常生活的我们甚至很难理解此时泯灭了道德感的祥太如何理解偷盗,“苟且偷生”是作为成人的治唯一可以教给祥太活下去的方法,我们甚至会设想假如超市和小卖店里的“东西是大家的”。这就是《小偷家族》里是枝裕和实现的异质性思考,电影巧妙地通过祥太的视角产生一种窥视感和故事推动力。
三、现代与传统——“女性身体与社会精神指向”
《小偷家族》里所塑造的女性是现代而复杂的。初枝是个老太太,看似善良守护着毫无血缘关系临时拼凑的家,却也常常小偷小摸或者找前夫的儿子(即亚纪的父亲)要钱;信代是个中青年女性代表,却敢于反抗虐待自己的丈夫,犯下命案后仍心安理得地生活;亚纪则体现了年轻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迷失与生存,身着暴露衣服在风俗店卖笑,对于自己喜欢的客人予以精神抚慰和热情拥抱。这些底层职业在电影中不是道德价值层面的批判,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关怀,衍化为底层人民自热而然的生存方式,甚至充满了困惑。“身体是审美开始的地方,是审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被长期遮蔽的主体”[2],电影中通过出卖身体或精神的商品化使作品内涵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后现代性,如同亚纪这样的少女们将自己打扮得如同礼物商品一样端坐在玻璃窗里,希望自己的拥抱可以给四号客人安慰,信代也与亚纪曾经是一样的职业,说明了这个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唯有通过商品交换来拥有情感,而人自身的异化又与空间的异化叠加在一起,身体所托的空间是电影中日本街头的风俗店。风俗店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就是典型的异托邦空间,连接着幻觉性与补偿性的空间,“一种异位有某种创造幻觉空间的作用,这种幻觉公然排斥所有真实的空间和人类生命在其中被加以隔离的所有真实位所。这样的异位是更具幻觉性的。”[3]这个空间被设计为一个商品展示橱窗,但摄影机视角与窗内人保持一致,不是由外向里,而是由里往外看那些需要精神抚慰的路人看客。
另一个有趣的电影空间是老年人的游戏大厅,电影再次使用高角度俯拍,展现了一大堆老年人拿着丰富的游戏弹珠在打游戏,其中初枝老太太还偷了旁边老人的游戏弹珠。这个看似荒唐喜剧的空间场景实际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写照,这种游戏机叫“柏青哥”,是一种赌博性质的游戏机。游戏大厅空间的写照折射了现当下日本社会的老年人问题,优渥养老金和无工作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年人终日无所事事,年青一代啃老族大量出现,这也是电影故事中“柴田一家人”之所以聚拢在一起的前提。“从收入构成来看,日本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劳动所得,占总收入的74.1%,而高龄者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养老金等收入,占总收入的67.5%。”[4]是枝裕和创作《小偷家族》的灵感正是来自日本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有关养老金欺诈的社会新闻。家中的老人去世后,家庭成员隐瞒了老人的死讯,继续违法领取老人的养老金。“在日本,阶级分化在过去五年越来越明显,对那些生活没有保障的人群,这部电影就是他们发声的机会。”[5]《小偷家族》是目前为止是枝裕和电影中最具显著异托邦哲学思考的,如他自己说“这是一部充满寓言性的现实主义作品”,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从陌生偶然走到一个屋檐下,温暖、沉重、真挚的情感、暧昧的身份、内心的秘密和惊悚的欺骗都被交织在了一起,这个看似荒谬的故事确有一个真实可信的社会背景。“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完成,少子化、单身化与老龄化相互叠加,致使高龄单身家庭数量迅速增长,并逐渐形成了‘无缘社会’中的‘孤族’群体。在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与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的综合作用下,日本社会出现了高龄者‘孤独死’现象。”[4]不仅仅是高龄者,整个日本社会群体都越来越深陷孤独,最终演化为一种社会问题,给日本社会带来严重冲击。正是这个成为电影故事的情感基础、人物设定的原始动力、观众理解电影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更像是对社会空间的实验场和预言家,而不是白日梦,是积极参与到社会空间中。
有些人说,是枝裕和是新现实主义作者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人说,是枝裕和的电影是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表达,而事实上他所做电影的初衷并不仅为了再现生活,或自我陶醉表达,而是为了交流去呈现社会。尽管是枝裕和的电影作品表面上展现的是传统保守的空间语言,实际上直指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是对人性之恶的表现,是对现代道德秩序的怀疑。是社会之于电影,更是电影之于社会的双向互动,正如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费罗所提出的那样——“电影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