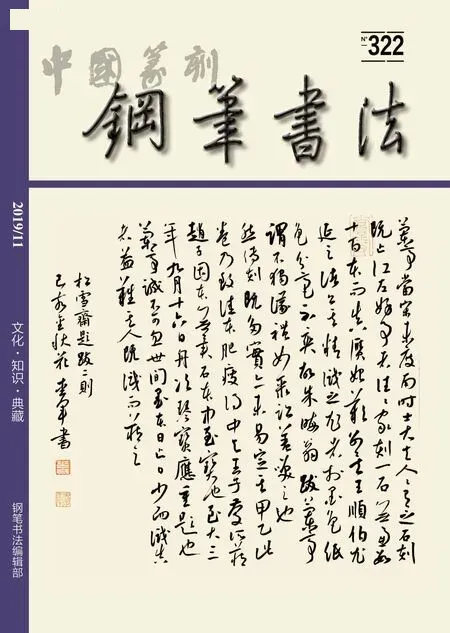以撒随笔之三
——百岁得名
2019-11-14朱以撒
文︱朱以撒
1979年的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一结束,苏局仙老先生一夜成名,他以百岁高龄参与竞争,获得了一等奖。去年以前,知道他的人还很有限,只限于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作为一个老文人,他历经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书写不辍,尤其临近百岁,书写水平无疑已经十分固定。然而百岁这一年意义非同寻常,由于获奖而声名鹊起。水平当然还是一样,但声名提高了,求字的人挤破门槛,来信纷飞。这是一个非常有幸的晚年,开怀之至。一方面基于一位书法家的长寿,一方面得益于他有参与比赛的积极性,还有另一方面是常年的磨砺有了竞赛的能力。这一事件给人的启示是明显的——一个人成名有许多的方式,但是参加比赛,无疑是最快捷的一种。
此后,还没有听说比他更年长的人参赛并获一等奖。比赛使人改变了平素的看法。先前,认识苏老先生的人不过认为他是书法爱好者,是个爱写毛笔字的老先生,但水平达到何种程度,没有一个尺度可以衡量。因此是模糊的,不明确的,没有等第可言。是这次比赛给了人们评判的标准,因为以数字来说明是最为明确和果断的——每个人见到一等奖,都知道它的含意,除非对数字浑然无觉。此时人们看苏老先生的眼光,得到了改变,也就是受到了比赛的引导。其实,人是昨日之人,字还是昨日之字,只不过经历改变了,也使人的感觉改变。这种比赛效应在后来被张扬开来,赛事无尽,参赛不已,许多人的成名就是从比赛获奖开始的,以至于成了比赛控,以参赛为务。
如果没有比赛活动,书法家的作品就不可能有如此醒目的等级之分。用一个比赛的形式,让千万件作品在评选程序中走过,擢拔优秀,分出等级。不管名实相符还是名实不符,比赛的成绩还是能左右人的判断的。如果一个人不断地参加比赛并不断地获奖,也就越发巩固了他人对自己的认识,因为比赛的成绩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了他。会有这么一些人,研究比赛套路达到切实有效,成为模式,使比赛成为可授受的一门功课。如此参赛,当然不是苏老先生那时的心情,自然而然毫无刻意,以此心情获奖,真是一件幸事。和他同时代的人,可能也写了一辈子的字,从未有过获奖,也视为正常。晚清、民国间的一些文人,哪有过获奖的记录——在某些时段,文人在艺文上所达到的品位,是被默认不能以比赛方式来衡量高下的,文艺终究不是武艺。
对一个人来说,书写是一件快乐的事,即便年迈也不辍笔,成为精神生活之必须。至于谁高谁低,可以高自标许,也可以毫不在意。如果一个人不参与比赛,可能处于混沌之中,没有相应的尺度测量,也就不明朗。这很像有人藏了一件古董,专家认为很有特色不可多得,对其制作风格进行了分析。主人虽然快慰之至,但还是要追问市价几何方才罢休,也就从风雅转为俗用,这种现象似乎越来越明显了。英国诗人蓝德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样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审美的妙用就是把玩赏评诸家之风格差异,寻找其不同的表现之美,而不定高下等级。每个人都是独异的,都应充分发展自己的艺术自由,创造出差异之美,如明人解缙认为:“庄重典雅,山野富丽,浓厚纤巧,随其所遇,各造其极。”偶尔涉及比赛当然很有意思,如苏老先生,积年书写砉然天开,的确是一件奇事,而参加这么一次就足够了。
现在再谈起苏局仙先生,已经隔世,不知者居多。而一些书法家没有参赛之经历,却能长久为人记取。人们常说道的林散之、沙孟海、启功诸家,并不以参赛为人熟知,却无人不知,可见不参赛也是可以成就长久之名。当代书坛与既往书坛所不同的表现方式有许多,赛事终年不绝,以至有的从少年到老年,参赛已达数百回,可见参赛可以让人痴迷,获取声名。有的书法家不在参赛之列,却注定要流芳久远,这就令人思索,肯定是有其他一些因素在支持他,使他声名自远,不因时日的流逝而湮灭。这也是可以效仿的成名之路,它不似参赛获奖那般有声有色一时热闹,更多是不动声色静默以处,往深处走。
当然,面对这么一个指向,要有更沉实的定力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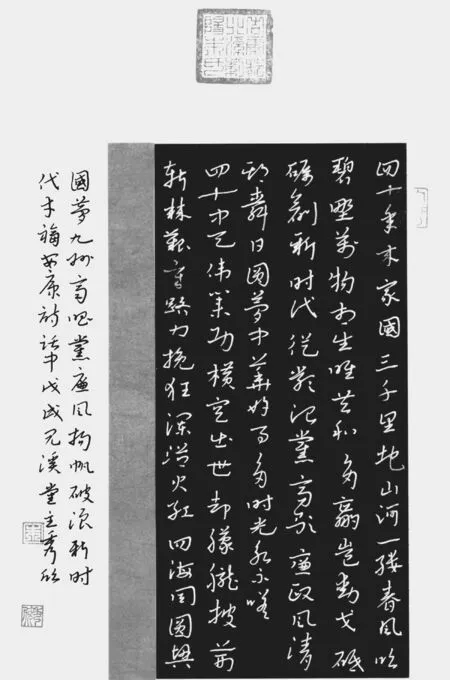
朱秀欣 第十二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成人组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