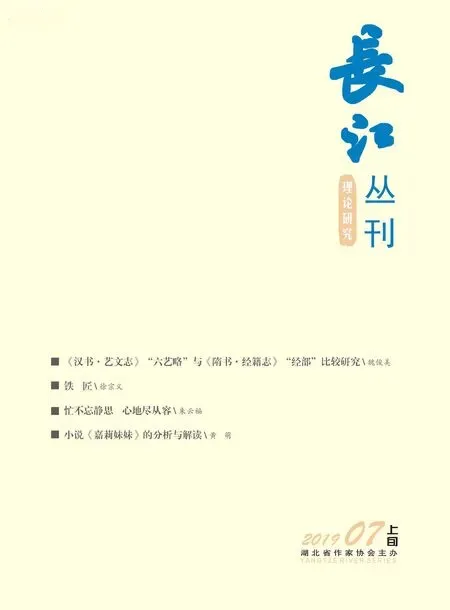为什么要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
2019-11-14■
■
1992年春节临近,接到潘凯雄打来的电话,问我回不回湖北。潘师兄的一向诚恳而又略带提示性的语气,我不陌生:“广东《当代文坛报》的陈志红要篇重头稿件,我春节回武汉没有时间,你代劳一下。”临了还叮嘱上一句:“要有份量哦!”
师兄的吩咐,自然不敢怠慢。那时候我和同学毛浩试着联手写过一些评论。所谓联手,学的也是师兄陈思和、李辉、李洁非、潘凯雄他们的样子。既然答应了,就得当回事。写什么呢?很自然地想到了一直思考着的一个话题:60年代出生作家群。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说的话题。这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与我在《青年文学》从事的编辑工作不无关系。
一
1984年7月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才21岁,那时候真年轻!在大学的最后半年,我把当时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作品全都看了一遍,最大的触动是读了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样才和一群同学到的北京。
正因为年轻,就特别关心年轻的文学气息。读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兴奋之余,写了篇短评,发在《作品与争鸣》上;刚从文学编辑室分出去的《青年文学》杂志,也约我为陈染的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写过同期短评。1985年10月的一天,社领导王维玲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当代吗?我说是。就这样离开文学编辑室,去了《青年文学》编辑部。
不必再去编冷冰冰的古典文学读物,而是与活生生的青年作者打交道,自然心情大好。何况那个时候正是文学刊物的鼎盛时期,方方面面的青年作者们还特别倚重文学刊物的编辑,仿佛他们有什么真经似的。那个时候各种文学活动也多,做文学刊物编辑真是如鱼得水。
到《青年文学》不久,领导就派我去长沙,为编辑“湖南青年作家专号”打前站,我在韩少功家里不识深浅,高谈阔论;1986年7月,回复旦参加完学校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返京途中,和学长宋遂良老师同行,当晚在济南宋老师家里与李贯通一见如故,第二天在张炜家中神聊一天,兴尽而返;1986年8月,编辑部的同事们在办公室里谈论王朔发在《啄木鸟》上的中篇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都觉写得好。好什么好,一位编辑说,以前的都让领导给毙了!我心直口快道:你就再拿一篇呗。后来,王朔的《橡皮人》到了编辑部。篇幅过长,领导破天荒地决定:在11、12月分两期刊发。正值全国青创会召开,人手两册《青年文学》,王朔更是让人侧目;1987年,《青年文学》发表了刘震云的早期代表作《新兵连》,我一时兴起,给《文艺报》写了篇短评,震云读后还特地寄来封表扬信……那个时候,在《青年文学》做编辑,还真有亲身参与当代文学运行的在场感。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结识的这些已经成名或正在成名的作者,都比我年长。他们都是60年代之前出生的,平日里阅读他们的作品,读到的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受,而这又不是我这个年龄所能具备的。就很本能地向四处打量:我的同龄人在哪里,在想什么,有谁在写,写了什么。所以,在1986年年底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见到姚霏、孙惠芬、迟子建、庞天舒、刁斗,就有一份见到亲人般的感受,即便有的才初次相识,也觉心灵相通已久。
二
那个时候,编辑部里总是人来人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的评论家张兴劲,也常来编辑部聊天。1987年的夏天,我对他说起:现在有一批很年轻的作者势头很好,他们都是60年代出生的。他很感兴趣。张兴劲是张炯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时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兴劲在协助研究会办一份叫《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的内部刊物。他嘱咐我写一篇关于这些青年作者的创作综述。于是在1987年第10期的刊物上,出现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还被放在了头题,文章的标题是:“属于自己年纪的文学梦想”,副题为:“1960年代出生作者小说创作述评”。这是我有关60年代出生作家的想法,第一次见诸文字。
“1960年代出生的作者”这样一种提法,应该是首次出现。所以要以出生的年代划分作家群体,更多的是《青年文学》的定位使然,它要永远关注更为年轻的作者。同时,这也是我作为《青年文学》的一名青年编辑、作为青年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对同龄人的创作出于本能上的关注,并没有太多学理上的顾虑。当时较为流行的说法是,作家在哪个年代成名的,就被称为某个年代的作家。比如说王蒙、刘绍棠、李国文,他们就被大家习惯地称为“50年代的作家”;有过知青经历的作家,则被称为“知青作家”,等等。产生以出生年代来划分作者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想来,可能还有点愤青的意思。最直观的感触是,1960年代出生的作者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走进社会、走向文学的,与其他作者在生活经历和文学姿态上有明显不同。初衷和本意在于:希望文坛关注更为年轻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在《属于自己年纪的文学梦想》这篇文章里,我提到了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程青的《那竹篱围隔的小院》、孙惠芬的《变调》、李逊的《被遗忘的南方》、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提到了陈染、苏童、钱玉亮等人,并对他们的创作作了简单的归纳和初步的分析。文章发出后,有多大反响我不清楚。记得随后不久,我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团中央灰楼里,很偶然地碰到了曾镇南先生。他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想法有点意思。这是我所听到的反馈之一。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1992年年初。6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然从个体扩展为层面,由隐转显。尤其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先锋写作”,在文坛独树一帜,广受关注。而它的代表人物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吕新等,均为60年代出生。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创作群体。我一直琢磨着想个说法,好好做篇文章,说说他们与其他作家的不同,谈谈他们呈现的新的特点。
这个时候,我在《青年文学》做编辑已有八个年头了,对同龄人的创作比其他人更留意、上心,也更了解和熟悉。《青年文学》要不断面对更新、更年轻的作者,我作为《青年文学》的编辑,我的作者队伍里早已有了一大批60年代出生的作者。我觉得我有责任为同龄作家摇旗呐喊,甚至还以为非我莫属、义不容辞。既然凯雄师兄盛情相托,那我就好好写写这个其他人尚未关注的话题吧。
于是,“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说法就这么脱颖而出。
三
我认为,60年代出生作家有着与前几茬作家明显不同的特质。这既是我在《青年文学》的实际观察,也是我设身处地的个人思考。在我当时的认知里,前几茬作家,指的是50年代成名的作家、知青作家和后知青作家。所以,我用“第四茬作者群”来特指“60年代出生的作家”。我给《当代文坛报》写的文章,题目就叫“第四茬作者群”,中心话题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前几茬作家到底有什么不同,核心概念是“60年代出生作家群”。《当代文坛报》(双月刊)在1992年第1期上,把这篇文章放在很显眼的位置,还把文章的一些主要观点拎出来,放在文章前面。看来,评论家、副主编陈志红是很重视这篇文章的。我也算是对得起潘师兄的托付了。这篇八千多字的文章,在当时好像并没什么反响。我有印象的是,这份刊物没多久就停刊了,应该是经费困难的缘故。
90年代初,全民经商热浪滾滚,文学被“边缘化”已是实情。文学刊物纷纷各找说辞,扯旗嘶喊,“新写实”“新都市”“文化关怀”等说法,可以看成是不甘于边缘化的努力。1993年下半年,黄宾堂接任《青年文学》主编,我任副主编。《青年文学》怎么办?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也要有说法。1994年1月13日上午,我们在京组织召开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讨会”。我记得雷达、陈骏涛老师,李洁非、王必胜、潘凯雄、陈晓明、格非、蒋原伦、李兆忠等参加了会议。大家都觉得话题很新鲜,值得探讨。这次研讨,实际上是为《青年文学》要开辟一个有关“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主打栏目,在进行专家咨询。研讨会后,我把会议的成果和我个人的想法,写成文章《新说法:60年代出生作家群》,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文汇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很快作了转载。“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说法,开始受到文坛和社会关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连续介绍中,我还补充过一些观点。“60年代出生作家群”,被简称为“60后作家群”,这是不是海外版编辑杨鸥的贡献,我没有求证。我的印象中,“60后”这一后来被广泛沿用的概念,最早就是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1994年,《青年文学》第3期出现了这样一个主打栏目: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此后每期推出一位或两位“60后”作家及其作品,一直到1997年第10期,长达四年,一共推出了60余位“60后”作家的作品,包括余华、苏童、格非、迟子建、毕飞宇、徐坤、邱华栋、麦家等。并且这些作家还是当期的封面人物。
在一份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持续推出一个年龄层面上的青年作者和作品,它所受关注的程度,显然不是我们当初的一个想法、一篇文章所能比拟的。对此,不同年龄层面的人们会有自己的不同看法,“60后”本身也会众说纷纭。就像打开了一个盒子。
我记得,时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兴安随后编选过一套6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合集,评论家洪治纲后来出版过《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的专著,多年之后,媒体人胡野秋还做过60后作家群的系列访谈,并出了书。1998年7月,《作家》杂志推出“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应该是继《青年文学》“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之后的顺势所为。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对“70后美女作家”的议论,越出了文学和文学刊物的边界。进入新世纪,“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的“青春写作”,大放异彩,所谓“某某后”的说法,从文学全面推衍到社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用语,成为一种公共认知。
四
提出一个概念,并不重要;是谁提出,更无关紧要。何况一个即便是很职业、很专业的说法,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遭遇,也从来由不得自己。
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是对当时文学生态的实际考量;而“某某后”的流行,则是社会认知所必然。关注更为年轻的社会群体的成长,这是社会的进步。
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所以能接受以出生年代划分社会群体这样一种认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所起到的深刻作用。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一代人成长经历和内心生活的规定和塑造,是以出生年代划分人群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最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比如说,“50后”与“上山下乡”的关联,“60后”与改革开放的同步等,一个新的青年群体走上社会舞台时,它所对应的社会发展节点,铸就了这一代人的基本群体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只不过是从文学具体操作的层面上,直观而真切地切入了一个后来引发反响的社会公共话题。
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初衷和本意,只是希望文学和社会更加关心、关注年轻一代的文学成长,而这又是建立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前提上,仅此而已。
断关心、关注更为年轻的社会群体的成长,这是社会发展的前景和希望使然。文学亦然。这是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这一说法的最原初的动因。
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中。面对新的变化、新的进展,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说法,从来是题中应有之义。